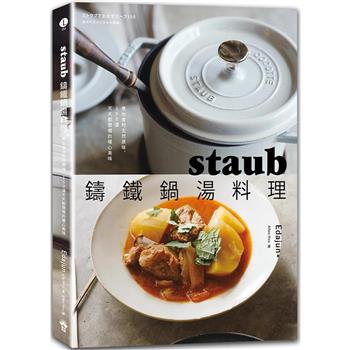圖書名稱:前面有什麼?
我想知道,迷宮的後面⋯⋯有什麼?
滅火器樂團成軍二十週年首本音樂成長小說!
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記住你不妥協的樣子!
★ 〈島嶼天光〉、〈末日列車〉創作樂團——「滅火器」成軍二十週年紀念。由《白搖滾》作者張仲嫣執筆,歷經多次訪談,真實和虛構交錯,寫就第一本記錄台灣樂團成長的音樂小說。
★ 深刻書寫少年夢想追尋、親子跨世代對話,是一本融合音樂、土地與社會思辨的人文之書。
◎ 本書內容
音樂交織成一片繁茂巨林,
男孩們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去,
踩踏於長大和失去的變奏之間,
他們還是不放棄做夢,並且保持溫柔。
「我始終認為,寫字的本質是撕裂傷口,探究受傷的皮肉筋骨。每一道傷,都是新生可能的突破口。與團員相處的過程,我時常在恍惚間遇見傷口的重合點。近似移動的軌跡——高雄、台中、台北——使我隱隱約約見得一座巨大的冰冷迷宮,我們早在以為倖免時身於其中。」——張仲嫣
青春彆扭的像支打不開的可樂瓶,
掩藏一百種隨時爆炸的祕密。
當想說些什麼的欲望試圖敲開瓶蓋,
創作的引信在體內點燃,
前面有什麼?是停不了的寫、沒有盡頭的唱。
任迷宮兜轉至記憶原鄉:高雄八重洲、新堀江、原宿廣場,
自青澀的追尋一路唱到黑暗盡處的島嶼天光,
他們將生命丟失的拼圖一一撿回,
為時代配樂,在母語彈唱間傳遞火種,
或許每個人、包含島國本身就像龐克一樣無法被標籤定義,
唯有直視晦澀才能感受光明、撫摸傷痕才懂得勇敢的隱喻。
二十年了,迷宮裡的男孩始終對抗長大;
「再不瘋狂,可就老了呢!」
本書完整呈現「滅火器」成團二十年奮鬥歷程,作者貼合時間軸虛實交錯,提煉樂團沿途走來的疼痛拉扯、彼此相伴至今的情誼,並鋪展台灣龐克搖滾的音樂生態。
故事折射出青年面對學業、前途與理想的茫然困境,不避諱體制內各種遺憾傷痂、以及和家人好友間的愛怨對峙。沒有人是壞人,但還是會留下傷痕。於是找不到出口的迷惑只好交給音樂了……跟著龐克批判、思辨,其中仍保有面向世界的純真,對待自我的誠實;「這是我的人生,我有權利自己作主!」
這份「作主」並非衝動孤行,而是為生命負責的起點——
面對源源不絕的惡意,
未來還是一直一直來!該怎麼辦呢?
只好繼續唱、繼續寫;
不低頭屈服,就是他們所選擇、
最對得起自己的生存方式。
◎ 書封設計概念
「唱片是圓的,不管怎麼最後都會轉回原點,起點也是終點,終點又是起點。」
本書封面由知名設計師莊謹銘操刀,整體色調以「滅火器」鮮明的紅、黑搭配呈現。主視覺結合文內反覆出現、探問「前面是什麼?」的迷宮意象,設置一「CD圓迷宮軌道」,貫穿音樂與理想,隨著唱盤輪轉,彷彿穿行於現實、記憶和未來之間。
作者簡介
張仲嫣
生於絲絨革命,來自南國高雄。柏林洪堡大學準碩士生。
極度膚淺任性的女子,人生以2017年仰望的那道極光一分為二。生無可戀,知道自己終將下地獄,決定在此之前順從靈魂原欲。現居柏林,遇見了生命太多可能與掙扎。可若還有選擇,仍將毫不猶豫,奔向來時那條滿是傷痕的路。
著有實驗性音樂小說《白搖滾》。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