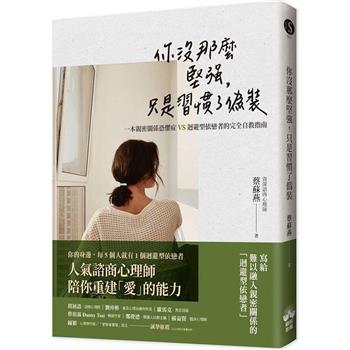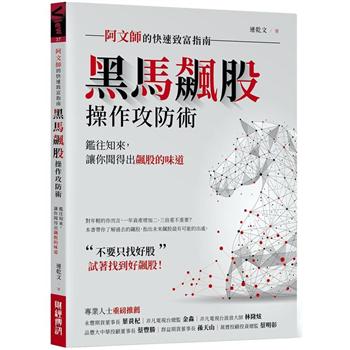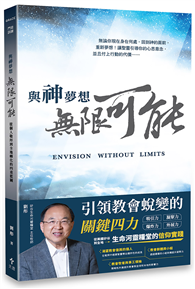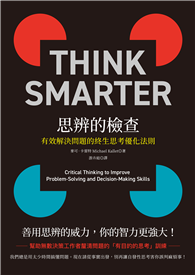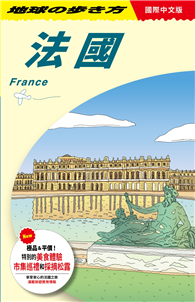在中國現代小說中,「風景描寫」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現出形態各異的面貌。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直到世紀的結束,小說裡的風景也不斷地變化色彩,這裡面有作家對小說文體上的考量佈局,也牽涉到了作家的審美觀點、文化理想、社會思潮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本書以文本研究的方式,爬梳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包括美學意義上的風格特徵,以及更深一層的意識形態等,並對這些形色各異的面貌進行闡釋。書中聚焦的範圍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中共建國,述及魯迅的《故鄉》裡的荒村、沈從文《邊城》中的老渡口、廢名《橋》上的各色風光、蕭紅《呼蘭河傳》河畔的花園、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太陽及河流等現代名家鉅著中自然景色的書寫和象徵。
本書特色
本書聚焦在魯迅、沈從文、蕭紅、丁玲、廢名五位中國現代小說家的作品中,「風景描寫」的不同面貌,自然界中的花草樹木、河流山川,在進入作家的「視野」後,產生了觀點各異的「藝術處理」,而最終產出各色的美學特徵,表述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點。
封面文案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斷章》
作者簡介:
張夏放,1968年出生於陝西臨潼。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職語文出版社。曾做過鄉村教師,文學雜誌編輯。主編普通高中語文選修教材兩種,出版譯作一種。發表論文、小說、詩歌等近百篇(首)。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夏放的這部論著所涉及的話題,是一個新穎而有價值的話題。
我曾無數次在碩士生和博士生學位論文開題論證時對同學們講一個觀點:寫論文,首先題目要好,有了一個好題目,百分之七十就已經拿下了。所謂的好題目,就是那個話題別人沒有想到你想到了,不是一個大家說來說去都說爛了的話題;既然是一個少有人談論的話題,那麼你談什麼就有什麼,一切意思都是新鮮的,做順了很容易達抵圓滿之境界。寫論文―我說的是寫一篇好論文,其實與寫小說同理,也得有巧妙的選擇和構思。寫小說,特別是寫那些很文學很有藝術性的小說,在選材上一定是很有講究的,出人意料,這是最起碼的。寫小說,最忌諱的就是你所選擇的材料是無數的人從正面看到的材料。這樣的小說做起來很費勁,但再費勁也難以讓人稱道。寫論文也是這樣,話題太正,即便是再用力,也難以讓人看了雙目為之一亮的。而不幸的是,人們卻習慣於從正面和成千上萬的人一道打量這個世界,並且會煞有介事地將一些司空見慣的事情和道理看得十分嚴重。殊不知,這樣的事情和道理談與不談其實意思不大。夏放做博士之前是寫小說的,他當然懂這個道理。做這個題目,證明了他的敏銳,他的聰明,他的眼光,他的別具一格。題目一出,當時我就說:就是它,做。在對碩士生和博士生們講怎樣選擇學位論文時,我會不厭其煩地講這個道理,而差不多每次都要以夏放的題目選擇作為最有說服力的例子。
中國現代文學歷時三十年,在浩浩蕩蕩的中國文學史中,它只是一個極其短暫的時段。但這個時段似乎非常特殊,雖然上下不過三十年,但對它的關注和投放的研究力量卻廣大和強大到不可思議,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圍繞它而形成了一個專門的、重要的並且是十分顯赫的學科。它吸引了中國一大批有思想、有素養、有功底、有才情的人,今日之文壇,佔據重要位置的學者、批評家和學術明星,竟然有許多都是在這個學科工作的。形成如此局面,可能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其實,這裏是有一篇文章可做的,只可惜至今還沒有人做過)。時間之短,涉足人員之多,規模之宏大,體制之完整,也造成了這個領域學術話題生產的緊張。年年歲歲,關於這個時段的文學的研究著作絡繹不絕,時至今日,長篇短幅,不說浩如煙海,也可稱得上洋洋大觀了。其中,還有不少稱之為「工程」的重大專案。對這個時段出現的作家作品,無論大家還是小家,無論是上品還是下品,也無論是老翁還是少壯,都有研究者反覆「侵擾」和光顧,真不知道無人到達的荒地還有沒有了。夏放卻要做這個時段的文章,多少帶有挑戰的意味。到底還能做些什麼?這就看夏放的眼力了。事實上,對一個領域的研究即使達到了「圍殲」的聲勢,達到了席捲一切的「掃蕩」狀態,研究的可能性卻依舊是存在的。對任何一段時期的文學研究,都是無法真正窮盡的。但難度顯然加大了。夏放做的這個題目,居然還不是這個領域被有意無意忽略的細微末節的話題或是一些無人問津的邊角料,而是重大的話題。天網恢恢,並非疏而不漏,漏掉的還可能是大魚。夏放談論的話題,顯然是一個隱藏於學術盲區的重大話題。這個話題之下的幾位作家,都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關於他們的研究,在我們的感覺裏,似已無話可說了。但夏放卻非說不可―說他們的風景描寫。風景描寫的話題不是多多少少說過了嗎?誰不知這幾位都是風景畫大師?但夏放說的風景描寫並非是通常意義上的風景描寫。過去說這幾位的風景描寫,只是從寫作手段的意義上去說的,是個方法技巧,而且從沒有當個什麼大事去看待過。夏放說風景描寫超越了方法技巧的層面,而到達了意識形態的層面。他是深入到風景描寫的背後去看這幾位作家的風景描寫的。運用的理論,已不是創作論意義上的理論,而是種種現代的學術話語資源,這些話語具有很濃重的形而上的意味。過去,也很少見到以如此大的規模來談論這個話題的,更少有將這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放到這個話題下來一起論述和比較的。這一學術性工作無疑是具有開拓性的。
對於夏放的學術語風我也是很欣賞的。夏放是經過了專門的學術訓練的,他很瞭解學術文章的寫法以及論述的腔調。今天這個世界,是一個非常講規範化的世界。論文怎麼寫,用什麼樣的語言進行表述,經過那些專門訂立規範的人員一次又一次的修訂之後,已經程式化了―程式化到了刻板,你必須要照這個規範的樣式去完成你的論文寫作,不可越雷池一步。這樣的規範對一部生動的多姿多彩的學術文章寫作史視而不見。勃蘭兌斯式的寫作、斯太爾夫人式的寫作、尼采式的寫作,還有王國維式的寫作,就不算是學術文章的寫作嗎?事實上,即使被我們認為是標準的學術文章寫作的那些人,比如黑格爾,比如海德格爾,比如福柯等,他們的學術表達也並非就一定合我們現在的學術規範。這個規範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將個人的寶貴經驗融入他的寫作之中。對客觀性的絕對化強調和對主觀性的絕對排斥,使文章的寫作人已經失去自我,個人的寶貴經驗變得一錢不值。還有一點,就是個人的才情被徹底打壓。一種集體性的語體,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當下學術刊物、學術論壇的唯一語體,彷彿,凡學術就必須操如此腔調說話。如今,看學術文章,我們除從署名得知作者是誰,從文字的風格已很難看到作者的身份了。夏放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開始他的學術寫作的。他知道學術規範是他必須跨越的門檻,但他又不願完全屈從於這樣的規範。他希望他的論文是一個叫夏放的活生生的人寫的論文,夏放的名字不僅僅是在署名處得以出現,而應該在整個文章中始終隱形地存在。我喜歡他的才氣,他對文學的感悟能力,他在文學創作實踐中獲得的純粹的理論家們所無法提供的寫作經驗。我們讀到了一部學術規範無法挑剔的,卻有著表述個性的論著。他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可讀性的論著。
這本書的意義還在於我們對風景意義的再度認識。它既關乎文學,也關乎我們的生存取向。它可能會引發我們對風景描寫的人文性思考。今天,我們不無悲哀地看到:現代小說已不再注目風景了―最經典的現代小說已完全放逐了風景。當年,川端康成稱他與自然的關係是「幸運的邂逅」,而如今風景在小說中已無一寸藏身之地。原因種種,其一,人類進入現代之後,對自然已失去了崇尚與敬畏之心。其二,工業文明使自然在退卻與貧化,城市與人口的膨脹,在一天天地擠壓著風景,現代人的肉體與靈魂從一開始就缺乏自然所給予的靈氣與濕潤。其三,現代人的閱讀已經失去了足夠的耐心,再也無心閱讀那些有關風景的文字,更難體會風景的境界了。其四,現代作家的寫作功底薄弱。風景描寫其實是考量作家寫作能力的一個指標,從某種意義上說,風景描寫是所有描寫中最見功底的。鑒於這種種原因,現代小說在我們毫無覺察中遠離了風景。而我以為這些還並非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原因在於現代人的審美趣味與審美意識的歷史性變異。我們看到,在經過相當漫長的時間之後,一些現代的文學藝術家無聲地達成一個共識―這一共識雖未被一語道破,更未加認證,但卻使人堅信不疑: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於對醜的審視,而不能寄希望於對美的審視;美是虛弱的、蒼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矯情的,美的淺薄決定了它不可能蘊藏什麼深刻的思想,而醜卻是沉重的、無底的、可被無窮解讀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思想恰恰藏匿於其背後。我們知道,風景的被注意,是與雅致、雅趣、雅興聯繫在一起的。既然這一切已被冷淡與放逐,風景在小說中也就自然消失了。噁心的感覺、陰冷的感覺,不可能來自冬天的太陽、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這是一個失去風景的時代。現代小說因缺乏古典小說中的森林、草原、河流、小溪、露珠與青草,使閱讀變得焦灼、枯澀,怎麼說也是一種缺憾。在如此情形之下,閱讀夏放這部研究風景描寫研究的著作,與魯迅、沈從文、廢名、蕭紅、丁玲再度相遇,也許會使我們有更合適、更美好也更正確的希望和思考。
曹文軒
2014年2月7日于北京大學藍旗營住宅
名人推薦:推薦序
夏放的這部論著所涉及的話題,是一個新穎而有價值的話題。
我曾無數次在碩士生和博士生學位論文開題論證時對同學們講一個觀點:寫論文,首先題目要好,有了一個好題目,百分之七十就已經拿下了。所謂的好題目,就是那個話題別人沒有想到你想到了,不是一個大家說來說去都說爛了的話題;既然是一個少有人談論的話題,那麼你談什麼就有什麼,一切意思都是新鮮的,做順了很容易達抵圓滿之境界。寫論文―我說的是寫一篇好論文,其實與寫小說同理,也得有巧妙的選擇和構思。寫小說,特別是寫那些很文學很有藝術性的小說,在...
章節試閱
緒言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斷章》
一
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1980)中以「風景之發現」來考察日本「現代文學」的形成過程,在他看來,「所謂的風景與以往被視為名勝古蹟的風景不同,毋寧說這指的是從前人們沒有看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勇氣看的風景」。然後他又把這兩種風景的不同與康德所論及的美與崇高的區別聯繫起來,「被視為名勝的風景是一種美,而如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樣的風景則為崇高。美是通過想像力在對象中發現合目的性而獲得的一種快感,崇高則相反,是在怎麼看都不愉快且超出了想像力之界限的對象中,通過主觀能動性來發現其合目的性所獲得的一種快感」。從這樣的區分中,柄谷行人進而認為「現代的風景不是美而是不愉快的對象」,日本的「現代文學就是要在打破舊有思想的同時以新的觀念來觀察事物」。
若以柄谷行人的這種看法來看待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風景,大體也不差,因為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也是「破舊立新」(包括在形式上廢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這一點在中國現代小說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對比一下魯迅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和古典小說《紅樓夢》中的風景描寫就可以看出,前者的風景(比如《故鄉》、《藥》中的一些描寫)並不見得是「美」,更多的是一種「不愉快的對象」,而後者的風景多是一種可供玩賞的「美」(古典詩詞起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現代小說有一個「現代」任務,就是它參與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中去。這一點也和日本現代文學有幾分相似,如柄谷行人所表白的那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1983)中指出以小說為中心的資本化出版業對國民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我在本書中所考察的文言一致也好,風景的發現也好,其實正是國民的確立過程」。柄谷行人在這裏提到的「國民」是英文nation的翻譯,中文則譯為「國家或民族」,所謂的nation state則譯為「民族國家」。最有意思的是,柄谷行人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風景」在確立「民族國家」時所起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nation是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張,族群共同體遭到解體後,人們通過想像來恢復這種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產生的。這是否可以和民族這一概念聯結在一起還沒有定說。再以美利堅合眾國為例,nation的社會契約側面是以國歌《星條旗永不落》(Stars and Stripes)來表徵的。可是,只有這一點是無法建立起共通的感情之基礎的,而作為多民族國家又不可能訴諸於『血緣』,故只好訴諸於『大地』。就是說,這是通過讚美『崇高』風景之準國歌《美麗的亞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來表徵的。」這是把「風景」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雖然它還只是一個表徵。如果聯繫到中國的一首在各種聯歡晚會中很流行的歌曲《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大概也能看出同樣的「表徵」,中國同樣是多民族國家,如果不能以血緣來聯結時,還可以用「花」來聯結,因為人們根據「常識」就會知道,在大自然中各種花是可以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的。
從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柄谷行人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這個角度來考察現代文學中的風景的,也是本書參考的一種視角,因為在魯迅開創的現代鄉土小說(風景描寫在其中不可或缺)中,大多是著眼於所謂「國民性」的問題的,而這一點往往是和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嚮往密切相關的。柄谷行人沒有更多地從風景的「審美功能」來考慮,而在一些小說家兼學者的眼裏,小說中的「風景」更多是從小說藝術方面來「看」的。以往有關小說藝術的研究中,專門研究風景的不多,人們往往也只是把風景當作小說故事發生的一個背景。比如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中很少提到小說中的風景描寫,他談的是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圖式、節奏等等。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1985)也很少談到風景描寫,只是在談到「輕逸」,提出要讓語言輕鬆化時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寫風景的詩,而不是引用小說。大衛‧洛奇(David Lodge)的《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 1992)中有一章標題是「開頭」,提到小說開頭的方式有多種,其中有一種就是「小說可以從描寫故事發生地點的風景開始,即電影評論者所說的『佈景』。例如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在《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中一開始就對埃格頓希斯進行了一番描寫,格調低沉。E‧M‧福斯特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24)中一開始對昌德拉普爾也進行了一番導遊性描繪,文筆優美雅致」。該書還有一章是「異域風情」,大衛‧洛奇寫道:「帝國主義及其餘波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前所未有的旅遊、冒險和移民潮。在這股大潮中,作家或者說那些有望成為作家的人自然也被捲了進來。結果是,近一百五十年來的小說,尤其是英國小說,大都以異域風情作為背景。」 這中間自然有對異域風景的描寫,很顯然從這些風景描寫裏能看到很濃厚的殖民主義或烏托邦色彩[比如笛福(Daniel Defoe)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中談到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時,認為屠格涅夫的風景描寫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既生動又明確的寫法」,當人物出現在這樣的風景中時會產生一種「感人效果」。詹姆斯在分析巴爾扎克(Balzac)的風景描寫時認為這體現了他的「地方色彩」,並拿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石榴村》為例說,「這個故事實際上是為了那些它所涉及的種種迷人的景觀而存在下去的―一座綠蔭環繞的白色的房子,半隱半現地建築在那條法國大河岸邊的一座砌著臺階的小山的斜坡上。坦率地說,我們可以認為,換了一個人,手上有著同樣多的事要做,絕不會為了這些景觀而特別費神去描寫一番,或者把它們描繪得並不假借任何外力就使它們本身躍然紙上。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都蘭之子,我們必須這麼說,他懷著拳拳的孺慕之情,用非凡的雄渾之氣,以各種藉口,抓住各個時機,描寫他自己的父母之鄉」。如此來說,巴爾扎克的這一點與沈從文倒有些相似,沈從文寫湘西時也是懷著同樣的熱忱。對小說中的風景描寫論述得比較完備的是曹文軒的《小說門》,有一章的標題就是「風景」。曹文軒認為,風景是小說的「一個重要元素」,接著他詳細分析了小說中風景描寫的若干類型(比如現實主義是「如實描寫」,浪漫主義描畫的其實是「心靈中的風景」,象徵主義則是把風景當作「一種象徵」)、風景的意義(主要是風景在小說中的審美功能,比如「引入與過渡」、「調節節奏」、「營造氛圍」、「烘托與反襯」、「靜呈奧義」、「孕育美感」、「風格與氣派的生成」等)、風景描寫的藝術經驗、失去風景的時代的特徵(分析現代主義小說不再注目風景的原因)等等。
緒言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斷章》
一
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1980)中以「風景之發現」來考察日本「現代文學」的形成過程,在他看來,「所謂的風景與以往被視為名勝古蹟的風景不同,毋寧說這指的是從前人們沒有看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勇氣看的風景」。然後他又把這兩種風景的不同與康德所論及的美與崇高的區別聯繫起來,「被視為名勝的風景是一種美,而如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樣的風景則為崇高。...
目錄
目次
推薦序/曹文軒
緒言
第一章 返鄉路上「蕭索的荒村」
第一節 荒村
第二節 雪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邊城的「渡口」
第一節 水
第二節 樹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呼蘭河畔的「後花園」
第一節 樹
第二節 後花園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河流上空的「太陽」
第一節 在黑暗中
第二節 水
第三節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橋」上的風景
第一節 竹林
第二節 桃園
第三節 橋
第四節 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目次
推薦序/曹文軒
緒言
第一章 返鄉路上「蕭索的荒村」
第一節 荒村
第二節 雪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邊城的「渡口」
第一節 水
第二節 樹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呼蘭河畔的「後花園」
第一節 樹
第二節 後花園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河流上空的「太陽」
第一節 在黑暗中
第二節 水
第三節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橋」上的風景
第一節 竹林
第二節 桃園
第三節 橋
第四節 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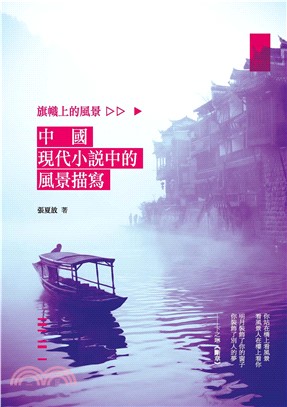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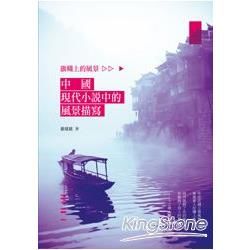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