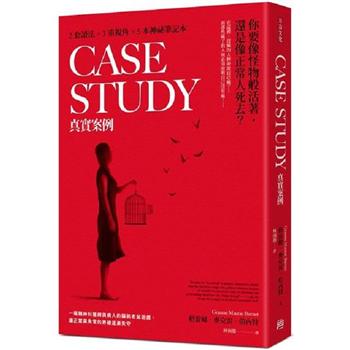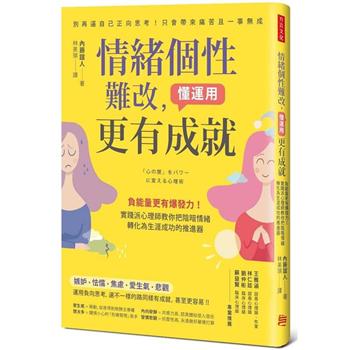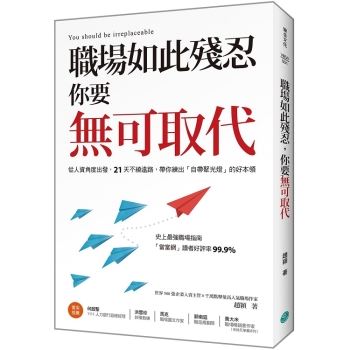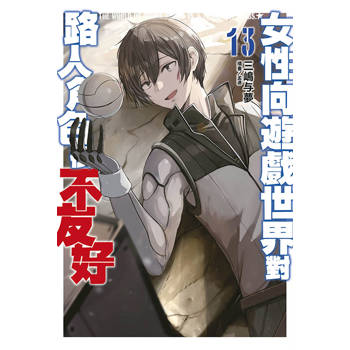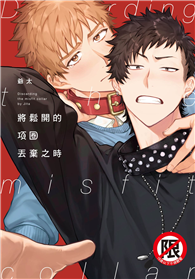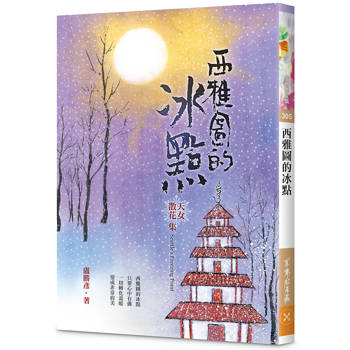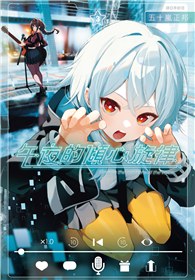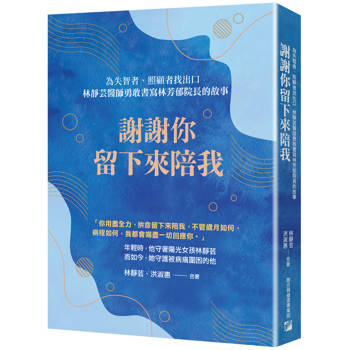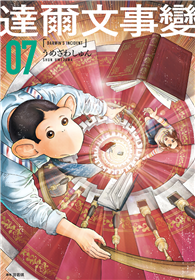國內重大自然災難新聞傳播相關研究自九二一開始發展,回顧過去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災難新聞出現問題大抵為:一、災難新聞報導內容不時出現不符合專業規範的新聞表現,包括密集報導血腥驚悚畫面、違反客觀專業原則、罔顧新聞倫理等;二、記者為搶快、搶獨家,在災難現場採訪時干擾現場救災、賑災,採訪行為也時有造成災民二次傷害的情形。
相對於過去採取結果論、常以新聞內容進行分析,本書採取「回到新聞工作者具體的勞動論述和實作」的角度,藉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經驗和故事敘述,帶出新聞現場的困境與行動,及其導致的結果。
本書共分為六章,以2009年的八八風災和2011年的日本三一一複合式災難這兩個重大災害的新聞工作經驗研究作為基礎,藉由與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分析和解釋災難新聞產製過程,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種種不確定性,如何造成記者做新聞的勞動條件、記者(身心)安全、新聞專業表現的惡化。本書研究發現,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災難情境中,新聞工作者雖然不乏有追求新聞公信力者,卻也有許多人以追求個人或組織利益為訴求來「做」新聞,而這些文化腳本也影響了八八風災和三一一複合式災難的新聞產製實作走向,導致臺灣新聞的實際表現偏離傳統的專業倫理,最後歸納記者的專業反思、職業認同,由此提出未來建立重大災難新聞專業的建議。
本書特色
為什麼臺灣災難新聞面對社會持續批評,卻未能作出修正、回歸新聞專業?
跟隨進入災難新聞的後臺,見證重大災難新聞是如何被記者「做出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張春炎的圖書 |
 |
$ 210 ~ 270 | 在重大災難中做新聞: 新聞專業、記者安全與文化實作
作者:張春炎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5-07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在重大災難中做新聞:新聞專業、記者安全與文化實作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春炎
1978年出生於宜蘭,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災難與環境新聞研究、傳播科技與社會研究、東南亞傳播研究、東南亞移民工研究。研究多發表於《臺灣傳播學刊》、《新聞學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傳播研究與實踐》、《科技、醫療與社會》、《思與言》、《傳播、文化與政治》、《傳播文化》、《台灣東南亞學刊》、《環境教育研究》等優良期刊。
張春炎
1978年出生於宜蘭,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災難與環境新聞研究、傳播科技與社會研究、東南亞傳播研究、東南亞移民工研究。研究多發表於《臺灣傳播學刊》、《新聞學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傳播研究與實踐》、《科技、醫療與社會》、《思與言》、《傳播、文化與政治》、《傳播文化》、《台灣東南亞學刊》、《環境教育研究》等優良期刊。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一、災難新聞的學理脈絡
二、研究問題:如何研究災難新聞產製?
三、研究方法與經驗資料
四、本書章節安排
第二章 臺灣新聞專業的社會文化分析
一、導言
二、獨占到寡占期:黨國體制下的新聞專業文化(1962~1992年)
三、自由競爭期:市場化的新聞專業文化(1993~1999年)
四、惡性競爭期:競逐微利的新聞產製文化(2000~)
五、結論:結構與行動―共同形塑新聞專業文化
第三章 打破常規:重大災難新聞產製的不確定性
一、導言
二、採訪的不確定
三、現場連線、採訪衝突與工作壓力
四、重大災難新聞產製分工的不確定性
五、小結
第四章 重大災難新聞工作的因應、反思與專業詮釋
一、導言
二、記者的詮釋與反思:採訪倫理與公共倡議
三、編輯的詮釋與反思:當個新聞協作者
四、新聞主管的詮釋與反思:後勤、支援與指導
五、主播的詮釋與反思:最後的守門員
六、小結
第五章 三一一大地震新聞工作的經驗反思與記者安全構思
一、導言
二、記者安全的能與不能
三、災難新聞採訪與倫理反思
四、建立記者安全的災難新聞產製行動指引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論
一、導言
二、回應本書的三個研究問題
三、結論發現:不確定性導致結構與能動的緊張關係
四、反思與建議:邁向更具記者安全觀的災難新聞產製文化
五、近期災難新聞研究議題與發展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附錄二
一、災難新聞的學理脈絡
二、研究問題:如何研究災難新聞產製?
三、研究方法與經驗資料
四、本書章節安排
第二章 臺灣新聞專業的社會文化分析
一、導言
二、獨占到寡占期:黨國體制下的新聞專業文化(1962~1992年)
三、自由競爭期:市場化的新聞專業文化(1993~1999年)
四、惡性競爭期:競逐微利的新聞產製文化(2000~)
五、結論:結構與行動―共同形塑新聞專業文化
第三章 打破常規:重大災難新聞產製的不確定性
一、導言
二、採訪的不確定
三、現場連線、採訪衝突與工作壓力
四、重大災難新聞產製分工的不確定性
五、小結
第四章 重大災難新聞工作的因應、反思與專業詮釋
一、導言
二、記者的詮釋與反思:採訪倫理與公共倡議
三、編輯的詮釋與反思:當個新聞協作者
四、新聞主管的詮釋與反思:後勤、支援與指導
五、主播的詮釋與反思:最後的守門員
六、小結
第五章 三一一大地震新聞工作的經驗反思與記者安全構思
一、導言
二、記者安全的能與不能
三、災難新聞採訪與倫理反思
四、建立記者安全的災難新聞產製行動指引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論
一、導言
二、回應本書的三個研究問題
三、結論發現:不確定性導致結構與能動的緊張關係
四、反思與建議:邁向更具記者安全觀的災難新聞產製文化
五、近期災難新聞研究議題與發展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