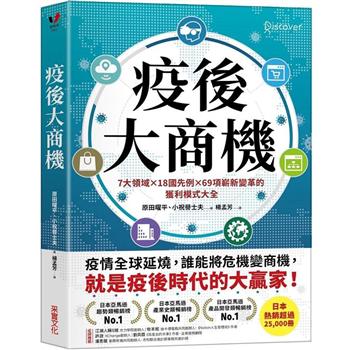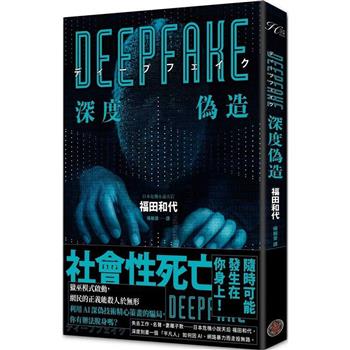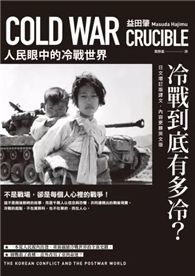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張青萍的圖書 |
 |
$ 190 ~ 280 | 大海的女兒:張青萍散文集
作者:張青萍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18 語言:繁體/中文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0 電子書 | 大海的女兒--張青萍散文集
作者:張青萍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11-01 語言:中文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張青
張青是小說《水滸傳》中的人物,外號「菜園子」,在小說第十七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中首次由魯智深提及。他本在孟州道光明寺種菜,卻因為小事殺了寺裏的僧人,逃往大樹坡作劫匪。他在該處結識了孫二娘,二人再一起在十字坡開設酒店,用蒙汗藥為害過往行人,做人肉包子的生意。後來,他跟隨二龍山眾頭領加入梁山泊,坐上第一百零二把交椅,司職「打探聲息」、「邀接來賓頭領」並負責管理「西山酒店」。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