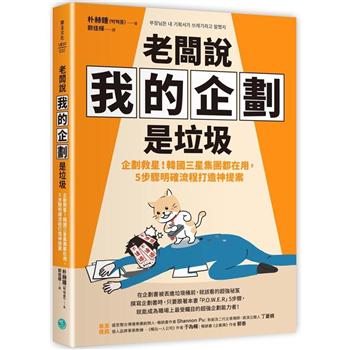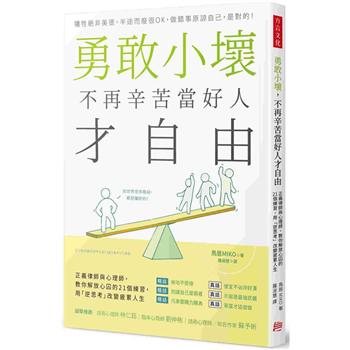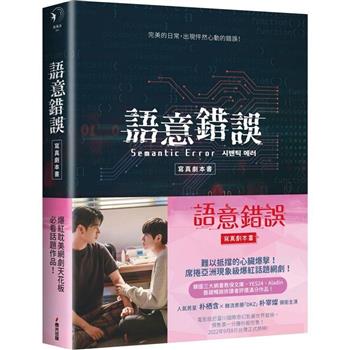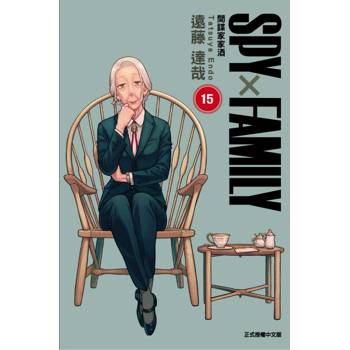6
克萊兒是我的雙胞胎姊姊,所以不管我喜不喜歡,她的話語就像我腦袋裡的另一個聲音。接到海莉死訊,我第一個打電話的人是她。嗯,這麼說不盡正確,第一通好像是打給我媽。航空公司半夜電話通知我墜機意外,但我根本不記得自己撥了電話。
「喂?」母親接的電話,聲音惺忪低沉。「喂?」我聽得見她床邊的漆黑和闃寂被我砸碎的聲音。「誰啊?」
我沒說話。一開口等於允許聚集在門口的憤怒暴民闖入我的領地。「喂?」她又問了一次,然後說了聲「變態」就掛上電話。
海莉死了,而我媽說我是變態。你知道的,這種小事就是會永遠記得。
郊野或森林某處仍冒著煙,行李、屍首與扭曲焦黑的機身殘骸四處散落。而在災難現場的某處就躺著海莉,我幾小時前才吻別的女人。她如雲的金色秀髮、纏繞我的那雙修長大腿、慧黠明眸、扁扁的鈕釦鼻和我怎樣也吻不夠的巧薄嫩唇,都在那裡,伴著四周散落的碎裂焦黑殘骸,死絕了。不可能,我了解這是事實,但我就是無法明白過來。
鏡中的男人看似明白了。他臉色蒼白憔悴,眼底有東西顫抖:某種閃爍著恐懼但未形於表情的東西。可是我什麼都感覺不到。我快速打量了鏡中的男人,對他微微笑。他回給我一個神智不清的歪嘴笑臉。我讓我們兩個露出驚恐表情,接著是悲傷,彷彿我正在參加某種表演訓練課:一群瘦得皮包骨的白痴圍坐著對彼此的誇張表演鼓掌叫好,而某些絕不可能成為女星葛洛麗亞.史萬森的人正學著她吐出小雪茄煙霧,說些讓人有聽沒有懂的意見。海莉死了,我卻他媽的杵在鏡子前。我一直覺得自己不配得到她的愛,若需要什麼來證明我不配,只要盯著我的臉就能發現。
「海莉死了。」我大聲說出來,聲音迴盪在屋內像晚宴上放了個響屁。一般人接到這種電話會變得激動失控,不是嗎?應該會尖叫痛苦地否認,倒在地上嚎啕悲鳴,或者猛捶牆壁,直到血肉模糊,分不清破碎聲音源自凹陷的牆壁或者骨裂的拳頭。但我只是站在床邊,搓著後頸,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我是震驚到不知所措,這樣一想就令人欣慰多了,因為海莉不該被當成這種失控舉止的可悲藉口。
我的第一個直覺反應是打電話。第一個想要打的對象是海莉。我撥了她的手機,不知道自己想聽到什麼。接通後立刻出現她的留言:嗨,我是海莉,請留下訊息,我會盡快與您聯絡,謝謝,掰。這則留言是那天晚上她在廚房錄的,隱約可聽見背景傳來洛斯和我看電視的笑聲。過去幾年這則留言我聽了無數次,熟悉到老早就充耳不聞。可是現在我清楚聽見她冷靜自信的聲音、想盡快錄完的匆忙語氣,以及家人歡笑的背景聲音。她不可能走了,她在電話裡頭,每字每句的確出自她的口。死人怎麼會有語音留言呢?一聲嗶,我知道電話正在錄我的聲音。「嗨,寶貝。」我愚蠢地說出這句,僅僅這句,沒有其他話語。然後掛上電話。
可怕自私的念頭不請自來進入我腦海,一個接一個,整群魚貫而來,就像你好心幫老太太開門,結果後面十五個人就這麼順理成章走進來,你被困在那兒成了門房。其實你只是要幫一個老太太而已。
我要怎麼辦?
我要住哪裡?
還會有人愛我嗎?
我想像海莉一絲不掛,從浴室門口走進臥房,走往床邊對我露出挑逗的渴望笑容。還會有女人赤身裸體對我那樣笑嗎?當下,在這個可怕時刻,我知道會有其他裸女,想到這裡我感到可恥無比。但,就算有,她們會像她那樣凝視我嗎?
還有一個念頭,這個念頭最糟糕,卻不會讓我胃痛,反而讓我有一種扭曲的輕鬆:我知道她沒機會不愛我了,她永遠都是愛我的了。我的確是個超級大渾蛋,連我都沒想到自己這麼可惡,不過從這個念頭,就知道我的確如此。
海莉死了。我努力理解這件事。她不會回來,我永遠都不可能見到她。這些事沒一件對我有意義,它們只是文字,只是未被證實的假設。我現在該怎麼辦?海莉死了,海莉死了,海莉死了。我似乎必須永遠抓緊這個想法,才能繼續過日子,才能去做我該做的一些事。
該做什麼事?我他媽的一點都不知道。我隨即想到洛斯,他正在走道另一頭的房裡睡覺,他可能會因這個噩夢驚醒,永遠無法再無憂無慮地入睡,無法再以過去的方式呼吸、微笑、哭泣、思考、咳嗽、走路、眨眼、撒尿、歡笑。此刻他還不知道,仍安穩地睡著,這點很殘酷也很不公平。我知道面對他的哀傷會比面對我自己的更難捱,我想在他陷入混亂、失控衝出家門前比他早一步離開,這樣就不必看到他那雙頓時明白人生已然驟變的雙眼。
現在該做些什麼?
繼續打給某人。某個知道該怎麼做的人。
我又拿起電話。
「喂?」克萊兒的老公史蒂芬咕噥地問。
「我可以和克萊兒說話嗎?」
「道格?」他滿口睡意,「拜託!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四點半,我必須和克萊兒說話。」
「她在睡覺。」他堅定地告訴我。史蒂芬從沒喜歡過我,當初我激動要求克萊兒別嫁給他,還列出一長串他不適合她的理由,所以他對我很不滿。尤其婚禮時我更沒品地(這點不能否認)在敬酒時表現出惡毒態度。我辯駁說,這是因為我年輕不懂事,況且那時也喝得酩酊大醉。
「我不能等。」
「發生了什麼事嗎?」
海莉死了。「我就是要跟她說話。」
話筒隱約傳來窸窣聲,克萊兒接起電話,啞著剛甦醒的聲音,滿頭霧水:「道格,幹,搞什麼呀?」克萊兒那張嘴是出了名的三句不離髒話。即使嫁給全康乃狄克州最富有的豪門小開,她仍將這習慣當成小時候得到的珍貴紀念品,隨時抓緊不放。
「海莉的飛機掉下來,她死了。」終於,我說出口。好像有某種冰冷堅硬的東西卡對地方了。
「什麼?」
「海莉死了,她的飛機失事了。」
「喔,天啊,你確定嗎?」
「確定,航空公司打電話來通知的。」
「他們怎麼確定她在那架飛機上?」
「她就是在那架飛機上。」
「啊,幹。」她咒罵完後開始哭。我想叫她別哭,不過旋即想到我還沒掉淚,加上發生這種事情總得有人哭,所以我決定任由克萊兒替我哭泣。我靜靜聽著。
「我現在過去。」她說。
「沒關係,不用。」
「閉上你的狗嘴。我一小時內就到。」
「好吧。」
「要不要我打電話給爸媽?」
「不要。」
「問了個蠢問題,抱歉。」她的呼吸聲愈來愈吃力,因為她正忙著在房裡走來走去穿衣服,邊吼著史蒂芬要他閉上那張爛嘴。「洛斯呢?」
「還在睡覺。」我回答,又喚了聲:「克萊兒。」
「什麼?」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專心呼吸,吸、呼、吸、呼。」
「我想到某些很變態的東西。」
「你是驚嚇過度。沒事的。我要上車了。」
幾分鐘後電話傳來一陣長長的撞擊聲。
「操!」
「怎麼了?」
「剛剛撞到車庫門。」
「天啊,妳還好吧?」
「沒事。」她說:「他媽的整扇門倒下來,我乾脆直接輾過去。」
「小心開車。」
「無所謂啦,聽著……」她忘記自己拿的是家用無線電話而不是手機。一開出車道,電話就失去訊號,斷了線。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強納生.崔普爾的圖書 |
 |
$ 237 ~ 264 | 還會有人愛我嗎?
作者:強納生.崔普爾(Jonathan Tropper) / 譯者:郭寶蓮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9-11-0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6頁 / 16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還會有人愛我嗎?
你原以為已經抵達幸福的終點、找到今生的歸屬,但誰知命運弄人?當你傷心徬徨不知如何走出悲痛,切記呀:其實,人生沒有什麼快樂的結局,只有快樂的日子、快樂的時光,別閃躲,放膽去追尋吧!陪你流著眼淚捧腹大笑豁然開朗深入骨髓的感動 絕無冷場的風趣 百無禁忌的麻辣尼克.宏比不能比 艾倫.狄波頓甘拜下風療傷笑果大勝《ps我愛妳》 破碎的心保證痊癒電影AfterHailey原著小說 全球電影龍頭派拉蒙影業全力籌拍中海莉沒能留下半句叮嚀,更來不及再說一次我愛你,只留下種種回憶讓道格觸景傷情。他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去愛任何人了。「海莉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海莉留給他的除了一顆破碎的心,還有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繼子洛斯。「我努力理解這件事。接下來該做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我隨即想到洛斯,從此以後,他恐怕再也無法安然入睡,無法像過去那樣呼吸、走路、眨眼、撒尿……」正值青春期的洛斯情竇初開又打架鬧事樣樣來,道格在面對傷痛之餘,還是得要分出精神來收拾洛斯製造的各種殘局,在他們先是針鋒相對、後來真情流露、終至互相力挺的心碎父子拉鋸戰中,一個寂寞空虛慾火焚身的有夫之婦、一名封閉了感情的心理輔導老師、道格那日漸痴呆的父親、吞藥成癮的母親、剛懷孕卻想離婚的姊姊和趁人之危得到幸福的妹妹,闖進了他們原本就已一團混亂的生活。這些內心各有殘缺的人們,時而互相取暖,時而彼此傷害,聯手演出一場高潮迭起、精彩可期、既賺人熱淚又令人笑倒在地的療傷喜劇。「還會有人愛我嗎?」答案就在這個瘋狂卻又真實的故事裡。
章節試閱
6克萊兒是我的雙胞胎姊姊,所以不管我喜不喜歡,她的話語就像我腦袋裡的另一個聲音。接到海莉死訊,我第一個打電話的人是她。嗯,這麼說不盡正確,第一通好像是打給我媽。航空公司半夜電話通知我墜機意外,但我根本不記得自己撥了電話。「喂?」母親接的電話,聲音惺忪低沉。「喂?」我聽得見她床邊的漆黑和闃寂被我砸碎的聲音。「誰啊?」我沒說話。一開口等於允許聚集在門口的憤怒暴民闖入我的領地。「喂?」她又問了一次,然後說了聲「變態」就掛上電話。海莉死了,而我媽說我是變態。你知道的,這種小事就是會永遠記得。郊野或森林某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強納生.崔普爾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09-11-03 ISBN/ISSN:978986173571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