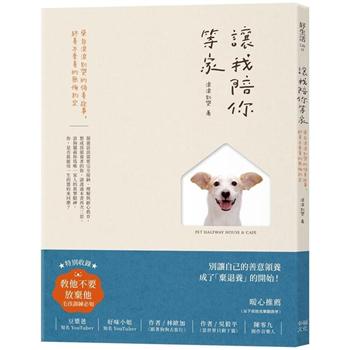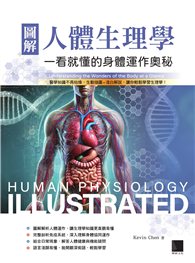[初終]。
唐制,凡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牖東首,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疾困,去故衣,加新。徹藥,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四人坐持親體。有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氣絕。氣絕,廢牀寢地。主人啼,餘皆哭。
喪主於床東,服三年之男子於其下。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期功以下之同姓,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主婦、眾婦女坐於床西;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內外皆素服。主人坐於牀東,啼踴無數,眾主人在主人之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妻之後,哭踴無數,兄弟之女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藳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幃外之西,北面東上,以服為行。無服者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及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以上俱開元禮。唐制,品官初終之制,自遷正寢至不食。後代此制有簡略。清至今,亦有不若是者,王氏復禮家禮辨定言杭俗曰:「人之既死,有初終敲磐,浴水令孝子先飲少許」,吾鄉[湘鄉]之人喪,亦有所謂﹁請水﹂之俗,初終,執事者執銅鑼一面,楮錢若干,於河湖井窪處,擊鑼焚楮,諸子、婦、女、孫等皆隨拜,三喚魂兮歸來。台灣近俗亦有此制,謂「乞水」,作為擦拭屍體用。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彭天相的圖書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喪禮撮要箋釋
《喪禮撮要》箋釋
中國傳統喪禮哀戚肅穆,極盡人道。全由其合乎國人情性,凝聚為民族之道德支撐。該書集古代中國喪禮精華,考證有據,詮釋精詳;上下貫通,圖文並茂。學人可據此參究典籍,讀者可依此排比演繹。
——徐兆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簡介:
彭天相(1893-1943)著
字戒頑,生於清光緒十九年,湖南湘鄉府(今雙峰縣)人,清國子監生,誥授湖南奉政大夫(正五品銜),民國初年任湖南長沙工會主席。
彭衛民(1987-)箋釋
湖南雙峰人,西南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國立高雄大學研修生。先後參與或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西南政法大學重點項目等課題十餘項,在《史學彙刊》(臺灣)、《學術界》、《社會科學論壇》、《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科學報》等CSSCI、THCI學術刊物與報紙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學術成果三次獲得西南政法大學成果特等獎與重慶市學術年成果二等獎,部分文章為《人大複印資料》、《儒學中心》(臺灣)等全文轉載,先後獲得「第七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重慶市十佳讀書人」、「重慶市學術標兵」、「重慶市學術創新先進個人」等獎項。
章節試閱
[初終]。
唐制,凡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牖東首,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疾困,去故衣,加新。徹藥,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四人坐持親體。有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氣絕。氣絕,廢牀寢地。主人啼,餘皆哭。
喪主於床東,服三年之男子於其下。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期功以下之同姓,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主婦、眾婦女坐於床西;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妾、婢...
唐制,凡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牖東首,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疾困,去故衣,加新。徹藥,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四人坐持親體。有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氣絕。氣絕,廢牀寢地。主人啼,餘皆哭。
喪主於床東,服三年之男子於其下。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期功以下之同姓,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主婦、眾婦女坐於床西;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妾、婢...
»看全部
作者序
宋序
孝之大端,生:敬、養,死:葬、祭。而能傳承衣缽,弘揚精神者,則更堪稱大孝。賢弟子彭衛民求學之餘,窮經習禮,不畏繁縟,箋釋其先尊曾祖彭公天相之遺著喪禮撮要,頗得真意,令人欣慰。台灣大學曾教授建元先生首肯其功,並玉成其在秀威出版社刊印發行,更可喜可賀。對建元先生及秀威編輯嚴謹問學,不分出身,只重學術,獎掖後學之舉,本人衷心感謝並由然而生敬意。
衛民同學孜孜以求,考覆勘校,承其先尊遺作而成喪禮撮要箋釋,使之問世於浮燥之當下,於公於私,均堪稱功德。亞聖曰:「唯送死以當大事」。古往今來,「棺槨衣衾」...
孝之大端,生:敬、養,死:葬、祭。而能傳承衣缽,弘揚精神者,則更堪稱大孝。賢弟子彭衛民求學之餘,窮經習禮,不畏繁縟,箋釋其先尊曾祖彭公天相之遺著喪禮撮要,頗得真意,令人欣慰。台灣大學曾教授建元先生首肯其功,並玉成其在秀威出版社刊印發行,更可喜可賀。對建元先生及秀威編輯嚴謹問學,不分出身,只重學術,獎掖後學之舉,本人衷心感謝並由然而生敬意。
衛民同學孜孜以求,考覆勘校,承其先尊遺作而成喪禮撮要箋釋,使之問世於浮燥之當下,於公於私,均堪稱功德。亞聖曰:「唯送死以當大事」。古往今來,「棺槨衣衾」...
»看全部
目錄
宋序
曾序
徐序
箋釋凡例
[初終]。
[書遺言]。
[三復]。
[訃告於親族]。
[聞喪奔喪]。
[設屍?]。
[沐浴]。
[小斂法]。
[襲奠]。
[飯含]。
[治棺]。
[立喪主]。
[家祭所需職事]。
[大斂法]。
[告闔棺]。
[結魂帛]。
[招魂]。
[置靈座]。
[置銘旌]。
[諡法]。
[制杖]。
[成服]。
[五服制度]。
[朝夕奠]。
[停葬]。
[新喪生日]。
[補儀節內稽顙二字辨]。
[告啟期]。
[作神主]。
[置功布]。
[置雲翣]。
[開塋域祀土神]。
[遷柩中堂]。
賑孤科條
[祭廟王土地儀節]。
[祭大舉儀節]。
[祭路文]。
[...
曾序
徐序
箋釋凡例
[初終]。
[書遺言]。
[三復]。
[訃告於親族]。
[聞喪奔喪]。
[設屍?]。
[沐浴]。
[小斂法]。
[襲奠]。
[飯含]。
[治棺]。
[立喪主]。
[家祭所需職事]。
[大斂法]。
[告闔棺]。
[結魂帛]。
[招魂]。
[置靈座]。
[置銘旌]。
[諡法]。
[制杖]。
[成服]。
[五服制度]。
[朝夕奠]。
[停葬]。
[新喪生日]。
[補儀節內稽顙二字辨]。
[告啟期]。
[作神主]。
[置功布]。
[置雲翣]。
[開塋域祀土神]。
[遷柩中堂]。
賑孤科條
[祭廟王土地儀節]。
[祭大舉儀節]。
[祭路文]。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彭天相(著)彭衛民(箋釋)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06-14 ISBN/ISSN:978986609480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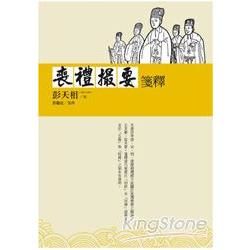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