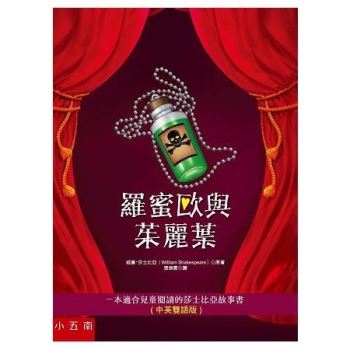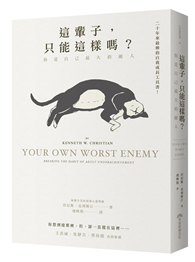一次造訪這裡,是三年前的九月初。黑暗的海面上浮現點點漁火,那是釣烏賊的船隻。就像是被蠟燭的火炎吸引住一般,當時的我泡在浴缸裡好久,就這麼出神地看著外頭。
原本很喜歡久泡在熱水裡,不過自從生病之後,我就一直注意水溫不能過熱,並提醒自己不要泡太久。即便如此,這晚我還是泡了很長一段時間,比平時都要久。
這裡看來一切都沒變,但總覺得有些不一樣。例如我是第一次和老闆娘見面,而另一個接待我的女侍也不是熟面孔。還有一個鎮日窩在地爐旁吸菸,自稱是老闆娘父親的老爺爺,現在也不見蹤影。
當時,代替老闆娘經營這家旅館的,是老闆娘的妹妹,名字叫做志津子。志津子當時已遠嫁東京,但在得知姊姊出車禍後,毅然決定回來幫忙。年約三十五、六歲的她,接待客人的手腕其實並不高明,一看就知道是個生手。不過,想笑的時候就開懷大笑,面對其他員工的建議也能虛心接受,努力用心又直率。我對志津子是有好感的。
但在這三年間,我從未想起志津子。當時的我也只住了一晚,在那之後,我也不清楚她到底幫忙了多久。她住在保谷市裡,丈夫是個音樂老師。只有在說起自己肚皮不爭氣的時候,才能看到她的落寞神情。
我在睡衣外頭罩了件棉袍,從冰箱裡拿了罐飲料。
我拚命去回想志津子的臉,卻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微笑時向旁邊展開的唇邊黑痣,讓我記憶鮮明。我這才發覺,當時或許是在閒適的旅情催化下,才會不自覺地將志津子加以美化,至於對這家旅館有好印象,應該也是基於愛屋及烏的心理吧!
女侍送來了晚餐。
「這裡的海浪還真不小。」
「這樣還算好的呢。要是暴風雨一來,浪可是會高到連海岸對面的岩石都看不見呢。」
「妳在這裡做很久了嗎?」
「我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做的。」
「妳是當地人?」
「是啊,我是在這兒土生土長的。」
我將目光投向窗口。俐落地將料理擺上矮桌的女侍映入窗中玻璃。
「以前我曾來過這裡一次,當時有一個……」
這時,我看到女侍背後有人影晃動。一位身著茶綠色和服的女性進來了,她在門口緩緩坐下。我無法繼續剛剛的話題,眼睛直盯著窗戶玻璃看。
窗外,化為一片黑影的松樹林彎著枝葉,像是被強迫禮敬一樣。紛飛的大雪,無情地拍打著海岸公路上的路燈。
大雪中出現的女人,看起來就像靜靜駐足在空中一樣。
因為一直沒回頭,所以志津子只是抬著頭,一副不知道該不該叫我的樣子。
「那麼接下來就拜託妳了。」,雙頰紅潤的女侍端著盤子走了。
我壓抑住自己騷動的情緒,回過頭去。
「好久不見了。」志津子將頭低了下去。
我回到矮桌旁,緩緩坐下。
「真是巧啊!才剛剛想起妳,想跟剛才那個女服務生打探妳的消息,沒想到妳就出現了。真是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為是幽靈呢!」
我的聲音比想像中高尖許多。面對毫不掩飾再會欣喜的我,志津子也一副鬆了口氣的樣子。
「看到您的名字時,我也有股說不出的高興呢。」
和以前一樣的可愛笑靨。嚴肅的時候,她唇邊的黑痣會沒來由地讓她看起來性感嫵媚。但只要她一笑,那黑痣又會讓她看起來如同少女般天真無邪。
我又再度看到了她那似乎連臟腑的縐褶都潔白無垢的天真爛漫。於是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來。
「不好意思,讓我來幫你斟酒吧。」
志津子跪坐著前進,拿起啤酒瓶。
「妳要不要也喝一點?」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志津子站起身,將冰箱上的玻璃杯取下,回到矮桌前。
我們為了再次重逢而乾杯。
在志津子的殷勤相勸之下,我開始朝料理動筷。菜色有甜煮海螺,以及牡丹蝦與烏賊的生魚片等,這是以海鮮為主的豐盛晚餐。
「那個女服務生是新來的,我和老闆娘又是第一次見面,總覺得有些寂寞。對了,連妳父親我也沒瞧見。」
「父親進養老院去了。他的老人癡呆越來越嚴重,我們家人已經照顧不來了。」
「以前來的時候看他還滿有精神的啊,他還常在地爐邊跟我們這些客人聊天呢。」
「看來酒精倒能幫他醒醒腦。」志津子輕舒雙眉,開心的笑了。
我伸手夾了片烏賊生魚片,問她「妳這次也是來幫忙的嗎?」。
志津子將拿著玻璃杯的手放回膝上,搖了搖頭。「我是去年夏天才決定回到這裡的」。
她的眼神失去了光采,但也只是一瞬之間而已。很快的,她又恢復了爽朗的表情。
所謂「事出必有因」,不過從外表看來,倒是看不出她內心曾經嚴重受創;也許是和老公鬧翻了無處可去,才回娘家來吧,這樣的猜測應該是八九不離十。一旦心裡萌生那種青梅竹馬般的情感,就會忍不住想要介入她的內心世界。「您好像跟以前來的時候不一樣了呢。」,此時,她用天真無邪的眼神,反客為主的率先探詢我的內心世界,這讓我只好把想問的話給吞了回去。
「哪裡不一樣了?」我喝著啤酒反問。
「您以前看起來,好像比較適合去那種片山津或是山代附近的繁華溫泉大街,而不是我們這種鄉下的小旅館。」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妳父親也曾在地爐前說過同樣的話。他說一個老大不小的男人一個人住在我們這種鄉下小旅館,感覺還真是噁心。」
「父親怎能說出如此失禮的話!」志津子的臉頰登時紅了起來。
「我還問他這附近有沒有能跟我作伴的女人,結果他笑說『留在我們村裡的女人,都只有老太婆而已啦』。」
當時,我也想過要到加賀附近,那條有藝妓的溫泉大街去輕鬆一下的。但最後,我還是按照預定行程來到能登半島。
志津子大大地點了點頭,「他說的果然沒錯」。
「咦?」
「當時父親曾對我說,通常一個人來的男客都是很寂寞的,所以總要我去陪陪他們。」
「您的父親真是體貼啊!」
「體貼過頭囉!」
我笑出了聲音,志津子也抿嘴而笑。窗戶的玻璃也被風吹得嘎嘎作響。曾幾何時,斜吹的雪已將窗櫺染白。
志津子的皮膚白皙,俐落的下巴線條雖美,卻透露出一絲寂寞。相對的,她的雙唇就顯得厚實許多,笑的時候還會露出一對門牙。雙眼皮雖然明顯,眼睛卻不大,一雙眼睛像是用筆快速劃過一樣。她將盤起來的頭髮往後紮,然後揉成一團向內側塞入。她的瀏海彎曲起伏,突顯出她那擁有美麗的弧線的前額。
三年前她穿的是洋裝,但我想肩膀窄的她穿起和服更為合適。
我著實嚇了一跳。自己竟然用男人的眼光來看志津子。即使是在渴望女人的三年前,我也不曾用這樣的眼光看她。一個沒有心機的率直女人跟一路伴隨我到能登內地的旅愁一拍即合,這讓我對她產生了過度的好感。這下可好了,原本那個晚上的目標只是一個靜謐的鄉村,可如今自己的心裡,卻佈滿了其他想法。
「要再來一瓶啤酒嗎?」
「不,謝了。」
「怎麼了嗎?我記得您以前……」志津子一臉驚訝。
「我生了場病,所以現在一天只能喝一瓶。啊,真是無奈啊。」
志津子的臉上出現了微笑。「是什麼樣的病呢?」
「心肌梗塞。酒是還可以喝一點,但醫生嚴禁我繼續抽菸。這還真是痛苦啊。」
「想必您一定是個大菸槍對吧?」
「以前每天都要抽上兩包的。」
「那工作呢?」
「我休息了一年左右。現在妳知道為什麼現在的我,不適合去那種熱鬧的溫泉大街了吧。」
「原來如此」,志津子平靜地說。「這些我可都一點都不曉得呢……」。
「不過,無事一身輕倒也不錯。」
志津子開始準備牛肉的炭烤。
「來這裡之前,我去了趟神渡神社。記得妳曾經告訴我那裡的神是有求必應,所以上次來的時候才在回家之前去了一趟。」
「原來我說過那樣的話啊。」
「是啊」,我告訴她女兒還因為這樣而考上了第一志願。
「不過最近好像失效了呢,那裡的神明似乎越來越不靈驗了。應該是在去年的這個時候吧,那裡的佛鈴讓人給偷走了。」
「所以才換了新的嗎?」
「在那之後,神明好像就變得不靈驗了」,淺笑的目光背後,蘊藏著一抹黯淡。
「也許這有點多嘴,不過,請問妳先生……」
志津子抬起她的粗眉,將視線游移在空中。「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面對她像是將悉心照料過的野鳥放回空中翱翔的眼神,我的心一陣抽蓄。
不過,到很遠的地方去這種說法倒是令人玩味。這是指他過世了嗎?如果是這樣,那志津子也顯得太過冷靜了。所以我想應該是和別的女人跑了,或者是失聯了吧。
志津子像是回過神般,轉換了說話的語氣。「回東京之後,我就換了家報紙」。
「妳是指改訂了我們報社的報紙?」
「是啊。本來還想找找裡頭有沒有鹽野先生寫的報導,但仔細一想,一個報社的部長是不可能親自寫報導的。」
上次來這裡的時候,剛好是決定誰是下一任部長的升遷年。明明只是三年前的事,現在想起來卻覺得好遙遠。
無視於報紙推銷員的黏人推銷術以及禮物攻勢,也不管老公的懷疑眼神,她就這樣訂了我們報社的報紙,想想還真令人感動。
「那麼……妳覺得我們家的報紙如何?」
「東京版的專題報導還滿有趣的。裡頭詳細的介紹了現在年輕人的動向、玩樂場所還有性意識等等,其中有好多東西都讓我大開眼界呢!」
那篇專題報導,是一個年輕女記者經過詳細調查後撰寫出來的。開不完的會、還有出不完的差……。我想起了自己當年忙碌不堪的樣子。
志津子身上還留有濃濃的都市味。她結婚的時候,一定是滿懷著憧憬到東京去的吧。如果她跟我想的一樣,是因為跟丈夫分開而不得已回老家,那此類東京的話題應該會讓她感到相當難受。我偷偷看了看志津子,她的表情依然平靜。
我討厭兀自想像著志津子的遭遇,而對她產生憐憫的自己。這只是我在為自己的不幸尋找同病相憐的感覺罷了。
窗外的雪激烈敲擊著窗戶,發出陣陣吼聲。我在喝盡杯中的啤酒後,打破了沉默。
「神渡神社裡有座筆塚對吧?今天我在那底下的狹窄道路上,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議的景象。」
「喔,你看到了什麼呢?」
「一個新娘竟在草繩的那一端,把一袋紅包交給一個留著白色山羊鬍的老人。」
志津子睜大眼睛說:「喔,你說那個啊,聽說那是我們這裡的習俗。」
「聽說?所以連妳也不是很清楚囉?」
「我聽父親說在他年輕的時候,這裡常舉辦這種儀式。就是在村子的入口結上草繩,擋住從別村嫁到這裡的新娘,然後新娘再包上一定數目的金額給這村子裡的人。如此一來,新娘就能正式成為這個村子的一份子。」
「因為當時剛好下雪,我還以為自己坐上時光機回到了過去呢!」
「上次舉辦這個儀式已經是在好幾十年前了。那個留著山羊鬍的老人是這個村子的長老,他的孫子要和珠洲市的一位女性結婚,所以他再三要求自己的孫子,希望婚禮能遵照傳統習俗。」
「我覺得其實他們應該是想把繩子繫在海岸公路上才對。」
「也許吧,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剛剛也到他們的婚宴現場去幫忙,新娘可是個大美人喔。」
「沒想到這裡也有正值適婚年齡的年輕人啊?」
面對我的笑話,志津子輕輕皺了皺眉,她說:「當然有啊,還不少呢。」
我睜睜地看著志津子。她的長睫毛上下交疊,眼神向下探。
「今晚的興致不錯,真想再喝它一瓶。」
此時志津子嚴肅地搖搖頭。「你得乖乖聽醫生的話才行」。
「反正這事也只有天知、地知、妳知、我知而已,就讓我再喝一瓶吧。」
「不行!」她將眉毛往上揚,再次搖頭。
那副倔強少女的模樣,真是惹人憐愛。
突然,志津子的表情緩和了下來。「剛剛那瓶啤酒被我喝了一半,所以只要將這第二瓶酒一人一半,就不算違背醫生的叮嚀。」
志津子從冰箱拿出第二瓶啤酒。剩下的烤牛肉成了我們的下酒菜,於是我又喝了起來。
「今天的客人可不少。妳一直待在這裡,不去招呼其他客人可以嗎?」
「住這裡的大多是那位新娘的親朋好友,所以我想,不到半夜他們是不會回來的。你要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嗎?」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也吃了一驚,沒想到自己竟說得如此悠哉。
「反正這段期間也不是什麼旺季,就請你在這裡好好休養吧。你們這些報社的人……」,大概是沒想到自己竟會脫口而出,志津子眨了眨眼,忽然不說了。
「我們這些報社的人如何啊?」
「我要說的是,你們平常看起來總是一副匆忙急躁的樣子,所以我想,大概很少有機會可以像現在這樣好好休息吧。」
「說得也是。新聞是活的,我們得掌握住每分每秒才行。」
「要再來一碗飯嗎?」
「好啊。」
「這段期間有到彈曲灘去嗎?」志津子邊添飯邊問。
「最近很不巧,一直都在下雨,我看八成明天也去不成。嗯,這樣好了,在聽到鳴砂的音色之前,我就一直住在這裡好了。」
志津子將添好的飯放在我面前,然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有什麼好笑的?」
「咦?難道你不知道嗎?」,志津子收起了笑臉。「一年多前,福井的三國外海上有座油輪觸礁了,結果整座海灘都受到了影響」。
「這事我知道,結果,漏出來的原油也波及到這片海灘了嗎?」
志津子點了點頭。「原本大家還拚命地維護這座海灘的清潔,想說很快就能讓這片鳴砂再度響起美妙的音樂,誰知道現在卻……」。
「可惜了這個觀光勝地。」
志津子將重新熱過的味增湯遞給我。「在沙灘能再次響起樂曲之前,你就在這兒好好休養吧。不過,這家旅館的旅客通常寥寥無幾,你可能會感到很無聊喔」。
「正合我意,我正想一直住在這兒」,雖是半開玩笑的口吻,但內心深處卻是真的如此渴望著。
我想遠離時代的洪流,獨自逗留在這間寂寥的旅館裡。
「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吧?」志津子感嘆地說。
「真的不知道這片沙灘何時能恢復嗎?」
志津子搖搖頭。「總覺得神渡神社的佛鈴被偷之後,所有的衰事就都來了」。
志津子的後頸帶著一抹淡淡的紅,還有雲靄般的髮絲遊戲其間。一個應該不到四十歲的女人,究竟對這種地方有著什麼樣的期待呢?還是她已經決定遠離塵囂,決定無論如何都要以笑臉迎人來度過餘生?
我發覺自己已被志津子深深吸引。
突然,隔壁房裡傳來一陣非同小可的風聲。接著是碗盤被打破的聲音。
我和志津子不由得面面相覷。
拉門這時也嘎搭嘎搭作響。
「我去看看怎麼回事。」志津子跳也似地站起身,出了房間。
我也跟著到走廊查看。志津子在門口縮著肩膀,往出事的房間裡窺看。她的瀏海隨風擺盪著。
我就站在志津子的背後。
酒壺和小碟散落在榻榻米上。窗戶就這麼開著,讓雪吹了進去,蓋住半個以上的坐墊。衣架則被強風,吹倒在牆壁上。
有個男人站在窗邊。他一副不在乎被雪擊臉的模樣朝窗外看。白雪將他粗壯的雙肩染白,又在下個瞬間乘著風,濕潤了榻榻米。
那是我在神渡神社遇到的那個男人。
我走過志津子身旁,進入房間。
我斜眼看了一下那男的。他的臉看起來像是被壓扁的藥罐。忽然,他遲滯的眼神瞄了過來,眼珠的轉動顯得相當遲鈍,看來醉得不輕。
吹進來的雪,弄濕了我的雙頰和肩膀。我將視線離開那名男子,想把窗戶關上。
「你是誰啊?」
我的肩膀被他抓住了。正想回頭時,志津子說話了。
「客人,你的酒快涼了喔。」
志津子嚴肅但清亮的聲音,讓那名男子的手,從我肩膀處滑下。
關上窗戶後,風雪顯得遙遠許多,而那名男子就一直站在那兒。
「唉呀,怎麼濕成這樣,我去拿件新的來……」
志津子拉開壁櫥,拿出睡衣和棉袍。
看著新的睡衣和棉袍,男子似乎沒有伸手接過來的打算。
志津子一臉溫柔,毫不在意地說:「那我就放在這兒喔」。
我在走廊看見了個人影,那是老闆娘。老闆娘背後還站了個平頭男子,一副不好惹的樣子。
「到底是怎麼啦?」老闆娘眉頭深鎖。
平頭男子瞇著眼,結實的雙肩左右搖晃著進入了房間。
「欽次!不可以!」志津子搖了好幾次頭,然後將目光朝向老闆娘。「姊姊,沒事的」。
「可是……」,老闆娘盯著散落一地的酒壺。
「都說沒事了」,志津子將那個叫欽次的男子給推了回去。
欽次回頭看看老闆娘。
老闆娘大大點了個頭。「既然妳都這麼說了,那就交給妳了。得給我好好善後啊」。
「是。」
老闆娘走遠了。志津子把門關上。
「真是的,喝酒喝成這樣!」志津子彎下膝,開始收拾散落在榻榻米上的酒壺。
我原想幫忙收拾,但志津子低聲喚道:「我來就好,你還是坐下吧。」
我沒聽志津子的,就這麼跟著她跪在榻榻米上。
志津子的應對舉止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她既不膽怯,也不高傲,與那名醉客大相逕庭。從她那像是對付一個鬧脾氣的孩子般的態度,就可以讓人清楚的感受到,她的體貼與溫柔。
我看著輕輕被挽起的和服袖裡,她那白皙細緻的雙手。伸出的手指,心無旁鶩地收拾著散落一地的食物。塗上透明指甲油的指甲上,微微透著鮮紅。
一只缺了一角的盤子,滾到了暖爐的旁邊。
那名男子依舊站著看向窗外。
她應該是跟這位客人素昧平生才對。儘管如此,志津子還是對他採取包庇的態度,這點讓我覺得很不解。不過,她的舉止實在是太自然了,要是一直深究下去,我想可能會越來越看不清她的內心。我被一股新鮮的驚奇給圍繞住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愛,美在不能愛的圖書 |
 |
$ 45 ~ 176 | 愛,美在不能愛
作者:藤田宜永 / 譯者:彭建榛 出版社:大好書屋 出版日期:2010-06-01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愛,美在不能愛
※重製書 原書名:流沙/唐莊文化
《轉轉》日本直木賞作家&推理名家 藤田宜永最美麗且苦澀的愛戀之作。
我們的愛,跨越道德邊界,
終將如浪濤擊岸,美麗,旋即碎裂……
這是一個晚冬至早春的短暫悲戀物語,有人性掙扎,有理性與感性的擺盪,也有為愛不顧一切的勇氣。真愛無悔,在道別之前,請容我再一次任性!
兩度與死神擦肩而過的鹽野,在能登半島展開了地圖素描之旅。旅途中,他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在僻靜小旅館裡接待客人的志津子。這是一段不被允許的愛,悲傷、辛酸又充滿濃濃日本風情。
在熾熱狂烈的男歡女愛中,穿插著許多當地的風俗、軼事及鳴砂的傳說…..
作者簡介:
藤田宜永 (Yoshinaga Fujita)∣作者
1950年出生於日本福井縣。早稻田大學中輟後前往法國,任職於法國航空公司。1980年回國後開始執筆寫作。1986年以《野望的迷宮》(野望のラビリンス)一書出道。1995年,以《鋼鐵騎士》(鋼鉄の騎士)一書獲得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以及日本冒險小說協會大賞特別賞;1996年,以《來自巴黎的遺言》(パリからの遺言)一書獲得日本冒險小說協會最優秀短篇賞。1997年,以《樹下之思》(樹下の思い)等小說開闢了戀愛小說的新領域。1999年的《求愛》(求愛),獲得了島清戀愛文學賞,2001年的《愛的領域》(愛の領分)則獲得了直木賞的肯定。其他還有著有《鮮豔》(艶めき)、《異端之夏》(異端の夏)、《就是要愛》(愛さ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左腕の猫》(左腕上的貓)、《恋しい女》(戀慕的女人)等作品。
譯者簡介:
譯者/彭建榛
1979年出生於台灣省新竹縣,淡江大學日語系畢業,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肄業,目前專職翻譯。
譯有《膽小鬼愛哭鬼諸葛孔明》、《腦內污染》、《第一次找工作就成功》等書。
章節試閱
一次造訪這裡,是三年前的九月初。黑暗的海面上浮現點點漁火,那是釣烏賊的船隻。就像是被蠟燭的火炎吸引住一般,當時的我泡在浴缸裡好久,就這麼出神地看著外頭。
原本很喜歡久泡在熱水裡,不過自從生病之後,我就一直注意水溫不能過熱,並提醒自己不要泡太久。即便如此,這晚我還是泡了很長一段時間,比平時都要久。
這裡看來一切都沒變,但總覺得有些不一樣。例如我是第一次和老闆娘見面,而另一個接待我的女侍也不是熟面孔。還有一個鎮日窩在地爐旁吸菸,自稱是老闆娘父親的老爺爺,現在也不見蹤影。
當時,代替老闆娘經營這家旅...
原本很喜歡久泡在熱水裡,不過自從生病之後,我就一直注意水溫不能過熱,並提醒自己不要泡太久。即便如此,這晚我還是泡了很長一段時間,比平時都要久。
這裡看來一切都沒變,但總覺得有些不一樣。例如我是第一次和老闆娘見面,而另一個接待我的女侍也不是熟面孔。還有一個鎮日窩在地爐旁吸菸,自稱是老闆娘父親的老爺爺,現在也不見蹤影。
當時,代替老闆娘經營這家旅...
»看全部
目錄
1 神渡小旅館
2 謎樣姐妹花
3 地圖素描之旅
4 理性的枷鎖
5 失控的激情
6 私下的約定
7 志津子的祕密
8 彈曲灘清掃日
9 人心的變化
10 半調子的玩家
11 斷崖上的櫻花
12 淒美的悲戀
13 悲傷的靈魂
14 能登的夕陽
2 謎樣姐妹花
3 地圖素描之旅
4 理性的枷鎖
5 失控的激情
6 私下的約定
7 志津子的祕密
8 彈曲灘清掃日
9 人心的變化
10 半調子的玩家
11 斷崖上的櫻花
12 淒美的悲戀
13 悲傷的靈魂
14 能登的夕陽
商品資料
- 作者: 藤田宜永 譯者: 彭建榛
- 出版社: 大好書屋 出版日期:2010-06-01 ISBN/ISSN:978986248095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