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性」競技場
過去三、四十年來,有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世人投注了大量思想、情感和資產,拋頭顱灑熱血,追求所謂的人類價值和人權,捍衛人性尊嚴和人類生命。但同時,科學和哲學卻在不知不覺間,以驚人的破壞力,動搖了我們對「人」的傳統觀念。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何在,開始出現矛盾不一的見解。如果連「人」這個概念都莫衷一是,那「人類價值」又該從何說起?當前,人類和人性(humanity)都陷入了困境,但威脅並非來自眾所周知的「大規模毀滅」和生態浩劫,而是人在「概念」層次出現了危機。
追究危機的來源,有以下六個:首先是靈長類動物學者收集了許多實例,顯示猿猴和人類非常相似。學者指出,過去公認專屬於人類「理性」的種種能力,猿類都有,例如使用語言、製作工具、符號想像和自我意識等等;你想到什麼人類擁有什麼能力,靈長類動物學家就能找到某種猿類,證明牠們也有類似的能力。依據客觀標準,黑猩猩和人類幾乎沒有差別,火星來的人類學家很可能會將兩者歸成一類,就像有些人類科學家將「智人」稱為「裸猿」或「第三種黑猩猩」,或者主張擴大「人屬」的範圍,將猿類囊括進來一樣。過去數百年來,人類和其他靈長類究竟有什麼差異的問題始終爭論不斷(西方中世紀有許多人稱其他靈長類為「墮落的人」),在我們這個時代更複雜混亂到了極點。人類到底是「裸猿」,跟其他猿類只有某些身體特徵不同,還是蒙神感召的「靈猿」,因為獲得意識而超越其他同類,演化成為獨一無二的物種?
其次,動物權運動興起,讓我們不得不努力尋找各種理由,說明人跟其他物種到底有什麼不同而必須另眼相待。過去普遍認為人和動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但如今這條界線越來越模糊,兩者的差別有時甚至不比人種之間的差異還明顯。現代社會面對「人之異於動物者幾希」的問題,有時會提出非常極端的看法,例如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就主張動物是機器,而人體雖然也是機器,卻包含靈魂。笛卡兒的追隨者更進一步主張:被打得哎哎叫的狗與其說是因為痛,不如說因為牠像樂器,所以只要敲打就會出聲。這樣的見解並非從外在可見的事實推論出來——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波林布洛克(Lord Bolingbroke)伯爵便說,只要是正常人,都不可能認為「公牛和教堂報時鐘」完全沒有差別。話雖如此,但就像歷史學家湯瑪斯(Keith Thomas)所說的,這樣的主張讓人可以名正言順壓榨動物,不會覺得太過殘忍、不可饒恕。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以目前的知識和理解來看,人和動物並沒有絕對的分野,要再像笛卡兒一樣主張人性獨一無二,已經不大可能了。於是,面對同樣的問題,有些人選擇了另一個極端,提倡所謂的「深層生態學」。動物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就大力抨擊人類的「物種歧視」思想,而呼籲「人性之上的平等」。凡事都按客觀事實立論的人通常傾向支持動物權;英國政治學教授葛雷(John Gray)從科學和哲學的角度切入,跟辛格一樣提出尖銳的批評,質疑人和其他物種到底有什麼區別。此外,現代社會還出現各式各樣不以生物學標準來定義的「人」的概念(人是製作工具的動物、人是擁有語言的動物、人是會煮食的動物、人是有意識的動物、人是有想像力的動物、人是道德的動物等等),然而,只要仔細反省就會發現,這些主張都不夠嚴謹和周全。
第三,人自認為「人」不只是生物分類的問題,還具有道德意涵。現代社會面對這一點在思考時,都無法迴避古人類學提出的問題:「從演化的角度看,人類是在哪一個時間點上獨立出來的?」前人在「人屬」和其他物種之間劃下的界限,已經被古人類學全盤否定了。過去有的物種被歸為跟我們人類同一屬別,有的則被歸成「類猿」的南猿,但現在看來,兩者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不同。只要檢視化石資料就會發現,許多根據過去的定義絕對會被視為是「人」的特徵,例如雙足行走、腦容量大、使用工具和雜食等等,古代很多物種也有,有的物種甚至不在人類演化族譜裡面。尼安德塔人在當前學術界引發激烈爭論(詳見本書第四章),就充分顯示有些人的內心極度不安,因為他們發現其他物種也有跟人類似的心靈、情感和道德抉擇能力。關於尼安德塔人是不是「人」的爭論,有些說法和用字竟然跟十九世紀輿論爭辯黑人是不是人非常類似,實在讓人驚訝。
第四,哲學界有一個懸宕已久的問題是,物種的區分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物種都各有基本且不變的特徵嗎?或只是人為了辨別方便、隨意分類的結果?過去,這兩種看法都有支持者,彼此僵持不下。然而,生物學過去五十年左右的進展似乎讓其中一方占了上風。根據現今對演化的理解,要證明甲特徵只有甲物種才有,而且甲物種的所有成員都有這項特徵,幾乎是不可能的。物種之間的界線既模糊又不斷改變。甲物種和乙物種之所以各自成類,原因通常不盡相同,而且就算物種成員有共同的特徵,我們也找不出來。任何東西都可以自成一類,完全不需要明顯特徵。換句話說,物種分類是暫時的,隨時可能改變,既非永恆也不是不得不然。我們現在之所以屬於「人類」,不是因為我們具備什麼特質,而是我們認定人是自成一類。
第五,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哲學界開始重新思考人類過去界定自己所以為人的許多關鍵概念,例如意識、推理、想像和道德情感等等。靈長類動物學和古人類學的發現讓我們相信上述這些「人的」能力不但不斷在演化,而且連非我族類也可能擁有;人工智慧研究則讓我們不由得猜想其他人造事物也可能擁有「人的」特質。因此,機器人可以像迪士尼電影《森林王子》的猴王路易一樣:是盪樹之王「也是人」。和我們分享世界的可以是人造人,而非人親生的人。這樣的世界或許永遠不會到來,但我們還是不得不因而重新思考人的本質。
最後,基因研究讓人類有方法判定誰是同類,同時測量人和其他物種的差距。結果卻出乎意料,人類頭一回發現自己和禽獸原來這麼相似。基因學也讓科幻小說《人魔島》莫洛博士的構想有可能實現、甚至威脅人類:藉助基因技術,非人類物種也能具備人的特質。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生物,要怎麼歸類呢?這些想像中可能存在的生物會如何影響我們對人類自身的看法?
關於人是什麼,二十世紀的人類擁有最寬容的定義——只要能跟其他族群繁衍後代的就是人類;儘管如此,二十世紀卻也是歷史上最殘暴不仁的時代。於是,「新人道主義」應聲而起,文化交融使得種族主義失去市場,也讓人權和人的概念畫上等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晚期,在我們了解「人性」的路上又出現兩個新方向,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帶來更多痛苦。首先是社會要求墮胎合法化的聲浪高漲,創造出新的「次人」領域,亦即尚未出生的胎兒;但從前胎兒被認為和成人相同,擁有完整的人權,於是乎有人提出「人素」(personhood)的概念,主張重新定義胎兒的地位,而「人之所以為人到底是基於生物遺傳還是文化?」的老問題也再度引發關注。不只人的過去出現問題,人工智慧和基因工程的發展也讓人的未來陷入危機。政治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言的「後人類」未來真的會實現嗎?或者,既然我們到現在還想不透人是什麼,不如乾脆擴張人的定義,將問題推到以後?
本書計畫從「歷史」切入,藉由回顧「人性」概念的演變來回答這些問題。這麼做是因為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們對於自己身為人類這件事很有把握,也自信有能力辨認彼此身上的人性,卻從來沒想到我們非常了不起地擁有如此包容的觀點,就算膚色和文化差別很大,還是能看出彼此共通的人性。我們現在對「人」的理解其實是近代的產物:歷史上大部分社會中的大部分人要是聽到現代人對人類的寬容定義,肯定會覺得非常訝異。絕大多數古人連了解「人」這個字的含意或在語言中找到同義詞都有困難,他們頂多用它來指稱同類而已。對古人來說,同類以外的是他者、異類,跟野獸和魔鬼一樣。現代區分人和非人的準繩其實並非理所當然,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而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為了理解人性而不斷辛苦探索的結果,目的是希望既能清楚區分人和非人,又不至於像過去種族主義和族群中心主義一樣將某些同胞排除在外。根據目前爭論的走向和我們現有的知識來看,想要回答上面的問題似乎不可能完整,甚至不可能成功。我們現在不可能得到最後答案,因此本書接下來要做的只是回顧「人性」概念的歷史,而非探討概念所指涉的人。當然,就算只討論「人性」的歷史,以本書篇幅來說還是太過龐大,但由於它非常重要,之前又沒有人做過類似研究,相關文獻零散不全,因此與其撰寫一部窮究之作,不如簡單介紹梗概,或許還能收到拋磚引玉的功效。
我們現在對「人是什麼」有理所當然的看法,這一點其實讓我非常擔心,因為這樣的自滿在我們面對新挑戰的時候反而是個阻礙。而且,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覺得現在的定義不需要調整,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必須不斷檢視「人性」的概念,以便彌補缺陷。古人類學家希望能讓更多人猿類成為人類的一員,靈長類動物學家試圖重劃人屬的範圍,好將黑猩猩容納進來,道德論者則對剝奪胎兒和臨終之人部分人權的做法大加抨擊。不同領域的人都在挑戰「人性」概念的極限;或許它比我們認為的還有彈性。人性概念的演變和延伸——也就是本書接下來的主題——還沒有結束。面對「人是什麼?」和「誰是人?」的問題,現代人心中的答案已經迥異於過去不同文化所提出的想法,但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卻跟過去一樣困難。
這麼說來,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擺脫體內的人猿,卻不停渴望成為天使。我們在演化之路上到底前進了多少?又還有多遠要走,才能真正擁抱完整的人類家族,永遠和其他生物區分開來?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就像科學研究一樣注定沒有終點,只有不斷模糊過去確定的答案。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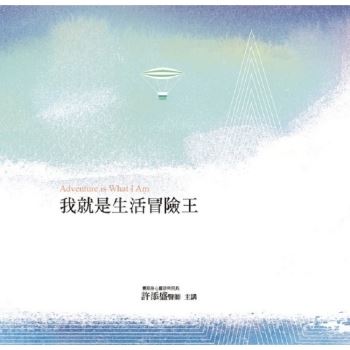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