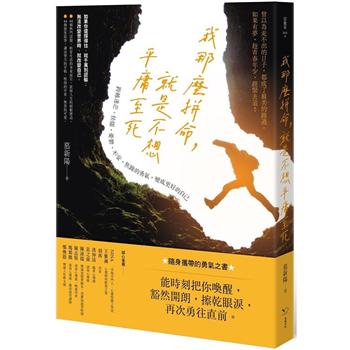理論使人明智。理論就是一組相互關聯的假定,幫助人們解釋事物為什麼會這樣或那樣發生。理論就是通過抽象、推測和思辨後再現的現實。理論就是旨在解釋和理解事物而進行的思維過程。
一種看法認為,人類對國家現象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而對國際關係的考察僅僅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本書不同意這種看法。本書認為在現代國家誕生的400至500年之前,學者、軍事家和政治家們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對國家間關係的思索。本書將闡述這些思想進程中的主要概念和主題,梳理出一條近代歷史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線索。本書特別指出,這條傳統往往在大規模的戰爭中發生動搖和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在此例:這場戰爭與其說催生了國際關係理論,不如說給國際關係理論傳統帶來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提供了新的側重點、輪廓線,促進了學科的覺悟,以及指明了發展目標和方向。本書將對出現在這個轉折點前後兩側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討。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圭恰迪尼對洛倫佐政治行為的描述:這個車類拔萃的洛倫佐是否在自覺地運用均勢理論?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從洛倫佐本人的書信中看,並沒有清晰一貫的均勢邏輯來指導他的外交政策思想。洛倫佐可能只是比其他統治者更加老練而已,而且與同代人的其他統治者一樣,他運作外交政策就是因勢論事,並沒有既定的模式。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所闡發的均勢理論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創見,而不是論述對象的本來意圖。 洛倫佐不太可能根據均勢理論來行動,可能是圭恰迪尼把他描述成這個樣子。同當時的其他統治者一樣,洛倫佐熱衷於短期的目標,而不是持久的國際關係。他的決策通常十分果斷,行動十分迅速。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價值觀裡,耐心地培養信用和善意是不合時宜的,這一時期政治家的指導原則是機會主義而不是周密計劃。對文藝復興時代的統治者而言,國際關係是一場收益高、見效快的危險博弈:“它是在一種興奮異常的狀態下進行的,混合著狡詐、鹵莽、殘忍等被大肆宣揚的所謂‘美德’。”(Nicolson,1954)圭恰迪尼卻試圖用均勢理論來解釋洛倫佐的行為。因此,應該由圭恰迪尼,而不是洛倫佐,榮膺現代國際關係早期理論家的美譽。重現修昔底德
王哈迪尼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因此學者們認為他對意大利政治的描寫是他個人外交經驗的反映。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這樣。圭恰迪尼的均勢理論很可能並非取自其本人的外交實踐,而是他把古代學者的觀點運用到了當時的政治現實當中。很可能的情況是,圭恰迪尼發現了修昔底德,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人類最早從政治倫理角度論述和分析國家間戰爭的巨著。
修昔底德探討了這場戰爭的原因和性質,這是一場發生在一貫活躍、創新的海權國雅典和相對謹慎、遲鈍的陸權國斯巴達之間的戰爭。在氣勢恢弘的長篇敘事過程中,修昔底德始終緊扣住一個主題:關於野戰、圍城、結盟、分裂,以及最重要的——戰爭對於人的影響,它不可避免地使“人類的精神墮落”。修昔底德還對當時各個傑出領袖的性格以及影響力進行了分析。這種性格分析的方法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人都試圖效仿。
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雅典人曾經宣稱:“強者憑藉權力為所欲為,而弱者只能俯首聽命。”(TbLmydides,1980)而這同時意味著,小國通過結盟可以遏制強國的擴張野心。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幾個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Lebow and Strauss,1991)
修昔底德關於古代希臘城邦之間的結盟政治和戰爭行為的描述,啟發了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對他們時代中相互競爭的城市國家的研究。圭恰迪尼等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借鑒了修昔底德的均勢觀念。在被埋沒了千年之後,修昔底德重新與西方政治理論建立了聯繫。修昔底德是跨越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一個在古代的希臘,一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只有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才能真正了解他對後世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
【結論】
馬基雅維里的觀點給自己招來了罵名,17世紀的學者普遍認為《君主論》是在邪惡的感召下寫出來的。在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尼科洛‧馬基雅維里就是魔鬼的代言人,有時撒旦也被人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者”。圭恰迪尼逃過了這些道德家們的怒罵,儘管通過比較,他的著作有時能使馬基雅維里變得合理合情。
馬基雅維里徹底拋棄了以上帝為中心的中世紀思想體系,正是這一點給他招來了尖銳的攻擊。他在幾個世紀裡遭受的辱罵,主要是因為他如此振聾發聵地摧毀了中世紀的世界觀。馬基雅維里出生在中世紀的末期,意識到統一的基督王國的夢想已經毫無意義。這使那些篤信基督神學世界觀的人深感震驚。馬基雅維里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同圭恰迪尼等其他人文主義知識分子一樣,他堅信通過對歷史事件的分析,知識界可以協助政治家製定明智的政策。而這個分析的過程不應該受道德、倫理因素的干擾。馬基雅維里認為,他的使命是描述事物本來的面目,而不是追求事物應該是什麼樣。他強調指出,政治的現實就是君主們無一例外地都根據自身利 益行動。圭恰迪尼同意這個看法,他還把這個規律推廣到對所有政治行為者的解釋;甚至“那些如此賣力地鼓吹自由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個人利益”。
通過這些主張,馬基雅維里和圭恰迪尼宣告了現代世界與中世紀基督世界的決裂。這一決裂確立了他們在理論界的重要地位。他們背叛了正統。他們還顛覆了古典政治理論中的很多假定。中世紀的世界觀以上帝為中心,而馬基雅維里和圭恰迪尼關注的是世俗國家。中世紀哲學認為神創造了自然和人類社會,他們則認為自然是既有的、與人類社會相分離的,而社會是由人來決定的。中世紀思想家設定了上帝的仁慈,為人類的道德生活和靈魂救贖制定了規則,而他們只思考人的行為,力圖從人類行為中尋找經驗和教訓。
【從上帝到君主】
馬基雅維里和圭恰迪尼把上帝從學術界的視野中驅逐了出去。他們並不是公開地宣布上帝不存在,而是悄悄地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從對靈魂救贖的關注轉移到對國家安全的探究。在擺脫了神學的糾纏之後,馬基雅維里宣佈在道德領域存在兩個範疇,具備各自特定的利益和倫理法則。一個需要遵循公正、誠實、憐憫等其他基督教道德標準,而另一個服從於國家利益的要求。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里顯得更加直言不諱。在國與國的關係中,上帝不是合法的道德權威,君主才是最終的裁判者。君主只遵守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道德規則。
圭恰迪尼完全贊同。在他的筆下,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也是一場由“虛偽的、陰險的、撒謊的和狡詐的”人參與的瘋狂而危險的遊戲。君主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注意可能顛覆其國家的挑戰和可能助長其實力的機會。君主必須時刻以自我利益為指南,必須假裝和隱藏自己的意圖,誇大自己的實力,掩蓋自己的弱點。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君主必須拋棄文明社會的個人道德,遵守國家的集體利益——因此,儘管人喜歡公開討論事情,但出於政治上的謹慎,君主幹萬不要袒露個人隱私;儘管說謊在道德上會遭到譴責,但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君主應該培養說謊的本事。圭恰迪尼心目中的君主完全適應這樣一個野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報復不僅是可受的,而且是必須的;安全意味著敵人不能傷害你,儘管他們時時刻刻都在圖謀!……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托布約爾‧克努成的圖書 |
 |
$ 130 二手書 | 國際關係理論史導論
作者:托布約爾‧克努成(TorbjrnL.Knutsen) / 譯者:余萬里、何宗強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1-01 語言:簡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國際關係理論史導論
托布約爾•克努成介紹了從中世紀到當代的諸位思想家關於國際關係的思想,並圍繞戰爭、財富、和平和權力這四個恆久不變的主題追述了其發展的過程。
這本書對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看法發出和挑戰,並展示了七百多年來學者、士兵和政治家位在這一領域的思想成果。叢中世紀國家和主權概念的起源開始,作者汲取了無數傑出思想家的精髓。從馬基雅維里、霍布斯到黑格爾、盧梭、馬克思,以及當代思想家,如伍德羅•威爾遜、列寧、摩根索和華爾茲,這些人都對20世紀國際關係作為獨立學科的出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過修改和增補後,本書的最後部分還介紹了國際關係研究的最新進展。
作者簡介:
托布約爾•克努成(Torbjorn L.Knusten)是挪威特倫海姆大學的國際關係學副教授。
章節試閱
理論使人明智。理論就是一組相互關聯的假定,幫助人們解釋事物為什麼會這樣或那樣發生。理論就是通過抽象、推測和思辨後再現的現實。理論就是旨在解釋和理解事物而進行的思維過程。
一種看法認為,人類對國家現象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而對國際關係的考察僅僅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本書不同意這種看法。本書認為在現代國家誕生的400至500年之前,學者、軍事家和政治家們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對國家間關係的思索。本書將闡述這些思想進程中的主要概念和主題,梳理出一條近代歷史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種看法認為,人類對國家現象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而對國際關係的考察僅僅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本書不同意這種看法。本書認為在現代國家誕生的400至500年之前,學者、軍事家和政治家們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對國家間關係的思索。本書將闡述這些思想進程中的主要概念和主題,梳理出一條近代歷史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緒論:為什麼寫國際關係理論史?
第一部分序曲
第一章上帝、罪人及國際關係理論的起源
西方世界的衰落和興起
中世紀的三大文明
西方政治理論的源頭
中世紀知識的演變(革命)
西方的特殊背景
第二章現代世界的根基:文藝復興時期的國際政治
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
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觀與政治
馬基雅維里:在美德和自利之間
圭恰迪尼:權力的記錄者
結論
第二部分近代
第三章槍砲、戰艦與印刷術:16世紀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社會創新、經濟變革與政治權力
轉折的時代
16世紀的兩大理...
第一部分序曲
第一章上帝、罪人及國際關係理論的起源
西方世界的衰落和興起
中世紀的三大文明
西方政治理論的源頭
中世紀知識的演變(革命)
西方的特殊背景
第二章現代世界的根基:文藝復興時期的國際政治
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
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觀與政治
馬基雅維里:在美德和自利之間
圭恰迪尼:權力的記錄者
結論
第二部分近代
第三章槍砲、戰艦與印刷術:16世紀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社會創新、經濟變革與政治權力
轉折的時代
16世紀的兩大理...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