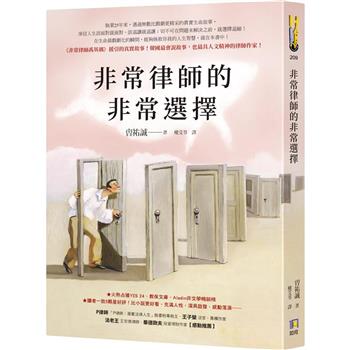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曹味東的圖書 |
 |
$ 221 ~ 280 | 後民族格局
作者:曹味東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民族」可以從人們共同的出生、語言和歷史當中找到其自身的特徵,這就是「民族精神」;而一個民族的文化符號體系建立了一種多少帶有想象特點的同質性,並由此而讓居住在一定國土範圍內的民?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屬性,儘管這種屬性一直都是抽象的,只有通過法律才能傳達出來。一個「民族」的符號結構使得現代國家成?了民族國家。但是,自1960年代末開始,這種民族國家的制度化形式越來越受到全球化的衝擊。
民族國家著眼於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詞表達的是一種動態的圖景,它們會不斷挑戰邊界,直到摧毀「民族大廈」。新的動態結構的意義在於動搖了空間和時間層面上的限制。把一定領土範圍內的統治者轉變成?掌握速度的大師,這就使得民族國家失去了其權力。當然,國家不能與防禦相提並論。國界更多的是充當一道閘門,從「內部」對各種潮流進行適當的調節。全球化過程是否削弱了民族國家的能力?民族國家是否無法捍衛其系統的界限和自主調節與周圍世界的交換關係?如果屬實,又是哪些全球化過程在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一個民族社會的民主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何種程度受到了影響?民族層面上出現的缺失,在跨國層面上是否可以找到功能等價物?
哈伯瑪斯從當前德國國內政治以及國際政治的發展脈絡,去探討、批判和重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民族」概念的轉變。他特別提出所謂「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在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界以及其他現實政治領域引發強烈的討論,甚至成?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推行政治、文化改革的理論基礎。此外,哈伯瑪斯在2001年4月訪問中國大陸時,也擷取本書的〈災難與教訓〉、〈論人權的合法性〉,在北京和上海兩地發表,引起眾多的迴響。
作者簡介: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在西方世界被公認20世紀西方社會、政治思想上,公認的關鍵性思想家。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成員,其研究領域涉入多層面的學門,也因此被視為如同百科全書般豐富理論的思想家。
他的研究論文具有畫時代意義,其重要的代表著作:《關於交往行為的理論》、《社會理論或者社會技術理論》、《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側面》、《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關於「時代精神狀況」的提綱》、《政治短論集》等等。譯者:曹衛東,曹衛東,1968年5月生於江蘇阜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學博士,現?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交往理性與詩學話語》、《權力的他者》等;編有《哈貝馬斯文集》(第1卷《合法化危機》、第2卷《包容他者》、第3卷《後民族結構》)、《霍克海默文集》(第1卷《?蒙辯證法》)、《話語政治與民族認同》等;譯有《價值的顛覆》(合譯)、《神學美學導論》(合譯)、《宗教社會學》、《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合譯)、《後形而上學思想》(合譯)等。
- 作者: 曹味東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570823801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9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