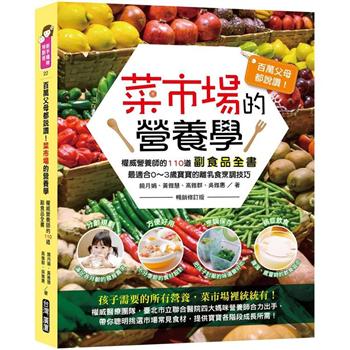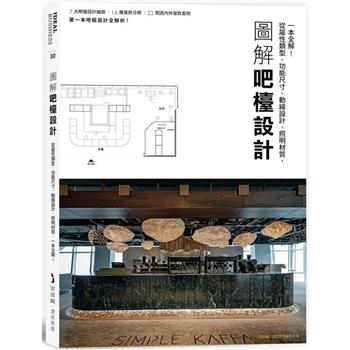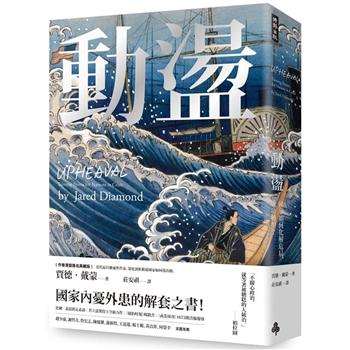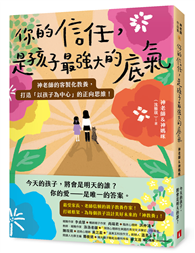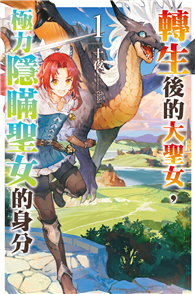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
閱讀臺灣文學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79年,那時我剛到上海讀研究生,專業是現代文學,方向是做「五四」文學。當年在北京的《當代》和《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永遠的尹雪豔》(白先勇)、《譚教授的一天》(李黎),是大陸最先刊載的境外作品、也便是最早進入我閱讀視野的臺灣文學作品。儘管這兩位作家其時都身在美國,可不知為什麼,那時大家都是把它們看作臺灣作家、臺灣小說的——那時還沒有「海外華文文學」這一說。(也或許,和得知白先勇乃民國時期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譚教授」的原型據稱就是「五四」元老、時任台大教授的臺靜農這些「背景」有關吧)。
初讀之下,不禁暗自驚訝:海峽的那一邊,原來竟也有如此高水準的作品!不由便慢慢地把臺灣及香港的作家作品納入了自己的專業閱讀範圍之內,倒並不是隨便看看消遣的。那時候,我們這些「二進宮」的老學生,有個習慣──從餐廳裏買了飯菜拿回宿舍吃,於是,吃飯時、睡覺前,就是互相之間交流的黃金時段,主要話題呢,不外乎各人當天看的專業著作或雜誌上近期刊登的新作品,常常為一些新作品爭得面紅耳赤,有時忘乎所以、欲罷不能,還真是有點「廢寢忘食」的味道。畢業後到蘇州教書,先還是弄弄老本行,開的課也就是低年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再加上一門高年級的選修課《五四文學流派》,對臺灣香港文學的閱讀習慣雖還是持續著,卻並沒有動念把它引進自己的研究和教學範疇。
1986年的某天晚上,有幾個同學到捨下來玩,海闊天空的閒聊中,她們異口同聲地向我推薦起了三毛,說:「老師,您看過三毛嗎?沒有書的話,我們那裏就有啊,什麼時候借給您看。」她們告知了同學們當下閱讀的熱點,還說不少女生甚至都成了「金(庸)迷」,說來說去,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開設有關的選修課。
現在回想起來,1988年我終於下決心在蘇州大學開講《台港文學研究》,把學術視野拓至「境外」,就主觀方面而言,是緣於導師、同窗、學生的三重情:許傑師是「五四」元老,60年前就在吉隆玻主編華文報紙的文學副刊,我師從他讀研時,常聽他講起當年在南洋的往事;北京師範大學的同窗、僑生塗乃賢15年前已經變身為香港作家「陶然」,那兩年重又恢復聯絡,不斷寄來作品;當下,喜愛三毛、金庸、瓊瑤的中文系學生熱切的建議和厚望。就客觀而言,則是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格局調整的整體環境使然,我在拙著《他者的聲音》一書的序中有過說明,此處不贅。
古人雲:「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如此地既讀又教,研究遂漸顯必要。很自然地,一篇篇有關臺灣、香港乃至海外華文文學的論文寫了出來,專書也出版了幾種。
收入本書的論文,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 、教學臺灣文學的部分成果。量既不多,亦似不成體系,今不揣翦陋,以為芹獻。身處江南,研究臺灣(及香港)之學,並無地緣之利,若要寫史,在我,似無可行性:私心以為,倘若不能親自把第一手的原始史料遍讀一過,爬梳剔抉一番,豈可輕言寫史?──文學史書寫之類的「宏大?事」是我不敢問津的。故所作以研讀作家文本、觀察文學現象為主,兼及對研究方法的思考。倘若有所感有所得,便寫點東西,長短不論,務必要有心得(或新得),否則不寫也罷。為學謹以「四不一沒有」自勵:不嘩眾取寵,不人云亦云,不信口開河,不故步自封;沒有感悟、心得絕不動筆。幾十年來大陸的風風雨雨曾經親歷,「文革」中的閉門讀禁書,仍自歷歷在目,在南北兩所最好的師範大學曾親聞謦咳的師長(如北京師大的穆木天、李長之、陸宗達、啟功、俞敏等,華東師大的許傑、施蟄存、徐中玉、王元化、錢穀融等)幾乎都曾遭遇過不公平批判和非人磨難的經歷,給我的問學之路、治學之思刻下了濃重的印記:任何時候都要有自己的堅守,趨時附勢不為,批判文章不寫,敬畏學術,把文學的還給文學,與其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莫如為情造文。
從私人的角度說起來,臺灣本與我的家族和個人素無因緣,在那裏,可謂既無親眷,亦無朋友。但自從閱讀了臺灣文學作品(後又延伸閱讀了不少兩岸有關臺灣的各類出版物——特別是歷史書和旅遊書)以後,竟從心底裏對臺灣這個地方平生出一份親近感來,讓我自己也不禁暗自稱奇。後來因緣際會,還真結識了不少臺灣朋友——多是學界中人,彼此相處甚洽;又四到臺灣,兩度客座,全臺北西南東幾乎「走透透」,更令我越加喜歡這方山水這裏人。如此讀、行、觀、思,相激相蕩,互動共生,我和臺灣之間的情分,就用得著幾句古人的詩了:「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辛棄疾)「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對我而言,臺灣就是我的「青山」、「敬亭山」。
回想這二十多年,在我的閱讀經驗和情感經驗中,臺灣文學、以及由此而來的「臺灣」 的種種,真可算是我無日無時不在心中追尋的的一份「愛」。如今,重看這些年寫下的這些關於臺灣的文字,油然想起的,居然又是辛棄疾的那幾句絕妙好詞:「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但願我這些觀察和思考,能讓賞光閱讀拙著的臺灣朋友知悉,有一個大陸學人,是這樣觀察臺灣的文學、思考臺灣的種種的,雖說卑之無甚高論,但皆出諸真情。倘能如此,則於願足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曹惠民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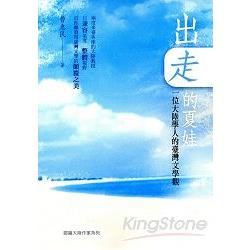 |
$ 315 ~ 378 | 出走的夏娃:一位大陸學人的臺灣文學觀【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作者:曹惠民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0-10-01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出走的夏娃:一位大陸學人的臺灣文學觀【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論述了臺灣文學的一些重要現象(如戰後鄉土小說與散文、現代派詩歌、女性寫作、通俗文學、同志文學與酷兒寫作、原住民文學、自然寫作等)的成就及其文學史意義;選評了吳濁流、鍾理和、余光中、華嚴、鄭愁予、張曉風、席慕蓉、古月、陳冠學、粟耘以及從李昂、朱天文、蘇偉貞到邱妙津、陳雪、洪淩等戰後與新世代作家的創作與其衍變,多有個人化的解讀,認為 「顛覆」已成為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創作的普遍傾向;亦就兩岸文學的聯繫與異同作了探討比較;並由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具體解析,進而求索臺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提倡整體觀察、比較研究與兼容整合,彰顯了理論視野與學術氣度。
作者簡介:
曹惠民,男,1946年生於中國江蘇南通。中國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目前擔任中國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學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館特約研究員。著有《他者的聲音》、《多元共生的現代中華文學》及《百年中華文學史論》、《台港澳文學教程》、《閱讀陶然》等。
作者序
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
閱讀臺灣文學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79年,那時我剛到上海讀研究生,專業是現代文學,方向是做「五四」文學。當年在北京的《當代》和《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永遠的尹雪豔》(白先勇)、《譚教授的一天》(李黎),是大陸最先刊載的境外作品、也便是最早進入我閱讀視野的臺灣文學作品。儘管這兩位作家其時都身在美國,可不知為什麼,那時大家都是把它們看作臺灣作家、臺灣小說的——那時還沒有「海外華文文學」這一說。(也或許,和得知白先勇乃民國時期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譚教授」的原型據稱...
閱讀臺灣文學的經歷,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79年,那時我剛到上海讀研究生,專業是現代文學,方向是做「五四」文學。當年在北京的《當代》和《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永遠的尹雪豔》(白先勇)、《譚教授的一天》(李黎),是大陸最先刊載的境外作品、也便是最早進入我閱讀視野的臺灣文學作品。儘管這兩位作家其時都身在美國,可不知為什麼,那時大家都是把它們看作臺灣作家、臺灣小說的——那時還沒有「海外華文文學」這一說。(也或許,和得知白先勇乃民國時期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譚教授」的原型據稱...
»看全部
目錄
目 次
自序: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I
輯一 現象流派論
顛覆之美─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之走向
出走的夏娃─試論臺灣女性寫作敘述主體的建立
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
臺灣自然寫作的流脈
記憶在山海間還原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身份書寫與文化內涵
在顛覆中歸返─我觀旅臺馬華作家群
華文鄉土文學的真價
現代派詩歌:從此岸到彼岸
藍星‧余光中與新月
通俗小說生態的比較考察
輯二 作家作品論
蕭條異代不同時
─《亞細亞的孤兒》與《倪煥之》對讀
鍾理和原鄉書寫的悲情
戰後臺灣鄉土散文七家論
情愛‧佛理‧人性─...
自序:燈火闌珊處 相看兩不厭I
輯一 現象流派論
顛覆之美─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學之走向
出走的夏娃─試論臺灣女性寫作敘述主體的建立
臺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
臺灣自然寫作的流脈
記憶在山海間還原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身份書寫與文化內涵
在顛覆中歸返─我觀旅臺馬華作家群
華文鄉土文學的真價
現代派詩歌:從此岸到彼岸
藍星‧余光中與新月
通俗小說生態的比較考察
輯二 作家作品論
蕭條異代不同時
─《亞細亞的孤兒》與《倪煥之》對讀
鍾理和原鄉書寫的悲情
戰後臺灣鄉土散文七家論
情愛‧佛理‧人性─...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曹惠民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0-10-01 ISBN/ISSN:9862215879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8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