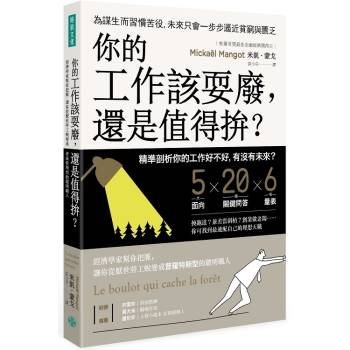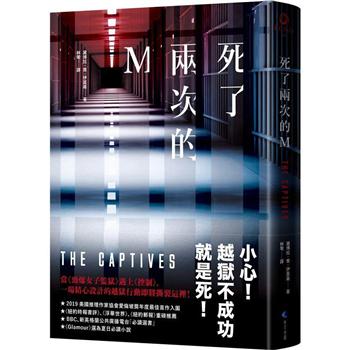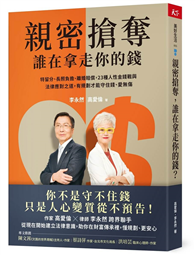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史蒂芬.金強推「非出版不可的故事」:《奔跑的記憶》是麥拉提創作的第三篇長篇故事,但這篇「小說」沒出精裝版,沒出平裝版,是個無法翻著看的故事,因為起初麥拉提只是把內容錄進錄音帶,製成有聲書來販售。二○○三年,史蒂芬.金「聽」到了這篇故事,大為驚豔,在《娛樂週刊》專欄內大讚這是一個出版社「非出版不可的故事」,促成《奔跑的記憶》文字版問世。
*著名好萊塢劇作家執筆,令人淚濕枕畔。
*售出14國版權,改編電影由哈利波特3的導演Alfonso Cuar?n執導,將於2009年上映。
在人生的分岔口,愛是你唯一的指引
一趟單車上的追尋之旅,重現一個家庭關於愛與失去的記憶
成年版《麥田捕手》+單車版《阿甘正傳》+美國的「唐吉訶德」
榮登《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暢銷書排行榜
「我就是這樣愛你,鉤子。我愛你,勝過世界上任何其他東西。就連我發瘋的時候,我都會想著你的好,希望好事會發生在你身上。還記得你怎麼找我嗎?還記得你是怎麼在水塔底下找到我,讓我騎著你的腳踏車回家,你跟在一邊跑嗎?所以我才擔心。我擔心你已經停下來,不跑了,我不要你這樣。我要你一直跑。我要你記得,繼續跑下去。」
史密西.艾德,43歲,體重126公斤,腰圍46英寸,上有老父老母,還有個美麗的姊姊蓓莎妮。喜歡的食物只有啤酒、蝴蝶餅,和香菸。跑步、單車則是他早已放棄的嗜好。
這年的八月天本該一如往常,突來的意外卻衝擊平凡的家庭。短短數日內,史密西的雙親接連過世。宛如接到葬禮的邀約,一封信自遙遠的美國西岸寄達,告知失蹤二十餘年的蓓莎妮如今落腳何處。為了將姊姊接回美國東岸的羅德島家中,史密西騎上了心愛的鐵馬,開始萬里長征,橫跨美國大陸。他遭人誤會為綁架犯、流浪漢,遇見鬱鬱不得志的傳教士、罹患重症的花農、樂天知命的卡車司機……無數失落的靈魂與他分享了生命的片段與風景。
孤寂的旅途上,只有一條電話線連結史密西與青梅竹馬的鄰居諾瑪。史密西在自己的回憶裡,一塊塊拼湊出姊姊心中那個神祕聲音的真相,也在一通通如自剖如告解的電話中,體悟流浪與追尋的意義。
相信自己曾經被愛,然後,重新開始…
奔跑的記憶【上路運動】
今天起,請在下面幾件事裡挑至少一件去做:
★開始閱讀,如果你曾經愛看書。你可以從<奔跑的記憶>開始。
★打電話給一個莫名其妙就疏遠了的朋友。
★重拾一種你荒廢已久的運動。
★拿出筆記,確實計畫你想了十年的旅行。
★辭職,如果你的星期一症候群長達五年。
作者簡介
朗.麥拉提Ron McLarty
出生於美國羅德島東天賜,知名劇作家、小說家、資深演員。一九七七年踏入影藝界,經歷豐富,除了於著名影集如《律師本色》(The Practice)、《法外柔情》(Judging Amy)、《Law & Order》、《慾望城市》等劇擔綱演出之外,也活躍於百老匯舞臺。他錄製的有聲書超過一百部,史蒂芬.金、丹妮爾.斯蒂(Danielle Steel)、Richard Russo、Elmore Leonard、Ed McBain、David Baldacci、Scott Turow等人的作品都由他獻聲詮釋。著有《奔跑的記憶》、《Traveler》、《Art in America》。現居於美國紐約市。
譯者簡介
秦於理
譯有《里斯本圍城史》、《豬頭滿天下》等。
成斐虹
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文字工作者。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