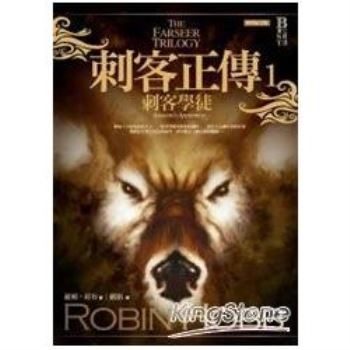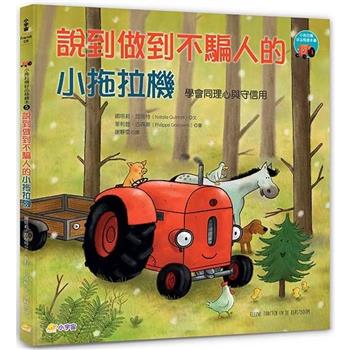朱利歐‧萊奧尼在《馬賽克拼圖謀殺案》中所選擇切入歷史的時間,讓他得以自由地穿梭於歷史真實與虛構間,撿拾著關於但丁的蛛絲馬跡,拼湊出但丁可能的真實面貌,增添他的血肉。而如同他筆下這位歷史上偉大的詩人偵探一樣,透過遊走於世俗政治與宗教的權力網絡間,努力還原出案件所隱藏的真實面貌,而直指宗教形上學中被刻意壓抑的真相。不僅是在案件的鋪敘,或是偵探的角色形構,甚至是重新詮釋歷史意圖上,朱利歐‧萊奧尼的《馬賽克拼圖謀殺案》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推理評論家陳國偉 專文推薦
一件慘無人道的謀殺案件,一個包藏禍心的學者團體,
一幅未完成的馬賽克巨幅壁畫,隱含著足以致人於死地的祕密。
但丁帶你遊歷中古世紀的罪惡城市,直搗地獄核心!
時間:十四世紀初的一個午夜
地點:義大利翡冷翠,廢棄的聖猶大教堂
死者:著名的建築師暨鑲嵌畫師安布洛喬
手法:雙手被綁在支柱上,臉上塗抹著石灰,被活活燒灼窒息致死
動機:遺失的未完成的巨幅馬賽克壁畫的草圖
嫌犯:第三重天!
剛成為翡冷翠執政官不久的詩人但丁,遇上了一起匪夷所思的恐怖謀殺案,案發地點在一座廢棄已久的教堂,頗有名氣的建築師安布洛喬負責該處馬賽克壁畫的繪製工作,卻發現被人綁在教堂裡的巨坑邊緣,用生石灰活活燒灼致死,屍體上則留下了五角星的割痕。未完成的壁畫雖遭刻意破壞,但仍看得出是由多種元素拼組而成的巨像,內容引用了聖經但以理書中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的夢境,馬賽克巨像的五個元素似乎暗示著翡冷翠的政治和宗教動盪,聖殿騎士的祕密海圖和傳說中的第五塊大陸。自認為全知全能、可以一手掌握整個世界的但丁,立即著手展開調查,發現命案牽扯到一群自稱「第三重天」的學者,這些成員包括自然哲學家、法學家、神學家、星相學家、航海家、建築師、藥劑師,個個來頭不小且十分聰明狡猾,全是為了祕密成立中的翡冷翠綜合大學而來,這其中究竟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陰謀?但丁如何遊走翡冷翠這個充滿著墮落、慾望與敗德,有如地獄般的城市,從而獲得真理?《馬賽克拼圖謀殺案》結合謀殺、詩學、歷史、神話、星相、政治鬥爭和宗教寓言,為歷史驚悚小說開創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格局,並且勾勒出了中古世紀時翡冷翠的迷人風貌。
作者簡介:
Giulio Leoni(朱利歐‧萊奧尼)
義大利作家,在獅子座和雙子星座的雙重影響下,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的午夜誕生於羅馬。他在大學時主修詩的視覺語言,畢業後曾在正規企業機構內工作了一陣子,自覺其個性更適合於混亂的人、事、物整體,以便藉此多方覓得故事題材。年輕時期的萊奧尼十分著迷於幻術魔法與中世紀文學,並且熱衷於研究「深奧而罕見」的問題,自認足堪擔當文藝復興時期哲學教師之職。在這些廣泛興趣的探索中,他拓展了許多關於占星術與算命學的知識,同時對迷人的幻覺藝術與異教儀式等亦多所涉獵。此外,他對於公元一二○○年這段時期的文學乃至上一世紀的前衛藝術都充滿好奇。在這其間,他創辦了內容探討詩和實驗文學的《象徵》雜誌,在這本雜誌中,萊奧尼盡其所好地對不尋常和無止盡的世界、歷史的爭議面貌(它的傳奇與光譜)、現實的真理和不確定的假設……等等問題加以剖析。自此,他找到了日後運用在每個故事中引人入勝的角色,並試著藉由言語讓他們生動鮮活起來。
二○○○年,萊奧尼以《美杜莎謀殺案(暫名)》(I DELITTI DELLA MEDUSA)一書,贏得(以偵探小說為主要對象的)「特德思奇獎」(il premio Tedeschi)。這本書首度介紹了具有特殊調查技能的桂冠詩人出場:書中的主角但丁被捲入了一項匪夷所思的陰謀,從而發揮出他傑出的偵探本領。對習慣於各類型偵探推理小說的讀者而言,很難想像從前在教科書裡讀到過的大詩人但丁,竟然也是一位調查員、幻覺與魔術的專家──這是朱利歐‧萊奧尼所賦予他的嶄新詮釋,充滿了驚奇與魅力。
奠基於對十四世紀歷史的深入研究,他在二○○四年寫出了《馬賽克拼圖謀殺案》(I DELITTI DEL MOSAICO),這是另一部以但丁為主角的冒險探案小說,在本書中,大詩人但丁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邪惡,隱藏在翡冷翠這座美麗的城市之中,遂以其完善的頭腦,循著令人震驚的祕密線索,去解開這幅極其複雜的犯罪拼圖。二○○五年,他出版了《光的謀殺案(暫名)》(I DELITTI DELLA LUCE),二○○七年出版《黑暗的十字軍(暫名)》(LA CROCIATA DELLE TENEBRE),連同之前的《馬賽克拼圖謀殺案》,可謂是翡冷翠詩人但丁的冒險三部曲。萊奧尼也嘗試寫一些適合青少年讀者的故事,以及許許多多的短篇故事,另外他還固定參與一本黑色推理雜誌的專欄寫作。
譯者簡介:
羅妙紅
2001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西方語學院義大利語言文學專業,獲取學士學位;2002年底至2003年底,去義大利特倫托大學留學,獲取了國際問題研究碩士;曾任職於義大利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處,從事了大量的口譯和筆譯工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翡冷翠,一三○○年六月十五日,夜半時分
他那細密的字體已填滿了好幾張紙,書桌上的蠟燭也越燃越短。從他落筆開始寫這份報告到現在,應該已過去好幾個鐘頭了。他停了下來,重新讀了一遍已寫好的部分。
他覺得疲憊不堪,偏頭痛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的太陽穴,令他毫無睡意。
「不錯,就是這樣!相反的假設能夠推翻錯誤的推理和事實。」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用手揉了揉額頭。
桌上有一個罎子和兩只杯子。他將罎中的水倒入一只杯子中,直到水從杯口溢出,流向地面,形成一窪細流,在磚塊鋪成的地板上流動。水流繞過那不規則的磚塊,滲入到地板上的一條裂縫裡。 「向下流,一定是向下流。」他高聲說道。他覺得眼前似乎有個身影正點頭表示贊同。
外面一陣聲響打斷了夜晚那完美的寂靜,有沉重的腳步聲,且那聲音越來越近,還伴隨著金屬撞擊的響聲,就像是有人在晃動樓板或是在舞刀弄劍。他將手伸向貼身衣服的口袋,那裡有一把他隨身攜帶的匕首。
攜帶兵器的人出現在他門外,而且是在深夜這麼晚的時間裡。晚間熄燈實行宵禁的鐘聲響過多久了?他突然覺得自己有些暈頭轉向。
他搜尋著可以讓他重新找回時間感的跡象,然而,透過狹小的窗戶向外望去,外面的天空依然漆黑一片,絲毫沒有黎明的影子。他悄無聲息地站起來,吹滅蠟燭,躲到門後。屏住呼吸,豎起耳朵,他傾聽著每一個細小的動靜。
門外,金屬碰撞的叮噹聲仍舊傳來,就好像一些士兵正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著什麼。但丁抓住匕首的把柄。此時,他聽到了兩聲低沉的敲門聲,接著,一個粗獷的聲音在呼喚著他的名字。 「但丁閣下?」
但丁動了動嘴唇,猶豫著,不知道該怎麼辦。聖皮耶羅修道院作為執政官府邸,應該有警衛巡邏,特別是晚上。他就任執政官職位的授職儀式剛剛結束,難道那些混蛋就想搗亂?
「但丁閣下,您在裡面嗎?請您開門。」
他不能再猶豫了,或許,他們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來向他這位執政官求助的。他迅速戴上有著長紗巾的執政官官帽,將刻有象徵翡冷翠的百合花圖案的印章戒指套到食指上,又仔細撫平了仿古羅馬風格的長袍上的皺褶,然後才拉開門的插銷。
「你想幹什麼?混帳!」他語氣尖銳地問道。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壯實矮小的男子,身上穿著一件過膝的鐵甲衣。鐵甲衣的上面,他沒有穿常見的印有百合花徽章的戰袍,而是加穿了一件盔甲。盔甲由多片金屬板做成,金屬板之間是靠皮繩連接在一起的。這男子的頭藏在一個戰盔下面,頭盔呈柱形,一如當時流行的十字軍頭盔的式樣。他的肩上挎著一把帶鞘的劍,腰帶上還赫然別著兩把短劍。
「宵禁熄燈之後禁止在城裡轉悠,只有強盜和扒手敢違反禁令,而他們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上絞刑架……我希望你已好好地考慮過後果。」詩人用威脅的口吻接著說。
那人無言以對。雖然身著戎裝,但他看起來不像個危險人物。即便如此,和他說話的時候,但丁的雙眼仍一刻也沒有離開對方的雙手。此人一隻手提著一盞油燈,另一隻手則空空的垂放在腰側。要擊倒他並不難,頭盔邊緣與身上的盔甲之間有一道拇指寬的縫隙;此外,從頭盔中露出的一部分臉,即便難以觸及,仍然提供了一個足以致命的突破口,如果一刀刺中其眼睛的話。
「我是警長,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我的公事,也是為了您的公事。他們剛剛選您當執政官,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們都得聽您的吩咐。」來人的語氣中透出某種抱怨,同時,他竭力挺直了那敦實的身軀。
但丁身體前傾,仔細端詳對方藏在頭盔中的臉部輪廓。從那十字形的開口中,隱約可見一個高高隆起的大鼻子和兩隻像老鼠一樣擠得很近的小眼睛。
現在,但丁認出他來了,的確是警長,市政廳警衛部隊的頭子,一幫土匪的頭子。 他鬆開緊握著匕首的手。「是什麼魔法讓我們的公事聯繫到了一起呢?」 「在聖猶大教堂,新城牆那邊……發生了一樁命案。」面對執政官,來人似乎猶豫不決,「一樁……或許需要市政廳權威人物介入的命案。」他結結巴巴地說。 「誰被殺了?」
警長沒有回答,他在費勁地試圖解開頭盔的繫帶。最後,他終於將那笨重的頭盔從頭上取了下來,大汗淋漓的樣子。「我們還不清楚。可是,最好您能親眼看看,您能去嗎?」
「先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 「好,有某種……某種超自然的、詭異的東西……」
但丁開始不耐煩起來。「讓我來判斷什麼是、什麼不是詭異之事,就像我們的先人說的,如果我們一無所知,一切對於我們而言都是令人驚奇的。」他拍了拍警長的肩膀,「你自然不是最適合辨別什麼是符合自然規律發生的,什麼則截然相反;只有對事實認真研究,對是非瞭若指掌,博學者才能區分什麼是司空見慣的事,什麼是奇特詭異之事──兩者之間存在天壤之別,你應該這樣想。」
「是的……我明白。」對方低聲回答。 「好吧,告訴我事實,而不是你所認為的。」 警長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一個男人,死了,在聖猶大教堂裡。被殺死了……我想。」 「你為何需要市政廳的最高權威介入此事呢?難道稽查罪案不是你的職責?」 「是的,當然……可是……反正,我覺得,您最好親眼看一下,求求您了。」
這最後的請求似乎讓他付出不小的代價。但丁瞪著他,那薄薄的嘴唇因憤怒而變了形。
「不是用眼睛看的,警長,而是用大腦!你需要的是我的大腦。你就像其他的盲人一樣!你找我找對人了……你真該謝謝聖施洗約翰──我們所有人的守護神,是他讓我當執政官的──如果情況像你所說的那樣嚴重的話。」
「那您去嘍?」來人又問,他的語調再次暴露了他的焦躁不安。「這兒有水,地上。」他指了指地板,接著說。
但丁沒有馬上作答,而是陷入了自己的沉思中。他將目光投向在天窗中露出的夜空,看著那些真實的星星和它們被畫在屋內藍色穹頂壁畫上的圖像。這真是他成為執政官的一種奇怪的開始方式。一種不祥的預感向他襲來,令他倍感不安。
但丁回過神來,猛然抬起頭,取過他此前放在屜櫃上的鍍金權杖。「我們走!」他命令道,領先跨過了門檻。
他們走過拱廊,通往各個房間的門一溜兒排開。但丁在想,其他五名執政官,他們那軟弱愚笨的大腦必定還沉浸在渾濁的睡夢中,那夢裡可能充斥著縱欲和暴飲暴食的幽靈。他停了下來,拉住警長的手:「什麼原因促使你來找我?」
對方清了清嗓子,似乎有些尷尬:「因為,因為人們說您比任何人都有學問。您是詩人,不是嗎?您寫了一部作品。」
「那我,一名詩人,能幫你什麼呢?」 「在那死亡中有某種不可思議的東西。」 但丁聞言決定不再發火,面對那樣一個蠢人,他又能說什麼呢?
「他們說,執政官當中,您最適合……」警長繼續說。 「適合幹什麼?」
「適合……適合追查神祕的事情。」警長用一種特別的語調吐出這幾個字,裡面夾雜著崇拜和懷疑。在此人簡單的頭腦裡,神祕的事情是罪行的前廳,詩人想,或許,此人把他也看作一個潛在的罪犯。看來等執政官任期一到,他就得開始提防此人。不過現在看來,此人確實需要他的幫助。可不是嗎?只見警長一邊煩躁地搓著雙手,一邊有節奏地將身體的重量從一隻腳挪到另一隻腳。
於是但丁舉步繼續走起來,警長默默地跟上他。 他們首先穿越那土質路面的大廣場,一輪圓月的光輝灑落在廣場上,地面上堆滿了烏貝蒂家族房屋的斷壁殘垣──它們是吉伯林派在貝內文托慘遭兵敗之後被破壞的。該戰役之後的三十多年裡,這座廢墟便成了這座城市建造新建築的採石場。老橋上油燈的微弱光亮為這一大片黑暗帶來了些許光芒。藉著燈光,可以隱約看見矗立在前方的烏貝蒂家族的領袖法里納塔家殘存的塔樓側面扶垛泝。
這些建築殘存的部分就像一顆顆從地上冒出來的殘缺不全的巨大牙齒。在道路規劃師的設計圖中,那片混亂的、幾被夷為平地的建築物所在地將成為城市真正的中心。從那往前,隱約可見將成為市政廳新大樓的建築那龐大的黑色身軀。工程已接近尾聲,高大的塔樓赫然可見。一個睡夢中的巨人,猶如被宙斯的閃電擊中的泰坦,正伸出一隻手抓向天空。無人知道那圍牆裡堆砌了多少塊沾染了吉伯林派鮮血的石頭。
巴別塔不也是以同樣的榮耀而建造的嗎?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種狂熱之中。破壞和建設。打敗高高在上者,然後用一種新的不可一世的傲慢來替代他,與此同時,妒恨已如同毒蛇一般在人們心中悄然萌生。
但丁轉向警長:「你說的是聖猶大教堂?……它可不是在第一圈城牆之內的一座堂區教堂,而是在城牆之外啊。」如果他沒有記錯,這座教堂非常遠,建在城門之外通往羅馬的大道上。「許多年前,它是一座屬於奧古斯丁隱修教派的修道院。在聖十字教堂,在關於方濟會修士的一堂課上,有人提到過它……」關於那些求學日子的甜美回憶在一剎那間浮現在他的腦海裡。「我原以為它已經被遺棄了。」他總結道。
「它是被遺棄了,確切地說,它曾經被遺棄過。奧古斯丁隱修會的人多年前棄之不顧,從那以後它就日趨破敗,直到紅衣主教會議決定重新修復它。我聽說,它將成為翡冷翠大學的所在地。」
「一所大學?」 「對……正是。」
「可翡冷翠沒有大學。」詩人疑惑地說。 警長聳聳肩,「反正,他們想在那裡建一所大學。您請,咱們乘我的馬車去。」 靠近染布商人雲集的廷多里路街角,停著一輛結實的四輪馬車。他們倆登上前方的位子,座位上方覆蓋著用麻布織成的篷布,隨從的警衛們則坐到後頭。待在那帳篷裡,詩人覺得又悶又熱,不過,至少,他可以不必與警衛們胳膊肘緊挨著胳膊肘地擠在一起。
馬車沿著石頭砌成的路面轟隆隆地跑了起來。拉車的馬對這不同尋常的夜間趕路似乎也不太樂意,不斷地發生偏離方向的錯誤。馬車在青條石地面上顛簸前進,綁在馬上的皮韁繩也無法減輕那陣陣顛簸。
在那跌宕起伏的晃動的折磨下,但丁的偏頭痛加劇了。他從身旁的車窗望出去,只看見冷峻的舊城牆朝後掠倒。隨後馬車拐向阿爾諾河,奔向感恩橋。在這裡,他們被看守出入行人的區域警衛攔住。藉著火把的光亮,警衛們認出了警長。在警長的命令下,他們撤去了攔住拱門的鏈條。
馬車漸漸駛離了市中心。阿爾諾河的對岸,空氣似乎越發稠密,人工鋪設的路面突然消失了,車輪開始行駛在被踩平的土路上,發出沙沙的響聲。先前有著石砌圍牆的建築物也被成片破破爛爛的木屋所代替。這些房屋位於通往羅馬的路邊,就像一大群衣衫襤褸的乞丐,只有不時出現的一兩座小教堂那較為高大的身影,以及開闊的田野和葡萄園,才能打破這著實令人乏味的風景。老橋的燈光早已成為回憶,四處漆黑一片,只有微弱的月光才帶來了些許光亮。
他們在黑暗中前進著。但丁覺得某種東西似乎出現在他們身邊。它危險、令人窒息,如同那層覆蓋在蔥蘢的草地上方的濃厚的黃色煙霧,當他們越來越接近郊區的時候,它似乎溜到馬車旁邊,幻化成形。那是罪惡,一種外來的罪惡,它先在城市的四周不斷變得稠密起來,然後,緊緊地將這座城市包裹起來。
「死者是誰?」他突然問道。只有在那一刻,他才發覺警長還沒有把死者的身分告訴他。有人幻化在虛無中,卻連名字也不被人用一句惋惜的話記起。但丁暗暗做了個趕妖除魔的手勢。
「不……我們還不知道。您等會親眼看看吧。」 但丁本想堅持再問,隨後,他無奈地聳了聳肩,不再作聲。歸根到底,這樣做是最好的,本來嘛,他就是被請來對此事做出解釋的,他寧願自己直接對事實做出判斷,而不是依賴於別人並不肯定的感覺。他的思緒重新回到了聖皮耶羅修道院自己的房間裡,回到他那被中斷的寫作中,他聽憑自己的身體隨著馬車上下晃動,力圖讓疲憊的身體得到片刻放鬆。 那座教堂位於阿爾諾河南邊約莫一英里的地方,處於一片開闊的鄉村地區中,現在已被新的第三重城牆圈入其中。最初,它應該是這條通往羅馬的道路上的一個堂區教堂。它的外面堆滿了建築材料、木工用的工具和軸線板。
教堂原來後殿的一部分被納入了新防禦堡壘的壁牆之中,舊鐘樓的底部被人用扶垛加固了,被改建為一座瞭望塔。這座建築在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經受諸多變遷的痕跡仍依稀可辨。這些變遷使它成為一座集宗教與軍事特徵為一體的建築,卻又令它顯得頗為怪異。教堂的正面,是一座有著尖拱的正門與兩扇狹小的十字形窗戶,那是某種海外古老建築風格的典型特徵。從海外歸來的朝聖者曾向但丁講述過類似的建築構造。
過去一定有人曾試圖將入口用柵欄圍起來,現在,柵欄的多處都被拆除或連根拔去了。那洞開的大門裡透出移動中的火把搖曳的光。
「屍體就是在那裡頭被發現的……」警長說,他像嗅到某種突如其來的危險的動物一樣張大了鼻孔。 但丁在街邊屠夫那裡的牲畜身上看到過類似表情,但他不認為警長是個懦夫。十一年前,在坎巴迪諾戰役沴中,當敵軍騎兵進攻他們那已經潰不成軍的部隊時,但丁曾看到警長奮力抵抗阿雷佐騎兵的進攻。為何他現在會在一座教堂門前感到如此恐懼呢?
太陽穴的絞痛再次強烈地向但丁襲來。他強忍住嘔吐,急躁地離開這個尚在猶豫中的人。他想盡快處理這件事,然後躲到他自己的屋裡,重獲安寧。但丁穿過昏暗的中殿,徑直朝底部那群手持火把的人走去。
「大人……等等!停下!」 背後傳來警長焦慮的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就像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毫無疑問,是疼痛擾亂了他的感知能力。用美德與知識武裝起來的精神不可能永遠都能夠戰勝脆弱的肉體,他痛苦地想。他走了二十幾步之後,聲音再次響起。
「等等,停下!」這次,聲音聽起來不一樣,伴隨著回聲。 陣陣眩暈令詩人失去了平衡,他踉踉蹌蹌地又走了幾步。就像幾個小時前在自己的屋裡一樣,他感到自己不是單獨一人。「什麼……」他困惑不解地喃喃問道。此時,一束光籠罩在他周圍,他感到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停下!死亡就在這!」 拉住他的是一個身著戎裝的年輕士兵,從他的頭盔裡冒出幾綹金色長髮。士兵手裡握著一支火把,籠罩住但丁的光芒就是它散發出來的。此人就像是突然間冒出來似的,一邊使勁拉住但丁的手臂,一邊放低火把,照亮他們腳下的空間。在那一剎那間,但丁看到了年輕人那湛藍的眼睛的反光。當他把目光轉到地上時,不由得驚呆了。
原來,他正站在一個深淵的邊緣。中殿的地面似乎被人從一側到另一側硬生生地橫向撕裂開了。一個無底洞在地板的中央敞開著大嘴,就好像有一個龐然大物從高處落下,砸裂了石頭地磚,朝地底深處直穿而入,如同突然從天而降的撒旦,只有左右牆壁邊上殘存的兩條寬不過一碼的狹長通道尚可通行。
只需向前再走一步,他就會葬身其中。他將手伸向額頭,擦了一把冷汗,蹲下休息。至少過了一分鐘,才覺得漸漸恢復了元氣,偏頭痛消失了。但丁將身體轉向他的救星,然而,那名年輕士兵已不見蹤影。於是,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深坑的邊緣,試圖掂量出它的深度。那一定曾經是個地下墓室,要不,這座教堂就是建立在另一座建築──一座帶有蓄水池的古羅馬大型別墅之上的。
他再次將目光投向空洞洞的後殿。此時,他的耳邊響起趕到他身旁的警長那氣喘噓噓的呼吸聲。「但丁閣下……幸好您及時停了下來。」
但丁覺得他的關切中帶著某種虛情假意的成分。他做了個推開對方的生硬手勢,然後,緊貼著牆壁,小心翼翼地沿著無底洞邊上那狹窄的過道挪步走了過去。
現在,但丁可以清楚地辨認出後殿牆壁附近一小群身著戎裝的人。他們手裡舉著火把,圍著一個由木樁搭成的腳手架。腳手架很高,頂部隱沒在黑暗中。他們將火光集中照在大家面前的一個人身上:一個對他們的躁動無動於衷的高個子男人。他的頭朝向中殿,就像是正在仔細觀察黑暗中的動靜,等待著某個人的到來。
但他的靜止不動中有某種異樣的東西:他的臉上好像蒙著一塊手帕,那手帕掩蓋了他的相貌特徵;他直挺挺地立著,雙手交叉在背後。
但丁驚詫不已,圍觀的警衛們臉上也是同樣難以置信的表情。此人似乎既是受害者,又是此命案無聲的目擊證人。
警長靠近但丁,如同一隻受到雷聲驚嚇的狗一樣想尋找慰藉。 但丁急切地走完剩下的幾步。他從一名士兵手中奪過一支火把,慢慢靠近屍體。 死者靠著腳手架的其中一根支柱,穿著灰蒙蒙的破舊衣服,雙手被綁在背後,雙腳叉開,雙膝微屈,似乎正處於一種一觸即發、馬上就會跳起來的狀態中。他的頭部和頸部都被一層石灰覆蓋住了,只能大致看出他的輪廓。
下意識地,但丁想伸手救他一把,但是他很快抑制住這種衝動──因為正是靜止不動否定了他體內尚有一絲生命氣息的可能。他的雙手被綁在支柱上,臉上的石灰泥覆蓋層已變成固體。他杵在那裡,略微前傾,活像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船頭雕飾──在地獄之河上面擺渡的靈魂的艄公卡隆特或許會把他用作自己的船頭裝飾,但丁這麼想。
「現在,您明白為什麼需要市政廳的最高長官出面了吧?我們必須……必須通知神聖的宗教裁判庭。這座改為民用的教堂裡有鬼……」警長結結巴巴地說。
他曾經多少次問過自己人類有多少無恥妄言,詩人對自己說,現在,它就在自己面前以最卑劣的形式出現。「你做得非常明智,帶我到這裡來。」他緩緩說道,「至於宗教裁判庭,現在,你先別讓他們介入此事。如果我認為合適而且有必要的話,我們有的是驚動他們的時間。」
第一章 翡冷翠,一三○○年六月十五日,夜半時分 他那細密的字體已填滿了好幾張紙,書桌上的蠟燭也越燃越短。從他落筆開始寫這份報告到現在,應該已過去好幾個鐘頭了。他停了下來,重新讀了一遍已寫好的部分。 他覺得疲憊不堪,偏頭痛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的太陽穴,令他毫無睡意。 「不錯,就是這樣!相反的假設能夠推翻錯誤的推理和事實。」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用手揉了揉額頭。 桌上有一個罎子和兩只杯子。他將罎中的水倒入一只杯子中,直到水從杯口溢出,流向地面,形成一窪細流,在磚塊鋪成的地板上流動。水流繞過那...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