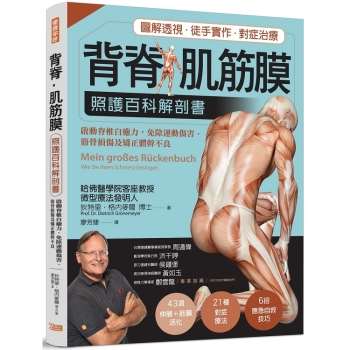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來源]:
一本關於畸形教育的「詩史」,輕盈詼諧的中學生活編年紀。13歲的朱夏妮,在人人皆認為全無詩意的地方,時時刻刻看到有詩,把痛苦和壓抑轉化成詩,在課間偷偷寫在作業本上……
[本事]:
樹藉花再生,人藉詩重活,再年輕的小樹也會開花,再稚嫩的小詩人也想舒活自己的情思、刷出自己的存在感。華文世界極年輕的、出生於2000年烏魯木齊的朱夏妮,拎著新疆的天地進入凡間,以她渾樸自然、觀察入微、又創意十足,尤其是深具反思和批判能力的詩語言,為我們的成人世界示範了在21世紀如何真正「刷出存在感」的書寫形式和方向。(白靈)
[慧眼]:
夏妮的詩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如此年幼的她,顯示出非凡的才能。
——哈金(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小學生透過清亮的眼睛讀世界,能讀到最美的意境。
——郎朗(鋼琴家)
朱夏妮的詩,感覺清新,富於意象,特別善於瞬間的感覺。
——北島(詩人)
在朱夏妮的詩裏,我感到一種和我完全不同、卻同樣深刻艱難的“處境”,小小年紀,不小的詩思!我想到少年的顧城,但有全然不同的語境。
——楊煉(詩人)
華文世界極年輕的、出生於2000年的朱夏妮,拎著新疆的天地進入凡間,以她渾樸自然、觀察入微、又創意十足、尤其是深具反思和批判能力的詩語言,為我們的成人世界示範了在21世紀如何真正「刷岀存在感」的書寫形式和方向。
——白靈(詩人)
兒童或少年寫的詩,不一定就很可愛,不一定就很清新,不一定就很稚拙,不一定就需要再成熟,為什麼?因為說不定他已經很成熟了,說不定他已經很冷酷了,說不定他已經很銳利了,就像任何一個成人的詩人一樣。在詩人的面前,年紀一點都不重要。朱夏妮就是如此。
——梁文道(作家、香港電視讀書節目主持人)
宋朝的美學是平淡,我們看梅堯臣,覺得這是詩嗎?如果我們把他的詩歌和唐朝比較起來,我們覺得宋朝能寫很好的詞,很美,但不能寫很好的詩。因此,如果從宋朝美學的平淡來看,朱夏妮完全是對的。
——顧彬(德國波恩大學教授、漢學家)
小夏妮的詩是春雨,淅淅瀝瀝地洗刷著我們生命的塵埃。這是孩子送給我們的一場非同尋常的大閱讀。在這個讓精神奴化為表演和娛樂的可恥的物欲之期,我們面對這樣的閱讀或將慚愧到不知所措。
——張煒(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
我們詩的源頭《詩經》裏的詩的語言是透明的,是一個詩人站在這裏,不需要借助於什麼,不像今天一個詩人說話的時候,你感覺他身後100多個詩人教他怎麼說。《初二七班》的這些詩,好處就在於它不是專業化的詩,它讓我重新找到那樣一種陽光照耀下,語言和事物核心的透明的直接的關係,我願意讀這樣的詩,因為我和這些詩之間是沒有障礙的,我馬上感覺這樣一個孩子她眼中的世界,她心中的喜悅、驚奇、哀愁、痛苦,都如此準確和直接地,像雨滴打在身上一樣,落在我的眼裏。
——李敬澤(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
中國教育所特有的,早被習以為常的緊張的教學關係,正被這風聲鶴唳中的一個孩子敏感地體會著。絕大多數孩子對於逃脫不掉的外來壓力只選擇忍受和抱怨,而所有這些痛苦和壓抑,卻逐一被朱夏妮轉換成了詩。
——王小妮(詩人)
朱夏妮使我想起不世出的說法語的少年詩人藍波,以及我二十餘年中學教師生涯中在一些日記、週記簿裡看到的幾位國中女生早慧、特異的詩的靈魂。
一一陳黎(詩人)
才女總是令人驚艷的。已出過多部詩文集,十五歲的朱夏妮尤其如此。
一一楊平(詩人)
作者簡介:
朱夏妮
2000年5月出生於烏魯木齊。10歲開始寫詩,參加第一、第二屆小學生詩歌節並獲獎,擔任第三屆小學生詩歌節評委。獲得首屆北京文藝網國際詩歌大賽優秀獎。參加武漢第四屆中國詩歌新發現夏令營,在上海舉辦「忘帶校卡的人——朱夏妮詩歌朗誦專場」。出版詩集《忘帶校卡的人》(2013)、《初二七班》(2014,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推薦)、《第四節課》(2014)和長篇小說《初三七班》(2015)。現在就讀於美國高中。
推薦序
序一
拎著新疆出發的小詩人 白靈
一隻很早就自動學會展翅、離巢試飛的小鳥,是什麼樣的鳥兒?一個很早就對這世界皺起眉頭、眼底充滿疑惑和不解的小女孩,會是什麼樣的女孩?
世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樣貌,在這位小女孩筆下和腦中被重新編織,她把她感受到的美與痛織在一處,成為這本詩集。對這位才十幾歲的小女生而言,詩,有時是她親手為自己安上的翅膀,隨時準備離地而去。詩,有時是她試著不願被處罰、不想被規訓所規訓的一種抵抗形式,
是她掙扎著不要被社會制度硬生生植入晶片,是個極有自覺的異類,甚至是異形。這位小女孩來自新疆,10歲開始寫詩,在大陸已出了詩集和小說,她叫朱夏妮。
出生在鳥魯木齊的她,是一匹從小慣於縱韁馳騁的小牝馬,不,她是不服管的,她眼底裝滿新疆的大草原,她根本是不願被安上韁繩和座墊的小野馬。一直在那裡讀完小學的她,早已看慣大山大河大漠大草原,有誰還可以從她心中搬走這些自由和廣袤呢?
「中學之前」她寫的詩多與當時所處新疆的天與地有關,視域內所見有太多美妙的事物。「小學之後」她飛到廣州讀中學,眼睛前後都是人,尤其進入制式的、競爭激烈、處處講究規則的教育體系後,她宛如被置放馬廄中,轉不過身。前後形成極大的反差,詩是她不得不的紓發方式。她暫時失去了飛的能力,此時詩是她的四蹄、她的馬鞭,詩是她半夜揚高前蹄的嘶嗚,詩是她抽打四周高牆發出的清脆咻叫聲。
因此只有小學階段是她張眼看這世界時,最舒坦、輕鬆、偶覺孤獨的快樂時光,在詩中她多以寫景詠物的方式寫下她眼底的新疆,那其中儲存的,可能會是她一輩子最美的記憶。這本詩集中最早的一首寫於2010年7月,那年她才10歲,詩題就叫〈七月〉,前半段說:
七月的草原是這樣的
指尖幾乎都能摸到天空上
飄著像乾旱了的土地似的雲
天下面的綠海上
是羊群們組成的黑白色的船隻
視線夠遠無所阻擋時,天地接連的地平線上飄過的雲宛似就在腰幹以下,伸手彷若即可觸及,「乾旱了的土地似的雲」說的應是草原的大起大落,「綠海」有時、「乾旱」也有時,朱夏妮都經歷過,因此面對「綠海」美景時或許都有一點擔心。她「指尖」幾乎摸到的「雲」是救不了「乾旱了的土地」的雲,而「草原」能成為「綠海」、「羊群們」成了「黑白色的船隻」,寫的是場景夠壯大夠遙遠夠夢幻,有不真實的感覺。總之,朱夏妮把會動的雲寫成不動的土地,動得不大的羊群和草原說成船隻行過海景,就顯現了她具有強烈形象思維和運作語言如畫筆的能力。
隔不到一年,她再寫的幾首詩也都是超齡的,如〈鳥鳴〉前半:
涼席剛鋪到床上的第一天晚上
窗外,一陣鳥鳴
連綿起伏
那聲音像硬幣掉在木地板上
像啃咬蘋果的牙齒觸摸紅白色果皮肉的聲音
像魚嘴伸向湖面吸氣的聲音
「鳥鳴」不好形容,她連用了五個比喻,所引是前三個,硬幣掉地、啃咬蘋果、魚嘴吸氣,一個比一個細緻而越需倚靠觀察並想像。其後是「高跟鞋踏向虛榮的大理石臺階」、「天使親吻孩子的聲音」,一個誇張一個親蜜,正好把連綿起伏的鳥鳴聲,用想像的伏加以捉摸。又比如〈禮拜天〉:
禮拜天
教堂門前 傳來
聖歌聲 鳥兒在教堂
尖頂上飛
影子像波紋一樣散開
雲在移動
教堂也彷彿在飄著
有人向我微笑
笑容很漂亮
我把耳朵貼在古石牆上
只能聽到空氣流動的聲音
像寂寞的呼吸
鳥影「波紋一樣散開」,雲動「教堂也彷彿在飄著」,真是不可思議的描景手法,卻非全然想像,而是心因感動而生錯覺似的美感。這種感受又不好與人說去,只能將耳附牆,尋找倚靠,卻只聽到「寂寞的呼吸」,這是一個早熟、古怪而孤獨的女孩,她才11歲。
與上述二詩寫於同月份的〈賽里木湖畔〉是她寫詩「元年」最具動態之美的一首詩:
湖邊的沙是銀白色的
駿馬奔騰在湖邊
馬蹄濺起的水花
打在騎馬人的衣上
他毫不在意
任馬飛奔
時間在倒流
在馬的喘息中
馬的鬃毛和騎馬人的頭髮
一同飛翔
這首詩讓筆者想起惠特曼《草葉集》中的〈騎兵過河〉一詩,〈騎兵過河〉寫的是一支長長的騎兵隊伍策眾馬入河出河的過程,時而遠鏡頭時而特寫鏡頭,多半是慢行或停頓,末了過河後隊伍旗幟昂揚,整軍後再度出發。朱夏妮寫的是一騎、一瞬之美,更集中的定鏡頭,只專注人與馬飛奔時幾乎合為一體的動人畫面。地點是新疆的極西,幾乎與中亞哈薩克相連的賽里木湖畔。水花打在騎馬人身上,形容馬步伐之大,「時間在倒流/在馬的喘息中」,形容馬的速度在喘息之際即彷彿超前了時光,而人髮與馬鬃來及跟上,像翅翼在追趕人臉與馬臉似的。此詩,不僅是人與馬合一,一旁觀賞的作者之眼也幾乎與其合一。她如此捕捉人事物的功力,令人訝然、驚異。
然而好景畢竟不常,上了天山的必須下山,進了沙漠的終必踏出沙漠,朱夏妮不能不回到凡間,遠去到廣州要進中學的她,在上學之前她知道再看到「雲和天是永遠的夥伴/就像草原和牛糞/不會分開一樣」(〈那天在山上〉)的日子已經結束,此後「湖讓大地保管/自己的身體/它的靈魂通過我的眼睛/來到我心裡」(〈藍湖〉),只有倚靠湖的靈魂在她心底駐紮下來,否則「糖果沒了 只剩糖紙在努力讓自己飽滿」(〈沒了〉),她告訴自己今後「你去找鏡子拿回你曾經的笑容吧/你把孤獨埋進你的練字本裡去吧」(〈孤獨的小孩〉),「你」即她自己,這是她與自我對話的一種方式。
朱夏妮幾乎是在說新疆的靈魂「通過我的眼睛/來到我心裡」,那是一個兒童還在身心快速成長的初階說的真心話。寫過《眼與心》、研究過兒童心理學的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即強調兒童接觸世界第一時刻的重要性,因為他們是基於身體對世界的「觸摸」去認識了世界。亦即認識的發生不是通過意識,而是通過整個身體(尤其是眼睛)浸入、親臨現場時才算「觸摸到」的結構而作用的。只有身體必然得與發生場域有所連繫時,接觸到世界才能同化為身體的內在形式。同時,兒童最初的語言完全也是通過身體來表達自我的,語言的表達能力即是通過身體的表達而獲得的,是先有那個知覺世界才能過渡到那個文化世界和語言世界。當然這時父母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10歲之後,朱夏妮的爸爸媽媽開始培養朱夏妮,推薦她讀的書竟已有《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簡愛》、《飄》、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omer,1931-2015)的詩歌等等,這種早熟的閱讀可能成就了朱夏妮無數次內在的奇幻之旅,也成就了她以語言內化新疆、「拎起新疆」成為她身體一部份的能力。
然則,何以新疆的草原不能是她一直可以拿來畫畫和書寫的作業簿?新疆的天山不能一直用作她案頭的筆架、寒凍時擋風的窗櫺?桌沿的鹽湖和柴窩堡湖不能是她的墨水瓶?放在浴室的賽里木湖不能是她洗臉沐浴吹風的澡盆?客廳裡頂著瓷罐的少女、跳舞的阿瓦古麗們、哈薩克人大自然的樂曲、愛睡覺的羊群不能一直走在她微笑的眼睛裡?廚房裡鍋蓋掀開的沙漠、冰箱打開的冰原不能一直是她寂寞時數星星、孤獨時作夢的地方?事實殘酷地告訴她,「時間」已經「像夢一樣離去」(〈小院裡〉),之後才隔沒多久,她竟已是「被書本夾在中間的樹葉」(〈中秋節〉),「天被鎖在帶著紗的窗外」「滲了奶油的藍色 /在很遠的地方默想」(〈那片窗外的天空〉),她想不到自己離新疆竟然有那麼遙遠了。
才上中學三個月,她過的已經是〈籠子〉似的生活:
這裡的風帶著聲音滑冰
偶爾在你腳下絆倒
每個人都在過濾聲音
這裡的聲音沉重
風背不動它
聲音不會飛
比氣泡更容易消失
圍牆足以擋住它的去路
「聲音滑冰」,偶爾還在「腳下絆倒」,說的是聲音超速、甚至失速,又要小心翼翼地「過濾聲音」的都市生活,聲音沉重、不會飛、風背不動它,對應的都是新疆,因為在那裡,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但「星星把我忘了/把這裡忘了/把來這兒的路也忘了」(〈忘了〉),新疆即使再回去也回不去了,她一天天要面對的是她沒有一樣喜歡的課程內容和老師。她說政治課老師你的笑罕見/去動物園也看不到」(〈致政治老師〉),上英語課:「我的心掉下一米/又慢慢地爬上來/我裝成上你的課/的樣子/身子僵硬」(〈致英語老師〉)。連上她最拿手的語文課:
你在黑板上寫下
我不喜歡的內容
可我必須要記下
像是把心框進一個心形的木框裡
我只能自己用刀一點點剝小我的心
讓它有地方跳動
我想去外面看看
可那兒有被老師修理過的
扎人的花草 (〈致語文老師〉)
她無處可逃,轉而求助她的信仰:
我想去天上
可是我沒有衣服
天上會很冷嗎
聖母只穿一件紗裙子
天上有老師嗎
有老師我就不去了 (〈我想去天上〉)
老師竟成了阻擋她去天上與聖母見面的理由!因為老師那麼嚴厲,常處罰她,罰掃地、罰擦黑板、罰倒垃圾,發考卷是用擲的,「卷子掉在我臉上」(〈考 〉),唱國歌時她「眼光掃過這個班/當她眼睛看到我時/我稍稍加大了聲音」(〈唱國歌時〉),連同學她都不喜歡,作弊的、告密的、言不由衷的⋯⋯。比如告密後,就會「有人用眼睛發出的光/擊打我眼睫毛/使它彎曲 烤焦 發出香味」(〈間諜〉)。比如說班長維持紀律時賊頭賊腦:「耳朵聽鹽的味道/聞我們輕聲的細語/耳朵和鼻子/帶動你的上眼皮/粉筆摩擦粉灰落下/黑板上有一個代表我/的數字」(〈致班長(二)〉),比如初一的代表上臺發言,「他把學校/喊成一個後花園/把書本的味道/喊得香得/在校外都能聞到」(〈開學典禮(二)〉),這使得她跨進校門「我的身體拖著我的心/去我不想去的地方/接受 這裡的人/看表一樣的看我/我不願意穿獄服一樣/統一的服裝」(〈校門〉),她小小心靈的痛可想而知。
但她不可能屈服,她是拎著新疆離開新疆的人,那是她胸中不可能被折疊被壓縮的廣天大地。她轉而使出她的看家本領,用冷筆,應該說,用小說的筆,寫她所看到的一切,比如寫女老師對某小男生的「另眼相待」和曖昧動作:
路過他的桌子
她會讓時間先睡一會
他沒穿長褲的
有很多腿毛的腿
讓她的身體傾斜
短髮搖晃
她走過他的椅子
手與他的白色校服擊掌
快速走過別的桌子(〈絆〉)
「讓時間先睡一會」、「身體傾斜/短髮搖晃」、「手與他的白色校服擊掌」等的描述,均準確地寫出了她觀察對象的小動作和細節。她有一雙銳利可怕的眼睛,甚至對黑暗角落產生關注:
掃把和簸箕
住在一個房間裡
那裡潮濕和溫暖
我每天都會去看它們
把手浸在有光的盆子裡
把帶有陽光的水
帶給它們(〈關於黑板之三:有陽光的水〉)
她想向耶穌懺悔,因為「你的眼睛裡/只有我向下望的雙眼/佈滿血絲/重複的回答/在固定的時間/念珠生了綠色的鏽」,說的均是在制式化教育下,毫無彈性的日子,但可能此時沒有長者如在新疆時姥姥阿姨們的帶領,她在黑暗中,看不到耶穌。
這本詩集記錄的最後一天是2013年3月21日,她13歲,政治課上她寫的,題目是〈政治考試47分〉,末半說:
她的聲音好聽
像睡前講故事的聲音
我無法安睡
風穿過防護欄
到我手上
從這裡我看不到天
只有深綠和淺綠的樹
綠色窗戶的住宅樓
看樣子,在那當下,只有寫詩才是她唯一的脫困方式了,她真誠無諱地記錄了政治高於一切的體制下一個幼小心靈心中的痛、苦、扭曲和不滿,對這種將人極度「異化」的系統的反彈,能以誠實且清新、直白又具有創意的詩語言說出,是連大陸眾多的成年詩人們都說不出口的。
然而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也在某個程度上經歷過類似的過程,卻也未見得完全解脫。有誰見過臺灣的小朋友寫過這樣一系列的詩作?因此此詩集能在台灣出版,就深具意義,值得教育和文化工作者作為借鏡,重新思考孩子創造力的無限可能性,當朱夏妮說天的「藍墨水不均勻地/滴進湖裡」、說「鞋裡的泥湯/想念草上的雨」、說「湖面有皺紋/湖在搖/哄著倒影睡覺」,她說的是心中對美的感動,而「美育」何曾成為我們教育體系重要的一部分呢?此詩集也可讓家長明白,培養孩子接觸大天大地、不阻止他們自主地感受和批判的關鍵為何,同時對小朋友及早接觸自然、培養閱讀和寫作的能力也深具啟示性,尤其是各類文學和詩的接觸。
樹藉花再生,人藉詩重活,再年輕的小樹也會開花,再稚嫩的小詩人也想舒活自己的情思、刷出自己的存在感。華文世界極年輕的、出生於2000年烏魯木齊的朱夏妮,拎著新疆的天地進入凡間,以她渾樸自然、觀察入微、又創意十足,尤其是深具反思和批判能力的詩語言,為我們的成人世界示範了在21世紀如何真正「刷出存在感」的書寫形式和方向。
序一
拎著新疆出發的小詩人 白靈
一隻很早就自動學會展翅、離巢試飛的小鳥,是什麼樣的鳥兒?一個很早就對這世界皺起眉頭、眼底充滿疑惑和不解的小女孩,會是什麼樣的女孩?
世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樣貌,在這位小女孩筆下和腦中被重新編織,她把她感受到的美與痛織在一處,成為這本詩集。對這位才十幾歲的小女生而言,詩,有時是她親手為自己安上的翅膀,隨時準備離地而去。詩,有時是她試著不願被處罰、不想被規訓所規訓的一種抵抗形式,
是她掙扎著不要被社會制度硬生生植入晶片,是個極有自覺的異類,甚至是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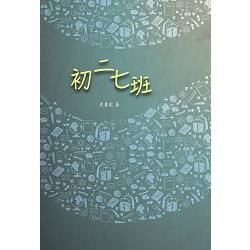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