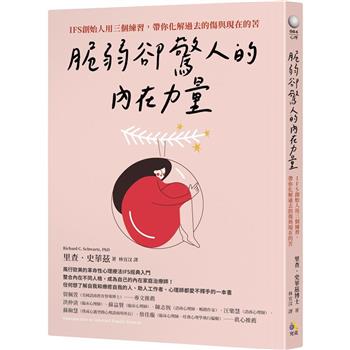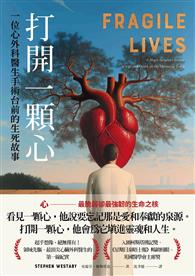李哲洋,在台灣當代音樂發展史或教育史上,始終是個與眾不同的特例。
其父親因受到白色恐怖的牽連而早逝,連帶也讓李哲洋被列入「特殊名單」中,使他終其一生遭到學院體制的排除和拒絕,未曾獲得任何「正式音樂教育」的學位文憑。
然而,李哲洋依舊熱愛音樂。即使縮衣節食,也要追求知識;即使艱辛跋涉,也要秉持田野的精神,深入山林採集音樂;即使編輯部只有他一人如老牛拉車,他也要努力為台灣撐起一本具分量的音樂雜誌。因此,不意外,深知箇中道理的有識之士皆認為,李哲洋的理論基本功,早已超越了當代某些專家學者。
李哲洋長期以來持續筆耕不輟,累積超過上百篇的音樂論述、報導、隨筆、雜文,尤其跨至民俗學及人類學的音樂觀察,迄今仍是值得反覆閱讀的時代經典。可惜在其有生之年,缺乏機會將其研究結晶整理為具有系統性的專書,致使一般讀者大眾難以深入瞭解此人在當代台灣音樂文化史的重要意義,以及其建構內在思想上的知識脈絡。
本書集結並精選41篇論述,以四大脈絡——民族音樂的探求、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未來、傳統音樂與童謠研究、從雜誌編輯到音樂教育,將李哲洋一生為音樂奉獻的成果進行綜理與爬梳,並透過當代藝文工作者的旁觀記述,為李哲洋生前的形象賦予栩栩如生的描繪。期望透過他談樂的文字,還原其為音樂知識歌唱的聲音。
各界推薦
周婉窈(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雷驤(作家、畫家)
明立國(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退休教授)
葉綠娜(鋼琴家)
林暉鈞(小提琴家)
黃國超(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莊效文(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吳家恆(古典音樂電台主持人)
周婉窈│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哲洋,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台灣一等人才,但生在黑暗時代,時代的暗黑只差沒完全吞沒他。白色恐怖奪走他的父親,他失學、赤貧、終身受監控,賣房子決心出國也不獲准;受限於學歷,必須忍受主流學界的掠奪,最後連天都不假壽,只在人間56年;離世後,家屬捐給公家的大宗資料也遭部分毀損。這是怎樣的人生?這是怎樣的戰後台灣?但李哲洋沒被擊垮,面對劫難,他奮發、堅毅、不屈,為他的時代點燃一盞小灯,為後世留下珍貴的精神與物質遺產,這本《李哲洋談樂錄》是「焚而不燬」的印記,非常值得大家閱讀,尤其原住民音樂的部分。白恐時期有嚴格的「官式用語」,不照著寫一定惹禍,何況是李哲洋;拂掉沙礫重現本色,還他歷史定位,是我們的責任。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看見李哲洋,是台灣社會的進步。在這個「無名」的音樂工作從事者的身上, 我們可以見證到進步的腳步,從來都不會輕漫順遂。因為缺乏正義,一直都是台灣社會的特徵。
雷驤│作家、畫家
此書一觀,就像清晨的一陣風,彼時的樂壇氛圍又回來了。
明立國│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退休教授
李哲洋的理念與實踐,與台灣體制內的音樂文化形成若即若離的一種輔助、並行甚至批判的力線,讓台灣音樂史多了一些值得反思的角度與層次。
葉綠娜│鋼琴家
李哲洋老師總對所有事物充滿著自然流露的熱情,加上追根究底的好奇心與細膩的心思,為一個時代的台灣音樂史蹟及音樂人留下了最寶貴的記錄。《李哲洋談樂錄》之出版,會讓我們更加認識這位默默耕耘、奉獻的音樂人。
林暉鈞│小提琴家
不論讀者有興趣的是歷史、音樂、或是思想,《李哲洋談樂錄》都是一本必讀的好書。想知道李老師是什麼樣的人,不需要知道他的人生故事,直接讀他的文字就好了。那種平等看待各種文化的胸襟、對人對社會的關心、以及冷靜銳利的分析力,不管在什麼時代都是罕見的。
許多人為李老師抱屈,我認為不必。就算再苦,他熱愛音樂,就一輩子從事音樂工作;喜歡學問,就做了一輩子的研究。國民黨可以毀了他的家庭,卻不能禁錮他自由的靈魂;可以剝奪他就學的權利,卻無法阻止他成為一位頂天立地的學者。世上本來就沒有公平與正義,只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追求幸福的唯一憑藉。
在我心裡,李老師仍然騎著他的越野車,背著器材,奔馳在某個人跡罕至的山徑。只是他走得太快太遠,我們望不見他的背影而已⋯⋯
黃國超│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一直以來,我深深覺得李哲洋先生在戰後台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這本書的出版,適足以補足許多人心中長期的缺憾,並且讓我們有機會再一次親炙他的熱情、毅力與進出田野、書房間的觀察、思索跟文字風采。希望這個澆灌戰後台灣民族音樂採集、調查、研究的老實園丁,不再被民眾遺忘!
莊效文│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我一直以為,人類的教養與文明的建立是一種累積的結果,「知識」絕對不是以當下坊間最流行的「淘汰觀」而存!正如同那些年,李哲洋的書寫,給我、也給後世們最珍貴而至極為深刻的影響,讓我們站在他的肩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
我們欣見李志銘編輯《李哲洋談樂錄》的出版問世,因為李哲洋的書寫無疑是「科普」的教材與範本,即使到了今天依舊如此!這些書寫經過志銘兄的整理成冊,讓這此書更形一部「台灣音樂知識史」或「台灣音樂思想史」的文獻,而我思我想也正合志銘兄所言:這也正是在我們現今這個時代之所以需要重讀李哲洋的關鍵理由。
吳家恆│古典音樂電台主持人
在記憶中,我初次看到「李哲洋」三個字是在念高中時,但是當時,這就是一個名字,沒有引我進一步追索。讀了《李哲洋談樂錄》由李哲洋公子李立劭所寫的〈序──家中的考古及歷史行動〉,才知拼圖的另一半:一位孜孜不倦的書寫者,才會讓一般讀者也接觸到他的著作;一位辛勤的田野工作者,累積大量的蒐藏;在世時因政治因素而身處學院門牆之外,死後遺留的文物捐給藝術學院,未得妥善保管而損壞。再讀李志銘主編李哲洋當年所寫的文字,對他的勤奮與見地感到佩服,對他的才具沒有得到充分施展感到嘆息,對於他留下的文物因官僚無心而損毀感到痛心。所幸仍有有心人,編成《李哲洋談樂錄》,或可迎來對李哲洋、對過去半世紀台灣音樂學術史的重新評價。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哲洋等的圖書 |
 |
$ 395 ~ 475 | 李哲洋談樂錄
作者:李哲洋等 出版社:艾巴克影像體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1-15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李哲洋談樂錄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哲洋
1934年生於彰化,1950年考入「省立台北師範音樂科」,隔年因受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所牽連,遭校方藉故勒令退學。自此輾轉當過書店店員、台肥公司製圖員,1962年起任中學音樂教師,後執教於實踐家專及藝專。除了北師一年的學習外,李哲洋的音樂知識全靠自學,涉獵範圍廣泛。1963年開始進入山地部落採集原住民音樂,並於1966至1967年間參與「民歌採集運動」。1971年擔任《全音音樂文摘》主編,負責策劃該雜誌編譯工作長達十九年。他也從日本出版界翻譯了不少古典音樂和舞蹈理論的經典名著,僅靠一己之力累積了大量的田野錄音採集資料,乃是台灣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先行者。1990年因病去世,留下了大批的手稿、筆記、藏書、聲音和影像等珍貴文獻現存於北藝大。
編者簡介
李志銘
1976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著有《半世紀舊書回味》、《裝幀時代》、《裝幀台灣》、《裝幀列傳》,書話文集《讀書放浪》、《舊書浪漫》、《書迷宮》,以及聲音文化研究《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新作《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於2022年10月出版問世。目前專事寫作。
李哲洋
1934年生於彰化,1950年考入「省立台北師範音樂科」,隔年因受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所牽連,遭校方藉故勒令退學。自此輾轉當過書店店員、台肥公司製圖員,1962年起任中學音樂教師,後執教於實踐家專及藝專。除了北師一年的學習外,李哲洋的音樂知識全靠自學,涉獵範圍廣泛。1963年開始進入山地部落採集原住民音樂,並於1966至1967年間參與「民歌採集運動」。1971年擔任《全音音樂文摘》主編,負責策劃該雜誌編譯工作長達十九年。他也從日本出版界翻譯了不少古典音樂和舞蹈理論的經典名著,僅靠一己之力累積了大量的田野錄音採集資料,乃是台灣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先行者。1990年因病去世,留下了大批的手稿、筆記、藏書、聲音和影像等珍貴文獻現存於北藝大。
編者簡介
李志銘
1976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著有《半世紀舊書回味》、《裝幀時代》、《裝幀台灣》、《裝幀列傳》,書話文集《讀書放浪》、《舊書浪漫》、《書迷宮》,以及聲音文化研究《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新作《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於2022年10月出版問世。目前專事寫作。
目錄
序文|家中的考古及歷史行動/李立劭
前言|主編的話/李志銘
序章|追憶李哲洋身影
音樂民俗學者李哲洋/無心子
音樂的生活者——李哲洋其人及其思想/明立國
擦身而過/吳季札
在逆流中尋找生命的泉源——李哲洋/鄭水萍
告別音樂會——白色青年李哲洋紀念/雷驤
夕照下的絕筆/雷驤
李哲洋的音樂書寫——蘊藏於「民族/音樂」辯證敘述裡的生命經驗/范揚坤
第1輯|民族音樂學的探求
亞洲的音樂概貌
民族主義音樂釋義
從花岡一郎忠奸問題談起
流行歌與民歌之異同
流行歌與民歌的異同
漫談黑澤隆朝與台灣山胞的音樂——研究台灣山胞音樂的第一塊穩固的踏腳石
山胞音樂提示
賽夏族矮靈祭歌舞素描
矮靈祭歌舞
布農族合唱曲的是非
台灣山胞音樂〈序〉
與呂炳川博士一夕談——難得開口說話的道道地地的台灣山胞音樂專家
呂炳川實至名歸,以「山胞音樂」享譽東瀛
記一位殞逝的音樂學者——憶呂炳川博士
談「音樂的起源說」——任何人都能隨意說的話題
第2輯|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未來
中國現代樂府——第二次發表會聽後感
樂壇新氣象
一個我行我素的音樂家——談被誤解的李泰祥
日本作曲家談——中國當代的音樂
外記: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
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
音樂學懺悔錄——「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之訂正
《中國鋼琴曲集》問世的時代意義
大師與阿彬——中國近代音樂史補白之一
電子樂器點滴——本世紀發明的新樂器
第3輯|傳統音樂與童謠研究
台灣童謠(上)
台灣童謠(下)
新和興歌劇團的《白蛇傳》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絲竹合奏求變
第4輯|從雜誌編輯到音樂教育
漫談「全音」音樂文摘的編輯
我與《全音音樂文摘》
四十年來台灣的音樂期刊——音樂雜誌是領導時代?或反映時代?
音樂閒話
漫談音樂著作權
音樂圖書館
音樂工業人才的培養
二十一世紀音樂史裡的一頁
音樂無國界嗎?
民樂在音樂教育上的新評價
樂興時刻
樂評管見
附錄|生命的軌跡
李哲洋年表
李哲洋編譯著作
目前已出版的相關李哲洋田野錄音
參考文獻
前言|主編的話/李志銘
序章|追憶李哲洋身影
音樂民俗學者李哲洋/無心子
音樂的生活者——李哲洋其人及其思想/明立國
擦身而過/吳季札
在逆流中尋找生命的泉源——李哲洋/鄭水萍
告別音樂會——白色青年李哲洋紀念/雷驤
夕照下的絕筆/雷驤
李哲洋的音樂書寫——蘊藏於「民族/音樂」辯證敘述裡的生命經驗/范揚坤
第1輯|民族音樂學的探求
亞洲的音樂概貌
民族主義音樂釋義
從花岡一郎忠奸問題談起
流行歌與民歌之異同
流行歌與民歌的異同
漫談黑澤隆朝與台灣山胞的音樂——研究台灣山胞音樂的第一塊穩固的踏腳石
山胞音樂提示
賽夏族矮靈祭歌舞素描
矮靈祭歌舞
布農族合唱曲的是非
台灣山胞音樂〈序〉
與呂炳川博士一夕談——難得開口說話的道道地地的台灣山胞音樂專家
呂炳川實至名歸,以「山胞音樂」享譽東瀛
記一位殞逝的音樂學者——憶呂炳川博士
談「音樂的起源說」——任何人都能隨意說的話題
第2輯|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未來
中國現代樂府——第二次發表會聽後感
樂壇新氣象
一個我行我素的音樂家——談被誤解的李泰祥
日本作曲家談——中國當代的音樂
外記: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
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
音樂學懺悔錄——「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之訂正
《中國鋼琴曲集》問世的時代意義
大師與阿彬——中國近代音樂史補白之一
電子樂器點滴——本世紀發明的新樂器
第3輯|傳統音樂與童謠研究
台灣童謠(上)
台灣童謠(下)
新和興歌劇團的《白蛇傳》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絲竹合奏求變
第4輯|從雜誌編輯到音樂教育
漫談「全音」音樂文摘的編輯
我與《全音音樂文摘》
四十年來台灣的音樂期刊——音樂雜誌是領導時代?或反映時代?
音樂閒話
漫談音樂著作權
音樂圖書館
音樂工業人才的培養
二十一世紀音樂史裡的一頁
音樂無國界嗎?
民樂在音樂教育上的新評價
樂興時刻
樂評管見
附錄|生命的軌跡
李哲洋年表
李哲洋編譯著作
目前已出版的相關李哲洋田野錄音
參考文獻
序
前言
主編的話/李志銘
回顧過去,無論是在台灣當代音樂發展史或教育史上,李哲洋都是個相當與眾不同的特例。
他早年家庭生活困頓、父母離異,十七歲時又受到父親白色恐怖事件牽連,而被迫從當時僅僅念了一年的台北師專音樂科退學,自此列入有關單位的「特殊名單」中,終其一生未曾獲得任何「正式音樂教育」的學位文憑,就連想要出國進修也完全不被允許。
儘管屢遭學院體制的排除和拒絕,卻仍阻擋不了李哲洋內心對於追求音樂知識的狂熱。於是他開始到書店打工,靠著自學美術繪畫,考入基隆的台肥公司擔任製圖員,之後更勤奮自修通過普檢,轉任基隆三中的音樂教員。即便經濟拮据,也要不惜縮衣節食來購買各類音樂專業書籍進修苦讀。
在學識上,李哲洋除了早期中小學曾經接受一些基礎教育之外,其它外語知識如英文、日文、法文,乃至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幾乎全由自習而來。昔日同在藝專任教的鋼琴家好友吳季札形容他是「在這個年代已經罕見的自我修業的學者」,並且強調「與哲洋爭論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是一位極謙虛的君子,極有禮貌,因而也是強者,一個真正的強者」。戲劇學者邱坤良亦曾以李哲洋和呂炳川、史惟亮三人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在民族音樂研究的用功程度猶在許常惠之上」。文史工作者鄭水萍甚至在一篇緬懷李哲洋生平事蹟的傳記文章裡轉述指稱:「他的功夫在理論上已超過當時師專的某些老師。」
古籍《左傳》有云,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用現代話來說,「立德」意指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則是提出真知灼見的言論,並將之形諸文字、著書立說,以被後人永遠銘記。此三者當中又以「立言」影響最為深遠。
唯令人惋惜的是,一向熱愛廣泛閱讀、在朋友眼中堪稱博學多聞的李哲洋雖是自學有成,長期以來也一直持續筆耕不輟,累積數十年超過上百篇的音樂論述、報導、隨筆、雜文散見《全音音樂文摘》、《大華晚報》、《夏潮》、《教育文摘》、《雅歌月刊》、《青蓓雜誌》、《音樂生活》、《音樂與音響》、《出版家》、《藝術家》等各大報章雜誌,卻因有生之年始終沒有整理集結自己的文章,以專書出版問世,致使一般讀者大眾很難真正深入去瞭解李哲洋在當代台灣音樂文化史的重要意義,與其建構內在思想上的知識脈絡。
自始欠缺「立言」的遺憾,直到李哲洋過世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二○二二)方才有了轉捩的契機,這也正是筆者編纂《李哲洋談樂錄》這部著作的微言大義之所在。
勤勉自學民族音樂的理論泉源
向來好學的李哲洋雖未能完成音樂科班學業,但在其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唯有透過大量買書閱讀來充實自己,加上多方面的興趣,遂養成了熱衷蒐集資料文獻的習慣,舉凡音樂教育、作曲理論、樂評隨筆、民歌採集、童謠研究、民俗學、人類學等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以致形成了他思想上較廣的視野面向。
追溯李哲洋對民族音樂的首度接觸,在他二十九歲那年(一九六三)參加救國團舉辦的一次登山訓練活動中,無意間聽到同隊一位學員哼唱著客家歌謠,歌中濃厚的鄉土韻味,勾起了他早年曾在客家村住過一段日子的強烈鄉愁。自此追尋民族音樂的意念便在他心中滋生蔓延。後來由於外祖母是賽夏族的關係,李哲洋也開始進入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庄鄉的賽夏族部落,和當地原住民喝酒搏感情之餘,順便搜集一些音樂素材。
及至一九六六年,李哲洋因參與史惟亮成立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繼而推動「民歌採集運動」初期的田野調查,需要援引國外發展相對成熟的音樂學相關知識作為採集工作的理論參考,於是他率先翻譯了日本民族音樂學的權威學者小泉文夫(Fumio Koizumi, 1927-1983)早期經典著作《日本伝統音楽の研究1:民謡研究の方法と音階の基本構造》部分篇章內容,包括〈民歌的概念〉和〈民歌的蒐集〉,陸續發表在翌年(一九六七)五月和六月《音樂學報》連續策劃兩期的「民歌專號」當中。
約莫這段期間,西方興起的「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也逐漸捨棄過去狹義的系統音樂學框架,開始採用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從文化與社會脈絡的角度來詮釋、重新發掘音樂背後的豐富意涵。就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下,小泉文夫即以日本傳統音樂為研究起點,注重民間音樂的採集和分析,並將民歌視為一種基本文化,即作為所有日本傳統音樂基礎的體現。
影響所及,觀諸李哲洋日後針對民族音樂研究撰述的許多文章當中,幾乎都能明顯窺見小泉理論的身影。
比方小泉認為,民歌應從音樂、文學、民俗等多重角度綜合看待,而民歌或民樂本身的音階結構亦反映了日本人的基本音高感,且應從聆聽者的經驗中掌握音樂的實質,並強調日本音樂應該體現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不僅僅是模仿西方藝術音樂。如是對照李哲洋在〈山胞音樂提示〉與〈民樂在音樂教育上的新評價〉等文中再三提及,當年他在五峰鄉賽夏族一連數日聆聽矮靈祭現場吟唱四度平行疊音調(Organum)的親身體驗,由此闡述「一個人在怎麼樣的音樂環境下,自然而然會具有某種音感」、「我這裡欲以強調的音感,便是這種音樂的音感、格調的音感,而不僅僅是西樂和弦的音感」。相較這類說法皆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針對採集民歌的基本認知,小泉文夫在〈民歌的蒐集〉一文表示「純粹的民歌將急速地消失,頗難區別純粹的與都市化了的民歌」,並指出「原來由鄉間的傳承者保存下來的民歌,經過都市的流行歌手洗禮之後,如果這些東西一旦倒流回到原地,則很可能會把原有的東西驅逐出去,這對於民歌本身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如果不是先明瞭古老的民歌形態之前,對於民樂的研究者是一項頗為困擾的事」。同樣重視民歌本身具有歷時性(Diachronique)變遷特質的李哲洋,毋寧也在〈流行歌與民歌的異同〉文中強調:「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顯然流行歌是民歌的延展或蛻變,況且本質無異於一般人以為的民歌,以及部落歌謠中的俗謠」、「所謂俗謠,實在是小社會的流行歌;所謂流行歌,實在也是大社會的俗謠」。 除此之外,李哲洋也曾對台灣童謠產生濃厚的興趣,還為此做過相關題材的田野調查,並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雄獅美術》雜誌上。無獨有偶,小泉文夫在其代表作《日本伝統音楽の研究1》一書中,亦將童謠視為民歌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礎出發點。小泉指出,童謠的聲音組織和音調清楚地顯示了民歌最基本的元素。
跨域的人生風景:從民間學者到雜誌編輯
小泉文夫作為日本民族音樂學的先驅,在他主持國內外諸多研究項目的同時,也不斷藉由商業出版與大眾傳播媒體的長期合作,將源自世界各地的民間音樂介紹給學院專家以外的普羅大眾,進而在日本社會帶動了「民族音樂」的熱潮。
當時透過自學鑽研民族音樂理論的李哲洋,對於小泉文夫既能跨越學院體制藩籬、又能廣泛影響社會大眾的學術成就,他雖不能至,卻也心嚮往之。
儘管李哲洋對音樂懷有巨大的熱情,但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後代的他,不僅無法取得大專音樂科系的正式學位,更無緣出國深造,因此只能透過學院體制外的迂迴方式來參與音樂活動。因此,他毅然接下了《全音音樂文摘》這份刊物的編輯工作,雖然從未掛主編之名,卻肩負主編之責。該雜誌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創刊,至一九九○年一月正式休刊,中間曾停刊數次又復刊,共計發行一百三十三期。
《全音音樂文摘》雖以專業的古典音樂題材為主,內容卻十分豐富多元,且重視版面閱讀的編排設計、圖文並茂,舉凡古典樂派、國民樂派、印象樂派、現代音樂、美國民歌,甚至到搖滾樂都有涉及。其中某些特定主題的專集策劃更是首開時代風氣之先,即便今日看來也依然頗具前瞻性:比如「舞蹈與音樂特輯」漫談西方現代舞與古典音樂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共生關係;「民族音樂專輯」探討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對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影響,並延伸引介印度、非洲、中南美洲和北歐的民族音樂;「亞洲音樂特輯」生動記載了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賽夏族矮靈祭,以及早年亞洲作曲家聯盟初成立時在台灣的活動紀錄;「電子音樂專集」則是展現出彼時電子樂器革命掀起的新世界。
執編《全音音樂文摘》近二十年來(一九七一—一九九○),李哲洋同時身兼民間音樂學者、中學教員、大學兼任講師等多重角色,他幾乎就像條老水牛那樣勤勉賣力、兢兢業業,一邊自掏腰包購買設備採集民歌做研究,一邊持續讀書翻譯寫稿熬到半夜,還要負責每個月按時編出一本夠分量的音樂雜誌。
話說當年李哲洋之所以「一生懸命」、甘願為這份刊物付出遠大過金錢報酬的心力,主要理由除了透過雜誌社本身與其資助者「大陸書店」的進口管道,能夠讓他更方便取得來自國外(大多是日本)的音樂書刊唱片等第一手資料之外,當然還有在精神方面與知識上的滿足,如此一來,他的文章也才有更多機會在公眾媒體上刊登。
日常生活中,李哲洋對待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很熱情、健談而好客,每當一聊起音樂話題便欲罷不能,加上身為雜誌主編,自家書房就是《全音音樂文摘》編輯部,妻子林絲緞也是知名舞蹈教育家,夫妻往來的朋友很多都是藝文界的人物,家中訪客也總是川流不息。當時較常前來串門子的親朋好友,主要包括雷驤、戴洪軒、張邦彥、徐松榮、林崇漢、郭芝苑,畫家楊識宏、呂晴夫,還有小說家七等生、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等,另外還有他們各自帶來的家眷妻小或其他藝文界友人。
在李哲洋家的客廳裡,這群朋友之間很容易彼此交流、吸收到關於音樂文學藝術的各種新資訊和新觀念,在昔日那個資訊匱乏的時代,儼然形成一種類似民間公共論壇性質的客廳沙龍聚會。作曲家徐松榮便曾在一篇論文訪談回憶:「在所有朋友當中,對他創作觀念幫助最大的,應首推李哲洋。」
不被體制化的自由思想
早年因父親涉入白色恐怖事件的影響而經常受到情治人員「關注」,李哲洋往往將自已內心真正的情緒藏得很深,平常外表看來總是一副樂觀開朗的樣子。但從李哲洋留下的諸多文章隨筆內容看來,他的文字風格亦是恰如其人,具有濃厚的日常生活談話氣息,在客觀的理性當中帶著一絲抒情的感性與詼諧的幽默,用以鼓舞或激勵他身邊的一眾知交。譬如在〈台灣山胞音樂序〉、〈與呂炳川博士一夕談〉等文中,便能明顯感受到李哲洋頗為偏愛使用「對話式」的互動文字來展現人物訪談現場的鮮活畫面。
觀察近些年來的台灣本地音樂學界在全面納入「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之後,所謂的「論文發表」、「學術研討會」,越來越像是少數圈內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在的空虛與犬儒,當然更不要奢望能對當代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力,似乎也無人藉此討論如何增進開拓未來教育和獨立思考之功效。尤有甚者,某些學者教授只在乎驗證自己的學術理論,抑或選擇性地只看到他們想要看的那一小部分,見樹不見林,而非真正重新檢視、深入瞭解當年在複雜的政治社會脈絡底下,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音樂人物整體生命的真實面貌。
類似的情況,李哲洋早在〈四十年來台灣的音樂期刊〉這篇文中便有所提及:「音樂期刊的內容委實足於反映此間音樂界的風潮。就作者、譯者的身分而言,近十年來,出自於音樂工作者的文章十分有限,尤其由音樂學專業人才執筆的,更是鳳毛麟角(升等論文姑且不論)⋯⋯這充分反映目前音樂界普遍缺乏對音樂遠大的理想,只坐享前人植樹成蔭之涼快,這是值得探究的隱憂。」
據此而論,當年李哲洋正因為立足於學院體制之外,所以才能夠站在一般讀者大眾的角度去思考一些嚴肅議題,也由於他始終不被定型在某一特定專業領域,李哲洋的思想範疇才因而更加寬廣、自由,字裡行間更不乏深具批判性的反思洞見(Insight),既深諳各家理論思想之精髓,卻又不拘泥於理論形式之框架。這也正是在我們現今這個時代之所以需要重讀李哲洋的關鍵理由。
最終,為了讓本書內容更親近一般讀者,也更符合李哲洋文章裡彷彿與好友聊天的話語氛圍,故將書名喚作《李哲洋談樂錄》。此處唯需說明的是,當時(約莫八○年代以前)由於時空背景跟現在不同,文中多以「中國」自稱「台灣」,或以日治時期的「高砂族」、「番人」,甚至是戰後初期的「山胞」來稱呼原住民。本書為了呈現文獻史料的原始面貌,特此保留當年的時代用語,並無歧視之意。
另外,早期李哲洋亦有一些文章屬於時效性的引介訊息,比如介紹錄音器材之類,雖在當時具有參考價值,如今卻未必要收錄,同時筆者也把一些較不具可讀性,以及偏向音樂技術分析的教材式文章拿掉,暫不列入書中。而所有這些文章(包含未被收錄的)書目資料全都會放到後面的參考文獻裡,連同其它已出版的編譯著作、田野錄音與生平年表一併收入附錄當中,以供未來研究者能夠一窺李哲洋作品的全貌。
主編的話/李志銘
回顧過去,無論是在台灣當代音樂發展史或教育史上,李哲洋都是個相當與眾不同的特例。
他早年家庭生活困頓、父母離異,十七歲時又受到父親白色恐怖事件牽連,而被迫從當時僅僅念了一年的台北師專音樂科退學,自此列入有關單位的「特殊名單」中,終其一生未曾獲得任何「正式音樂教育」的學位文憑,就連想要出國進修也完全不被允許。
儘管屢遭學院體制的排除和拒絕,卻仍阻擋不了李哲洋內心對於追求音樂知識的狂熱。於是他開始到書店打工,靠著自學美術繪畫,考入基隆的台肥公司擔任製圖員,之後更勤奮自修通過普檢,轉任基隆三中的音樂教員。即便經濟拮据,也要不惜縮衣節食來購買各類音樂專業書籍進修苦讀。
在學識上,李哲洋除了早期中小學曾經接受一些基礎教育之外,其它外語知識如英文、日文、法文,乃至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幾乎全由自習而來。昔日同在藝專任教的鋼琴家好友吳季札形容他是「在這個年代已經罕見的自我修業的學者」,並且強調「與哲洋爭論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是一位極謙虛的君子,極有禮貌,因而也是強者,一個真正的強者」。戲劇學者邱坤良亦曾以李哲洋和呂炳川、史惟亮三人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在民族音樂研究的用功程度猶在許常惠之上」。文史工作者鄭水萍甚至在一篇緬懷李哲洋生平事蹟的傳記文章裡轉述指稱:「他的功夫在理論上已超過當時師專的某些老師。」
古籍《左傳》有云,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用現代話來說,「立德」意指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則是提出真知灼見的言論,並將之形諸文字、著書立說,以被後人永遠銘記。此三者當中又以「立言」影響最為深遠。
唯令人惋惜的是,一向熱愛廣泛閱讀、在朋友眼中堪稱博學多聞的李哲洋雖是自學有成,長期以來也一直持續筆耕不輟,累積數十年超過上百篇的音樂論述、報導、隨筆、雜文散見《全音音樂文摘》、《大華晚報》、《夏潮》、《教育文摘》、《雅歌月刊》、《青蓓雜誌》、《音樂生活》、《音樂與音響》、《出版家》、《藝術家》等各大報章雜誌,卻因有生之年始終沒有整理集結自己的文章,以專書出版問世,致使一般讀者大眾很難真正深入去瞭解李哲洋在當代台灣音樂文化史的重要意義,與其建構內在思想上的知識脈絡。
自始欠缺「立言」的遺憾,直到李哲洋過世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二○二二)方才有了轉捩的契機,這也正是筆者編纂《李哲洋談樂錄》這部著作的微言大義之所在。
勤勉自學民族音樂的理論泉源
向來好學的李哲洋雖未能完成音樂科班學業,但在其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唯有透過大量買書閱讀來充實自己,加上多方面的興趣,遂養成了熱衷蒐集資料文獻的習慣,舉凡音樂教育、作曲理論、樂評隨筆、民歌採集、童謠研究、民俗學、人類學等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以致形成了他思想上較廣的視野面向。
追溯李哲洋對民族音樂的首度接觸,在他二十九歲那年(一九六三)參加救國團舉辦的一次登山訓練活動中,無意間聽到同隊一位學員哼唱著客家歌謠,歌中濃厚的鄉土韻味,勾起了他早年曾在客家村住過一段日子的強烈鄉愁。自此追尋民族音樂的意念便在他心中滋生蔓延。後來由於外祖母是賽夏族的關係,李哲洋也開始進入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庄鄉的賽夏族部落,和當地原住民喝酒搏感情之餘,順便搜集一些音樂素材。
及至一九六六年,李哲洋因參與史惟亮成立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繼而推動「民歌採集運動」初期的田野調查,需要援引國外發展相對成熟的音樂學相關知識作為採集工作的理論參考,於是他率先翻譯了日本民族音樂學的權威學者小泉文夫(Fumio Koizumi, 1927-1983)早期經典著作《日本伝統音楽の研究1:民謡研究の方法と音階の基本構造》部分篇章內容,包括〈民歌的概念〉和〈民歌的蒐集〉,陸續發表在翌年(一九六七)五月和六月《音樂學報》連續策劃兩期的「民歌專號」當中。
約莫這段期間,西方興起的「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也逐漸捨棄過去狹義的系統音樂學框架,開始採用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從文化與社會脈絡的角度來詮釋、重新發掘音樂背後的豐富意涵。就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下,小泉文夫即以日本傳統音樂為研究起點,注重民間音樂的採集和分析,並將民歌視為一種基本文化,即作為所有日本傳統音樂基礎的體現。
影響所及,觀諸李哲洋日後針對民族音樂研究撰述的許多文章當中,幾乎都能明顯窺見小泉理論的身影。
比方小泉認為,民歌應從音樂、文學、民俗等多重角度綜合看待,而民歌或民樂本身的音階結構亦反映了日本人的基本音高感,且應從聆聽者的經驗中掌握音樂的實質,並強調日本音樂應該體現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不僅僅是模仿西方藝術音樂。如是對照李哲洋在〈山胞音樂提示〉與〈民樂在音樂教育上的新評價〉等文中再三提及,當年他在五峰鄉賽夏族一連數日聆聽矮靈祭現場吟唱四度平行疊音調(Organum)的親身體驗,由此闡述「一個人在怎麼樣的音樂環境下,自然而然會具有某種音感」、「我這裡欲以強調的音感,便是這種音樂的音感、格調的音感,而不僅僅是西樂和弦的音感」。相較這類說法皆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針對採集民歌的基本認知,小泉文夫在〈民歌的蒐集〉一文表示「純粹的民歌將急速地消失,頗難區別純粹的與都市化了的民歌」,並指出「原來由鄉間的傳承者保存下來的民歌,經過都市的流行歌手洗禮之後,如果這些東西一旦倒流回到原地,則很可能會把原有的東西驅逐出去,這對於民歌本身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如果不是先明瞭古老的民歌形態之前,對於民樂的研究者是一項頗為困擾的事」。同樣重視民歌本身具有歷時性(Diachronique)變遷特質的李哲洋,毋寧也在〈流行歌與民歌的異同〉文中強調:「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顯然流行歌是民歌的延展或蛻變,況且本質無異於一般人以為的民歌,以及部落歌謠中的俗謠」、「所謂俗謠,實在是小社會的流行歌;所謂流行歌,實在也是大社會的俗謠」。 除此之外,李哲洋也曾對台灣童謠產生濃厚的興趣,還為此做過相關題材的田野調查,並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雄獅美術》雜誌上。無獨有偶,小泉文夫在其代表作《日本伝統音楽の研究1》一書中,亦將童謠視為民歌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礎出發點。小泉指出,童謠的聲音組織和音調清楚地顯示了民歌最基本的元素。
跨域的人生風景:從民間學者到雜誌編輯
小泉文夫作為日本民族音樂學的先驅,在他主持國內外諸多研究項目的同時,也不斷藉由商業出版與大眾傳播媒體的長期合作,將源自世界各地的民間音樂介紹給學院專家以外的普羅大眾,進而在日本社會帶動了「民族音樂」的熱潮。
當時透過自學鑽研民族音樂理論的李哲洋,對於小泉文夫既能跨越學院體制藩籬、又能廣泛影響社會大眾的學術成就,他雖不能至,卻也心嚮往之。
儘管李哲洋對音樂懷有巨大的熱情,但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後代的他,不僅無法取得大專音樂科系的正式學位,更無緣出國深造,因此只能透過學院體制外的迂迴方式來參與音樂活動。因此,他毅然接下了《全音音樂文摘》這份刊物的編輯工作,雖然從未掛主編之名,卻肩負主編之責。該雜誌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創刊,至一九九○年一月正式休刊,中間曾停刊數次又復刊,共計發行一百三十三期。
《全音音樂文摘》雖以專業的古典音樂題材為主,內容卻十分豐富多元,且重視版面閱讀的編排設計、圖文並茂,舉凡古典樂派、國民樂派、印象樂派、現代音樂、美國民歌,甚至到搖滾樂都有涉及。其中某些特定主題的專集策劃更是首開時代風氣之先,即便今日看來也依然頗具前瞻性:比如「舞蹈與音樂特輯」漫談西方現代舞與古典音樂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共生關係;「民族音樂專輯」探討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對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影響,並延伸引介印度、非洲、中南美洲和北歐的民族音樂;「亞洲音樂特輯」生動記載了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賽夏族矮靈祭,以及早年亞洲作曲家聯盟初成立時在台灣的活動紀錄;「電子音樂專集」則是展現出彼時電子樂器革命掀起的新世界。
執編《全音音樂文摘》近二十年來(一九七一—一九九○),李哲洋同時身兼民間音樂學者、中學教員、大學兼任講師等多重角色,他幾乎就像條老水牛那樣勤勉賣力、兢兢業業,一邊自掏腰包購買設備採集民歌做研究,一邊持續讀書翻譯寫稿熬到半夜,還要負責每個月按時編出一本夠分量的音樂雜誌。
話說當年李哲洋之所以「一生懸命」、甘願為這份刊物付出遠大過金錢報酬的心力,主要理由除了透過雜誌社本身與其資助者「大陸書店」的進口管道,能夠讓他更方便取得來自國外(大多是日本)的音樂書刊唱片等第一手資料之外,當然還有在精神方面與知識上的滿足,如此一來,他的文章也才有更多機會在公眾媒體上刊登。
日常生活中,李哲洋對待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很熱情、健談而好客,每當一聊起音樂話題便欲罷不能,加上身為雜誌主編,自家書房就是《全音音樂文摘》編輯部,妻子林絲緞也是知名舞蹈教育家,夫妻往來的朋友很多都是藝文界的人物,家中訪客也總是川流不息。當時較常前來串門子的親朋好友,主要包括雷驤、戴洪軒、張邦彥、徐松榮、林崇漢、郭芝苑,畫家楊識宏、呂晴夫,還有小說家七等生、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等,另外還有他們各自帶來的家眷妻小或其他藝文界友人。
在李哲洋家的客廳裡,這群朋友之間很容易彼此交流、吸收到關於音樂文學藝術的各種新資訊和新觀念,在昔日那個資訊匱乏的時代,儼然形成一種類似民間公共論壇性質的客廳沙龍聚會。作曲家徐松榮便曾在一篇論文訪談回憶:「在所有朋友當中,對他創作觀念幫助最大的,應首推李哲洋。」
不被體制化的自由思想
早年因父親涉入白色恐怖事件的影響而經常受到情治人員「關注」,李哲洋往往將自已內心真正的情緒藏得很深,平常外表看來總是一副樂觀開朗的樣子。但從李哲洋留下的諸多文章隨筆內容看來,他的文字風格亦是恰如其人,具有濃厚的日常生活談話氣息,在客觀的理性當中帶著一絲抒情的感性與詼諧的幽默,用以鼓舞或激勵他身邊的一眾知交。譬如在〈台灣山胞音樂序〉、〈與呂炳川博士一夕談〉等文中,便能明顯感受到李哲洋頗為偏愛使用「對話式」的互動文字來展現人物訪談現場的鮮活畫面。
觀察近些年來的台灣本地音樂學界在全面納入「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之後,所謂的「論文發表」、「學術研討會」,越來越像是少數圈內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在的空虛與犬儒,當然更不要奢望能對當代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力,似乎也無人藉此討論如何增進開拓未來教育和獨立思考之功效。尤有甚者,某些學者教授只在乎驗證自己的學術理論,抑或選擇性地只看到他們想要看的那一小部分,見樹不見林,而非真正重新檢視、深入瞭解當年在複雜的政治社會脈絡底下,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音樂人物整體生命的真實面貌。
類似的情況,李哲洋早在〈四十年來台灣的音樂期刊〉這篇文中便有所提及:「音樂期刊的內容委實足於反映此間音樂界的風潮。就作者、譯者的身分而言,近十年來,出自於音樂工作者的文章十分有限,尤其由音樂學專業人才執筆的,更是鳳毛麟角(升等論文姑且不論)⋯⋯這充分反映目前音樂界普遍缺乏對音樂遠大的理想,只坐享前人植樹成蔭之涼快,這是值得探究的隱憂。」
據此而論,當年李哲洋正因為立足於學院體制之外,所以才能夠站在一般讀者大眾的角度去思考一些嚴肅議題,也由於他始終不被定型在某一特定專業領域,李哲洋的思想範疇才因而更加寬廣、自由,字裡行間更不乏深具批判性的反思洞見(Insight),既深諳各家理論思想之精髓,卻又不拘泥於理論形式之框架。這也正是在我們現今這個時代之所以需要重讀李哲洋的關鍵理由。
最終,為了讓本書內容更親近一般讀者,也更符合李哲洋文章裡彷彿與好友聊天的話語氛圍,故將書名喚作《李哲洋談樂錄》。此處唯需說明的是,當時(約莫八○年代以前)由於時空背景跟現在不同,文中多以「中國」自稱「台灣」,或以日治時期的「高砂族」、「番人」,甚至是戰後初期的「山胞」來稱呼原住民。本書為了呈現文獻史料的原始面貌,特此保留當年的時代用語,並無歧視之意。
另外,早期李哲洋亦有一些文章屬於時效性的引介訊息,比如介紹錄音器材之類,雖在當時具有參考價值,如今卻未必要收錄,同時筆者也把一些較不具可讀性,以及偏向音樂技術分析的教材式文章拿掉,暫不列入書中。而所有這些文章(包含未被收錄的)書目資料全都會放到後面的參考文獻裡,連同其它已出版的編譯著作、田野錄音與生平年表一併收入附錄當中,以供未來研究者能夠一窺李哲洋作品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