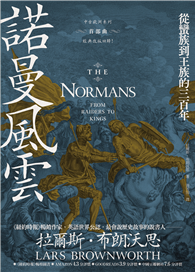母親歸於塵土,父親身陷囹圄。
妹妹被送養至美國,成為養父母的掌上明珠;
而他則孑然一身地離開菊島,渡臺尋覓新生。
曾經平凡的一家四口,在意外之後幻化為泡影──
十三歲的他,親眼目睹美滿家庭是如何一夕間分崩離析,更因此被迫與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分離。
十五年之後,失散多年的兄妹終在家鄉澎湖重逢,他們回到位於紅羅村的老宅撿拾回憶、登上鳥嶼向至親道別。
縱使兩人分隔千里、別離數年,兩兄妹仍依循著血脈的呼喚,最終回到了那座承載著傷痛的菊島;他們找尋那些關於家、關於愛、關於過去、關於血緣的記憶……
「我發現自己無法再想像,我們一家四口的命運於過去那一分歧點上如何能有另番走向,昔日那些對過去的妄想,盡由一份透著悲哀的命定感所取代……」
本書特色
★ 血濃於水卻未曾謀面的親人、本無瓜葛卻因命運而生的親緣──
★ 在背叛的真相水落石出之際,他們逐漸明白了「家人」真正的意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家沂的圖書 |
 |
$ 210 ~ 270 | 菊島之約【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李家沂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24-06-26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菊島之約
內容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