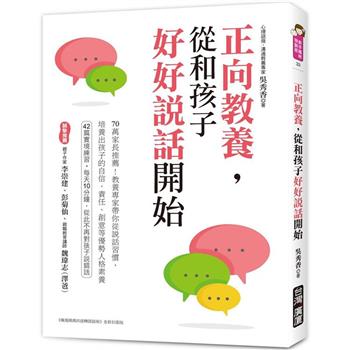百餘年前,中國的文章多以文言寫就,雖然白話文從唐宋後就作為書面語應用於小說、戲曲上,但未取得社會地位。直至二十世紀初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作為現代中國的文體革命,致力於書面語的再造,冀在新文字中實現統一國語和言文一致的目標。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卻掩蓋了巨大的危機:以西方語言文字的觀念看待漢語和漢字,人為地割裂了與歷史的有機聯繫,暴露了漢語寫作和現代中國在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困境。漢字的倉促簡化和文言教育不足,也使我們數千年的文化傳統面臨失傳的危險。
本書以文言和白話之間的消長起伏為線索,通過對於清末文字改革運動、五四文學革命、大眾語運動、民族形式論爭等系列史實的清理,檢討書面語革新和文體建設的成敗得失,並深入探討言文一致、漢語歐化等重大問題。
本書是百年以來對於白話文運動進行系統反思的大型理論著作,也是迄今為止對這一話題深入研究的重要的學術成果,適合對白話文運動或書面語轉變有興趣的讀者閱讀。作者引用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論以分析白話文運動的成就與危機,以及與當時政治壓力的關聯,闡述當中的歷史意義,追尋其中的學術脈絡。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春陽的圖書 |
 |
$ 672 ~ 791 |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作者:李春陽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1-11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李春陽
李春陽是一名中國男子體操運動員。他在1992年巴塞隆納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參加了男子體操團體比賽並獲得銀牌。他也參加了1990年北京亞洲運動會,共收穫一枚金牌和兩枚銀牌。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