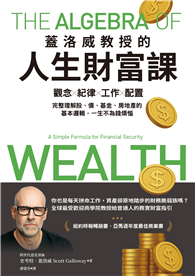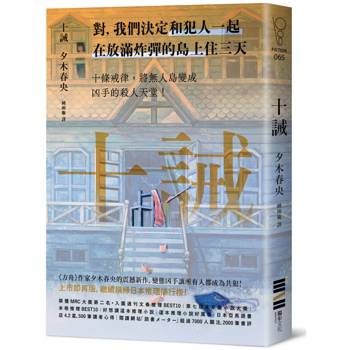一 (節錄)
之所以能確定那是除夕夜的前一晚,是因為當天傍晚我給家裡打了電話,告訴母親過春節不能回家的消息。我是在晚飯前,在樓下鏽跡斑斑的電話亭裡,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現在是春運,車票根本買不到。」其實我根本沒有去了解車票情況。
「機票呢?機票能買到嗎?」母親在電話那頭,仍不放棄嘗試讓我回家。
「機票錢是我一個月的工資……」
「回不來就算了,記得明晚煮點餃子吃,過年呢。」
「好的,知道了。」
「如果買得到燒紙,明天晚上就在路口給去世的親人燒點紙吧。」
……
我想如果打完電話回去路上看到有人賣燒紙,就象徵性的買一些,明晚也算是給自己找點事情做。當然事實上是不會有的,除了見到一隻在垃圾堆裡尋覓食物的貓之外,其他什麼活物都沒看到。超市員工也早就像被僵屍追趕一樣逃離這裡,哪裡還能買得到餃子呢。
然後我上樓回到住處,也就是我的出租屋。
回到房間,撕開桶裝速食麵,用電水壺燒水,加兩根火腿腸和一個滷蛋,泡三分鐘,連湯都喝得一滴不剩。這時候剛過九點,天已經黑得十分徹底。我坐在被子裡,打開CD隨身聽放著Michael Jackson的唱片。Michael是中學時代最喜歡的偶像,記得有一次在課間向女同學表演捂著褲襠的舞蹈,被老師看到臭罵了一頓,站在教室後牆直到上午課結束。當〈One day in your life〉這首歌響起時,逐漸有了些睏意。想起還沒有寫日記,便拿起日記本,一邊翻看著之前記了些什麼,一邊回想著今天發生的事情。
當看到在去年七月一日,也就是拿到大學本科畢業證當天,在日記本上寫下的話時,記憶又被帶入到這輾轉反側的半年時光裡:終於畢業了,我可以逃離這裡了,逃避這個城市二十多年來禁錮在我身體上的各種桎梏。
作為一個在新千年得益於大學擴招政策僥倖進入一本大學的新產物,畢業後,我離開北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鄉,隻身來到一座陌生的南方城市,供職於一家還能稱得上體面的設計公司,說體面,也就是因為上班的地方在市中心一棟三十多層的寫字樓裡。大學擴招,讓大學生這個金飯碗開始掉色,好像從工廠車間流水線生產出來,數量龐大且無個性。非要貼一個標籤拿到市場上售賣,也只能是「促銷」。
六月畢業,經歷了百無聊賴沒有功課的暑假。八月底用了三天時間下決心,乘火車,租房,面試……三個月後,伴隨我轉入正式員工,季節也慢慢來到了冬天。儘管立冬已至,但氣溫並沒有像北方現在那麼低,也就維持在二十攝氏度上下。不過南方的冬天,令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最不適應的,是潮溼。床單被子像吸了水的海綿,溼答答裹在身上,變得不再乾燥。在嚴重的回南天,清早打開窗戶後,牆壁就像剛做完劇烈運動一樣滲出水珠。牆頂的一些地方,牆皮因為潮溼開始脫落,這裡的人也給它起了個形象的名字─壁癌。
由水土不服展開的不適應還有很多,周遭陌生孤寂,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未來像深淵一樣充滿未知,根本沒辦法把它和理想扯上關係。不過難得的是,我並沒有一絲想要打退堂鼓的意思。我告訴自己這是理所當然,既然選擇了離開家,孑然一身來遠方闖蕩,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挫折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我這樣安慰自己,也算是鼓勵自己,在這個城市任性的生存下去。
過往的浮想聯翩,伴隨〈One day in your life〉歌曲的結束而暫停。我簡單記了當天的事情,拔掉耳機,關掉床頭燈,鑽進被子裡。黑暗侵占了整個房間。
有些冷,我覺得。不過這氣溫已經好過家鄉的冬天,那邊已經有了要下雪的節奏。童年時與朋友滾雪球是冬天少不了的娛樂項目。我們最後總是會劈開雪球,看裡面一圈圈的同心圓,然後不停叫嚷著「看,年輪,年輪」。小孩子的我們並不清楚那些同心圓是不是和大樹產生年輪的原理一樣。樹木以產生在自己身體上的自然記號來記錄年齡,準確無誤。這種神奇的力量,讓童年時代的我總是在想,自己身上某個地方是不是也存在著這種神祕而奇特的記號呢?
到這時我還沒有睡著,當回憶一旦碰觸到童年時,那個男人總是會順其自然地出現。也有可能和母親打電話時提到燒紙有關。
那是父親去世前一年,季節記不清了,只記得那天太陽還沒落山。他和我面對面站在家附近一間學校開闊的操場中央,這就是記憶的開始。周圍有沒有其他人?在記憶中沒有。天氣是冷還是熱?也完全沒有印象穿得是厚衣還是單衣。他俯下身子,有沒有摸著我的臉?記不清了。然後,對我說了幾句語重心長的話。就這些,記憶到這裡就結束了。
這算是什麼呢?就算自己添油加醋再渲染些氛圍,這記憶怎麼想都超不過十秒鐘。但這事本身一定發生過,我非常肯定這不是幻想,更不是理療師為了撫平創傷給我杜撰的記憶。他說了什麼,那些話當時一定被我聽到耳朵裡,只是想不起來了。這段記憶在我大腦中留下唯一感覺,是我很確定那些話具有某種嚴肅性,就像在遠處看著月台上即將分別的男女,儘管聽不到說了什麼,但知道一定最真切的表達。
每每想到這件事,我都會聯想或者是杜撰話的內容,是跟我道別嗎?「聽著,爸爸可能有一天要離開你和媽媽,答應我,做個勇敢的男孩子。」無非就這樣吧,對於一個已經知道自己肺癌晚期的人,又能說什麼呢?說不定我也回應了他,但對一個八歲的孩子說這些話,又怎麼指望我能理解其中的含義呢?
曾看過一篇新聞報導,有研究發現人類大腦海馬回中藏有一些隱性神經元,當受到某種非常嚴重的刺激,這些隱形神經元就可能釋放出非常早期的記憶。「忘記的事情只是暫時想不起來而已。」這句話或許是有道理的。
「某種非常嚴重的刺激」具體指什麼?
如果那篇新聞有些科學依據,那時他在我面前傾吐出的語言,應該會儲存在大腦中的某些隱形神經元中。等待著某種嚴重刺激下釋放出來,又或者永遠無法釋放,最終隨著熊熊烈火被徹底消除。
這段記憶不時便會浮現在我腦海裡,只要思緒有空隙,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突然冒出來。但唯獨不會在夢裡出現,我記得從來沒有夢到過這段場景。夢這東西確實很奇怪,沒有人可以主動創造出一個夢,而夢裡發生的情景(在什麼地方)、對話(語言內容)、心情(悲傷急切或是開心)卻又真實清晰。這些東西是憑什麼被創造出來,可能要讀讀佛洛依德才知道。那段記憶如果真的出現在夢裡,或許某一次就會變的完整,從他嘴裡流出的語言就會成為確切的文字傳進我耳朵。
沒有夢到過,一次都沒有。
差不多就是這個時間點,即將像每一個悄然入睡的夜晚一樣,即將滑入睡眠的那一刻……
我突然發現自己站在一個空曠的場地中央,非常陌生的地方,從未有印象到過這裡。不記得來這裡之前在做什麼,記憶上一秒仍然停留在與父親的那段記憶。現在要去哪裡?更是毫無方向。周圍的景象到還非常真實。環顧四周,發現這裡應該是一個非常大的已經乾涸的引水渠,用水泥鋪成的渠道一直延伸到視線盡頭,不遠處能看到幾處水窪。寬度也十分驚人,起碼比得上一個足球場。想像著從附近的高山或者丘陵將水引流過來,就會形成一條寬闊的人造河。我站在引水渠底,抬頭向兩邊望去,只能看到左手一端頂上拉著鐵絲網,另一端上面傳來似乎是汽車駛過的聲音,可能是條公路。
天空陰沉,從遙遠天際隱約響起雷聲,風刮不起來,顯出死悶的沉寂。我刻意感覺著自己的身體,從頭到腳,包括生殖器,沒有發現任何異樣。
大腦在一遍遍發送著強烈的信號,為什麼會在這裡?這是哪兒?這就像問自己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世界一樣,根本得不出答案。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仍是除夕夜前一晚下樓給家裡打電話時候的衣服,長袖黑白條紋T恤,外面套一件黑色輕薄羽絨服。牛仔褲下面是紅色Converse帆布鞋,襪子也沒有錯。我撐開褲腰,內褲也是自己的,來這裡以後在街邊二十塊三件的平角褲。摸摸口袋,沒有錢包,手錶也丟掉了。
在確認了這些之後,我看到引水渠右手邊一面的水泥牆壁修了一道爬梯,一直向上通往頂端。走近才發覺,原來這一端高牆實際非常高,畫在爬梯旁用來測量水位的刻度有三十米。沒什麼好猶豫的,總不能站在原地不動。我握住有些生鏽的鐵桿,很真實。梯子背後有圓形的保護欄,讓膽小的我覺得還算安全。爬到一半就覺得心跳加速,伴隨著嗓子乾渴。
爬到頂端用了很久,雙手已經完全通紅,額頭和後背滲出許多汗。果然是一條公路,眼前一輛紅色的轎車飛馳而過,因為開的太快,眼睛追尋不到車牌的信息。回頭向下望去,剛才莫名其妙出現的地方,沒有任何異樣。引水渠另一端的鐵絲網之外,像是剛剛拆除過一大片建築,成了荒地。有人騎著自行車以平常速度穿過。
公路邊的人行道狹窄得只容得下一個身位,前後同樣仍望不到盡頭。不遠處有一座天橋橫跨公路。我目的明確地走上去,從更高的角度眺望遠處。高速公路兩端向天際無窮伸展。天橋下去是種植著南洋杉的綠化帶,綠化帶後面就是城市,是那座城市嗎?之前沒有從這麼高遠的角度俯瞰過那座南方小城,總覺得與印象不同,現在看過去,樓房的高度非常平整,好像園林工人用大剪刀剛修整過的灌木叢。
通過南洋杉綠化帶中間的小路,我進入到城市裡。
眼前的建築並沒有哪裡讓我覺得異樣,感覺上的確是我工作的這座城市。街邊店鋪像往常一樣營業,只是街上人流明顯少了很多,時間上似乎已經過了農曆新年。
一家經營當地特色小食的飯店門口,兩個穿著廚師服裝的男人在抽菸,看來不是吃飯高峰時間,天空中仍找尋不到太陽的蹤跡,判斷不出更加具體的時刻,雷聲頻率很慢,不仔細等待很容易錯過。沿著街道走了很久,總算碰到一個中年婦女迎面而來,她穿著很樸素的冬衣,挎單肩包,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像是被柴米油鹽填滿的生活早已奪走。
我抬起手向她打招呼:「你好,請問迎賓路怎麼走?」這種名字命名的街道,彷彿在這個國家每一座城市都有。不需要任何創意與想像,隨便將一些諸如友誼、建設、迎賓之類的詞加在前面就好了。
「對不起,沒聽說過有這條路。」她沒有運用任何表情,只是在動嘴回答。
沒有?我對在這裡的公寓位置很有把握。
中年婦女用讀不出任何信息的眼神看著我,像是在盯著一隻停在眼前的蒼蠅,忽然之間她連手也不抬,只是轉過頭說:「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右轉後第一個路口,再左轉。」
還沒來得及做出詫異的表情,她已經從我身邊擦過。
我想走到前面的路口再問問好了,剛轉過路口,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映入眼簾,廣告牌的形狀和氣勢非常熟悉,很像公寓附近經常看到的那個,記得不久前看到是新款大眾汽車廣告。而此時廣告牌只是在純白色的背景中間以黑色字寫了一句英文,「follow your heart and vote for the truth.」,落款是動物自治聯盟。完全不理解是什麼產品和組織。話說回來,如果真的是公寓附近的那個廣告牌,那麼從前面過去第一個路口便是住的地方了。簡直和剛才中年婦女所指的一樣。我開始隱隱對這裡覺得不對勁。天陰的程度在短短的時間裡加重了,溼氣也隨之開始高漲。但又總覺得不會下雨,哪有在農曆新年剛過就下雨的說法。
按照印象,或者說是中年婦女所指的方向,住了大概半年的公寓完好無損的呈現在眼前。我懷著想要快點回家的急切心情接近它,樓下路邊的電話亭依舊鏽跡斑斑,我遲疑了片刻,像是在等電話鈴響起。側目間,路對面的公車站有很多人站成一排在等車,看上去十分有規矩,好像他們從來都是這麼做的。
無論如何先回到住處看看,雖然也不知道有什麼類似能揭開謎團的東西,但那裡就像RPG遊戲角色一開始出現的地方,總隱藏著通關線索。老式的六層樓房,兩個門洞,灰色外牆,挨家挨戶突出的防盜網,像迎賓路一樣在各個城市都如出一轍,懷疑他們全部用的都是同一張建築圖紙。
一切都是本來的樣子。破舊的樓道,牆面貼滿疏通下水管道的小廣告,隨意歪著的廢舊自行車。我快要上到頂層,轉過來,看到602公寓的房門虛掩著。
我凝視著那扇門,好像想要去思考些什麼,腦子卻全是空白。走上前推門進去,一眼看盡的房間,沒錯,是那間吃掉我三分之二工資的公寓。只是,房間空了,準確的說,屬於我的東西都不見了。寫字檯還在,沒有電腦,床上只剩張床墊,衣櫃裡也空空如也。總之所有和我有關的東西全部消失了,和我第一次拉著行李箱進來時一模一樣……
眼前這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令我非常不自在。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楊洋的圖書 |
 |
$ 270 ~ 285 | 另一個世界奏響的月光曲
作者:李楊洋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2-06-17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另一個世界奏響的月光曲
男主人公在大學藝術系畢業後從北方家鄉前往南方城市工作。在一次意外之後,他發現這個世界在某些地方變得和以前不同。在他遇到自稱是黑白無常的傢伙時,被告知自己已經死掉,並需要在下一個清明節前搜集到一個人活著時的名字,才能去見到閻王。在死後的世界,他遇到了舞蹈系女生子淩,動物自治聯盟的朱丸和貓王。在和他們的交往中,逐漸對生死有了不同體悟。而當他見到閻王時,才知道了自己的死亡其實另有蹊蹺……
作者簡介:
▎李楊洋
陝西西安人。畢業於西北大學新聞學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曾任職網站記者編輯、報社編輯,現定居香港。
作品有《毛線君的理想國》(2018,上海)
章節試閱
一 (節錄)
之所以能確定那是除夕夜的前一晚,是因為當天傍晚我給家裡打了電話,告訴母親過春節不能回家的消息。我是在晚飯前,在樓下鏽跡斑斑的電話亭裡,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現在是春運,車票根本買不到。」其實我根本沒有去了解車票情況。
「機票呢?機票能買到嗎?」母親在電話那頭,仍不放棄嘗試讓我回家。
「機票錢是我一個月的工資……」
「回不來就算了,記得明晚煮點餃子吃,過年呢。」
「好的,知道了。」
「如果買得到燒紙,明天晚上就在路口給去世的親人燒點紙吧。」
……
...
之所以能確定那是除夕夜的前一晚,是因為當天傍晚我給家裡打了電話,告訴母親過春節不能回家的消息。我是在晚飯前,在樓下鏽跡斑斑的電話亭裡,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現在是春運,車票根本買不到。」其實我根本沒有去了解車票情況。
「機票呢?機票能買到嗎?」母親在電話那頭,仍不放棄嘗試讓我回家。
「機票錢是我一個月的工資……」
「回不來就算了,記得明晚煮點餃子吃,過年呢。」
「好的,知道了。」
「如果買得到燒紙,明天晚上就在路口給去世的親人燒點紙吧。」
……
...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這麼想來,我應該是在二月二十號除夕前一天晚上睡覺時死掉的。
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考慮著自稱是黑白無常的兩個傢伙走之前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想想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這個世界有些奇怪。」沒錯,就是從那之後,這個世界的某些細節處,變得與活著時的認知有些不太一樣了。我盯著牆壁陰陽兩面結合處的那條垂直線,讓記憶像倒放的錄像帶一樣,再次確認著那個終點,也是起點……
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考慮著自稱是黑白無常的兩個傢伙走之前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想想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這個世界有些奇怪。」沒錯,就是從那之後,這個世界的某些細節處,變得與活著時的認知有些不太一樣了。我盯著牆壁陰陽兩面結合處的那條垂直線,讓記憶像倒放的錄像帶一樣,再次確認著那個終點,也是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