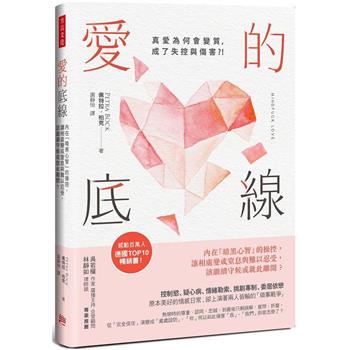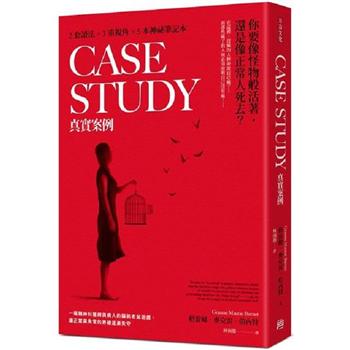過去十年來,台灣學術圈中最具活力的新興領域非「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STS)莫屬。STS的跨領域精神充分體現在它組成的多元,涵蓋了諸如:科學史、科學哲學、性別研究、醫學與護理、社會學、人類學等各大範疇。這些年來,社群成員經由引介西方各種研究取徑,繼而發展出扎根本土的在地研究,持續展現了這個學門旺盛的企圖心與理想。本書主編從台灣出發,邀集華文世界學者分享研究成果,實為台灣STS出版的重要里程碑。
回顧歐美STS發展史,愛丁堡學派曾經是重要且璀璨的一頁。三十年來,該學派人才輩出,諸如巴恩思(Barry Barnes)、布洛爾(David Bloor)、夏平(Steven Shapin)、麥肯其(Donald MacKenzie)、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人,都是執學界牛耳的人物。而愛丁堡學派所揭櫫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四大信條等,更為人所耳熟能詳。
《科技與社會》邀集華文STS社群之研究者,以愛丁堡學派的「社會建構論」為主軸,展開批判性的回顧與前瞻。全書共分兩部分:總論部分集中在理論的探討,包括了由宏觀角度闡析科學知識與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以及從微觀視角來解析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等;專論部分則以具體的爭議研究為主,諸如微積分的「發明權」爭奪、標準化過程中的技術爭論、環境正義的論爭、中醫存廢論戰、翻譯工作的權力競逐等問題。這些文章呈現出的多元研究特徵,使讀者能一窺愛丁堡學派之堂奧。
作者簡介:
(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小紅,中國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李正風,中國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沈小白,英國愛丁堡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
徐飛,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哲學部教授
程志波,中國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陳瑞麟,台灣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黃瑞祺,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黃之棟,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崔波,中國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樊春良,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文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戴東源,台灣靜宜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蘇俊斌,中國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喜見這本書能承先啟後,既紮根於愛丁堡學派在知識社會學及科學哲學的基礎,生動闡述學派近二十年較主要的理論和應用發展;亦立足於華人學者的視點和脈絡,開拓愛丁堡學派在華文學術界發展和應用的前沿。誠意推薦給所有懷抱人文關懷、留心科學在社會發展的朋友。
——蕭亮思(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
「愛丁堡學派」這個屬於20世紀70年代的名字,會為21世紀的科技與社會學科在中文社會的發展帶來什麼啟發?藉由這本匯集兩岸著名學者學術論文的集子,讓我們看到科技與社會的創始、發展與未來。
——方薌(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媒體推薦:喜見這本書能承先啟後,既紮根於愛丁堡學派在知識社會學及科學哲學的基礎,生動闡述學派近二十年較主要的理論和應用發展;亦立足於華人學者的視點和脈絡,開拓愛丁堡學派在華文學術界發展和應用的前沿。誠意推薦給所有懷抱人文關懷、留心科學在社會發展的朋友。
——蕭亮思(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
「愛丁堡學派」這個屬於20世紀70年代的名字,會為21世紀的科技與社會學科在中文社會的發展帶來什麼啟發?藉由這本匯集兩岸著名學者學術論文的集子,讓我們看到科技與社會的創始、發展與未來。
——方薌(廣州中山大...
作者序
導言
為愛丁堡學派設下嚴苛的目標
黃之棟
(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我有這麼個印象,就是說許多STS的人相信他們的研究進展已經超越了強綱領。他們覺得這個綱領在1970年代也許真的很有趣,但他們認為自己現在做的是些很不同、或更有深度的、還是說是更有趣的事情。但我猜測真正的情形是,許多人發現強綱領太難了。我猜他們沒給自己設下個嚴苛的目標。⋯⋯對我來說,這(事實上)就像是在對自己說:讓日子簡單點過吧!在我們找到事情的起因之前,不要這麼掙扎的研究了吧!讓我們快速地從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來展現解釋的多樣風貌。然後,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種比老方法更優的新研究法。我認為這是在規避那些最有深度且最有趣的問題。當我察覺到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我認為這個領域就不會再往前邁進了。(布洛爾2010)
一、緣起:從自強活動到自強運動
一切都是從2008年的夏天開始的。
愛丁堡大學的科技與創新研究社群(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SSTI)每年夏天都會舉辦「自強活動」(retreat)。找個好日子,選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集思廣益共同思考下一年的方向。不同於一般的郊遊踏青,「自立自強」真的是愛丁堡自強活動的主題。在為期兩天的自強活動裡,會議當然是重頭戲。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每位成員除了輪番上台報告過去一年的研究成果之外,主辦單位每年也都會邀請一位貴賓,和與會者一同擘畫未來。
每年的貴賓,總是我們醒目的諫友,鞭策著大家前進。2008年的自強活動正是這麼一個轉捩點。來自荷蘭的黎朋(Arie Rip)教授,在會議上為愛丁堡學派(特別是當中的強綱領)把脈,並為我們設下了挑戰。他問到:在巴恩斯(Barry Barnes)與布洛爾(David Bloor)等前代學者相繼退休之後,在下個十年裡愛丁堡學派到底要走向何方?對他而言,愛丁堡學派在三十年前跨出了一大步之後,近年來似乎是步履蹣跚,以致遭遇了理論與實際的搖撼。我們出現了能否存續與持續創新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問題,在場的新生代決定接下擔子,正面迎接這個挑戰。場中英語系國家的學生決定主編一本書;中文社群的師生也決定開始我們自己的「自強運動」。當時與會的李正風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黃之棟同學(時為愛丁堡大學科技與社會博士生),以及2009年到愛丁堡訪問的黃瑞祺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開始了一系列的工作。共同催生了這本兩岸合作的專書。
二、編輯旨趣:多元開放、嚴謹審查
雖說是要「變法革新」,打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中文學界面對了與西方不同的挑戰。對很多採取拉卡托許式(Lakatosian)想法的西方學者而言,愛丁堡學派的研究方法早已是舊瓶新酒,了無新意。但對中文世界來說,此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尚在起飛階段。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對強綱領的辯護,而是對它批判的理解。基此,批判的回顧與前瞻是本書的首要目標。
在確立了這個主旨之後,問題非但沒有因此結束,難題反而接二連三的到來。首先,愛丁堡學派是什麼?更具體的說,誰屬於愛丁堡學派?這個學派的主張又有哪些?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有些人在愛丁堡,卻不屬於愛丁堡學派;也有些人不在愛丁堡,但卻屬於愛丁堡學派;更有些人自認自己不屬愛丁堡學派,卻一直被誤認為是這個學派的成員。環顧英國(與歐洲)的科技與社會學界,名家們或多或少都與愛丁堡學派有著些許淵源。不同於其他的書籍,我們不願用斷定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而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基本上,我們希望用本書來體現愛丁堡學派多元研究的特徵。
也許比前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愛丁堡學派的特徵為何?這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正如布洛爾(2010)教授所言,愛丁堡學派是別人替他們冠上的稱謂,他們並不以此自稱。在本書第一次編輯會議中,與會者一致認為愛丁堡學派的最大特徵,在於這個學派的學者都主張某種程度的社會建構論,也就是認為社會事實(包括科學在內)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建構出來的。本書即以此為主軸,開始向兩岸學界徵稿。總之,我們希望藉由這本引介並批判社會建構論的書,一方面加深中文學界對社會建構論以及愛丁堡學派的認識;另一方面藉此反思社會建構論三十年來的成果與限制。當然,作為前述愛丁堡學派「自強運動」的一環,我們也希望經由這個集體的反省,總結出新的方向。
本書所有收錄的文章都經過嚴謹的匿名審查機制,編輯也為每篇文章提供了修改意見,然後作者再對審查意見進行斟酌與修改,最後才由編輯會議討論並通過錄用。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以「尊重原著」為最高指導方針。不過,面對一本兩岸共同的創作,編者很難不對迥異的譯詞,進行適當的統一。不然,就連Bloor或Barnes教授的姓名,都可能會出現兩三種音義。這毋寧是要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之所以堅持把兩人翻成布洛爾與巴恩思,是因為這個譯法比較接近原來的發音。)基此,我們對人名、地名、常用書名、以及台灣慣用的專有名詞等做了適度的統一,其他部分則盡量不更動。畢竟,名詞的使用本身也反映出作者對該知識體系的理解。在「變動最小」的編輯原則下,讀者會發現人們津津樂道的愛丁堡學派四大信條(tenets),在不同篇章中也可能出現不同譯法。合先說明。
三、一個必要的辯護:我們怎麼看待每篇文章?
相信讀者在閱讀文章時,一定會立刻發現本書立場之多元,超乎想像。每位作者對主題的闡述與批判也有相當的差異。編者認為有必要把編輯的背景給「前景化」。總的來說,本書的編排必須被放在對黎朋教授挑戰的回應之下來看待。全書大致分成總論與專論兩部分。總論的部分集中討論愛丁堡學派的理論性議題;專論的部分則以具體的爭議研究為主,旁及我們對未來的展望。
我們要如何理解科學?戴東源的文章一開頭就替本書破了題。一般實證論者在理解科學時,總是用真理、價值中立、理性等等辭語來描述科學。在這種理解下,實際操作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也被描述成公正乃至無私的一群人。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戴文是國內少數探討有限論的文章,作者很有技巧地從觀察、理論與實驗等三個視角切入,由具體的實例出發帶領讀者一步步深入到愛丁堡學派的核心。經由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實踐中的種種概念與意義,並不是事先給定的,而是在不斷的運用中磨合出來的。由於這個緣故,文化與社會的要素一定會在科學的實踐中起作用,並與科學自身糾結在一起。這種隱而未顯卻又難分難解的狀態,一直要到我們把社會學的分析用來研究科學之後,才漸漸獲得梳理,傳統對待科學的看法也因此漸漸改變。除了系統地爬梳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貢獻之外,本文另一個有意思的部分是文末作者對科學知識社會學自反的理解。戴文認為,由於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不存在對科學「最佳的」理解,也沒有什麼理解科學最好的途徑。科學知識社會學如果尋求成為「唯一的」理解,那它反而會成為自己所反對的對象。作者進一步採取了多元論的立場,期盼能引入更多的方法與視角來研究科學。雖然戴文對此僅點到為止,但它替我們點出了新的方向。如何自反地來看待科學知識社會學,相信會是我們下一個努力的目標。
理解了強綱領的基本立論之後,如何把這些主張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ation),是我們在錨定強綱領學說體系座標時的必要工作。劉文旋的文章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漂亮地在理論的星海裡,標出了理論與理論間的相對位置。對初次接觸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人來說,最惱人的事莫過於得搞清楚這個名詞與「科學社會學」或是「知識社會學」的異與同。劉文一個表格就清楚標出了這三個如此相近,卻又這麼迥異的名詞。緊接著,他的文章轉入科學社會研究的三大傳統,勾勒了這些傳統所代表的三個走向,以及他們在科學與理性的思索上所投射出的光與影。由這三個參照點出發,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會是「在哲學與社會學之間」了。在本文的最後一個部分,作者亦回顧了強綱領的四大信條。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用了一個「非對稱」的方式來強調「對稱」的重要。為此,作者特別援引了布洛爾較早期的著作,來重新詮釋這四個信條的順序及意義。把對稱原則放到最後,不只是在邏輯上比較緊密且易懂而已。對作者來說,強綱領之所以強,正是因為它的對稱。對稱使得關於錯誤的社會學與關於真理的社會學合而為一,濃縮在「關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上。除了上述環環相扣的申論外,本文在幾個地方也對其
他中西文化的議題,如普遍性與特殊性等提出了反省。本文最後提出的問題,相信是當代華人學術圈必須嚴肅面對的議題。
前兩篇文章正確地替本書起了個頭。陳瑞麟撰寫的下一篇論文,把讀者引領到有限論的另一個視域裡。這篇文章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探索維根斯坦哲學在社會學與心理學上的應用。在詮釋維根斯坦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影響上,陳文以生動的實例闡析了「指物學習」的意義。具體來說,當某人遇到一隻既像鴨又像鵝的生物時,他如何確定眼前這個生物究竟是鵝還是鴨?人們一般會通過比較特徵與差異的方法,來作為確定概念的依據。不過,儘管這個人可以從過去的經驗中挑選出他認為最適合的概念來描述眼前這隻生物,這個人卻不能確定他此時此刻對概念的應
用到底正確與否。正因為過去的例子是有限的,過往的經驗顯然無法固定住一個概念的用法,每個概念的應用本身都應該是「開放且無終點」的。既然所有的應用都是開放的,社會會經由協商來產生出一套規約與慣例,並依此來確定某人在應用概念時是否符合這套規約。換言之,概念的適用是一種規則的遵循。就這點來看,科學知識社會學很明顯是一種維根斯坦科學。緊接著,作者轉而介紹另一種維根斯坦科學:分類的原形理論。該理論主張種類與概念都不是均質的。基此,一個種類之下不存在什麼所有個體都共有的特質。而人對個體特徵的區分,是人類群體認知的一種結果。此處作者以知更鳥與麻雀來說明鳥類原型的共識,是怎麼形成的。從這些說明來看,科學知識社會學與分類的原形理論既有共相亦有殊相。陳文最後正是在探討兩者之間的異與同。由於目前討論有限論主題的論文還不算多,本文以比較的方法來詮釋,更清楚的描繪了有限論的特徵。
以上幾篇文章大致是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來闡析科學知識的內容以及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然而,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中,還有一個著重科學家怎麼形成科學信念的微觀視角。實驗室研究就落在後面這個項下。採取微觀研究取向的學者,對於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也就是科學實作的部分更感興趣。由於實驗室是科學家平日生產科學事實的地方,如果我們能搞清楚科學知識在實驗室中的製程,以及實驗室這個特定的場域與社會的關係,那麼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就能更清楚認識知識社會建構的歷程。換言之,研究者不再甘於只是斷言科學知識與社會是有關係的,他們更希望的是精確地標定到底科學知識的哪個部分是建構的,以及它是怎麼被建構的。樊春良的文章即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對兩本實驗室研究的名著進行了批判性回顧。本文先依序對實驗室研究的目標、方法與成果做了詳盡的介紹,接著再沿著這三個主題提出一系列的反思。作者認為:「科學事實是建構性的」其實是我們研究的預設,而不是研究的結論;實驗室研究的「經濟人」類比,有隱喻失義之嫌;實驗室研究的民族誌研究法過於粗略,以致於這種研究法對科學家行為理解的解釋,成為附隨的解釋。作者在結論處更強調,實驗室研究得跳出「科學事實/知識是社會建構的」之綱領與框架,才能在未來取得發展。很明顯的,樊文對社會建構論採取的立場,與本書其他作者略有歧異,但本文仍不失為一篇極具啟發性的論文。
以上幾篇論文,集中討論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基礎理論與看法,可看作是本書的總論部分。接下來的各篇文章,則是上述理論的實際應用。每篇文章都分別由建構論的視角分析了一些重要的主題。在篇章的安排上,這個專論的章節又可以分成兩大部分,除了最後兩篇文章之外,絕大多數的文章都可以看作是某種爭議研究。經由一次次的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因子總是隱身在每次的爭論當中,默默起著作用。最後的兩篇文章,之所以放在最後,主要是想幫助我們重新找回歷史感與社會(學)感,讓研究者可以遊刃在歷史與社會學中。我們認為這點對從事微觀研究的人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在個案的分析當中,研究者很容易就迷失在細節裡。本書的最後兩篇論文,把我們從微觀再拉回宏觀,讓我們瞭解到不管是知識還是科學知識,我們的理解可以是很寬闊的。
專論的第一篇文章,是有關多重發現的問題。當好幾個(組)科學家都在鑽研同一問題時,誰該享有發明人或發現人的美譽呢?一般人在對待此問題時,大多採取線性的思考,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利用客觀時間順序,來判定多重發現的順序。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因為當事人可以主張以其他的判準來決定發現的先後。比如說:研究的整全性、深刻程度,以及研究者主觀上是否有意識到該研究的創新價值等等,都可以作為多重發現的判定條件。在程志波與徐飛共同撰述的文章裡,作者展現了微觀研究的特徵,他們以獨到的抽絲剝繭技巧為讀者解析微積分到底是誰發明的。經由這般細膩的分析,我們發現某個研究成果究竟是單一發現還是多重發現,其實與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情境有關。基此,多重發現不是一個客觀的事件,而是不同群體在這個議題上相互較量與妥協的結果。基本上,誰取得了語境定義權,誰就取得了合法性與優先權。正如作者所說的,跑得快不一定能贏得比賽,因為能不能勝出的關鍵是遊戲規則,而不在於奔跑的速度。這個結論對當下的科學研究很有啟發。幾乎每個科學議題都有好幾組人馬同時在進行研究,研究的能力與速度固然重要,但誰的研究成果會被認為是科學發現,進而取得優先權與發明權,則可能與其他的要素(如:話語權力的爭奪)有關。若如此,規則的制定權可能比什麼都來的重要。
接下來蘇俊斌的文章討論到技術爭論的問題。作者鎖定了標準化這個常用的技術爭議解決途徑來作為研究標的,拓展了他獨到的「準入—爭論—轉譯模型」(Access-Controversy-ranslation, ACT),並以此來概括標準化的協商過程。本文與前一篇文章最大的不同,在於作者實際參與了一個標準化的組織,直接參與並觀察了工作組內部的運作,完整追蹤了F 濾波器爭論的過程。由這個實際的案例,作者發現爭論的提出、評價以及最後的共識,都是立基於一連串的前提假設之上。蘇文把這些預設前提稱作「介觀標準」(meso-standard)。介觀標準是整個爭論得以取得最後共識的要件,因為它們是溝通過程所必須的。這個爭議研究最有「爭議」的地方,在於作者對介觀標準的詮釋。蘇文認為介觀標準的構成,不只是人與人的相互作用而已,還包括了人與物間的歷史實踐與作用。基此, 作者對「傳統」社會建構論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傾向提出了批判。具體言之,傳統的研究把科學與技術事實,看成是行動者(人)與行動者(人)的相互作用。這麼一來,所有的科學技術就變成一時一地行動者的建構結果了。若如此,則所有科學事實都只是片斷、特殊且不具有普遍意義的了。對此,作者採取了拉圖爾(Bruno Latour)對社會的詮釋,認為社會建構論中所謂的社會,既有人的因素也有物的要素在其中。質言之,「社會建構是由人和物共同參與的具有時間延續性的實踐總合。」當然,此處牽涉到著名的反對拉圖爾(Anti-Latour)論(Latour 1999; Bloor 1999a, 1999b)。編者不擬為愛丁堡學派再提出偏頗的辯護,此爭議的解決可能只得留給讀者去形成共識了。
雖然編者不想捲入爭議之中,但爭議裡頭隱含的爭議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王小紅的文章,即是處理發生在《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這本期刊中的論戰。這篇文章很有自反性的味道,因為它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方法,拿來分析發生在科學知識社會學裡頭的爭議。爭論的起因是計算論者把人工智能模擬科學發現系統BACON ,拿來作為拒斥強綱領的實例。這個對強綱領的挑戰,引起了各方激辯,此處討論的重點是:科學發現是否完全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爭論的兩個極端一為心智主義的科學發現觀;另一為社會學主義的科學發現觀。簡言之,強綱領的挑戰者,反對布洛爾等人把認知因素混同為社會因素的作法。他們認為這種混同排拒了心理學在此等議題上的地位。基此,挑戰者把BACON等機器發現程序用來作為捍衛心理學在科學發現研究上主導權的媒介。作者援引了伍爾加(Steve Woolgar)的看法,認為整個爭論的核心其實是:一場對社會學的限度的挑戰。換言之,問題的核心是我們要把「社會(的)」這個概念擴張到多大?對此,作者闡析了區分社會內部情境(認知因素)與外部情境的合理性,並指出了強綱領主張者之間的微妙差異。與前面幾篇論文類似,本文直搗核心,追問了社會學與社會的限度何在,也討論了這個模擬科學發現的爭議如何對強綱領形成挑戰。總之,以上三篇論文適合放在一起閱讀。
正義跟科學有什麼關係?黃之棟的個案研究提出一個有趣的視角,清楚且鮮明地展現了兩者間的合縱與連橫。他的研究也替不斷進展中的科技與社會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此處編者不打算深入探討正義與科學是如何交錯的問題,我們想把討論從正義拉到一些對社會建構論的批評上頭來。論者對社會建構論最常見的批判是:作為一個研究的方法,社會建構論迴避了對「真」(truth)與「假」(false)的討論,轉而把焦點放到了真假主張「建構」的過程上(Burningham and Cooper 2001)。然而,面對一篇討論環境「正義」的文章,我們似乎必須反省,當研究者說自己的研究興趣是在過程,而非真假的區辨時,他/她是不是已經背離了討論的核心?一個與此牽連的問題是,在面對「正義」的問題時,研究者到底應該站在哪裡?這是個與研究倫理有關的議題。以黃文來看,作者對待這三波浪潮時明顯的採取了「等距」的立場,但等距本身有沒有可能就是不對等的?具體來說,一般的研究之所以
比較常提到黃文中所說的第一波研究浪潮,根本的原因是:有比較多人支持第一波的看法。當我們用了幾乎同樣的篇幅來闡述第二波與第三波的少數說時,這樣的處理在實際社會問題上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值得吾人深思。當然,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社會建構論不對真假進行判斷的態度,可能只是純學術的思辯而已。由於環境正義這個主題與當下正在發生的環境運動息息相關,社會建構論的不區辨本身,就是一種區辨。因為這種立場,弱化了共識並暗助了少數說。當然,這類爭辯也是很有限論的。
下面兩篇文章基本上處理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衝突。李正風與沈小白合寫的文章分析了中國20世紀以來多次的中醫存廢爭議,以及當中科學觀演變的問題。大體來看,對待中醫的態度經歷了三次轉折。首先,20世紀20年代前後,由於中國多次遭逢列強進逼,因此作為傳統文化載體的中醫首當其衝成為批判的標的。在西化語境底下,反中醫成了反傳統的表徵。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為中醫的存續提供了依據,中醫更被寫入中國《憲法》中,取得了科學與法律地位。到了這個世紀,反對中醫的聲浪依然存在,只不過反對的理由從反傳統轉向了反偽科學上。中醫到底是科學還是偽科學,成了各方角力的戰場。由於中國的《科普法》中,明訂了抵制和反對「偽科學」的條款,反偽鬥爭取代了原先的反傳統鬥爭,成為爭議的焦點。整個中醫爭論有趣的地方,除了表面的中醫與西醫的問題之外,誠如作者所言,表象背後的真正爭點其實是中醫與科學的關係。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背景下的中醫爭議,其實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對科學的看法與態度。當然,由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看法與態度又可以串連成科學形象和科學概念的變遷史。本文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科學與法律的關係。在中醫取得了憲法層次的地位之後,它的科學地位也因而確立。在下位法層次爭執它是不是偽科學本身,就已經揭示了作者所言的由科學性到科學化的轉向,這些問題都是相當有限論的。當然,西方學界一系列關於「垃圾科學」(junk science)(Edmond and Mercer 1998)、劃界工作(boundary-work)(Gieryn 1983),乃至最近的數據品質條款(Data Quality Act)(US OMB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2001)等,也都值得未來進一步解明。
滿清末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個時期也表現出一種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列強進逼使得民族國家的概念在中國紮根,知識的生產與形構莫不環繞在如何解決當時內外交攻的困境上。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下,晚清的翻譯出版事業成了知識、價值觀以及表現方式的戰場。衝突與對話也凝聚在這個時期的譯書中。崔波的論文嘗試把滿清末年的翻譯與出版,放進西方知識全球化的向量中來觀察,並藉此說明知識建構的歷程。具體來看,作者認為不管是西方或東方,各方所提供的知識都是代表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識。但在翻譯的實踐裡,翻譯工作必然會產生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使得一方的特殊性普遍化。換言之,原本同屬地方性的西方知識,在翻譯的工作裡被賦予了優先權,進而產生文化主導權,並對知識的生產、評價乃至實際的閱讀過程發生影響。為了精確描述中、西兩種地方性知識在譯書問題上從碰撞到融合的過程,作者以橋接、填充、謄寫等概念來捕捉知識體系的更新與再建構。崔文並在結語中精準指出,知識的築模化體現的是多種知識權力的相互博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體用論與西學中源等問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做了深刻的分析,成功地為這個動盪年代的知識建構下了厚重的註解。
替本書壓軸的是黃瑞祺關於自反性的討論。自反性是強綱領四大信條中的一個,談愛丁堡學派就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自反性的問題放到了整個社會學的脈絡與演進中來觀察,而不只從科學知識的範疇出發。換言之,在討論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後,我們還是得把這個主題再「放回」社會學的傳統裡。如此一來才能更精確地掌握科學知識社會學在整個社會學中的學科位置。除了自反性的問題之外,本文還討論了社會批判理論給我們的啟示。雖然作者沒有直接點明,但本文替讀者勾勒出一個看似模糊、實則鮮明的輪廓:科技與社會研究與科學的關係其實是動態的,在科技與社會研究了科學之後,它的研究對象(即科學本身)也隨之改變了。由於這個緣故,科技與社會本身成了那個浮動的地平線(horizon),這也呼應了本書第一篇文章裡戴東源所描繪的情形。當然,解決的方法是不是多元論?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此外,本文為文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文章中所舉出的實例,如:銀行擠兌、股市預測、民意調查等,這些問題都是吾人可以再開展的新議題。比如說,愛丁堡學派中生代理論家麥肯其(MacKenzie 2009a, 2009b)即對當前的經濟危機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次級房貸發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前述自反機制的出現。換言之,當評比機構把某投機商品評為AAA(姑且翻譯為特優)時,人們就以為這些投資是絕對(或至少是特別)安全的。整個評比機制其實也是自反的。黃文在傳統與未來之間,讓我們有了更寬闊的視野。
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至少捕捉到了科學(與)知識的一部分。我們看到的東西離全貌還有多遠,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現階段唯一能說的是:我們已經為愛丁堡學派設下了嚴苛的目標。至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了黎朋教授的挑戰,這可能是讀者才能回答的了。
導言
為愛丁堡學派設下嚴苛的目標
黃之棟
(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我有這麼個印象,就是說許多STS的人相信他們的研究進展已經超越了強綱領。他們覺得這個綱領在1970年代也許真的很有趣,但他們認為自己現在做的是些很不同、或更有深度的、還是說是更有趣的事情。但我猜測真正的情形是,許多人發現強綱領太難了。我猜他們沒給自己設下個嚴苛的目標。⋯⋯對我來說,這(事實上)就像是在對自己說:讓日子簡單點過吧!在我們找到事情的起因之前,不要這麼掙扎的研究了吧!讓我們快速地從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來展現解釋的多...
目錄
導言:為愛丁堡學派設下嚴苛的目標
總論
第1章 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
第2章 科學知識社會學
第3章 維根斯坦與科學知識的社會學
第4章 從觀察到的科學到對科學的解釋
專論
第5章 強綱領視閾下的多重發現
第6章 關於技術爭論及其解決方式的社會學探討
第7章 人工智能機器發現系統是對強綱領的經驗拒斥嗎?
第8章 正義的「科學」?
第9章 從反傳統到反偽科學
第10章 以譯書為中心的晚清知識建構研究
第11章 自反性與批判社會學
導言:為愛丁堡學派設下嚴苛的目標
總論
第1章 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
第2章 科學知識社會學
第3章 維根斯坦與科學知識的社會學
第4章 從觀察到的科學到對科學的解釋
專論
第5章 強綱領視閾下的多重發現
第6章 關於技術爭論及其解決方式的社會學探討
第7章 人工智能機器發現系統是對強綱領的經驗拒斥嗎?
第8章 正義的「科學」?
第9章 從反傳統到反偽科學
第10章 以譯書為中心的晚清知識建構研究
第11章 自反性與批判社會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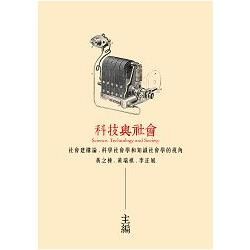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