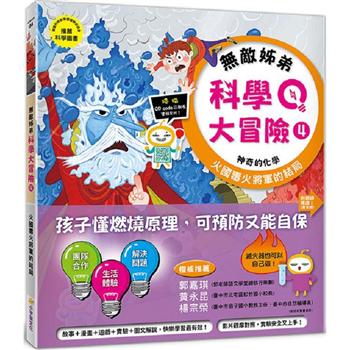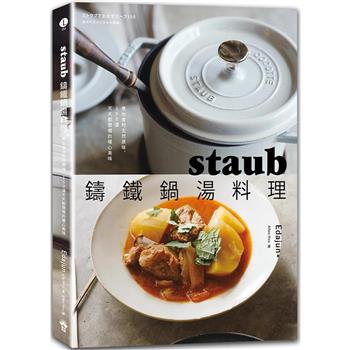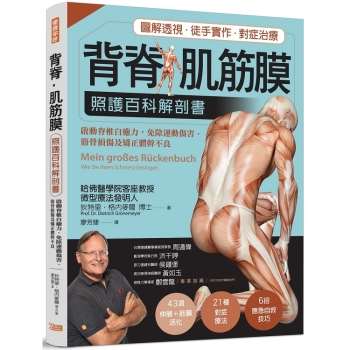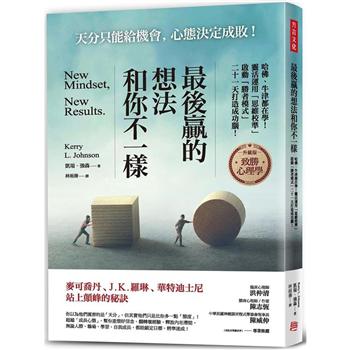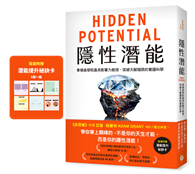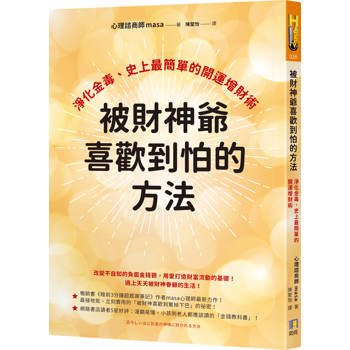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淑伸的圖書 |
 |
$ 322 ~ 460 | 認識司法精神醫學:一個犯罪者「究竟是真的瘋了,還是只是壞人」?寫給律師與大眾讀者的精神醫學實務指南
作者:薇薇安‧雀恩‧許奈德曼 / 譯者:李淑伸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1-03-13 規格:21cm*14.8cm (高/寬) / 平裝 / 360頁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我們怎麼知道某人是瘋子還是壞人?//
當瘋狂與疾病對決,有可能兩者兼有嗎?或者還有其他選擇?
在那些舉世矚目的重大新聞事件中,我們經常看到一種「二擇一」的心態,某人要不是完全瘋了,就是異常的精神病態者。人們總是大力反彈,說精神疾病只是藉口,「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人有精神疾病,這群暴力的瘋子應該「轉念間回復正常」做出負責任的行為,否則就該關進監獄或處以死刑。
『我們評斷,但我們不了解。
很重要的是,在做出論斷之前,至少要先努力理解。』
在「瘋狂」對上「惡質」的世界裡,其實有許多的瘋狂混跡於劣行之中。也許這群犯罪者當中有些真的是惡棍,有些人生病了,有些是精神病態者,有些則是其他狀況。也許有些人被虐待到根本沒辦法做出任何理性決定的地步……
※本書特色
◎非精神醫學專業人士也可以輕鬆使用的友善精神醫學指南──涵蓋了我們需要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的理由,以及精神醫學在法律實務的應用。
精神醫學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本書所提及醫學知識與案例並不會因為司法系統的不同,而有地域上的差異。此外,有鑑於一般人對精神疾病認識的不足,重大刑案的精神鑑定每每掀起社會波瀾,本書既是寫給法律相關工作者,也是一本給大眾讀者的司法精神醫學入門指南。
◎什麼情況下須要進行精神鑑定?以及如何判定?──書中介紹與說明對精神狀態檢查、常見精神疾病診斷、可治療疾病與腦損傷、偽裝成精神疾病的健康問題及其他多項主題,並附有一份實用的精神醫學術語表方便讀者參考。作者更附上自己平日工作的基本評估格式,分享給需要的人士。
美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許奈德曼醫師長期從事精神鑑定工作,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為讀者介紹關於精神疾病的一些常見迷思以及精神錯亂的表現,討論這些症狀可能意謂著什麼,以及該如何完整地了解和解釋它們。這將有助於執業律師辨別出哪些類型的人可能需要聯絡精神科醫師,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領會、解讀和利用精神科醫師所提供的訊息。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犯罪者究竟是「真的」瘋了,還是只是壞人?
像是介紹如何識別精神病態者,以及如何明瞭和解讀他們的謊言,探討一些主題像是「詐病」與「偽病」的異同,以及引人注目的解離(例如「多重人格」)和失憶症抗辯主張。無論律師代表的是哪一方,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理解在法律實務上都可能關係重大。
◎ 在法律範疇的任何一處,你都可能與瘋狂相遇。
律師們時常遭遇各種行為怪異、患有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精神病態、性犯罪、學習障礙、先天缺陷、與其他行為和情緒問題的委託人和案件。他們往往沒有準備好了解精神醫學報告的本質,也不清楚精神評估鑑定的結構,以及如何在法庭上善用和質詢這些資料。本書為法律專業人士提供了辨識精神病患的工具,幫助他們在報告和證詞中掌握精神醫學的訊息和語言,書中主題包含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的必要性、精神醫學在法律中的應用、各種精神疾病的介紹,以及專家證人的使用。
※審訂人
黃聿斐|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精神科醫師/臺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
「作者許奈德曼醫師憑藉其豐富的司法精神醫學專業及工作經驗,嘗試以容易了解的語言及豐富的案例故事,在精神醫學專業與非專業間搭一座橋,以促進彼此的了解,特別是處理精神病犯/患的夥伴──律師或其他司法人員。
書中介紹生理疾病、處方用藥、毒品等可能引發精神疾病的樣態,以做為第一線接觸當事人的司法人員的常識。例如從未有過精神疾病史的中年女性,突發的狀似瘋狂的暴力行為,背後的原因可能是使用毒品,但也可能是因為治療紅斑性狼瘡大量服用類固醇治療的結果。原因不同,法律上的行為評價自應有所差異。作者並以自己撰寫司法精神醫學鑑定報告的格式,虛構了一篇鑑定報告,例示報告中應該呈現的項目,及各項目應有的內容及相關注意事項,這部分對於司法精神醫學鑑定的初學者,或是不知道從何評價司法精神鑑定報告良窳的法律人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法律與精神醫學雖是二門完全不同的專業,卻在許多領域發生關聯,因此促進雙方專業的互相了解及溝通刻不容緩。這本書雖不可能將法律人變成精神醫學專家,但可以讓法律人初步判斷行為人有否精神障礙的可能、是否需要精神科醫師的協助。至於怎樣才算『適任的』精神鑑定人/專家證人,就交由讀者自行發現了。」(摘自審訂序)
作者簡介
薇薇安.雀恩.許奈德曼Vivian Chern Shnaidman
美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
對司法精神醫學的興趣始於尚不知司法精神醫學這門學科之際。於布萊恩瑪學院(Bryn Mawr College)攻讀心理學期間,便計畫成為一名「在法庭告訴所有人案件真相的精神科醫生」,繼而前往世界百大學府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習醫。回國後,在美國首屈一指的醫學研究機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與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接受精神醫學訓練,並且於紐約大學完成司法精神醫學研究醫生培訓,開始全職從事司法精神醫學工作。曾在各種司法環境中工作,包括監獄、司法精神病院,以及專門關押性暴力犯罪者的監護設施等。
目前從事私人精神治療與司法精神鑑定,主要專注於民事案件,如兒童監護權、家庭暴力、停止親權、遺囑能力,以及許多難以形容的奇特案件。諮商和鑑定對象廣泛涉及司法精神醫學和一般精神醫學的各種主題,像是有虐待傾向的母親、精神病態的家長、移民評估、性犯罪者等。身為多個專業協會的成員,尤其活躍於美國法醫刑事鑑識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譯者簡介
李淑伸
台灣大學法學士,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歐洲文化政策與管理碩士,華威商學院(WBS)人力資源管理證書。曾任韓國又松教育基金會顧問、又松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