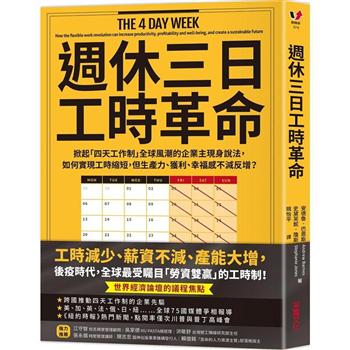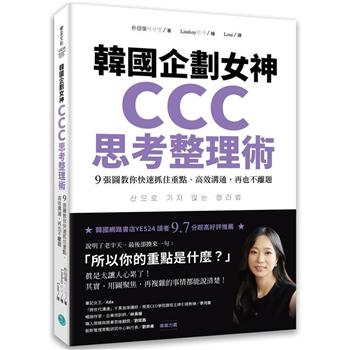本書是一位青少女以純淨的心,飛躍的靈思,寫成的生命詩篇。作者竹薇今年十八歲,就讀北一女中,原本應順利畢業、升大學,卻因一場不可逆料的病,使她的人生出現巨大轉折。醫師診斷她得的是「重度憂鬱症」,在十八歲生日前夕,嚴重的絕望感擊潰了她,她覺得「一切就此結束是最美好的句點」而企圖割腕自殺……。
距畢業僅三個月時,承受著身心煎熬與課業壓力,她決定休學。因為,她不願在「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下」混畢業。這段日子,她寫作、休息,等準備好了再出發。
每個生命都有他尋找出路的方式。在這場和生命的戰役中,竹薇以寫詩療癒,在絕望的深淵構築心靈的七彩虹橋,所有成長的掙扎、戀愛的淚水、憤怒的吼嘯,及狂妄的夢想,都譜寫成詩,或許青澀不夠成熟,但,低盪與飛翔、苦澀與甜美交錯的十八歲,原本就這樣。
竹薇和她周遭的每一個人,她的父母、師長、醫師、朋友,以堅定樂觀的心情勇敢面對病症,在相互了解中學習傾聽內心的聲音。生命,也許並無標準答案,讀完本書,你將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詩篇。
作者簡介:
竹薇
1985年生,射手O型,台北縣新店市人,曾入北一女中就讀,高三下學期因憂鬱症休學。嗜好打球、看小說、幻想,常以寫詩為抒發情緒之管道,相信「即使人生無解,過程仍是最動人的方程式」,本書是她的第一本詩集。
每個生命都有他尋找出路的方式。在這場和生命的戰役中,竹薇以寫詩療癒,在絕望的深淵構築心靈的七彩虹橋,所有成長的掙扎、戀愛的淚水、憤怒的吼嘯,及狂妄的夢想,都譜寫成詩,或許青澀不夠成熟,但,低盪與飛翔、苦澀與甜美交錯的十八歲,原本就這樣。
竹薇和她周遭的每一個人,她的父母、師長、醫師、朋友,以堅定樂觀的心情勇敢面對病症,在相互了解中學習傾聽內心的聲音。生命,也許並無標準答案,讀完本書,你將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詩篇。

 7 則評論
7 則評論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2004/07/10
2004/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