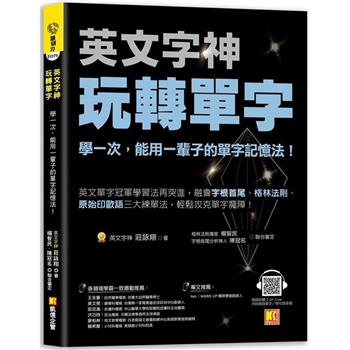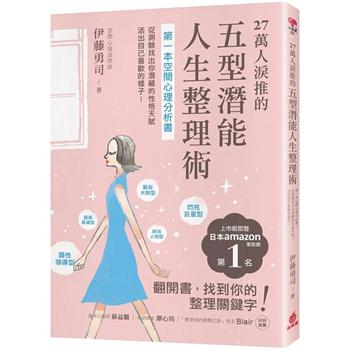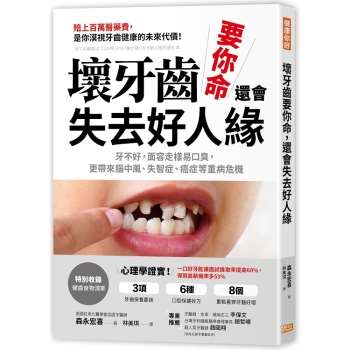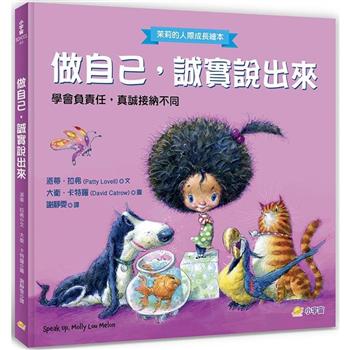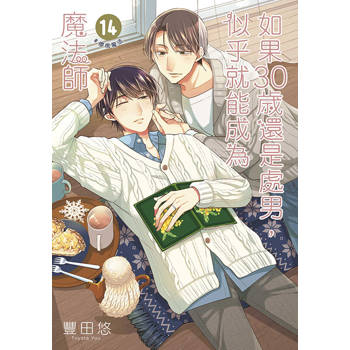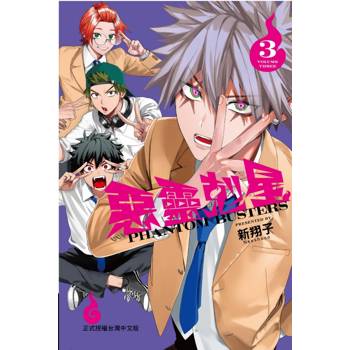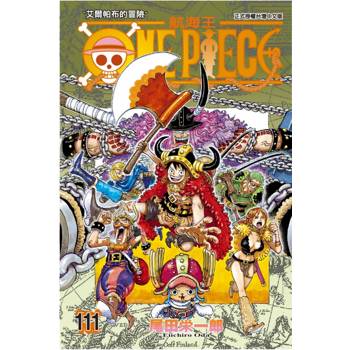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高麗篇》序
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
918年王建驅逐弓裔,高麗由此建立,並存續至1392年。在此期間,中國政權更替頻繁。10世紀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和十國。916年契丹建立後,逐漸成為東北亞的軍事強國。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隨後征服了長江以南地區的多個政權,但在整體軍事實力上較契丹而言並不佔優勢。12世紀初金朝建立,宋金聯合滅掉契丹,然而金朝勢力越來越強大,佔據了比原來契丹更多的華北地區。13世紀初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先後滅掉了金和宋,統一了中國,成為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帝國。14世紀後期,朱元璋建立明朝並開始統治中國。
中國的政權更替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北方的契丹、金朝和中原的五代、宋朝等相互爭奪霸權時,競相與高麗聯合,因此高麗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相反,當元、明等統一王朝出現時,對高麗而言,來自中國的外交壓力也會相對增大。這種情況下,高麗王朝的存續常被誤解為是依賴於外部的變數。然而,如果仔細考察高麗的外交史,就能發現它為了實現國家的生存和繁榮,非常善於處理與周邊國家的外交,以致於在當時急劇變化的東亞國際局勢中還能存續近五百年。
實際上,有不少事件充分展示了高麗的外交力量。高麗太祖深知後晉是契丹的附屬國,卻利用當時後晉試圖脫離契丹掌控這一點與後晉交好,從而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後三國」統一之後,太祖為了遠離北方鄰境的契丹並誘導渤海人前來投化,引發了「萬夫橋事件」。儘管與東亞的軍事強國契丹接壤,但是成宗、穆宗、顯宗為了吸收先進文化,更加希望與厚待高麗的宋朝開展外交,或者與兩者進行雙重外交。
在與契丹的第一次戰爭中,很多人建議高麗國王割讓北方領土或投降。但是,徐熙準確把握了契丹入侵的目的,提議與蕭遜寧(蕭恒德)談判,結果不但終止了戰爭,高麗還獲得了鴨綠江附近的江東六州。顯宗雖然在與契丹的第三次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他認為比起通過與宋朝開展外交獲得國家實利,維持和平更有利於國家利益,於是決意對契丹「事大」。高麗以勝者姿態主動「事大」契丹,這使得雙方在這段冊封關係中的地位差距不那麼明顯。文宗在與契丹的「事大」交往中重新展開對宋通交,故而從宋朝獲得了大量的回賜品,使高麗更加富強。武臣政變後,明宗即位,前去金朝告奏新王即位的高麗使節庾應圭面對對方的刁難依然忠貞不屈,感動了金朝君臣,使得金朝承認了高麗明宗的合法性,為穩固當時高麗的政權作出了貢獻。
即便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崔氏政權還是果斷向江華島遷都,繼續與蒙古進行抗爭。在戰局不利的時候,以答應蒙古要求的方式換得對方撤軍;之後對於自己的言而無信又使用各種外交辭令與對方周旋,前後堅持了三十多年。於是,1259年高麗太子和忽必烈的會面成為可能,並以比任何其他與蒙古對抗的國家都有利的條件實現了和議。「元干涉期」也有過將高麗降為元朝真正意義上的行省的所謂「立省策動」計劃,但是很多高麗人都希望國家能繼續存續,所以最終說服了元朝,使該計劃流產。1356年的反元改革表明,高麗人想要擺脫元朝政治干涉的渴望由來已久。
隨着明朝的登場以及恭愍王的暴亡,禑王的正統性成為問題,因此高麗在與明朝的外交上失去了主導權,並因貢馬問題經歷了諸多困難。但當明朝對高麗故土主張所有權,並試圖設置鐵嶺衛時,高麗果斷地採取了軍事行動。崔瑩的「遼東征伐」雖然因「威化島回軍」終告失敗,但這成為了轉變明朝對高麗認識的契機,高麗隨後與其重新確立了朝貢冊封關係。這種關係與高麗和契丹、金朝、宋朝所建立的關係相比雖然多少有些不利,但與高麗和元朝的關係相比還是略微有利的。
在高麗外交史上,最值得關注的是其對周邊國家侵略的積極抵抗和輝煌的勝利。高麗與契丹經歷了三次戰爭,與蒙古進行的戰爭更是韓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但高麗最終都沒有被征服。此外,曾是東亞禍亂的哈丹賊、紅巾賊、倭寇等的入侵在高麗的反擊下逐漸平息。在與蒙古的抗爭過程中,高麗雖然因叛亂而丟失過領土,但國家並沒有滅亡,最終也重新收復了失地。
高麗王朝在與周邊國家發生衝突,並多次進行長期戰爭的過程中,如果未能贏得民心,很可能面臨敗北。另外,高麗雖然是人口只有三百萬左右的小國,但是在戰爭交火、戰後處理、談判協商等方面展露了高明的外交手腕,從而能夠與強大帝國抗衡。最終,高麗王朝吸納渤海遺民,領有于山國和耽羅國的土地,使得領土比建國時更為廣闊,並將其移交給了下一個王朝——朝鮮,稱這是高麗取得的最高外交功績也不為過。
475年間,在東亞局勢的巨變中,高麗以自主的外交力量和能在戰爭中取勝的強韌軍事力量為基礎,成功地維持住了國家形態。這一結果並非順應着周邊局勢的變化自然而來,而是高麗以自己特有的力量主動應對爭取來的。因此,本書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試圖闡述高麗的傳統外交活動是如何讓高麗這一「國家地位」能在周邊國家獲得高於實際的評價和威望的。與此同時,本書也重新審視了國王和外交使者在達成上述結果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不論是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
基於這樣的編寫目的,本書將高麗的外交史劃分為十個主題。除了高麗外交史總論以外,剩下的主題根據不同時期分為五代十國、契丹(遼)、宋朝、金朝、蒙古和元、明朝等與高麗建立朝貢冊封關係的國家,以及日本、女真等外交地位與高麗對等或稍低的周邊國家及民族。按照不同的對象國進行分述,這樣既反映了當時東亞的國際局勢,也能將高麗的外交活動敘述得更加鮮活細膩。當然,也有一些內容因史料不足而未能深入探討。
需要指出的是,從10世紀到14世紀末,中國有多個政權並存,因此在敘述高麗與不同政權的外交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重複。例如,契丹及五代十國、契丹與宋朝、金朝與宋朝、蒙古與宋朝、明朝與北元等政權都是同時並存的,因此在敘述高麗與契丹的外交時要同時考慮到高麗與宋朝的關係,反之亦然。儘管有所重複,但在特定問題的論述上,還是有必要將相關內容作為背景再次提及。本書努力將除了總論以外的各章題目統一為「外交」,但實際上其內容也包括了「對外關係」。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書雖然由東北亞歷史財團策劃並出版,但執筆者並未被要求採用某特定的學說或用語。因此,在敘述高麗與契丹、宋朝、金朝等國的外交時,即便執筆者們針對某些內容看法不一,我們也沒有刻意進行統一。關於高麗和元、明之間的關係有多種闡釋,本書也都如實地尊重了執筆者的見解。由衷感謝執筆者們出色地完成了《高麗篇》的編寫。
《高麗篇》付梓之際,腦海中不免浮想起當時各篇的編纂委員們第一次聚首並決心打造一部真正以外交史為主體的「外交史」時的場景。要問目標是否已經實現,似乎還有不少內容需要修改和完善。但是,如果說這本書對編寫外交史而言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那麼我認為可以充分認可其價值。從這一點來看,本書可以理解為《高麗篇》「2018年版」或「版本1.0」。希望今後其他研究者能在此基礎上,創作出完成度更高的外交史著作。
《高麗篇》主編
李鎮漢
2018年12月
中文版序一
變與不變:夾縫生存之高麗
朝鮮半島,位居東北亞之核心,乃大陸與海洋之紐帶,亦為大國勢力交匯之所在。此特殊之地緣環境,奠定其於東亞國際關係中舉足輕重之戰略地位。自古以來,此地便是各方利益交錯制衡之競技場。面對強敵環伺之外部環境,擅長外交無疑成為求生之必備技能。誠如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所言,韓國位於強國之間,必須謹慎行事,外交上力求均衡,故而應比其他民族更精於「外交」之道(《金大中哲學與對話集》)。朝鮮半島高麗王朝(918–1392)之外交實踐,恰為此理之生動詮釋。
高麗時代,在朝鮮半島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之位置,今之韓國與朝鮮,其英文國名KOREA,即源於高麗(고려)。10至14世紀間,高麗面對東亞國際局勢之紛繁複雜、變幻莫測,歷經五代十國、遼、宋、金、元、明等政權之更迭與並存。高麗王朝與上述政權悉數建立外交關係,無論主動抑或被動,皆形成錯綜複雜之外交格局。每當東亞政治版圖劇變,皆對高麗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面對南北對峙乃至多國鼎立之中國政局,高麗如何在諸強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實為關乎國運之大事。高麗王朝非但未屈服於此複雜地緣政治環境,反而巧運外交智慧,靈活應對,轉危為安,化弊為利,終獲勝利。於彼風雲變幻之時代,高麗成功延續五百年國祚,超越同期本地區其他所有強權。
面對複雜多變之國際環境,高麗採取靈活多樣之策略以應對。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勢遊牧、漁獵民族,於其崛起擴張之際,皆曾對朝鮮半島懷有覬覦之心,對高麗進行不同程度之侵犯。面對如此嚴峻挑戰,高麗在頑強軍事抵抗之同時,亦積極展開外交斡旋。因軍事上未遭完敗,故高麗在與彼等外交談判中,尚能避免陷入被動。尤其於蒙古鐵騎長達40年之頑強抵抗後,高麗通過聯姻等方式,與元朝建立密切關係,保全宗廟社稷,使國家得以延續。高麗之外交地位,雖常隨外交關係之變化而轉變,然其作為事實上獨立國家之身分,卻始終未變。如女真(金)初奉高麗為「父母之邦」,後雙方結為「兄弟之邦」,最終變為君臣關係;蒙古(元)與高麗之關係,亦經歷「兄弟」至「舅甥」及君臣之轉變。高麗忍辱負重,以「輸誠事大」換取生存與獨立,展現其靈活應變和適應複雜環境之能力,以及外交策略之務實性。對於國際局勢之不確定性,作為小國之高麗,對周邊環境之變化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展現出非凡之敏銳性。在與宋、遼、金三國之互動中,高麗逐漸對各國實力對比有深刻洞察與清晰認識。1162年,宋朝明州向高麗傳牒,稱本朝戰勝金朝並俘金帝完顏亮,高麗並未輕信,稱「蓋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盡如其言」(《高麗史》卷18)。對於宋朝「聯金攻遼」,高麗指出「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奉勸宋朝「宜早為備」(《宋史》卷487)。高麗此立場固然有對自身安全之考量,然亦不可否認其對地緣政治形勢判斷之敏銳。
高麗善於因勢利導,往往能將地緣政治環境之挑戰巧妙轉化為機遇。其試圖在環伺之大國中保持平衡,臣服於遼、金、明之同時,亦努力與北宋、南宋、北元等保持聯繫,希冀各方互相牽制,避免被單一勢力完全控制或過度依賴一方,從而保持自身之相對獨立性。高麗曾謀求「聯宋制遼」,然隨國際形勢之發展,又圖借已勢微之遼朝對抗正崛起之金朝,認為「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宋史》卷487),勸宋放棄「聯金滅遼」。為擺脫元朝控制,明朝甫建,高麗即迅速遣使朝貢,與之建交,而後與明朝關係惡化時,又頻繁與北元互動,互為犄角之勢。正因高麗外交策略之靈活與務實,其非但未成為中國各政權爭奪下之犧牲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此博弈之受益者。遼宋在爭奪中國主導權之時,為拉攏高麗,屢對高麗成宗、文宗等統治者加封進賞,遼朝雖有軍事實力,亦得對高麗威恩並施,宋朝接待高麗使臣之規格,歷經「例同交趾」、「例同西夏」、「例同遼國」之不斷提升,最終將與高麗之外交關係升至「國信」級別;在遼金爭霸中,高麗亦伺機奪取保州等地,實現領土擴張。高麗巧妙周旋於中國對峙政權之間,此平衡外交策略使其保持相對獨立性,並能在不同勢力間尋得利益契合點,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展現出高超之外交手腕與靈活之應對能力。
於東北亞政治舞台之縱橫捭闔中,高麗亦在逐漸認識自我、實現自我。中國各政權競逐爭霸之際,高麗統治者亦曾建元稱帝,以「海東天子」自居。後隨內外形勢之變化,基於自身政權合法性之強化及國家生存發展之需要,高麗統治者對外主動奉五代、宋朝等中原王朝為正朔,積極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之東亞國際體系;對內則仿唐效宋,構建起一套與中原王朝完全對等、從中央至地方之統治體制,呈現「內帝外王」之象。
高麗朝廷在引進中原科舉制度時,特設「賓貢科」,積極選拔前來求仕之宋人,其中不乏在宋朝已取得功名者。有麗一朝,來自宋朝被任用於麗廷之「投化官吏」為數眾多,此在中朝歷史上皆屬空前絕後。此外,前往高麗之宋商,除商人本職外,亦身兼多職,尤其在「八關會」上充當「宋使」角色,向高麗國王進獻方物,這對高麗國王政治權威之構建起到關鍵作用。
高麗自視非「夷」,而以「華」自居,視契丹、女真、蒙古等為「禽獸」、「藩」、「胡」、「虜」等。尤為甚者,高麗自詡為女真「父母之邦」,通過授予女真酋長諸如「歸德將軍」、「懷化將軍」、「柔遠將軍」等官銜,使其定期朝貢。此舉充分彰顯了高麗欲構建以自身為核心之「華夷秩序」,並扮演文明教化引領者之決心。
每年十一月,八關會之盛況生動呈現了所謂「高麗式華夷秩序」或「八關秩序」。在雅樂〈萬邦呈奏九成〉之伴奏下,宋商、女真酋長、日本進奉商人、耽羅王室等依次向高麗國王進獻貢物,呈現出一幅「四方來朝」之壯麗圖景。此儀式不僅象徵性地宣揚了以高麗為中心之世界觀,更展現了高麗提升國際地位之強烈願望。
受傳統華夷思想之薰陶,及東亞國際局勢之激發,高麗之自尊意識日益強烈,尤以精英階層為甚。彼等藉由諸多文字創作,淋漓盡致地展現出民族自覺與文化自信。李承休所著《帝王韻紀》中有「遼東別有一乾坤,斗與中朝區以分」之句,即鮮明地強調了朝鮮半島之獨特地位與自主精神;而「並與帝高興戊辰,經虞曆夏居中宸」之語,則闡明朝鮮半島始祖檀君與中國聖王唐堯並世建國之事跡,意在彰顯其歷史淵源之深遠流長。此外,詩中「唐肅潛龍時,遊賞東山水……聖骨將軍孫,有女賢而美。遂合生景康,善射無倫比」之吟詠,更將高麗王室之血脈溯源至唐肅宗,以彰其血統之尊貴非凡。李氏另於〈雪中謝蓬庵相國惠玉粲〉中有「聖朝本是右文朝,文物煌煌掩唐漢」之壯語,豪言高麗文治之盛已遠邁漢唐。陳澕〈奉使入金〉中之「西華已蕭索,天東日欲紅」,則寓意深長地展現了高麗與宋朝東西並峙之格局,並以宋朝之衰微反襯高麗之崛起,流露出對高麗文化之高度自豪及與宋朝並駕齊驅於「中華」之熱切願景。
既有古代東亞國際關係史之研究,雖成果纍纍,卻多聚焦於漢唐或明清之世,而對於10至14世紀遼宋金元這一關鍵時期之探討,則顯薄弱。然基於漢唐或明清「經驗」所構建之「冊封體制」、「朝貢體系」等理論框架,於宋遼金元時期東亞之世,難免陷入困境,難以足履相適。彼時,遼、宋、金、元等政權踵續爭雄中原,華夷變態,風雲莫測,中原與半島雙方關係,亦隨之呈現出多樣化之特質。漢唐以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之「冊封體制」漸趨瓦解,而遼、金、元等遊牧、漁獵民族政權,則相繼對其進行重塑,其影響深遠,延及明清兩代。故深剖彼時東亞國際關係史,對於檢視並完善現有理論體系,具有不可或缺之重要價值。
時至今日,朝鮮半島仍是各方利害交錯制衡、危機一觸即發之敏感地帶。儘管當前東亞國際格局與千年之前高麗時代相比更為錯綜複雜,相關國家之實力與地位亦已今非昔比,但彼時高麗王朝所展現之生存智慧與外交策略,仍具有強烈之現實意義。高麗外交史是朝鮮半島史乃至東亞史之重要篇章,其為理解與探究古代東亞國際關係提供了珍貴實例,亦為現代國家處理類似複雜問題提供了歷史鏡鑒。
對吾人而言,朝鮮半島亦熟亦陌,吾人往往習慣於居高臨下俯視之,這無益於對其進行客觀認識,亦不利於藉此反思己身。鑒於高麗之戰略地位,宋人曾對其傾注熱情,撰有《雞林志》、《雞林類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等專書。今年適逢徐兢出使高麗歸來撰成《圖經》九百週年之際,期望《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之譯介,能夠重新激發中文學界對高麗乃至整個朝鮮半島之興趣與關注。
以上隨感雜談,不過是對前賢思想之引述,不敢妄稱有獨到之見。是為序。
李廷青
2024年12月於南國中山大學
中文版序二
外交史這一領域,旨在探究在歷史的關鍵場景中,各國如何判斷和營造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如何解決國家危機或敏感外交事件。另外,闡明國家如何與外部世界交流,積累國家財富並追求繁榮,這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東北亞歷史財團以「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為叢書主題,從2018年至2019年先後出版系列著作,包括古代篇、高麗篇、朝鮮篇和近代篇。鑒於近來中國學界的高麗史相關研究如火如荼,我們決定從中先將高麗篇譯成中文出版發行。
本書探明了高麗時代外交史的一大特性,即靈活應對國際局勢變化並展開多方外交。同時,本書也綜合考察了當時東亞各國在外交政策上緊密相連的部分。
「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叢書堅持將韓國的對外關係和外交歷史置於同一脈絡的原則,同時也尊重每個執筆者的學術立場。我們認為,根據研究者個人的問題意識和史料闡釋,百花齊放、各抒己見也是很必要。因此,書中可能會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主題和爭議焦點。
藉本書出版之際,我們期待在中國也能針對韓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展開一場真摯的「學術性」討論。尤其希望這能成為開創未來的年輕人深刻反思東亞歷史經驗的一次契機。
東北亞歷史財團理事長
朴枝香
2024年8月
總序
「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叢書出版的學術意義
外交史並不是單純的「外交歷史」,而是一個通過國內外主要事件所積累的認識和經驗的寶庫。國際政治的現實並不存在於抽象的狀態中,而是由國家在多歧的國際環境和對外關係下所選擇並實踐的外交行為建構而成的。這說明,如果不事先深入瞭解對外關係和外交史的背景和脈絡,國際政治研究就不可能擁有堅實的基礎。我們今天用來解說國際政治現象的主要概念,無一例外都基於西歐的特殊歷史經驗,並通過其解釋和概念化構建而成。從這一點來看,此次出版的「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叢書,其意義在於從我們的視角將我們歷史上出現過的史實和行為系統化,從而建立韓國國際政治學發展的新基礎。
毫無疑問,所有國家的外交政策都以追求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然而,就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功能而言,強國和弱國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外交史所具有的意義也不可能相同。對於韓國來說,外交史是韓國人的歷史生活向外呈現的一種記錄。但比這更重要的事實是,它也是我們民族面對國際環境所進行的挑戰和鬥爭的記錄。從這個意義而言,將韓國外交史與國內政治史區分開來或單純地將其作為韓國史的一個領域來處理,這可能會有歪曲整個韓國歷史的危險。這是因為,為了全面瞭解韓國歷史發展時的國際環境和結構以及政治選擇等內容,外交史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
韓國歷史是在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的緊密聯動下發展而來的。對內,被地域隔開的多個集團通過鬥爭和妥協形成並維持了國家形態;對外,與中國和日本——他們對朝鮮半島從未放棄過戰略性關注——鬥爭的歷史貫穿其中。數千年來,韓國在東亞這一歷史空間中,與中國、日本等國時而矛盾,時而共生,不斷成長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韓國外交史不僅包括韓民族,還包括其與周邊勢力的複雜關係。
韓國外交史以正確解釋韓國特性為任務,後者在各個時代可能存在不同表現;同時,它的研究對象包括東亞國際關係中的力量關係(從今天的觀點來說,是規制和調整對外關係的國際制度和國際法要素)、為解決國家危機或特定交涉事件作出貢獻的人物活動,以及經濟、文化交流等內容。特別是對於韓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探索,不僅擴大了韓國外交史研究的外延,還彌補了史料的不足,展現了韓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平等交往的樣貌。從這一點來看,韓國外交史可以說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另外,如果在韓國外交史上只突出國際政治層面,那麼韓國只能淪為強國政策所適用的「對象」而已。強國的政策——即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支配抑或日本的擴張侵略抑或俄羅斯的進軍等——以及韓國方面的相關應對,都再次反饋(feedback)到韓國國內的政治進程中,並產生直接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在應對中國這一強大勢力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被動性,抑或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對外國史料的一種依賴,這些都大大制約着韓國外交史的研究。因此,為了克服上述問題,有必要牢記一個事實:在韓國的外交史研究中,如何客觀地分析和敘述這些看似消極的各個方面,即確立「我們的」視角,是非常重要的。
當今,「外交史」尤其是「韓國外交史」,在韓國國內大學中的地位並不穩固。史學系側重於國內歷史,沒有系統地教授對外關係史或外交史;而在政治外交系,外交史也僅作為國際政治的邊緣科目勉強維繫命脈。或許其最大的原因在於,人們錯誤地認為國際關係是以強國為中心發展的,而韓國未能主動參與其中。韓國只是強國之間競爭和討價還價的對象,這種被動思維從根本上阻礙了人們去反思韓國曾在國際關係中主動選擇與開拓的那段歷史。從這一點來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由於這種情況,一直以來很難找到合適的教材來講授「韓國外交史」。在大學的教學科目中,大部分都是不加批判地引進西方所創立的學術體系進行教學,但就韓國外交史這一領域而言,很難直接翻譯國外教科書來進行教學。因為美國的東亞外交史所敘述的不過是他們的東亞政策,而日本人開創的東洋外交史大體上也只是從日本的擴張和中日競爭的觀點上來展開。
這次由東北亞歷史財團出版的「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叢書正是為了解決上述學術問題而邁出的第一步,從這一點來看具有重大意義。本書將韓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分為古代、高麗、朝鮮、近代等四篇進行敘述,旨在究明各時期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半島內部政治的變化和發展情況。特別要指出的是,包括國際政治學以及韓國史、日本史、中國史等多個領域在內的五十多名權威研究者共同參與了本書的撰寫。動員如此龐大規模的執筆團隊編撰韓國外交通史,這在我國學界是史無前例的。因此,本書所提出的論點和問題有望為今後樹立韓國外交史領域的學術標杆作出巨大貢獻。衷心感謝東北亞歷史財團贊助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同時也向贊同本書的編撰宗旨並對我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進行重新闡釋的執筆者們深表謝意。
東北亞歷史財團
韓國外交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
具大烈
2018年12月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鎮漢 主編的圖書 |
 |
$ 529 | 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
作者:李鎮漢 主編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4-09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李鎮
李鎮,字安□,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民籍,明朝政治人物。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
《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將韓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分為古代、高麗、朝鮮、近代等四篇進行敘述,旨在究明各時期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半島內部政治的變化和發展情況。
本書《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試圖闡述高麗的傳統外交活動是如何讓高麗這一「國家地位」能在周邊國家獲得高於實際的評價和威望。本書將高麗的外交史劃分為十個主題,除高麗外交史總論,亦根據不同時期分為五代十國、契丹(遼)、宋朝、金朝、蒙古和元、明朝等與高麗建立朝貢冊封關係的國家,以及日本、女真等外交地位與高麗對等或稍低的周邊國家及民族。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李鎮漢
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史學系教授、韓國海洋史學會會長、韓國歷史研究會前會長,研究方向為高麗時代史、中韓關係史、海洋史等,著有《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高麗時代貿易與海洋》、《高麗時代對外交流史研究》、《高麗前期官職與俸祿關係研究》等。
作者序
《高麗篇》序
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
918年王建驅逐弓裔,高麗由此建立,並存續至1392年。在此期間,中國政權更替頻繁。10世紀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和十國。916年契丹建立後,逐漸成為東北亞的軍事強國。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隨後征服了長江以南地區的多個政權,但在整體軍事實力上較契丹而言並不佔優勢。12世紀初金朝建立,宋金聯合滅掉契丹,然而金朝勢力越來越強大,佔據了比原來契丹更多的華北地區。13世紀初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先後滅掉了金和宋,統一了中國,成為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帝國。14世紀後期...
重新審視高麗時代的外交
918年王建驅逐弓裔,高麗由此建立,並存續至1392年。在此期間,中國政權更替頻繁。10世紀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和十國。916年契丹建立後,逐漸成為東北亞的軍事強國。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隨後征服了長江以南地區的多個政權,但在整體軍事實力上較契丹而言並不佔優勢。12世紀初金朝建立,宋金聯合滅掉契丹,然而金朝勢力越來越強大,佔據了比原來契丹更多的華北地區。13世紀初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先後滅掉了金和宋,統一了中國,成為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帝國。14世紀後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高麗時代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總論 001
一、高麗時代的外交 002
二、國際局勢的變化 003
三、外交關係的演變 012
四、外交史的歷史特徵 019
五、外交活動的諸面貌 025
六、今後的研究課題 029
參考文獻 031
第二章
高麗初期與中國的外交 037
一、太祖時期與中國的外交 038
二、惠宗—光宗時期與中國的外交 047
三、高麗初期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048
四、高麗初期與渤海、契丹的外交 051
參考文獻 055
第三章
高麗與契丹(遼)的外交 059
一、高麗初期與契丹的衝突 060
二、高麗與契丹的戰爭 062
三、兩國之間圍繞保州與榷場的衝突 0...
高麗時代對外關係與外交史總論 001
一、高麗時代的外交 002
二、國際局勢的變化 003
三、外交關係的演變 012
四、外交史的歷史特徵 019
五、外交活動的諸面貌 025
六、今後的研究課題 029
參考文獻 031
第二章
高麗初期與中國的外交 037
一、太祖時期與中國的外交 038
二、惠宗—光宗時期與中國的外交 047
三、高麗初期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048
四、高麗初期與渤海、契丹的外交 051
參考文獻 055
第三章
高麗與契丹(遼)的外交 059
一、高麗初期與契丹的衝突 060
二、高麗與契丹的戰爭 062
三、兩國之間圍繞保州與榷場的衝突 0...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