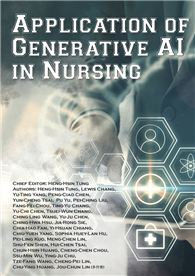我們應該已經出生
在無名的世界角落
像草沒有深根
在季節裡變得翠綠
隨時準備
──不受到任何創傷──
被連根拔起。
阿爾巴尼亞文使用的地區廣泛,分布於阿爾巴尼亞共和國、科索沃、馬其頓、希臘及部分東南歐國家,例如蒙特內格羅和義大利的阿爾巴尼亞族。
詩源於不同文化脈絡和傳統,湧現著各種不同的概念與觀點,也就使得詩這一文體,能夠從封閉文學體系之中被拯救出來的緣故。
《阿爾巴尼亞詩選 Anthology of Albanian Poetry》是台灣第一本以阿爾巴尼亞現代詩為主題的漢譯詩集,收錄20位以阿爾巴尼亞文寫作的當代詩人,從1944年出生的哲夫.施啟洛.迪.馬西霍(Zef Skiro Di Maxho),到1986年出生的曼卓拉.布拉哈吉(Manjola Brahaj),跨度超過四十年,擷取經典作品共計100首,呈現阿爾巴尼亞文學的歷史層面。
書中特別選入被尊稱為19世紀阿爾巴尼亞國家覺醒的重要人物之一,奈姆.弗拉謝里(Naim Frashëri)的作品,馬其頓以其名的奈姆日(Ditët e Naimit)國際詩歌節已舉辦二十餘年,本書譯者李魁賢更於2016年獲頒奈姆.弗拉謝里文學獎,是促成國際詩歌交流的莫大肯定。
本書特色
✽本書是台灣第一本以阿爾巴尼亞現代詩為主題的漢譯詩集,收錄20位以阿爾巴尼亞文寫作的當代詩人,擷取經典作品共計100首,呈現阿爾巴尼亞文學的歷史層面。
✽著名詩人亦是本書譯者李魁賢,獲頒2016年奈姆•弗拉舍里文學獎,賦予桂冠詩人榮銜,並聘為詩歌節榮譽委員;2017年國家文藝獎得主。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李魁賢〈Lee Kuei-shien〉的圖書 |
 |
$ 182 ~ 260 | 阿爾巴尼亞詩選 Anthology of Albanian Poetry
作者:[阿爾巴尼亞]塞普‧艾默拉甫(Shaip Emërllahu)編著 / 譯者:李魁賢(Lee Kuei-shien)譯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8-06-20 語言:繁體書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李魁賢
李魁賢臺灣詩人、文化評論人、翻譯家。1953年開始發表詩作 。現任世界詩人運動組織副會長。曾任台灣筆會會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詩被譯成各種語文在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印度、希臘、美國、西班牙、巴西、蒙古、俄羅斯、立陶宛、古巴、智利、尼加拉瓜、孟加拉、馬其頓、土耳其、波蘭、塞爾維亞、葡萄牙、馬來西亞、義大利、阿爾巴尼亞,等國發表。在2001年、2003年、2006年三度獲印度國際詩人協會推薦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共同發起人。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阿爾巴尼亞詩選 Anthology of Albanian Poetry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賽普.艾默拉甫(Shaip Emërllahu)
阿爾巴尼亞人,曾擔任報紙《Flaka》記者和文化編輯,現為泰托沃「奈姆日」(Ditet e Naimi)國際詩歌節主席,榮獲多項國內和國際文學獎。出版詩集有《歲月洗禮》、《破碎計畫》等,詩作被譯成法文、英文、希伯來文、西班牙文等多國語言,其詩集《人生襤褸》李魁賢漢譯,由秀威於2017年2月出版。
譯者簡介
李魁賢(Lee Kuei-shien)
從事詩創作和翻譯逾半世紀,創作超過千首、翻譯五千首,獲國家文藝獎、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評論獎、賴和文學獎、榮後台灣詩人獎、台灣新文學貢獻獎、行政院文化獎、吳三連獎文學獎、真理大學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另獲韓國、印度、蒙古、美國等頒予多項國際詩獎。
賽普.艾默拉甫(Shaip Emërllahu)
阿爾巴尼亞人,曾擔任報紙《Flaka》記者和文化編輯,現為泰托沃「奈姆日」(Ditet e Naimi)國際詩歌節主席,榮獲多項國內和國際文學獎。出版詩集有《歲月洗禮》、《破碎計畫》等,詩作被譯成法文、英文、希伯來文、西班牙文等多國語言,其詩集《人生襤褸》李魁賢漢譯,由秀威於2017年2月出版。
譯者簡介
李魁賢(Lee Kuei-shien)
從事詩創作和翻譯逾半世紀,創作超過千首、翻譯五千首,獲國家文藝獎、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評論獎、賴和文學獎、榮後台灣詩人獎、台灣新文學貢獻獎、行政院文化獎、吳三連獎文學獎、真理大學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另獲韓國、印度、蒙古、美國等頒予多項國際詩獎。
目錄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衣梅爾.齊拉庫(Ymer Çiraku)
奈姆.弗拉謝里 Naim Frashëri
哲夫.施啟洛.迪.馬西霍 Zef Skiro Di Maxho
馬里奧.貝利濟 Mario Bellizzi
巴斯理.查普立基 Basri Çapriqi
賀甫德特.巴吉拉吉 Xhevdet Bajraj
穆傑.布契帕帕吉 Mujë Buçpapaj
塞普.艾默拉甫 Shaip Emërllahu
安東.郭吉傑志 Anton Gojçaj
伊恕夫.謝里費 Isuf Sherifi
奈梅.貝基拉吉 Naime Beqiraj
薩拉吉丁.塞立夫 Saljdin Salihu
施里克.莉麗雅.布倫巴哈 Silke Liria Blumbach
伊萊爾.查吉蜜 Ilire Zajmi
歐琳碧.魏拉吉 Olimbi Velaj
帕立德.特非力齊 Parid Teferiçi
恩督.烏喀吉 Ndue Ukaj
傑頓.凱爾門迪 Jeton Kelmendi
雷笛雅.杜汐 Ledia Dushi
雅麗莎.魏拉吉 Alisa Velaj
貝爾福久列.闊瑟 Belfjore Qose
曼卓拉.布拉哈吉 Manjola Brahaj
奈姆.弗拉謝里 Naim Frashëri
哲夫.施啟洛.迪.馬西霍 Zef Skiro Di Maxho
馬里奧.貝利濟 Mario Bellizzi
巴斯理.查普立基 Basri Çapriqi
賀甫德特.巴吉拉吉 Xhevdet Bajraj
穆傑.布契帕帕吉 Mujë Buçpapaj
塞普.艾默拉甫 Shaip Emërllahu
安東.郭吉傑志 Anton Gojçaj
伊恕夫.謝里費 Isuf Sherifi
奈梅.貝基拉吉 Naime Beqiraj
薩拉吉丁.塞立夫 Saljdin Salihu
施里克.莉麗雅.布倫巴哈 Silke Liria Blumbach
伊萊爾.查吉蜜 Ilire Zajmi
歐琳碧.魏拉吉 Olimbi Velaj
帕立德.特非力齊 Parid Teferiçi
恩督.烏喀吉 Ndue Ukaj
傑頓.凱爾門迪 Jeton Kelmendi
雷笛雅.杜汐 Ledia Dushi
雅麗莎.魏拉吉 Alisa Velaj
貝爾福久列.闊瑟 Belfjore Qose
曼卓拉.布拉哈吉 Manjola Brahaj
序
序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
衣梅爾.齊拉庫(Ymer Çiraku)
阿爾巴尼亞當代詩是阿爾巴尼亞五百年詩史信而有徵的片段,從麥特(Mat)地區白石(Guri i Bardhë)的第一位作家彼德.布迪(Pjetër Budi)算起,經普里茲倫(Prizre)附近的哈斯(Has)地區彼德.博格達尼(Pjetër Bogdani),接著是奈姆.弗拉舍里(Naim Frashëri)、拉斯古什.波拉代奇(Lasgush Poradeci)、阿里.波多林亞(Ali Podrimja)等人,直到今日。所以這是不斷延續的文學之流,已經歷過如今公認傳統的形成,同時也影響到不斷再創造的新模式。這種傾向以此方式見證詩一貫的再創造,也是任何嚴肅文學的至高使命。
談論當代詩並加以論斷,實非易事。困難在於需費龐大作業,並有各種新的詩風和趨勢,從觀念上以及所顯示正式結構觀點看,很少達到迄今未明,甚至過度論述的實驗水準。但涵蓋所有世代的最大困難,在於詩文本賦予的特殊性,以結構而言,文字打破模糊含義的微妙,超越一般用法。正如阿爾巴尼亞詩藝賢德大師、古典詩人拉斯古什.波拉代奇所表達:「……詩創作是整體難以言宣的形而上學……詩具有驚奇、和諧及無窮美麗……」,甚至不由得詩人自己解釋。
從分類觀點,以「當代詩」為特徵之創造力,在編年意義上,正是從90年代起,提供讀者的詩創造力,以迄於今。就社會政治脈絡而言,在此大約三十年間,阿爾巴尼亞世界有頗多發展和累積社會政治挑戰,當然不止是詩的時代,而且詩本身也受到這些情況的強烈影響,藉此適應其特別機制。這些關係已經引起且見證相對應問題集合,還有寫作及其接受和詮釋的模式痕跡。
特別是,顧及這個時期是顛覆阿爾巴尼亞人際政治文化隔閡的好時機,在當代溝通整合過程中,阿爾巴尼亞詩的崛起具體可見,作者之間有新的自由接觸,以更為美感方式面臨「詩飛馬」的歡喜競賽。這個競賽節奏,儘管沒有噪音和喝彩,卻和每個「詩騎士」儘量要與其創作明星,在探索和追求方向有所不同的意圖相關,亦即邁步走上《新的詩路程》,正如著名詩人阿戈里(D. Agolli)此書名,對此結構體的委婉論述。
今天,阿爾巴尼亞詩來自以阿爾巴尼亞語寫作的所有地區,從完全或部分說阿爾巴尼亞語的國家(阿爾巴尼亞、科索沃、馬其頓、蒙特內哥羅或稱黑山、塞爾維亞),到散居地(遍布歐洲及其他各國),以迄義大利的著名阿爾貝勒斯(Arbereshs)歷史性社區。如今,這些不尋常邊界已不復存在,不再阻礙「阿爾巴尼亞詩匯集」的相互交流。
唯一現存邊界,比喻來說,與其「品質的代表性水準」有關。品質現在是其唯一全能屬性,隨後也用來界定和決定其交流水準。然而,事實上這種詩源於不同文化脈絡和傳統,湧現和投射各種概念和文體觀點為特徵的輪廓,也就是這種詩何以能從封閉文學體系所造成萎縮單調的危機中,拯救出來之緣故。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正好是目前在歐洲和全球詩流通的文學運動圈之一部分,跟隨他人也被他人跟隨。這是名望和價值的象徵,現在可與其他語言的創造力相比,作者沒有在自卑感的重壓下,感受到被輕視。因此,目前可明白看出阿爾巴尼亞詩,不可動搖地尋求新形式傾向,即遺傳精英意識,不在追求而是創造讀者。正如所說,可知在語言學上的激發精神,釋出詩意「寡言」字義的原子能量。
因此,也呈現作者(於此指詩人)受忽視地位不由得被邊緣化,不太像以前提出理念的傳教士,而是嘗試用自己文本,卻幾乎不涉及問題的直接社會或歷史情結。凡此皆反映出為促進詩藝自足/自主的意圖。可以看出相當可觀存在所謂簡約美學,即出版短小、簡略和零碎的文本,趨向於互文性拼貼模式。如果我們把著名阿爾巴尼亞史詩《英雄週期》的有名詩句「陽光強烈而溫暖少……」反轉,我們可以旁敲側擊為:「……詩歌光少,大為溫暖……」。意即,這種詩萌發並傳播其能量的模式,並非在外表宣告理念的潛在層面,而是在內部釋放藝術語言之能力和潛力的能量水準。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接受各種時代和個人的創造性貢獻,包括最受肯定和最年輕的詩人。20世紀90年代以後,法托斯.阿拉丕(Fatos Arapi)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書,發表許多文學評論,指出「這種詩性創造力隱喻的原始且動人軌跡」,也把透過詩人感傷的旅行記號歸類為「重大感傷的象徵論」。
這項詩的軸線保留冥想和不可思議的沉思,他甚至被認定為隨著國家劇本演出抗議的詩人,與燈光的悲傷傾出越過無盡海平面般的細節交揉在一起。海就如此存在於他的詩裡,以至於著名詩人阿里.波德里亞(Ali Podrimja)將這種存在特定為多維的、精打細算的象徵主義,成為「元神話」神祕出現。
對於阿戈里亦然,90年代以後,藉當前「美學昇華」,被烏托邦和謊言政治神話失望的疊加作用,展現富強創造力,如同「雙頭阿戈里交響樂」的第二樂章。先是完全屈服於藝術秩序,接著詩人開始被人類處境的存在動機緊密宰制,以全影燈投射,同時滲透到他的神祕地帶,作為無限複雜的存在。
在當代詩歌中,我們已見證過一種外型象徵論,以哲學性、反映「城市日常生活」、詳細繁複且具有啟發性的語言、藉宇宙觀點的全稱意象之冥想詩模式,接續上場。這些模式中有無數創作已經流傳,其中許多確實具備進入選集資格,甚至超過阿爾巴尼亞語言的文學區域。我們擁有主觀品味的權利,但也感嘆不可能接觸到如今正在全球交流和受到注意的所有阿爾巴尼亞人之創造力,所以在此提示對高度藝術成果具有貢獻的一份詩人名單。
除了早期已能夠自我肯定的詩人,例如A. Shkreli, A. Podrimja, Rr. Dedaj, Xh. Spahiu, S. Hamiti, M. Zeqo, S. Bejko, B. Londo, B. Musliu, A. Vinca, R. Musliu, K. Petriti, B. Çapriqi, M. Krasniqi, A. Konushevci等之外,還有許多如今正在建立個人聲望的其他詩人,例如V. Zhiti, A. Tufa, Sh. Emërllahu, M. Bellizzi, N. Ukaj, A. Gojçaj, A. Apolloni, M. Bupapaj, S. Salihu, J. Kelmendi等。
在阿爾巴尼亞詩裡,我們如今也有甚具天賦的女詩人集會廳,她們不但不若以前那麼罕見,而且在概念和風格方面都有傑出成就。其中,我們想到的詩人有L. Lleshanaku, I. Zajmi, R. Petro, L. Dushi, O. Velaj, S. Blumbach, M. Braho, D. Dabishevci, B. Cose,以迄Kate Xukaro,後者維持上述阿爾貝勒斯詩的已知傳統於不墜。
她們當然雅不欲將自己局限於女性主義問題領域,而已成功克服這個圈子,給讀者帶來不受非文學習俗約束的詩。
「讓詩人在歌中燃燒……」,Din Mehmeti的這種詩風以集中方式賦予詩,和當代詩人的任務。在「文學和詩的自由共和國」自治權內,正顯示他使命感的自足。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
衣梅爾.齊拉庫(Ymer Çiraku)
阿爾巴尼亞當代詩是阿爾巴尼亞五百年詩史信而有徵的片段,從麥特(Mat)地區白石(Guri i Bardhë)的第一位作家彼德.布迪(Pjetër Budi)算起,經普里茲倫(Prizre)附近的哈斯(Has)地區彼德.博格達尼(Pjetër Bogdani),接著是奈姆.弗拉舍里(Naim Frashëri)、拉斯古什.波拉代奇(Lasgush Poradeci)、阿里.波多林亞(Ali Podrimja)等人,直到今日。所以這是不斷延續的文學之流,已經歷過如今公認傳統的形成,同時也影響到不斷再創造的新模式。這種傾向以此方式見證詩一貫的再創造,也是任何嚴肅文學的至高使命。
談論當代詩並加以論斷,實非易事。困難在於需費龐大作業,並有各種新的詩風和趨勢,從觀念上以及所顯示正式結構觀點看,很少達到迄今未明,甚至過度論述的實驗水準。但涵蓋所有世代的最大困難,在於詩文本賦予的特殊性,以結構而言,文字打破模糊含義的微妙,超越一般用法。正如阿爾巴尼亞詩藝賢德大師、古典詩人拉斯古什.波拉代奇所表達:「……詩創作是整體難以言宣的形而上學……詩具有驚奇、和諧及無窮美麗……」,甚至不由得詩人自己解釋。
從分類觀點,以「當代詩」為特徵之創造力,在編年意義上,正是從90年代起,提供讀者的詩創造力,以迄於今。就社會政治脈絡而言,在此大約三十年間,阿爾巴尼亞世界有頗多發展和累積社會政治挑戰,當然不止是詩的時代,而且詩本身也受到這些情況的強烈影響,藉此適應其特別機制。這些關係已經引起且見證相對應問題集合,還有寫作及其接受和詮釋的模式痕跡。
特別是,顧及這個時期是顛覆阿爾巴尼亞人際政治文化隔閡的好時機,在當代溝通整合過程中,阿爾巴尼亞詩的崛起具體可見,作者之間有新的自由接觸,以更為美感方式面臨「詩飛馬」的歡喜競賽。這個競賽節奏,儘管沒有噪音和喝彩,卻和每個「詩騎士」儘量要與其創作明星,在探索和追求方向有所不同的意圖相關,亦即邁步走上《新的詩路程》,正如著名詩人阿戈里(D. Agolli)此書名,對此結構體的委婉論述。
今天,阿爾巴尼亞詩來自以阿爾巴尼亞語寫作的所有地區,從完全或部分說阿爾巴尼亞語的國家(阿爾巴尼亞、科索沃、馬其頓、蒙特內哥羅或稱黑山、塞爾維亞),到散居地(遍布歐洲及其他各國),以迄義大利的著名阿爾貝勒斯(Arbereshs)歷史性社區。如今,這些不尋常邊界已不復存在,不再阻礙「阿爾巴尼亞詩匯集」的相互交流。
唯一現存邊界,比喻來說,與其「品質的代表性水準」有關。品質現在是其唯一全能屬性,隨後也用來界定和決定其交流水準。然而,事實上這種詩源於不同文化脈絡和傳統,湧現和投射各種概念和文體觀點為特徵的輪廓,也就是這種詩何以能從封閉文學體系所造成萎縮單調的危機中,拯救出來之緣故。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正好是目前在歐洲和全球詩流通的文學運動圈之一部分,跟隨他人也被他人跟隨。這是名望和價值的象徵,現在可與其他語言的創造力相比,作者沒有在自卑感的重壓下,感受到被輕視。因此,目前可明白看出阿爾巴尼亞詩,不可動搖地尋求新形式傾向,即遺傳精英意識,不在追求而是創造讀者。正如所說,可知在語言學上的激發精神,釋出詩意「寡言」字義的原子能量。
因此,也呈現作者(於此指詩人)受忽視地位不由得被邊緣化,不太像以前提出理念的傳教士,而是嘗試用自己文本,卻幾乎不涉及問題的直接社會或歷史情結。凡此皆反映出為促進詩藝自足/自主的意圖。可以看出相當可觀存在所謂簡約美學,即出版短小、簡略和零碎的文本,趨向於互文性拼貼模式。如果我們把著名阿爾巴尼亞史詩《英雄週期》的有名詩句「陽光強烈而溫暖少……」反轉,我們可以旁敲側擊為:「……詩歌光少,大為溫暖……」。意即,這種詩萌發並傳播其能量的模式,並非在外表宣告理念的潛在層面,而是在內部釋放藝術語言之能力和潛力的能量水準。
當代阿爾巴尼亞詩接受各種時代和個人的創造性貢獻,包括最受肯定和最年輕的詩人。20世紀90年代以後,法托斯.阿拉丕(Fatos Arapi)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書,發表許多文學評論,指出「這種詩性創造力隱喻的原始且動人軌跡」,也把透過詩人感傷的旅行記號歸類為「重大感傷的象徵論」。
這項詩的軸線保留冥想和不可思議的沉思,他甚至被認定為隨著國家劇本演出抗議的詩人,與燈光的悲傷傾出越過無盡海平面般的細節交揉在一起。海就如此存在於他的詩裡,以至於著名詩人阿里.波德里亞(Ali Podrimja)將這種存在特定為多維的、精打細算的象徵主義,成為「元神話」神祕出現。
對於阿戈里亦然,90年代以後,藉當前「美學昇華」,被烏托邦和謊言政治神話失望的疊加作用,展現富強創造力,如同「雙頭阿戈里交響樂」的第二樂章。先是完全屈服於藝術秩序,接著詩人開始被人類處境的存在動機緊密宰制,以全影燈投射,同時滲透到他的神祕地帶,作為無限複雜的存在。
在當代詩歌中,我們已見證過一種外型象徵論,以哲學性、反映「城市日常生活」、詳細繁複且具有啟發性的語言、藉宇宙觀點的全稱意象之冥想詩模式,接續上場。這些模式中有無數創作已經流傳,其中許多確實具備進入選集資格,甚至超過阿爾巴尼亞語言的文學區域。我們擁有主觀品味的權利,但也感嘆不可能接觸到如今正在全球交流和受到注意的所有阿爾巴尼亞人之創造力,所以在此提示對高度藝術成果具有貢獻的一份詩人名單。
除了早期已能夠自我肯定的詩人,例如A. Shkreli, A. Podrimja, Rr. Dedaj, Xh. Spahiu, S. Hamiti, M. Zeqo, S. Bejko, B. Londo, B. Musliu, A. Vinca, R. Musliu, K. Petriti, B. Çapriqi, M. Krasniqi, A. Konushevci等之外,還有許多如今正在建立個人聲望的其他詩人,例如V. Zhiti, A. Tufa, Sh. Emërllahu, M. Bellizzi, N. Ukaj, A. Gojçaj, A. Apolloni, M. Bupapaj, S. Salihu, J. Kelmendi等。
在阿爾巴尼亞詩裡,我們如今也有甚具天賦的女詩人集會廳,她們不但不若以前那麼罕見,而且在概念和風格方面都有傑出成就。其中,我們想到的詩人有L. Lleshanaku, I. Zajmi, R. Petro, L. Dushi, O. Velaj, S. Blumbach, M. Braho, D. Dabishevci, B. Cose,以迄Kate Xukaro,後者維持上述阿爾貝勒斯詩的已知傳統於不墜。
她們當然雅不欲將自己局限於女性主義問題領域,而已成功克服這個圈子,給讀者帶來不受非文學習俗約束的詩。
「讓詩人在歌中燃燒……」,Din Mehmeti的這種詩風以集中方式賦予詩,和當代詩人的任務。在「文學和詩的自由共和國」自治權內,正顯示他使命感的自足。
李魁賢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