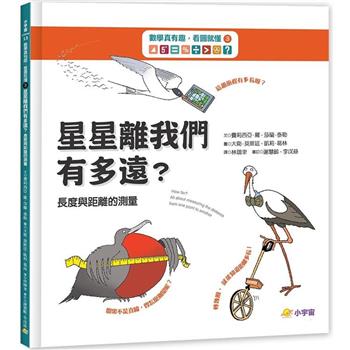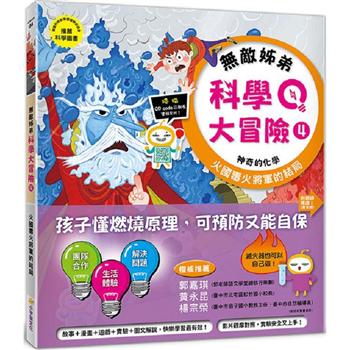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對Pangcah(阿美族)來說,radiw(歌謠)是活著的歷史,串起了人、動物、土地之間相互勞動與滋養的關係;radiw就是文學,代替文字成為傳達情感的載體。眾人傳唱歌謠,一代傳一代,從一個山頭唱到另一邊的海洋,隨著部落與人群的移動遷徙,歌也如同生物一樣,隨環境交融、變異與繁衍。
本書透過曾經採集阿美族歌謠的林信來,與當代吟唱母語歌謠的創作樂人阿洛之間的父女對話,演繹出極其豐盛的阿美族歌謠故事,以及林信來的生命行腳。
本書特色
1.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得主阿洛.卡力亭.巴奇辣,透過與父親林信來的對話,娓娓道出歌謠在Pangcah阿美族的生活、歷史與文化中的重要性與意義。
2.從生活中的歌謠理解Pangcah阿美族,既親近且容易解讀。
專文推薦
這是阿美族歌謠擺脫學術框定,回到真實的生活情境,為族人悲喜而自在歌詠的面貌。――Pasuya Poiconx浦忠成(前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現任監察委員)
這不只是阿洛父女採集過往歌謠的長期尋根之路,恐怕也是我們這些外來旁觀者,重新獲得機會,站到一個更合宜的視角,認真凝視下一個花東海岸。――劉克襄(作家,現任中央社董事長)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林信來的圖書 |
 |
$ 240 ~ 342 | 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作者:Calaw Mayaw(林信來)/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口述;藍雨楨/撰述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1-22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口述: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博士,電視節目製作人、導演、演員、創作歌手、主持人,長年耕耘原住民族社會文化議題。音樂專輯《Cidal Fulad太陽月亮》(2013)、《Sasela’an氣息》(2020)入圍多項金曲獎;2015年電影《太陽的孩子》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2016年電視節目《吹過島嶼的歌》獲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2019年主編書籍《吹過島嶼的歌》。只要太平洋的海浪不斷拍打,我們的歌就會一直唱下去。
口述:Calaw Mayaw 林信來
出生於花蓮玉里,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1967年參與民歌採集運動之東隊行程。自1970年代起,長期投入阿美族歌謠採集與研究,亦曾參與中研院、文建會委託之阿美族音樂調查研究計畫。著有《Banzah A Ladiu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1982)、《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1985)、〈南王聚落之音樂〉收錄於《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1987)、《宜灣阿美族豐年祭歌謠》(1988)。
撰述:藍雨楨
宜蘭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長期參與跨國藝術計劃的策展製作。在印尼田野研究期間,結下與南島的深厚緣分,希望以人類學觀點,持續拓展更多元的文化議題。近年與友人共同經營Trans/Voices Project,關注台灣和印尼跨國移工的藝文實踐,合著出版《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2021》。目前從事寫作、翻譯與藝文策展。
信箱:nautsing@iclould.com。
口述: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博士,電視節目製作人、導演、演員、創作歌手、主持人,長年耕耘原住民族社會文化議題。音樂專輯《Cidal Fulad太陽月亮》(2013)、《Sasela’an氣息》(2020)入圍多項金曲獎;2015年電影《太陽的孩子》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2016年電視節目《吹過島嶼的歌》獲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2019年主編書籍《吹過島嶼的歌》。只要太平洋的海浪不斷拍打,我們的歌就會一直唱下去。
口述:Calaw Mayaw 林信來
出生於花蓮玉里,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1967年參與民歌採集運動之東隊行程。自1970年代起,長期投入阿美族歌謠採集與研究,亦曾參與中研院、文建會委託之阿美族音樂調查研究計畫。著有《Banzah A Ladiu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1982)、《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1985)、〈南王聚落之音樂〉收錄於《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1987)、《宜灣阿美族豐年祭歌謠》(1988)。
撰述:藍雨楨
宜蘭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長期參與跨國藝術計劃的策展製作。在印尼田野研究期間,結下與南島的深厚緣分,希望以人類學觀點,持續拓展更多元的文化議題。近年與友人共同經營Trans/Voices Project,關注台灣和印尼跨國移工的藝文實踐,合著出版《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2021》。目前從事寫作、翻譯與藝文策展。
信箱:nautsing@iclould.com。
目錄
推薦序 在艱苦中堅持傳續祖先歌藝的孤獨身影 Pasuya Poiconx 浦忠成
推薦序 在Radiw中,成為真正的人 劉克襄
前言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場景
輯一、重返歷史
一、擁有三個名字的男孩
二、音樂路
三、我們需不需要自己的音樂?
四、回看民歌採集
五、尋找歌的烏托邦
六、東隊日記
七、土地上的採集者
筆記:原住民歌謠採集簡史
輯二、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一、radiw是什麼?
二、radiw的分類
三、radiw是一種說故事的行動(mikimad)
四、radiw是神靈的路——神話時間與集體記憶
五、一首很長很長的radiw——相聚與團結之歌
六、月亮與太陽——愛戀的radiw
七、地景與集體記憶的radiw
八、當我們完整彼此——mipaliw的radiw
九、Ohaiyan——自由的radiw
十、回顧的radiw
輯三、月亮太陽
一、童年的卡帶
二、重返Takoliyaw
三、老頭目
四、拼貼radiw的想像共同體
五、從逝落到氣息:阿洛的radiw
後記 Calaw mayaw 林信來
推薦序 在Radiw中,成為真正的人 劉克襄
前言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場景
輯一、重返歷史
一、擁有三個名字的男孩
二、音樂路
三、我們需不需要自己的音樂?
四、回看民歌採集
五、尋找歌的烏托邦
六、東隊日記
七、土地上的採集者
筆記:原住民歌謠採集簡史
輯二、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一、radiw是什麼?
二、radiw的分類
三、radiw是一種說故事的行動(mikimad)
四、radiw是神靈的路——神話時間與集體記憶
五、一首很長很長的radiw——相聚與團結之歌
六、月亮與太陽——愛戀的radiw
七、地景與集體記憶的radiw
八、當我們完整彼此——mipaliw的radiw
九、Ohaiyan——自由的radiw
十、回顧的radiw
輯三、月亮太陽
一、童年的卡帶
二、重返Takoliyaw
三、老頭目
四、拼貼radiw的想像共同體
五、從逝落到氣息:阿洛的radiw
後記 Calaw mayaw 林信來
序
推薦序
在艱苦中堅持傳續祖先歌藝的孤獨身影
Pasuya Poiconx 浦忠成
在原住民學術圈子中,偶爾有人會談及,哪一個是最早出國留學、最早取得博士學位、最早在大學任教之類的議題,哪一個是number 1 也常引起興趣。有一位真正最早在大專任教的原住民族籍教師,卻是現在很多青壯學者不認識的,他是Calaw Mayaw 林信來教授。
用「孤獨」形容他孤軍奮鬥的情境,我思考了許久。這不是現在已經擁有接近二百位博士、近千位碩士的原住民族社會可以理解的。他出生於1936 年,年齡相仿的如阿美族黃貴潮、吳明義及排灣族的林天生等,這是日本統治台灣不到十年即將結束的時期,他們都曾在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接受日式教育。二戰結束,新的政權到來,少年立即面臨環境巨大變化,而Calaw Mayaw 卻能快速適應,順利進入花蓮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山地班,開啟一生從事教學的門徑。二十七歲,再考入台灣師大前身的省立台灣師大音樂系,接觸西洋音樂理論與技巧,同時在分別自德國、法國返台推動「民歌採集運動」的史惟亮、許常惠教授的計畫之下,進入部落採集歌謠,這是重要的啟蒙與訓練。師大畢業之後,先在瑞穗國中、玉里高中任教,後來因為專業而受聘到台東師範學院音樂系。
在那樣的年代,不要說「山地同胞」的藝術文化,連「台灣」相關的議題探討都是嚴重的忌諱;但是Calaw Mayaw 在「正規」的教學之外,常常帶著妻兒走入阿美族的部落,以檳榔、米酒與香菸酬謝族人,先後採錄上千首各類歌謠。由這件事看,他是最早進入田野的原住民學者。後來經過整理,寫成《Banzah A Ladiu 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並於1981 年獲得中山文藝獎(顛覆原住民只能被調查、研究的刻板印象)。1988 年,時年五十二歲的林信來考取東京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卻由於經濟、身體的因素無法完成學業,束裝返台。後來教學外積極參與中研院、文建會與省府民政廳調查研究計畫,彙集豐富的Ilisin 資料檔案。這是林教授在學術道路上,孤寂卻又頑強有力的身影。
這本書寫的是Calaw Mayaw 生命的故事,小女兒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跟父親談話中引出老人對於Pangcah 歌謠radiw 的觀點與解說,再藉由Ado 自幼記憶的線索,幫助父親追回許多生命真情的段落,而具有人類學背景的藍雨楨也參與對話,多方蒐集相關資料,補充父女可能遺落的片段,進行必要的梳理,演繹成極其豐盛的阿美族歌謠故事與Calaw Mayaw 生命行腳的註解。這是阿美族歌謠擺脫學術框定,回到真實生活情境,為族人悲喜而自在歌詠的面貌。
學術的大哉問,Naluwan/hohaiyan/hahai 是「虛詞」、「無義」嗎?Calaw Mayaw 說:「我不知道,但是可以唱半天、一天啊!」這誠然就是得魚而忘筌的態度。他是我父親同年代的長者,卻有幸曾經跟他乾杯幾回,笑顏笑語,是一直不曾改變的風度。「山地平地化」和戒嚴的年代,Calaw Mayaw 長期以低調卻詼諧的姿態應對,背後的緣由,其來有自。
這是三個人共同完成的傳記與阿美族歌謠探討專書,只不過運用輕鬆、自在的對話方式進行完整而深入的詮釋,正好貼近Calaw Mayaw 的風格。有幸率先閱讀全文,深為Calaw Mayaw 在艱苦環境中堅持走上探索自身族群歌謠文化的道路而感佩,而Ado 以不同的方式接棒,父女薪傳,繼續前行,也令人動容。深知Ado 除了在創新的歌謠與演藝領域努力突破、精進之外,一直想要為父親與Pangcah 歌謠的因緣寫出完整而紮實的作品,沒錯,這一本就是!
推薦序
在Radiw 中,成為真正的人
劉克襄
還未展讀前,我的腦海一直浮昇著,阿洛描述小時自己族人居家的溫馨時光。大家透過歌謠的傳唱,帶出生活的親密連結。
我也想起早年,自己有幸在太巴塱聽過一首〈回到美好的夜晚〉,還參與吟唱和舞蹈。那種在鄉野的從容生活,家屋隔著矮牆,人與人互助和樂的畫面迄今難忘。
但只有這樣的認知嗎?當我如此浪漫地設定,想要從這本書裡獲得更多相似的共鳴時,卻意外地發現,自己走進一個不同於過往的世界。
那種情境好像走到海灘,凝視著遼闊的大海。在浪潮的湧動裡,享受生活裡難得的平靜。殊不知海面下,一直有著更為深沉的繁複變化。這一巨大流動的存在,其實是許多生命淘洗的絮語,必須不斷反覆地聆聽,才可能理解。
radiw 是書本裡主要探討的內涵。我所熟知的〈回到美好的夜晚〉,應該就是某一首radiw。但radiw 是什麼,卻不只是一般的地方歌謠。當它從書裡面源源不絕地以各種型態和內涵,被描述出來時,我隱隱察覺,還有一深邃的文化底蘊,尚未被世人所認識。
radiw 是如此複雜,難以同個年代一次定義,而是隨著時間的轉換,如菌菇般地膨大、換色和變型。各種歌曲類別,自有不同層次的方向和內容,呈現一個族群的悲歡離合。那是一個超越文字,比文字更真實的紀錄和情感交流。
這個阿美族歌謠的專有名詞,承載了太多美好的意義和價值。生活規範的一切和未來的制約,都在radiw 中微妙的轉變、調整。radiw 對族人來說,不只是以歌反映生活,radiw 便是生活本身。
書裡面的主角有兩位。太平洋戰爭前出生的林信來,是歌謠採集與研究者。阿洛是她女兒,在原運浪潮成長,抗爭中茁壯,是失落母語和文化的一代。
過往高壓統治,獨尊華語文化的年代,林信來採集了上千首阿美族的radiw。當時是極少數,懷有保存族群文化意識的先行者,長期默默地走在孤單的路上。相較於父親,阿洛如今是文化復振的推廣要角,也是吟唱母語歌謠的創作樂人。但面對著不同狀況的社會變遷,這一樁田野工作依舊只有少數人在努力。
許多radiw 如今失去被傳唱的機會,林信來和阿洛父女皆有意識地積極搶救,毋寧是令人欣慰和尊敬的。相對地,愈發突顯了歌謠採集的不易開展和紀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爬梳。
整本書裡的radiw 既是引線,也是燃點。透過父女間日常對話為主軸,親情溫暖和生活智慧交織於裡,不時激盪出花火,卻也有更多生命學習的養成。當他們探觸到不同面向,radiw 便不時以新的樣貌出現,彼此似乎也獲得不同的啟悟。每一個階段都可能孕育新的詮釋,看到更多的豐厚。
本書撰寫人作為第三者,受過人類學正規訓練,從旁觀測和書寫父女的對話,努力地拿捏自己合該扮演的角度,但也不時反省漢人的身分。我們隨著她充滿機智的文字,進入那個動人的靈性世界,更深刻地認識,一個被長期誤解的歌謠世界。
過去我們的體驗,並未從一個阿美族的位置思考。或者根本不曾存在對radiw 的基本了解。只就一些荒謬、膚淺的歌謠,浪漫地放大想像,進而形成長期認知的偏差。當唱歌取代文字,作為生活和感情表述的方法時,有很多看待事物的角度,阿美族跟漢人素來有著巨大的差異,生活氣息和美學價值也不盡相同。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多少會感受到過去的誤謬和錯誤,但看待事物,還很少像本書帶來的全面翻轉。書裡每一段內容,時時讓人汗顏。父女間一次次的對話,不斷地激發我們反省。
透過radiw,一個過去不曾遇見的花東,在眼前璀璨地繁花滿樹,但我們彷彿才抵達入口。這不只是阿洛父女採集過往歌謠的長期尋根之路,恐怕也是我們這些外來旁觀者,重新獲得機會,站到一個更合宜的視角,認真凝視下一個花東海岸。
當radiw 回來,讓一個阿美族成為真正的人時,radiw 也可能讓我們成為真正的旅人。
(本文作者為作家、中央社董事長)
前言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Radiw no o'rip,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一個新的嘗試
Pangcah 阿美族的我,無法不面對當代的自己。
Radiw 是歌,o'rip 是生命。
對Pangcah 人來說,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本書是一個重啟Pangcah 與當代思維對話的嘗試。台灣的原住民族除了面對族群、性別、階級、土地、環境等議題,我們的遭遇也無異於全球化的各種危機。當我們不再以Pangcah 的知識體系思考問題時,等同於這個民族是不存在的。
我的世代,經歷整套的國立編譯館教育養成,上過吳鳳神話的課本教材、大中華歷史地理的填鴨教育、說國語、學英文的思想獎勵、學習西方樂理、樂器和藝術美學的造詣。我的養成過程,是與自己的母體文化分離的一鏡到底的長鏡頭,如今要找回何謂Pangcah 的主體意象?絕非易事。
當代台灣的政治和社會語境下,原住民文化往往以大眾化、片面的印象呈現在社群媒體上,為了回應眾多氾濫的刻板印象,需要建立原住民主體意識的言述,找到與大眾對話的路徑,通往尊重與理解的道路才能打開。
採集,作為文化行動的一環
上個世紀的台灣,迎來了許多文化實踐的熱潮,父親趕上了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加入了「民歌採集」,從此踏上實踐自我的道路,一晃眼,就是五十年。我常常覺得,父親那一代的採集者是幸運的,也是最寂寞的。
幸運的是,他參與了台灣史上規模浩大的「民歌採集」,透過報導文學、報導攝影,展開了一段扎實精彩的採集之路,用他的筆、錄音機,還有一口流利的日文,深入台灣各個角落,挖掘出歌謠的故事與流變,即使採錄的方式設限於當時的體制和方法,但那個充滿氣力、理想主義充塞心頭的二十來歲青年仍全力以赴,其集體的成果,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文化實踐者。
中華民族主義浪潮衝擊下的台灣,沒讓「民歌採集」運動存活太久。許常惠、史惟亮等人的成果,被後輩譽為台灣民族音樂學的搖籃,但父親在這場採集運動後,被提及的次數卻寥寥無幾。他返回故鄉,後定居台東,透過歌謠採集,去接續書寫自己歌謠故事的路線,獨自走向這條孤單的路。
從自己的採集田調經驗,父親更確立了自己的道路。他長時間穿梭在山林海邊的部落野徑,透過歌謠、詩句、文化論述、族群觀點分析研究,他收集的歌謠,其實難以用當時的學術理論和方法呈現其脈絡與價值,但他企圖從自己族群的文學角度,建構出他所理解的Pangcah 美學知識體系。
如今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歷史中曾有那麼重要的口述採集,且沒有因為殖民與外來強勢文化的浸透而斷裂,這些人、這些歌,在歷史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要如何述說父親這一代民謠採集者的故事與價值,是我作為Pangcah 人,此生艱難的課題。
所幸,歷經了一年半反覆的訪談與記錄,我們終於找出了一個述說的方式。《Radiw no O'rip 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以跨世代的對話為主軸,這本書是一個微小的開始,也是巨大的跨越。
說故事的歌者、歌者說的故事
當初決定要撰寫這本書,源自我與父親長年的對話。作為紀實文學,整本書籍的節奏、氣氛、調性,也非常符合當年家父林信來先生的田調生活。
令我感到很欣喜的一點是,書中以我與父親兩人的主觀角度,取得較為寬闊的觀看視野、更貼近族人意識的深景,好讓我們凝視這些歌謠、歌者背後敘述的世界觀與口傳歷史。這些人就是說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也是唱歌的人,我們得以釐清當代情境下Pangcah 人的臉孔,重新辯證Pangcah 人對歌的靈觀、傳承、意念以及生命觀。
過去,台灣原住民的歌謠採集,往往去原民化,且缺乏討論與論證。大部分的採集工作者一進入部落,就會自訂歌曲標題、定義演唱曲目的傳統性與否,好像族人的歌唱是單獨存在的一種展演形式。這種把被研究者主體切除,普遍抽離的記錄形式,正說明了學界整體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膚淺看法。台灣這個缺乏文化辯證與累積的國度,其實是很寂寞的,而這樣的寂寞,恰巧微妙地呼應了當年1960 年代民歌採集中,那個唯一原住民籍的採集者——我的父親林信來先生——他在台灣踽踽獨行的寂寞。
歌謠之採集者的意義,若是為了「服務」,甚至成為某種文化詮釋的「占領」,就會生產出完全不同的內涵。那些常見的原住民歌舞,恰恰是以「服務」主流文化為習性的表演活動。如果意味著「占領」,那些展演活動就會走向一種文化霸權、強加定義的主張。因此,「解殖」成為我這個世代自我省察的重要關鍵字,也是讓我們跳脫西方、漢人音樂與思想,轉化Pangcah 生命史觀的重要線索。我們Pangcah 更希望強調對等交流的狀態,一旦交流固化,就失去了相互對話的意義。
為什麼要出這本書?這個問題在我心中有了答案。去建立原住民的主體意識,需要找到彼此對話的路徑,很高興一位非原住民籍的人類學碩士生藍雨楨出現了。這是一段自省式的田野過程,在我與父親、雨楨三者之間,有了重新對話、思辨、釐清、檢視的機會。雨楨從第三者的角度,將Pangcah 歌謠文化做了紀實性的記錄與詮釋,企圖還原當年採錄者與被採錄者的史觀,我們渴望看見這樣的口述文學,這是一場以初步的文化行動,連結大眾理解Pangcah 的一本書。
Radiw no O'rip
小時候,父親常常這樣對我說:「在這個島嶼台灣,我們Pangcah 應該是最能用唱歌記錄生命的民族,我們是最偉大唱歌的民族!」他總是驕傲地看著他採集的那些厚厚的資料與錄音帶,喜悅地說著。
我抬起頭看著爸爸,心裡想,就是那些每天在家裡錄音帶反覆播放的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這些老人家唱得吵死人的歌嗎?我不以為意地問了父親,那個聲音那麼尖,有什麼好聽?父親回答:
「能夠唱到像山一樣高、是本事,會被人尊敬的。」
我又問,那些歌都不知道唱什麼,一直唱聽不懂的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 反覆再反覆,很無聊啊,父親語重心長地回答我說:
「ho hay yan 是我們Pangcah 的密碼啊,跟祖先、天地萬物溝通的語言,是很深奧的,反覆再反覆唱,就像是海浪拍打的浪花一樣,一波再一波,一次再一次,重複再重複是我們Pangcah 想要回答自然萬物:『是的是的,我在這裡』,跟著自然萬物一起拍打,循環再循環啊!」
小時候的我,其實不以為意。長大之後,崇拜過許多西洋音樂,也風靡過不同時期的流行音樂。後來我在求學時,受到法國後殖民學者法農(Frantz Omar Fanon)《黑皮膚,白面具》的啟發,裡面有一句話:「一個法裔的黑人,當他講著一口流利的法語時,頓時之間,他覺得他的皮膚似乎白了一點。」
隨著自我認同的身分覺醒,我才知道那些以前mato'asay(老人家)唱的radiw,才是引領我一路不被強勢文化巨浪吞沒的路徑。的確,找回自己絕對是一條艱難的路:首先,會經歷過無數次的自我否定;然後是逃避,可能不時被迫沉默。不經意的強權洪流,足以沖淡祖先的榮耀;自卑的陰影,在社會的階級邊緣侵占了族人的心靈。這一路,就像碎片般,我們得慢慢地拼湊,才能趨於一個真正的Pangcah 人。
如今,我們還剩下什麼呢?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那麼就開始大聲唱我們的歌吧!我這樣篤定,從母語歌謠創作開始,一點一滴拼湊曾經被遮蔽、隱沒的價值。我在radiw 裡撿回認同,也撿回Pangcah 當代的浪潮與今日屬於我的抗爭。
radiw 成為我時時確立自己存在的一種姿態,是我閉上眼睛時,遙想與久遠祖先接軌的金色絲線。radiw 在o'rip 之中,像海浪拍打一樣,永遠不停息……。
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林信來先生、母親曾麗芬女士
以及那個曾經用歌說故事的人們,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 ~
在艱苦中堅持傳續祖先歌藝的孤獨身影
Pasuya Poiconx 浦忠成
在原住民學術圈子中,偶爾有人會談及,哪一個是最早出國留學、最早取得博士學位、最早在大學任教之類的議題,哪一個是number 1 也常引起興趣。有一位真正最早在大專任教的原住民族籍教師,卻是現在很多青壯學者不認識的,他是Calaw Mayaw 林信來教授。
用「孤獨」形容他孤軍奮鬥的情境,我思考了許久。這不是現在已經擁有接近二百位博士、近千位碩士的原住民族社會可以理解的。他出生於1936 年,年齡相仿的如阿美族黃貴潮、吳明義及排灣族的林天生等,這是日本統治台灣不到十年即將結束的時期,他們都曾在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接受日式教育。二戰結束,新的政權到來,少年立即面臨環境巨大變化,而Calaw Mayaw 卻能快速適應,順利進入花蓮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山地班,開啟一生從事教學的門徑。二十七歲,再考入台灣師大前身的省立台灣師大音樂系,接觸西洋音樂理論與技巧,同時在分別自德國、法國返台推動「民歌採集運動」的史惟亮、許常惠教授的計畫之下,進入部落採集歌謠,這是重要的啟蒙與訓練。師大畢業之後,先在瑞穗國中、玉里高中任教,後來因為專業而受聘到台東師範學院音樂系。
在那樣的年代,不要說「山地同胞」的藝術文化,連「台灣」相關的議題探討都是嚴重的忌諱;但是Calaw Mayaw 在「正規」的教學之外,常常帶著妻兒走入阿美族的部落,以檳榔、米酒與香菸酬謝族人,先後採錄上千首各類歌謠。由這件事看,他是最早進入田野的原住民學者。後來經過整理,寫成《Banzah A Ladiu 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並於1981 年獲得中山文藝獎(顛覆原住民只能被調查、研究的刻板印象)。1988 年,時年五十二歲的林信來考取東京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卻由於經濟、身體的因素無法完成學業,束裝返台。後來教學外積極參與中研院、文建會與省府民政廳調查研究計畫,彙集豐富的Ilisin 資料檔案。這是林教授在學術道路上,孤寂卻又頑強有力的身影。
這本書寫的是Calaw Mayaw 生命的故事,小女兒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跟父親談話中引出老人對於Pangcah 歌謠radiw 的觀點與解說,再藉由Ado 自幼記憶的線索,幫助父親追回許多生命真情的段落,而具有人類學背景的藍雨楨也參與對話,多方蒐集相關資料,補充父女可能遺落的片段,進行必要的梳理,演繹成極其豐盛的阿美族歌謠故事與Calaw Mayaw 生命行腳的註解。這是阿美族歌謠擺脫學術框定,回到真實生活情境,為族人悲喜而自在歌詠的面貌。
學術的大哉問,Naluwan/hohaiyan/hahai 是「虛詞」、「無義」嗎?Calaw Mayaw 說:「我不知道,但是可以唱半天、一天啊!」這誠然就是得魚而忘筌的態度。他是我父親同年代的長者,卻有幸曾經跟他乾杯幾回,笑顏笑語,是一直不曾改變的風度。「山地平地化」和戒嚴的年代,Calaw Mayaw 長期以低調卻詼諧的姿態應對,背後的緣由,其來有自。
這是三個人共同完成的傳記與阿美族歌謠探討專書,只不過運用輕鬆、自在的對話方式進行完整而深入的詮釋,正好貼近Calaw Mayaw 的風格。有幸率先閱讀全文,深為Calaw Mayaw 在艱苦環境中堅持走上探索自身族群歌謠文化的道路而感佩,而Ado 以不同的方式接棒,父女薪傳,繼續前行,也令人動容。深知Ado 除了在創新的歌謠與演藝領域努力突破、精進之外,一直想要為父親與Pangcah 歌謠的因緣寫出完整而紮實的作品,沒錯,這一本就是!
寫於劍潭 2021 年10 月7 日
(本文作者曾任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現為監察委員)
(本文作者曾任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現為監察委員)
推薦序
在Radiw 中,成為真正的人
劉克襄
還未展讀前,我的腦海一直浮昇著,阿洛描述小時自己族人居家的溫馨時光。大家透過歌謠的傳唱,帶出生活的親密連結。
我也想起早年,自己有幸在太巴塱聽過一首〈回到美好的夜晚〉,還參與吟唱和舞蹈。那種在鄉野的從容生活,家屋隔著矮牆,人與人互助和樂的畫面迄今難忘。
但只有這樣的認知嗎?當我如此浪漫地設定,想要從這本書裡獲得更多相似的共鳴時,卻意外地發現,自己走進一個不同於過往的世界。
那種情境好像走到海灘,凝視著遼闊的大海。在浪潮的湧動裡,享受生活裡難得的平靜。殊不知海面下,一直有著更為深沉的繁複變化。這一巨大流動的存在,其實是許多生命淘洗的絮語,必須不斷反覆地聆聽,才可能理解。
radiw 是書本裡主要探討的內涵。我所熟知的〈回到美好的夜晚〉,應該就是某一首radiw。但radiw 是什麼,卻不只是一般的地方歌謠。當它從書裡面源源不絕地以各種型態和內涵,被描述出來時,我隱隱察覺,還有一深邃的文化底蘊,尚未被世人所認識。
radiw 是如此複雜,難以同個年代一次定義,而是隨著時間的轉換,如菌菇般地膨大、換色和變型。各種歌曲類別,自有不同層次的方向和內容,呈現一個族群的悲歡離合。那是一個超越文字,比文字更真實的紀錄和情感交流。
這個阿美族歌謠的專有名詞,承載了太多美好的意義和價值。生活規範的一切和未來的制約,都在radiw 中微妙的轉變、調整。radiw 對族人來說,不只是以歌反映生活,radiw 便是生活本身。
書裡面的主角有兩位。太平洋戰爭前出生的林信來,是歌謠採集與研究者。阿洛是她女兒,在原運浪潮成長,抗爭中茁壯,是失落母語和文化的一代。
過往高壓統治,獨尊華語文化的年代,林信來採集了上千首阿美族的radiw。當時是極少數,懷有保存族群文化意識的先行者,長期默默地走在孤單的路上。相較於父親,阿洛如今是文化復振的推廣要角,也是吟唱母語歌謠的創作樂人。但面對著不同狀況的社會變遷,這一樁田野工作依舊只有少數人在努力。
許多radiw 如今失去被傳唱的機會,林信來和阿洛父女皆有意識地積極搶救,毋寧是令人欣慰和尊敬的。相對地,愈發突顯了歌謠採集的不易開展和紀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爬梳。
整本書裡的radiw 既是引線,也是燃點。透過父女間日常對話為主軸,親情溫暖和生活智慧交織於裡,不時激盪出花火,卻也有更多生命學習的養成。當他們探觸到不同面向,radiw 便不時以新的樣貌出現,彼此似乎也獲得不同的啟悟。每一個階段都可能孕育新的詮釋,看到更多的豐厚。
本書撰寫人作為第三者,受過人類學正規訓練,從旁觀測和書寫父女的對話,努力地拿捏自己合該扮演的角度,但也不時反省漢人的身分。我們隨著她充滿機智的文字,進入那個動人的靈性世界,更深刻地認識,一個被長期誤解的歌謠世界。
過去我們的體驗,並未從一個阿美族的位置思考。或者根本不曾存在對radiw 的基本了解。只就一些荒謬、膚淺的歌謠,浪漫地放大想像,進而形成長期認知的偏差。當唱歌取代文字,作為生活和感情表述的方法時,有很多看待事物的角度,阿美族跟漢人素來有著巨大的差異,生活氣息和美學價值也不盡相同。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多少會感受到過去的誤謬和錯誤,但看待事物,還很少像本書帶來的全面翻轉。書裡每一段內容,時時讓人汗顏。父女間一次次的對話,不斷地激發我們反省。
透過radiw,一個過去不曾遇見的花東,在眼前璀璨地繁花滿樹,但我們彷彿才抵達入口。這不只是阿洛父女採集過往歌謠的長期尋根之路,恐怕也是我們這些外來旁觀者,重新獲得機會,站到一個更合宜的視角,認真凝視下一個花東海岸。
當radiw 回來,讓一個阿美族成為真正的人時,radiw 也可能讓我們成為真正的旅人。
(本文作者為作家、中央社董事長)
前言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Radiw no o'rip,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一個新的嘗試
Pangcah 阿美族的我,無法不面對當代的自己。
Radiw 是歌,o'rip 是生命。
對Pangcah 人來說,
歌在生命裡,生命就是歌。
本書是一個重啟Pangcah 與當代思維對話的嘗試。台灣的原住民族除了面對族群、性別、階級、土地、環境等議題,我們的遭遇也無異於全球化的各種危機。當我們不再以Pangcah 的知識體系思考問題時,等同於這個民族是不存在的。
我的世代,經歷整套的國立編譯館教育養成,上過吳鳳神話的課本教材、大中華歷史地理的填鴨教育、說國語、學英文的思想獎勵、學習西方樂理、樂器和藝術美學的造詣。我的養成過程,是與自己的母體文化分離的一鏡到底的長鏡頭,如今要找回何謂Pangcah 的主體意象?絕非易事。
當代台灣的政治和社會語境下,原住民文化往往以大眾化、片面的印象呈現在社群媒體上,為了回應眾多氾濫的刻板印象,需要建立原住民主體意識的言述,找到與大眾對話的路徑,通往尊重與理解的道路才能打開。
採集,作為文化行動的一環
上個世紀的台灣,迎來了許多文化實踐的熱潮,父親趕上了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加入了「民歌採集」,從此踏上實踐自我的道路,一晃眼,就是五十年。我常常覺得,父親那一代的採集者是幸運的,也是最寂寞的。
幸運的是,他參與了台灣史上規模浩大的「民歌採集」,透過報導文學、報導攝影,展開了一段扎實精彩的採集之路,用他的筆、錄音機,還有一口流利的日文,深入台灣各個角落,挖掘出歌謠的故事與流變,即使採錄的方式設限於當時的體制和方法,但那個充滿氣力、理想主義充塞心頭的二十來歲青年仍全力以赴,其集體的成果,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文化實踐者。
中華民族主義浪潮衝擊下的台灣,沒讓「民歌採集」運動存活太久。許常惠、史惟亮等人的成果,被後輩譽為台灣民族音樂學的搖籃,但父親在這場採集運動後,被提及的次數卻寥寥無幾。他返回故鄉,後定居台東,透過歌謠採集,去接續書寫自己歌謠故事的路線,獨自走向這條孤單的路。
從自己的採集田調經驗,父親更確立了自己的道路。他長時間穿梭在山林海邊的部落野徑,透過歌謠、詩句、文化論述、族群觀點分析研究,他收集的歌謠,其實難以用當時的學術理論和方法呈現其脈絡與價值,但他企圖從自己族群的文學角度,建構出他所理解的Pangcah 美學知識體系。
如今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歷史中曾有那麼重要的口述採集,且沒有因為殖民與外來強勢文化的浸透而斷裂,這些人、這些歌,在歷史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要如何述說父親這一代民謠採集者的故事與價值,是我作為Pangcah 人,此生艱難的課題。
所幸,歷經了一年半反覆的訪談與記錄,我們終於找出了一個述說的方式。《Radiw no O'rip 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以跨世代的對話為主軸,這本書是一個微小的開始,也是巨大的跨越。
說故事的歌者、歌者說的故事
當初決定要撰寫這本書,源自我與父親長年的對話。作為紀實文學,整本書籍的節奏、氣氛、調性,也非常符合當年家父林信來先生的田調生活。
令我感到很欣喜的一點是,書中以我與父親兩人的主觀角度,取得較為寬闊的觀看視野、更貼近族人意識的深景,好讓我們凝視這些歌謠、歌者背後敘述的世界觀與口傳歷史。這些人就是說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也是唱歌的人,我們得以釐清當代情境下Pangcah 人的臉孔,重新辯證Pangcah 人對歌的靈觀、傳承、意念以及生命觀。
過去,台灣原住民的歌謠採集,往往去原民化,且缺乏討論與論證。大部分的採集工作者一進入部落,就會自訂歌曲標題、定義演唱曲目的傳統性與否,好像族人的歌唱是單獨存在的一種展演形式。這種把被研究者主體切除,普遍抽離的記錄形式,正說明了學界整體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膚淺看法。台灣這個缺乏文化辯證與累積的國度,其實是很寂寞的,而這樣的寂寞,恰巧微妙地呼應了當年1960 年代民歌採集中,那個唯一原住民籍的採集者——我的父親林信來先生——他在台灣踽踽獨行的寂寞。
歌謠之採集者的意義,若是為了「服務」,甚至成為某種文化詮釋的「占領」,就會生產出完全不同的內涵。那些常見的原住民歌舞,恰恰是以「服務」主流文化為習性的表演活動。如果意味著「占領」,那些展演活動就會走向一種文化霸權、強加定義的主張。因此,「解殖」成為我這個世代自我省察的重要關鍵字,也是讓我們跳脫西方、漢人音樂與思想,轉化Pangcah 生命史觀的重要線索。我們Pangcah 更希望強調對等交流的狀態,一旦交流固化,就失去了相互對話的意義。
為什麼要出這本書?這個問題在我心中有了答案。去建立原住民的主體意識,需要找到彼此對話的路徑,很高興一位非原住民籍的人類學碩士生藍雨楨出現了。這是一段自省式的田野過程,在我與父親、雨楨三者之間,有了重新對話、思辨、釐清、檢視的機會。雨楨從第三者的角度,將Pangcah 歌謠文化做了紀實性的記錄與詮釋,企圖還原當年採錄者與被採錄者的史觀,我們渴望看見這樣的口述文學,這是一場以初步的文化行動,連結大眾理解Pangcah 的一本書。
Radiw no O'rip
小時候,父親常常這樣對我說:「在這個島嶼台灣,我們Pangcah 應該是最能用唱歌記錄生命的民族,我們是最偉大唱歌的民族!」他總是驕傲地看著他採集的那些厚厚的資料與錄音帶,喜悅地說著。
我抬起頭看著爸爸,心裡想,就是那些每天在家裡錄音帶反覆播放的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這些老人家唱得吵死人的歌嗎?我不以為意地問了父親,那個聲音那麼尖,有什麼好聽?父親回答:
「能夠唱到像山一樣高、是本事,會被人尊敬的。」
我又問,那些歌都不知道唱什麼,一直唱聽不懂的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 反覆再反覆,很無聊啊,父親語重心長地回答我說:
「ho hay yan 是我們Pangcah 的密碼啊,跟祖先、天地萬物溝通的語言,是很深奧的,反覆再反覆唱,就像是海浪拍打的浪花一樣,一波再一波,一次再一次,重複再重複是我們Pangcah 想要回答自然萬物:『是的是的,我在這裡』,跟著自然萬物一起拍打,循環再循環啊!」
小時候的我,其實不以為意。長大之後,崇拜過許多西洋音樂,也風靡過不同時期的流行音樂。後來我在求學時,受到法國後殖民學者法農(Frantz Omar Fanon)《黑皮膚,白面具》的啟發,裡面有一句話:「一個法裔的黑人,當他講著一口流利的法語時,頓時之間,他覺得他的皮膚似乎白了一點。」
隨著自我認同的身分覺醒,我才知道那些以前mato'asay(老人家)唱的radiw,才是引領我一路不被強勢文化巨浪吞沒的路徑。的確,找回自己絕對是一條艱難的路:首先,會經歷過無數次的自我否定;然後是逃避,可能不時被迫沉默。不經意的強權洪流,足以沖淡祖先的榮耀;自卑的陰影,在社會的階級邊緣侵占了族人的心靈。這一路,就像碎片般,我們得慢慢地拼湊,才能趨於一個真正的Pangcah 人。
如今,我們還剩下什麼呢?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那麼就開始大聲唱我們的歌吧!我這樣篤定,從母語歌謠創作開始,一點一滴拼湊曾經被遮蔽、隱沒的價值。我在radiw 裡撿回認同,也撿回Pangcah 當代的浪潮與今日屬於我的抗爭。
radiw 成為我時時確立自己存在的一種姿態,是我閉上眼睛時,遙想與久遠祖先接軌的金色絲線。radiw 在o'rip 之中,像海浪拍打一樣,永遠不停息……。
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林信來先生、母親曾麗芬女士
以及那個曾經用歌說故事的人們,ho hay yan i ya o hai y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