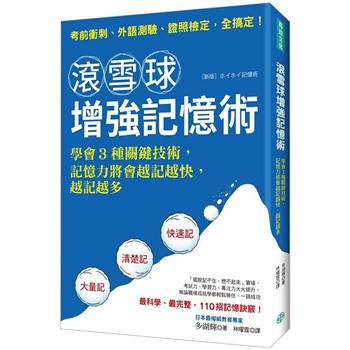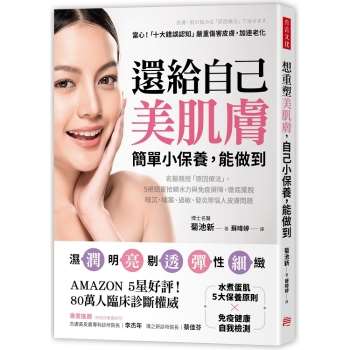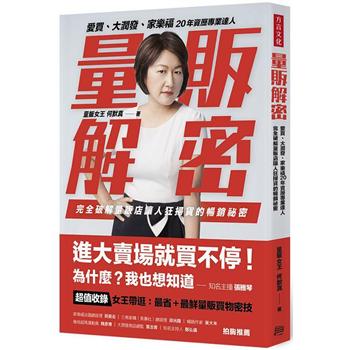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景框之外》系列活動:
10/21(日)誠品園道店3F文學書區(403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15:00-16:00 記錄紀錄──《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發表會
19:30-21:00 'Re'cord──《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導演座談
11/20-12/18 華山文創園區遠流別境(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中三館1樓)
每週二晚間7:00-9:00 出入景框:紀錄片與導演的對談
透過紀錄片的景框,所謂「真實」 是什麼面貌?放棄往往比不放棄更難?
拍出經典作品《無米樂》的莊益增與顏蘭權、戲謔柯賜海荒謬世界的黃信堯、培訓出無數學員的陳亮丰、綻放著自由姿態的曾文珍、睜眼戳出禽流感真相的李惠仁,本書以六位中生代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為對象,透過他們追尋紀錄片的不同取徑與思考,一窺台灣紀錄片的多元樣貌。
作者參考大量訪談與歷史資料,文體融合傳記、訪談與評論,內容不僅附錄紀錄片相關大事及導演作品年表,更淺顯地描述出紀錄片的美好與掙扎、意義與哀愁。是寫作品,寫紀錄片;也是寫人生,寫歷史。本書不只是寫給影迷或紀錄片專業人士,更是獻給熱愛生命、熱愛文化的讀者。
作者簡介: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成立於2006年9月9日,是臺灣第一個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近年來持續推動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益,以健全國內紀錄片環境、促進紀錄片產業發展為目標。自2009年起,出版了《愛恨情仇紀錄片》紀錄片導演訪談錄,每年開始固定舉辦「紀工聚會」系列講座、紀錄片工作坊,並主辦、協辦各種紀錄片相關活動。
紀錄片工會 http://docunion.blogspot.com
紀工報 http://docworker.blogspot.tw
林木材
本名林琮昱,南藝大音像管理所碩士,從事紀錄片推廣,包括影評撰寫、評審工作、編輯採訪、映演推廣、影展策劃、網站企劃等等,並走訪過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部落格「電影‧人生‧夢」曾獲華文部落格大獎首獎。重要經歷包括擔任2010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Programmer)、紀工報主編、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影展策展人等等。
電影.人生.夢 http://woodlindoc.blogspot.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問答之外 /聞天祥*
當台灣電影被視為成功復興,劇情片票房動輒以千萬、上億計算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從2010 到2012 連續三屆台北電影獎的首獎,都被紀錄片抱走;2011 年韓國導演李滄東(《密陽》、《生命之詩》)大陸演員黃渤(2009 金馬影帝)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也透露最讓他們感動和意外的其實是紀錄片。顯然台灣紀錄片的能力與潛力,依然不能小覷。
紀錄片在台灣已經走過很多階段:議題的突破、形式的開發、設備的更新外,還有設立專業系所、人才培力、舉辦影展、巡迴推廣,成立工會等。然而一直要到2009 年底,才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完成《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以問答形式為主的專書,讓
我們在影片的分析評論之外,聆聽到12 位創作者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與紀錄探索,有趣的是同時也凸顯了提問者(大多是當時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生)對於紀錄片種種大哉問的好奇、質疑,真確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自省與對話。
我曉得紀錄片工會的第一本書,出得很辛苦。因此得知第二本《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得以順利出版,不由興奮(這表示還有再續的可能)。與首作最大的不同,是這本新書不再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而是加以改寫。對我來講,這兩種形式並無優劣之分,一如紀錄片手法可以百家爭鳴。問題是:由誰來寫?他必須具備良好的文筆,又要深入瞭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而且我認為,他對投入這項計畫的熱情與理想要遠比他的學位資歷還來得重要!
林木材確實是最佳人選。他雖然年輕,但絕非紀錄片領域的生手。他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也擔任過2010 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影展統籌;但這些可能都不如他自2008 年起持續籌畫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加座談、以及持續更久的紀錄片評論書寫,更能證明他的專注。
正因如此,《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的可讀性就不只是導演們的開誠布公或訪問者的打破沙鍋,還包含了一個評論者的觀察角度。
例如他描述黃信堯的作品:
《唬爛三小》的動人在於,黃信堯不只將創作視為一種情緒宣洩,更重要的,透過貼身的個人角度和語彙,他將這些私人情緒與記憶「轉化」為具溝通性的事件,並在「命運/死亡」的母題下,以輕挑戲謔的態度,令生命中最負面難堪的遭遇、沉重的殘酷話題,成為一幕幕荒謬的人生劇本,揮霍奢侈,充滿傷感。
對於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他說道:
這是部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外在條件上,具備了「作業」與「作品」的雙重身份;內在條件則是唯有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對彼此都充滿「愛」,才可能誕生的作品。
林木材寫陳亮丰的那篇文字,則宛若平行剪;,穿梭在她以行政身份投入「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訓的經歷與感動,以及在九二一地震後改以導演角色參與、記錄的心得。通篇讀來,有如一場合作接力、多重辯證的回顧與反省:
紀錄片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隨著不同創作者而生的獨立視角、理解方式,讓這個世界有著無窮的變化與面貌,不斷解構人的慣態思想、固有觀念,即便是堅定有自信者,也不得不謙卑,學習包容與理解。
而以《不能戳的秘密》驚動朝野的李惠仁,在「驚爆內幕」之外,還具備什麼紀錄特質?他回推到《睜開左眼》:
《睜開左眼》無疑是部反省力十足的作品,構築起「故事」的影像素材包括動畫(小綠人的隱喻)、跟拍畫面、資料影像、自我演出,這部關於影像記錄者的紀錄片,甚至還帶點「後設」(meta)技巧??不會大刀一揮否定一切,仍呈現了人性中的辛酸與無奈,保有一絲寄望,隱含著淡淡的哀傷與失落。《睜開左眼》雖是批判的,但仍是敦厚的。
對於莊益增、顏蘭權叫好又叫座的《無米樂》,他除了詳細道出兩位導演紀錄角度的變遷始末,也在這部動人的作品看到一些隱憂:
值得肯定的是,《無米樂》成功跳脫出小眾的窠臼,讓更多人能接觸與認識紀錄片,但種種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恐怕是在現代社會中,人與土地的真實距離早已越來越遙遠。
除了流暢好讀,字裡行間還有熱情但清晰的評價,既是他回應給受訪導演的誠懇,更展現其寫作態度的標準。這些見解自可接受檢視,你無須全盤照收,卻無法否認它們能夠刺激台灣紀錄片的再思。
而教我忍不住想再問下去的是,這本書只寫了五組導演,卻有一半以上遭遇過自我表達卻被懲罰的經驗。是曾經封閉威權的時代擠壓出他們更大的質疑能量,還是敏銳易感的心靈開發了紀錄探索的觸角?從叛逆到寬大,從批判到自省,所有看似巧遇的生命彎流,到頭來卻成了凝聚創作藍圖的必經。這當中的每一次選擇,雖然從他們口中都是輕輕托出,其實對很多人而言都是沈重的難題。
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記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真實之外/蔡崇隆*
最近參與一部歷史紀錄片的製作,主題是台灣中部一個政治世家的三百年滄桑。研究人員與編導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考察歷史文獻與家族書信,再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再現先人面對時代考驗的反應與抉擇。
好不容易全片在暑假開拍,劇組以電影規格在古老宅邸揮汗拍攝,演員們則賣力地詮釋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穿梭片場,我不禁私下揣想,耗費這麼多人力物力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為了追求真實嗎? 但只要考證出了差錯,美術攝影做不到位,表演者的火候不夠,一切的努力就可能付諸流水,或許它仍可被視為一部有質感的劇情片,但與追求真實為目的的紀錄片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所以根本問題是,「真實」是什?? 如果不管劇情片,紀錄片或現今常見的劇情/紀錄混血片,都很在意真實與否,那?「真實」必然是個很迷人的東西。
我常有機會詢問學生或觀眾: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別是什麼? 得到的答案也多半和真實有關:「紀錄片比較真實……」,「紀錄片能呈現真實的人事物……」。在我自己的創作歷程中,讓我最有感覺的也是許多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所紀錄的人物點滴,例如蘇建和控訴警察刑求的激動語塞,公娼阿姨麗君與路人的街頭論戰,新移民強娜威與老公的家庭衝突……。這些難以預料,無法安排,更不可能重演的魔幻時刻,也許就是劇情片永遠不能夠完全取代紀錄片的原因。
但是,難道「真實」就是紀錄片的全部嗎? 我認為,它必然是核心價值,不過「真實」之外呢? 總還有些別的吧。首先,紀錄片的真實既然是透過影像的再現,就勢必只能是有限的真實或局部的真實,而不是如一般人常以為的---紀錄片能反映百分之百的真實。
再以我的紀錄片人物為例:有別於螢幕上的嚴肅,其實蘇建和是個蠻搞笑的人; 不同於畫面上的強悍,麗君與強娜威私下都頗為靦腆。哪一個他或她才是真實的? 我只知道,如果你認為透過一部紀錄片(不管它做的多好或多長),就可以完全瞭解一個人物的性格或一件事的來龍去脈,那就太天真了。你所能看到的,完全取決於導演/工作團隊想讓你看到什?,或以他們的能力,能讓你看到什?。
進一步來說,紀錄片的觀點將會對你所看到的真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樣是政治受難者的題材,曾文珍與顏蘭權,莊益增會有相當不同的切入角度。一樣是環境生態的題目,黃信堯與李惠仁會有大相逕庭的議論方式。你沒辦法?他們作品呈現的哪一個才是真實,你也不能抱怨他們都太過主觀。每一個作品不可避免的隱藏?創作者的個性,意識形態與成長歷程。所以我必須再次殘忍的打破許多人對紀錄片的幻想:紀錄片能客觀的反映它所紀錄的真實。也許現實環境與傳播媒體的表現令人失望,紀錄片相對客觀地呈現了較多真實面,但因此給予過高期待恐怕也沒有必要。
既然這樣,紀錄片還有什?好期待的? 對我來說,紀錄片值得珍惜的,本來就不在於真實或客觀與否的命題,而是如本書所介紹的幾位導演及其作品所揭示的,除了觀點之外,還有關切(concern)。兩者相乘而產生的巨大能量,你可以看到紀錄片有時如一把利刃,插向官僚主義的心臟; 有時如一道清溪,流過尋常百姓的村里; 有時如一顆奇石,投入幽暗歷史的深谷; 有時如一把探針,刺進私我最不可言說的痛處。如果不是出於對土地,社群,家庭及自我的熱愛與關切,我們不會看到這些傑出作品的誕生。
這些年中國熱席捲了西方世界,包括中國紀錄片也受到高度重視。中國大陸很像八零年代解嚴前的台灣,充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氛與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誠然是紀錄者的天堂。高度自由與富裕的台灣,好像就沒什?好紀錄了。所以雖然紀錄片徵件與競賽仍然屢見不鮮,但多半主題虛浮,為了獎金而來的參賽者也少見紮實作品。你不能說這些紀錄片沒有呈現任何真實的台灣,但你不太容易看到清楚的觀點,更難瞭解作者的關切是什?。
台灣真的沒有什?值得紀錄的嗎? 有學者研究指出,台灣近年來所累積的財富,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權貴階級,與絕大多數的中下階級根本沒有關係。社會新聞每隔幾天就會看到有人因為經濟困境而結束生命。直到我寫稿的此刻,被資方惡意離棄的華隆員工罷工仍然在持續。我並不是?紀錄片非得紀錄這些題材不可,但我好奇台灣眾多攝影機的方向到底是在哪裡? 如果只是跟隨?某些制式的主題起舞,沒有深入的田調或蹲點拍攝,那只是讓台灣無所不在的速食文化進一步啃蝕了紀錄片的寶貴資源而已。
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萬事萬物都可以消費,紀錄片大概也不例外。但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總是蘊含了一些資本巨獸食不下咽,或是吞下去也會吐出來的東西,那是一種對現存系統的省思能力,也是一種難以收編的反抗精神。所以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紀錄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過程。紀錄者的最大收穫,往往不在獎金,而在於路上的緣分與風景。也因為影片本身不是目的,所以當你發現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標時,或許紀錄的終點也已到來。
2009年推出《愛恨情愁紀錄片》時,我曾擔心台灣紀錄片的榮景即將消逝,三年後來看,舊的問題並未消失,新的危機已經浮現,例如南部紀錄片重鎮-南藝大紀錄所的招生人數逐年直線下降,中部國立美術館主辦的國際紀錄片雙年 展一直無法有效傳承策展經驗,北部歷史最久的本土紀錄片播出平台-公視紀錄觀點,因為片源不足,開始播出國外紀錄片。整體來說,台灣的紀錄片環境正在惡化中,雖然還有很多年輕的創作者留在這個領域,但是他們的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
三年前的導演訪談提供了原始的素材供讀者自行取用,但較不利於紀錄片的初學者,所以這一次的續集雖然也訪談了多位紀錄片工作者,但由木材在閱讀聽寫稿之後,再自行研究增補,以導讀的方式寫作本書。為了提高可讀性,木材的寫作策略也有如一部人物紀錄片,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畫面與有趣的情節。最重要的是,他也成功的描繪出每位創作者的獨特面貌,並引領讀者體會其作品的精髓。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面臨轉折的關鍵時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對紀錄片工作者與愛好者產生良性的刺激,對紀錄片專業與產業的提升做出貢獻,更期盼未來十年可以看到台灣紀錄片的新榮景。
名人推薦:*問答之外 /聞天祥*
當台灣電影被視為成功復興,劇情片票房動輒以千萬、上億計算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從2010 到2012 連續三屆台北電影獎的首獎,都被紀錄片抱走;2011 年韓國導演李滄東(《密陽》、《生命之詩》)大陸演員黃渤(2009 金馬影帝)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也透露最讓他們感動和意外的其實是紀錄片。顯然台灣紀錄片的能力與潛力,依然不能小覷。
紀錄片在台灣已經走過很多階段:議題的突破、形式的開發、設備的更新外,還有設立專業系所、人才培力、舉辦影展、巡迴推廣,成立工會等。然而一直要到200...
章節試閱
*景框外的真實──顏蘭權與莊益增*
「每次看到他們都像看到遊民一樣,想要問他們甘無呷飯!」吳念真導演這麼說。
莊益增與顏蘭權個子都不高,兩人外表看起來乾癟削瘦,喜歡戴帽子,穿著比自己身形大一號的深色T 恤和New Balance 球鞋,無論在何時,總像被一片揮之不去的憂愁之雲籠罩,彷彿有著捱不完的煩惱。低調的他們不會刻意與人交往,但只要一談起有意思的話題卻會聊個沒完,一搭一唱,互相消遣對方。淡泊、隨性、率直、憨傻、認真,這是許多人對他們的認識。
錯誤的第一步
兩人成為情人,是在1999 年之前;兩人成為拍攝搭檔,則是從1999年開始的。
在那之前,顏蘭權從東吳大學哲學系(輔修社會系)畢業,一年之後,隨即在家裡的支持下出國念電影,身為家中的老么,集各方寵愛於一身,從小她收到的禮物就是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幻想」自此在她的生命
中打下樁基。在高雄市前鎮區長大的她清晰記得,早在十四、十五歲就嚮往電影的世界,時常翹課去電影院,好奇著電影究竟是怎麼拍成的,她就是有股強烈的渴望想要參與這個不可思議的造夢工程。她先是到法國,卻因進入電影學院的門檻太高,法國也普遍較強調理論而非創作,輾轉到了英國繼續追夢。
「我在台灣完全沒有電影經驗,當時申請劇情片結果被打叉,後來聽說一位導師(tutor)看到我那個拍破爛藝術節的影片,就說把這個撿回來學紀錄片好了。那位老師對我說,紀錄片是所有技巧的學習。」就這樣,
顏蘭權進了雪菲爾哈勒姆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研究所一年級時(Postgraduate Diploma)攻讀紀錄片,二年級時她又轉回劇情片,最終取得了電影/電視製作的碩士學位(Master Degree)。而她最喜歡的導演是就是已逝的英國獨立電影先驅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1999 年9 月21 日,台灣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地震災害,中部地區哀鴻遍野,就像戰爭後的荒城。同個時間,顏蘭權從英國回台灣不久,她的電影劇本計畫得到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剛去了趟法國進行田野調查,不料才回國一週,就碰上了大地震。
她窩在台北的住處,每天坐在電視機前,腦袋一片空白,接收災民的哀嚎、國軍的英勇救人事蹟、大企業的愛心喊話、政府的援助政策等等資訊。兩個禮拜之後,她突然對這些千篇一律的轟炸感到疲憊,厭倦極了政治人物不切實際的話語,不滿電視上出現的各種良善、溫馨、憤怒、無奈的片面情緒和印象。「真正的災區究竟怎麼了?」她這麼問自己,相信一定還有些什麼是在電視框之外的。這股單純的念頭和衝動,後來領著年輕熾熱的她踏入紀錄片的世界。
她和三位朋友一起駕車前往災區,帶著一台非常小的DV 攝影機(SonyDCR-TRV900)想去尋求自己的真相。剛開始面對那些被地震破壞的景象,大夥總會發出驚懼的哀歎聲,也能與各地朋友討論或聆聽他們的心情。但日子一天天過去,每天映入眼簾的儘是灰濛濛的殘破景象,一幢幢坍倒的房舍與建築物,一張張雙目無神無魂的臉孔,一鄉鄉滿目瘡痍的城鎮。逐漸地,他們四人被週遭低壓的氣息逼得無法喘息,彼此之間越來越無言以對,沉默不語是面對懼怕無措最好的表達方式。顏蘭權回憶:「我跟朋友開車繞了災區一圈,那趟旅程是很恐怖的記憶。還記得每到一個災區,總會看到一些人在斷垣殘壁之中挖掘自己剩下的東西,那種經歷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想像的,也不單單只是親人的喪失,那是整個生活的崩毀。」
旅程的第六天,恰巧是父親六十九歲生日,家人打電話責備顏蘭權怎麼沒有回家替父親祝壽。當時的她認為這個百年災難實在是比父親生日要重要得多,但她還是打了電話向父親道歉,並且允諾明年七十大壽時一定會在父親身旁,「爸,我跟你說地震是台灣的災難,這個比較重大,生日你明年還有,明年我一定陪你。」父親說:「好啊!我沒意見,是妳姊姊一直罵妳。」
旅程的倒數第二天,他們來到了一個原住民帳棚區,但除了顏蘭權外,沒有人願意下車。她拿著攝影機想拍點什麼,災民們卻以為她是記者,一擁而上,熱情地對著鏡頭講述他們的慘狀,希望能夠幫忙傳播出去,以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救災資源。災民們的一廂情願和誤解,讓只是憑藉著衝動而來,內心沒有特別想法的她心虛不已。一個小小的影像工作者能做些什麼呢?只能努力持好攝影機,錄下他們的情緒和期望。突然間,一位原住民阿嬤抓住她的手,說「好冷,好冷,有沒有棉被,一條棉被。我,我..好想回家。」
旅程的最後一天,他們到了災情慘重的中寮鄉,天色接近暗暝,但鎮上卻無一處燈火,只有三兩居民默默佇立在房厝前。這是座真真正正的死城,死寂的氛圍透植大地,沒人有勇氣下車。半小時後,有人提議「我們回台北好嗎?」大家一致同意。回台北的路上,為了避免沉默的尷尬,大家東一句西一句地胡亂講話,卻沒有人提起災區的經歷。隱藏在喧鬧之下,是任誰也不願提起的,現實的慘景以及生命體驗的震撼..。
回到台北後,顏蘭權不斷地問自己:「身為一個肩膀無力、口袋無錢的影像工作者,究竟能為這次地震做些什麼?」災後是否正如一些文化工作者所說的,是一種轉機?是台灣社會運動再起的契機?還是能為這些長期被忽視的鄉鎮帶來新的發展曙光?對紀錄片依然懵懵懂懂的她,雖無法很明確地說出什麼紀錄片,但懂得只要肯花時間待在那裡,按下攝影機的Record 按鍵,事情就會被「記錄」下來,「記錄」本身即是目的,就有力量,於是她再次帶著攝影機進入災區,想用紀錄片檢驗這場災難,要等待這場災難帶來的意義。
1999 年11 月,顏蘭權正在從中部要返回台北的路途上,家人緊急來電告知父親病危送醫,三天之後父親便過世了。先前要為父親祝賀七十大壽的承諾,只能吞忍心中成為無語的遺憾。她在拍攝手記上寫著:「人生這種東西,沒有氣味,沒有形狀。有些時候你自以為的意義,突然之間潰散如飛絮,真正的意義卻在真空狀態中瀰漫,等你意識到的時候,一切已經失去重量,你只能無力地與它對峙,永遠也摸不著了。」
*荒謬世界 戲謔情真──黃信堯*
紀錄片不是真實?
柯賜海是個爭議的人物,他飼養大批流浪狗,每天開車載著狗兒到處走,因為流浪狗問題,與政府周旋了好幾年。他砸錢請人組成了一支電話部隊,在短時間內同時、密集地撥電話到公務機關,癱瘓電話線路,包括總統府、防檢局、立委辦公室等等都曾受害。
這份強傲十足的「狂人」形像,令黃信堯感到好奇,他想去探索這個人,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面對這麼一位特殊的拍攝對象,吳乙峰向黃信堯推薦日本導演原一男(Hara Kazuo)的作品《怒祭戰友魂》(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1987)。這部影片講述一位參與太平洋戰爭的退伍軍人奧崎謙三,長年以激進手段,要求天皇必須為戰爭的創傷負責,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這位強悍的主角甚至挑釁與脅迫原一男,直接挑戰導演的權力與地位,在雙方你來我往的激烈僵持中,終於發現隱藏在戰爭歷史中的重大秘辛。
某種程度上,《怒祭戰友魂》講的是導演如何面對一個極端強勢的對象。原一男沒有退讓,他以「搏鬥」形容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互動,他曾說:「紀錄片應該去探索人們不想探知的事情,把事物從陰暗中拿取出來..,就因為我是一個創作者,確切無誤地有欲望去涉足一個我不受歡迎的、他人的隱私世界,然後拽出點什麼東西來,把它暴露在敞亮的日光下,即便只是一兩件小事。這種影片方式和那種開始拍攝前預先得到對方許可,然後和拍攝對象討論來討論去是大相逕庭的。」
與柯賜海碰面後,黃信堯上了他的車,試圖解釋自己不是記者,而是研究生要完成學校作業,會長期來拍,可是他不聽也不在意,依然故我。黃信堯與他沒有太多互動,就這樣陸續拍了幾次,從早到晚像個小跟班在一旁側拍。許多媒體記者見狀,以為黃信堯是柯賜海請來專門拍攝歌功頌德影片的人,紛紛表示不屑,排擠嗆聲,冷嘲熱諷。
黃信堯沒有一一辯解,僅是將這些過程紀錄下來。
拍了不到一個月,2000 年12 月,柯賜海因「妨礙新聞採訪」而被拘提,遭新聞業者封殺,被釋放後突然與媒體達成和解,不再鬧場,他於是成為「舉牌達人」,媒體教導他靜靜地站在不知情的受訪者身後舉牌表達訴求。一個異議份子,在短時間內竟被媒體收編,甚至成為接通告的媒體紅人。黃信堯一度擔心自己的拍攝題目又消失了,非常緊張,誰都無法預期的是,一趟奇幻的旅程居然就此展開。
他發現自己對柯賜海其實不感興趣,遂將攝影機轉了方向,探索圍繞在柯賜海周圍的媒體、記者、警察、社會生態。
2001 年5 月,黃信堯因為學校交片期限已到,先將這些歷程初剪成《多格威斯麵》(Dog with Man)。在學校偌大的放映廳內公映,大家邊看邊笑,在幽默的氣氛中進行激烈討論。黃信堯隱約覺得,似乎還有一些想法模糊不清;2001 年9 月,他交了一個新版本給學校,學期製作也已有了成績分數,甚至已經開始進行畢業製作的提案,但對他而言,過程中仍有很多困惑,這趟旅程並不完整。
為了對自己負責,他決定繼續拍下去。《多格威斯麵》於是跟著時間一起「長大」,黃信堯重新剪接,加入了更多素材與想法,讓影片更趨完整!一直到2002 年1 月,柯賜海已變身為媒體明星,成為風靡全國的知名人物,上遍談話性節目,還到各大學巡迴演講,學生爭著要跟他拍照留念!他的談吐、個性、風格,已和當初完全不同。
得知拍攝對象有這麼大的轉折,朋友張益贍對黃信堯說:「當所有攝影機都不理柯賜海時,你就有存在的必要;當所有攝影機都在拍柯賜海時,就是你該離開的時候。」這令他開始思考影片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紀錄片
的存在意義和獨有性是什麼呢?
他在《多格威斯麵》中刻意模仿布袋戲的誇張腔調,以第一人稱的台語旁白做為主要敘事,講述故事經過並陳述自己的心情,使得影片詼諧好笑。更特別的是,他在片頭加上警語:「本『紀錄片』內容,若與『事實』有所出入,作者一概不予負責,請各位觀眾自行斟酌,是否需要觀看。」
在拍攝過程中,除了新聞媒體的沉淪內幕被狠狠地披露之外,對於柯賜海,黃信堯更體驗到了「真實」與「虛構」的難題。「很多片子喜歡使用訪談,可是訪談對柯賜海沒有用,是找不到真相的。面對不同人,他會有完全不同的說法,所以你會去想,關於訪談的真實與虛構到底是什麼?柯賜海在鏡頭前是表演?還是真情?我不知道。」他說。
面對柯賜海,面對以「真」為訴求的新聞媒體,雙重關係的加乘,讓在一旁側拍的黃信堯感到混亂、筋疲力盡,他的攝影機脆弱的無能為力,找不到辦法辨別真假。「真實」這份被認為是紀錄片裡最核心的價值,在他心中漸漸鬆動。雖然,紀錄片從來就不是客觀的表述,誰拿起攝影機,誰就掌握了主控權與詮釋權。
他說:「我覺得紀錄片不是真實,而是一種再創造。所以我在一開始就強調這個片子跟真實有所出入,我也希望觀眾不要相信我的片子,除了片頭提醒之外,也決定用布袋戲的談法。以前的旁白都是字正腔圓,為了說服觀眾,但我希望讓觀眾產生懷疑。」
除了虛構與真實的課題,看著柯賜海向媒體靠攏,一點一滴改變,黃信堯也轉而反省自己,到底為什麼要拍這部影片。片尾,他向柯賜海提問:「你可曾想過我也有在利用你?」柯賜海回答:「沒有,不太可能。你來拍的時候..」可是,黃信堯確實這樣想過。
*睜眼看真相──李惠仁*
通往秘密之路
拍攝《睜開左眼》時,李惠仁同時也正在進行另一部紀錄片。
自2004年製作《危雞危機》專題報導後,李惠仁心底藏有一個未對外人說的秘密。他常常自顧自的熬夜、上網、研讀英文資料,假日時拋家棄子,自己開車到中南部鄉下,常常看起來心事重重,好似在無人理解的孤獨中奮戰。這樣的行徑在辭去工作後變本加厲,除了打工賺錢貼補家用外,他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還會以「踏青」為由,帶著妻子一起南下,到偏僻的鄉間小徑散步。
幾次出遊,妻子劉瑋觀察到車內多了醫療手套、N95口罩、自調酒精、手術剪與黑色大塑膠袋,她沒有多問,只是覺得詭異可疑。李惠仁到底在做什麼?老公是傻了,還是瘋了?
李惠仁回想2004年的情形,H5N2禽流感在台灣大流行,撲殺了三十六萬隻雞:「當時所有媒體都在追,到底這個病毒是怎麼傳進來的?因為台灣以前從來沒有相關病例,當時有人質疑是非法疫苗傳進來?農委會否認,說是候鳥帶進來的,我覺得疑點很多,開始著手調查。..我陸續拿到的證據發現,是有人把病毒偷偷帶進來,偷偷進行疫苗培植,結果沒做好,才把病毒散出去,我把證據拿給農委會,農委會還是堅持候鳥帶進來的,我覺得實在太過份了,決定要讓真相水落石出。」
2009 年冬天,他才告訴劉瑋,自己已經反覆掙扎許久,想把一部放在心裡多年的影片拍出來,覺得這件事要讓更多人知道才行。這不是為了滿足私己的創作慾,而是不得不說的良心壓力。
原來,他一直都在關心禽流感的疫情發展,並親身涉入,踏青逛農舍就是田野調查,車上的不尋常設備,是解剖被丟棄在養雞場外死雞的工具。
「這幾年,我們一有空就會穿梭在杳無人煙的鄉間小路,到幾座雞場和工作中的雞農聊聊蛋價與雞隻健康程度,尤其在寒流來臨、風大雨大的夜晚或是清晨,更會不時去觀察雞場外是否有成堆死雞,被雞場工作人員丟到路邊。在這個過程中,我不但要幫開車中的李惠仁手忙腳亂地使用衛星定位導航找到他要去的目的地,更學會怎麼從遠方目測飼料塔形狀,判斷這座農舍是不是養雞農戶。」劉瑋談起調查的過程。
一開始,李惠仁什麼都不懂,他對農委會提出警告和質疑,官員總是以機密為由不願公佈,或是搬出英文或專業術語塘塞,甚至丟給他一本厚重的英文法典,請他自己回家翻閱,要他知難而退;他在鄉下路邊撿拾死雞,解剖屍體,要採集氣管、肺臟、腎臟送到生物科技實驗室化驗,但美工刀怎麼切都切不開,也不曉得器官的分佈位置和模樣。
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性和傻勁,他一頁頁認真研讀英文版的OIE(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法典,翻查畜牧獸醫學辭典,查閱美國、澳洲、日本的論文,甚至還以電子郵件直接詢問德國、義大利OIE 參考實驗室,終於漸漸明白HA 切割位(檢驗鹼性胺基酸的數目)、IVPI(靜脈內接種致病性指數)、HPAI(高致病性)病毒株、基因定序等專業詞彙,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專家學者請教,搞清楚了公衛系統的權責以及台灣與國際衛生組織間的規範關係。
他也從經驗中修正自己的錯誤,學會使用手術剪,知道該如何在最低限度下保護自己不受感染。幾年下來,他不辭辛勞,踏遍花蓮、台中、彰化、台南、屏東等地,解剖了超過兩百隻死雞,花了上百萬元和無數時間,忍受風吹雨打,髒亂惡臭,只為了戳破官僚謊言,讓真相大白。
「獨立調查的第一步,就是打破既有的框架!」他說。
在他的調查中,發現雞農因為害怕發生疫情雞隻會被大量撲殺,血本無歸,私下都會自己接種疫苗以降低死亡率,卻因此使得病毒在田野間交換基因,在官方於2004 年宣稱已經撲滅病毒後,2006 年病毒又再次出現,透過化驗他親自解剖的死雞,發現雞隻的基因序列已經改變,從高致病性變為低致病性,研判病毒已經台灣化;若是H5N1 禽流感病毒傳染到豬身上,就有機會與哺乳類流感病毒發生基因的重組或交換,那麼這個全能的
病毒很可能就會傳染到人類身上,造成大災難,要盡可能降低這種機率。禽流感也是國際矚目的「人畜共通傳染病」。
2006 年,在多個案例中,其實已經發現了這種可能性,死雞的HN基因間的鹼性氨基酸數目已從2004 年的三個轉變為四個,達到了OIE 所列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但政府始終仍堅稱台灣從未出現過,切勿危言聳聽。接下來的幾年,多次的研究報告都顯示IVPI 已經大於OIE 的規定1.2,但政府不曾依規定通報OIE,還開會「商量」科學實驗的結果,涉嫌隱匿疫情,竄改文件,李惠仁也收到匿名者寄來的實驗報告和診斷會議記錄。他看見專業傲慢,迂腐自大的國家機器是如何官官相護、藐視人民。
過程中,他盡可能蒐集資料,處處記錄,留下事證。但這一切,終究只有他一人知道來龍去脈,時間橫跨六年,議題又這麼複雜專業。李惠仁曾想過以「議題」區分,拍成六段影片,但這樣真的會有人看嗎?以效果來說,真的會有幫助嗎?
他想起在匈牙利參加INPUT 影展時,難以忘懷的德國紀錄片《神秘男孩之死》(The child, the death and the truth, 2010)。影片講述德國公共電視台質疑法國公共電視台所製作的一則以巴衝突新聞可能造假,經過種種科學方法和證據比對,發現這則報導的剪接手法疑點重重,刻意誤導並搧動民眾情緒,加深了以巴之間的國仇家恨。
片中實事求是、講求證據、無畏壓力的推論過程,令他大受鼓舞。回國後他取得了關鍵事證,又有一群教授學者和獸醫系學生在後頭默默支援他,說什麼也要將這一切拍成紀錄片。
劉瑋曾問他:「紀錄片擺明了民與官鬥, 你不怕嗎?家人的風險與未來你有沒有想過?」
李惠仁說:「我一人承擔,遇到了,只能向前,那麼多人在背後幫我,我怎能後退?請相信我和支持我。」他不是傻子也不是瘋子,除了良心使然,更希望留能給後代子孫挑戰權威、追求真相的勇氣。
*景框外的真實──顏蘭權與莊益增*
「每次看到他們都像看到遊民一樣,想要問他們甘無呷飯!」吳念真導演這麼說。
莊益增與顏蘭權個子都不高,兩人外表看起來乾癟削瘦,喜歡戴帽子,穿著比自己身形大一號的深色T 恤和New Balance 球鞋,無論在何時,總像被一片揮之不去的憂愁之雲籠罩,彷彿有著捱不完的煩惱。低調的他們不會刻意與人交往,但只要一談起有意思的話題卻會聊個沒完,一搭一唱,互相消遣對方。淡泊、隨性、率直、憨傻、認真,這是許多人對他們的認識。
錯誤的第一步
兩人成為情人,是在1999 年之前;兩人成為...
作者序
以筆代替攝影機/林木材
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難不去回想,自己曾經走過的紀錄片軌跡。
與紀錄片結緣,是2000 年的事。正值大學二年級的我對生命漠然,時常翹課在外遊蕩,偶然在高雄電影館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1990)。怎麼這些平常我一點也不認識的白化症者,竟對著我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生命中最深沉的秘密心事。面對他們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原來那是一種「重生」的經歷。
後來,我從企業管理系跨領域考上了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管理所,開始正式學習紀錄片。我試著持續寫影評,看讀紀錄片與相關書籍,然後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籌辦各種紀錄片活動,包括人文影像創意研習營、烏山頭影展、南方影展、《無米樂》上院線,並像遊牧民族般追逐著在各地舉辦的紀錄片放映會,結識了許多同好和前輩,努力從大家身上學習。
那時候我常常想著:「我是紀錄片的追星族!也是紀錄片的使徒!」有點狂妄自大,有點天真浪漫,但那卻是無比真實的心情。
退伍後,我移居台北,想試著靠紀錄片相關工作維生,做過的工作包括巡迴放映、影評撰寫、採訪編輯、選片評審、影展策劃、網站企劃等等,幾乎做遍了紀錄片推廣環節中的各項工作。
意外的是,今年(2012)是我踏入紀錄片領域的第十年,居然有了寫書的契機,對於只寫過影評及報導的我,無疑是個艱辛的挑戰。但過往經歷在時間的催化中成為經驗,默默支撐著我,讓我有能量與能力去理解書中所撰寫的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並能夠與他們對話。
做為一個長期的紀錄片影迷和推廣者,我關心的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下,每個人是怎麼開始接觸紀錄片的?為何願意投入其中?所主張的美學觀念是什麼?所認知的紀錄片是什麼模樣?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中,究竟紀錄片對個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概要成為我寫作時的基礎構想。
紀錄片工會在2009 年出版《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後,在2011 年繼續策劃,並交由蔡崇隆導演與南藝紀錄所學生進行《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研究計畫,共有十一位受訪者。但工會對於第二本書的出版有了不同想像,希望觀點能更明確,文體對讀者來說能更容易閱讀。
於是在工會的委託下,我接下了這份改寫的任務,學生們與受訪者的問答稿,是我改寫的主要參考素材,從中我挑選出了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並在遠流出版社的建議下,加入了李惠仁。
這樣的名單對我而言,除了因為個人能力而必須有所取捨外,所考慮的是,他們的年齡相仿,約莫在1970 年前後出生,是台灣中堅的紀錄片工作者,其所經歷過的八?、九?年代,恰恰是台灣社會與紀錄片發展上,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他們學習紀錄片的取徑都不同,各有動人之處,他們的作品採取的美學形式差異甚大,各有所長,更代表著台灣紀錄片豐沛的創作能量與多樣面貌。
我看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搜尋談論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也閱讀他們的自述、訪談與部落格,並且陸續補訪了幾次。一個強烈的念頭開始在心中躍躍浮現,我的小小心願是:透過文字,讓讀者深入認識這些主角,對紀錄片有所理解,並嘗試在歷史的光譜下,描繪出他們各自的座標所在,拼湊勾勒出台灣紀錄片的樣貌輪廓,找回台灣紀錄片在台灣電影史中應有的位置和價值。
大概是因為這種帶點不平的心情吧!所以我總在每篇文章中,刻意地強調解釋「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多面向工作室」、超視的「調查報告」等等影響了台灣紀錄片甚深的機構節目,也試著回到每位主角的思考脈絡裡,闡述他們所認知的紀錄片,然後再偷偷摻入自己的情感、心情與觀感。
那是看見他人以不同方式,投身奉獻於與自己相同的熱愛事物時,一種情不自禁的投射。
許多年前,我曾經是顏蘭權與莊益增的作品《無米樂》(2004)台南場上映的院線統籌,多年後我到他們家中,成為第一批看《牽阮的手》(2010)初剪版的觀眾;2005 年時,我在南方影展觀賞《唬爛三小》的首映,看起來很酷的導演黃信堯在座談中失聲痛哭,令我永難忘懷;2005 年,在看完陳亮丰的《三叉坑》後,因為執著於紀錄片中「真實」的問題,我特地實地走訪三叉坑一趟,而她在全景多年的「培訓者」身份,也令我格外憧憬;我很關心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1998)所引起的,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議題還是個人議題的激辯,翻遍了相關文章,只為了希望看見個人題材並不會削減紀錄片價值的說法;我在電腦前瀏覽著相關消息,關心李惠仁以《不能戳的秘密》(2011)轟動社會,一部紀錄片到底如何能翻天覆地、改變社會?
從觀眾到投入工作,從評論者轉為推廣者。如今,我竟有機會書寫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某種程度上,我也彷彿用文字,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他們的慷慨大方與信任,讓我終於能夠親身體會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Ogawa Shinsuke)所說的:「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從前從前,法國人提出了「攝影機鋼筆論」,認為攝影機就像筆一樣,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如今,在這個以影像閱讀為主的年代,我重新拿起筆來,在資料與影像海中,一點一滴地描繪紀錄片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期待透過自己的眼睛及筆觸,刻劃這些影像作品對時代的意義。
由衷感謝本書主角們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辛苦的編輯群吳家恆、陳芯怡、呂德芬、郭昭君,總是受我叨擾的吳文睿、徐承誼、陳薇如,還有在工作上給予我許多諒解和協助的吳采蘋與盧凱琳,以及一直給我最大支持的父母、岳母、妹妹與小姨子;更要感謝我的牽手陳婉真,她永遠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最在乎的人,我們因紀錄片聊到深夜而不罷休,為紀錄片爭論到面紅耳赤的次數與時間,遠比任何事物來得更多更多,能與她一同走在紀錄片的路上,是最最幸福的事。
我以為《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僅是此系列的開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關於台灣紀錄片的故事陸續出版,也期許自己,能夠一直一直、繼續繼續寫下去。
最後,願此書不致辜負工會與受訪者們所託,僅以此書獻給熱愛紀錄片的朋友。
以筆代替攝影機/林木材
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難不去回想,自己曾經走過的紀錄片軌跡。
與紀錄片結緣,是2000 年的事。正值大學二年級的我對生命漠然,時常翹課在外遊蕩,偶然在高雄電影館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1990)。怎麼這些平常我一點也不認識的白化症者,竟對著我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生命中最深沉的秘密心事。面對他們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原來那是一種「重生」的...
目錄
出版緣起
推薦序 問答之間/聞天祥
推薦序 真實之外/蔡崇隆
年表
景框外的真實──顏蘭權與莊益增
荒謬世界 戲謔情真──黃信堯
紀錄片不是目的──陳亮丰
自由的姿態──曾文珍
睜眼看真相──李惠仁
後記 以筆代替攝影機/林木材
出版緣起
推薦序 問答之間/聞天祥
推薦序 真實之外/蔡崇隆
年表
景框外的真實──顏蘭權與莊益增
荒謬世界 戲謔情真──黃信堯
紀錄片不是目的──陳亮丰
自由的姿態──曾文珍
睜眼看真相──李惠仁
後記 以筆代替攝影機/林木材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