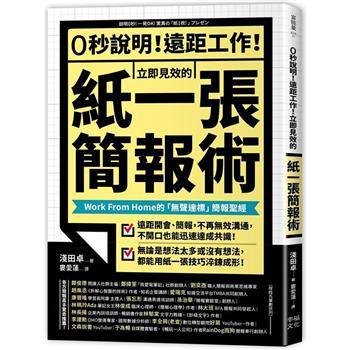中文版序
音樂的生命不在於浮華商業劇場的成功,
而在於鄉間業餘平民的鋼琴上。
──出自:蕭伯納,《華格納寓言》。
提起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眾人皆知是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前半的重要英國文學家,其最為國人熟知的作品,應為《皮格馬里翁》(Pygmalion, 1913/1914);這部作品之所以為國人所知,則經過了一個迂迴的過程。雖然早在三○年代裡,該作品在歐洲已先後三度被拍成電影,但是它之得以在廿世紀後半為世人所知,首先係得力於百老匯的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1956),該音樂劇被改編成同名電影(1963年)後,於英語系以外國家亦很受歡迎。藉由電影,國人的腦海裡留下了一位不苟言笑的語言學家和一位由醜小鴨變天鵝的美麗賣花女的愛情故事。至於蕭伯納其他的文學作品,就較少為國人所知了。
事實上,蕭伯納不僅以本身之文學作品傳世,他更是英國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裡重要的音樂評論家。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一個音樂家庭,父親為伸縮號手,母親為聲樂家,蕭伯納從小在充滿音樂的環境長大,很早就接觸到了歌劇,也曾學習聲樂,並曾立志要成為男中音歌唱家。莫札特是其一生裡最崇拜的作曲家,尤其是《唐.喬凡尼》更不時被蕭伯納拿來與他人作品相比較,彷彿是歌劇之源;在《華格納寓言》一書中,亦不時可見此一現象。
一八七六年,蕭伯納廿歲,離鄉背井來到倫敦,也從此開始他的音樂評論生涯。由於他的文字流暢精鍊、對音樂感覺敏銳,不僅有自己的見地,並且不耍弄專有名詞,依舊能明確表達對所評論音樂內容的看法,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蕭伯納即能獨樹一格,成為倫敦舉「筆」輕重的樂評家。在《華格納寓言》的最後,蕭伯納亦曾自我解嘲地寫著:「我本人看過非常多的專業性、商業的藝術表演,可說經驗豐富,大部分人沒辦法負擔這些費用(我之所以看了這麼多,原因是早年我得靠寫評論餬口)……」(見202頁〈沒有華格納的華格納主義〉)他的樂評文章在他生前及死後,分別以不同的方式集結出書,為當時的英國音樂環境留下見證。其中,於一八九八年首次出版的《華格納寓言—揭開《尼貝龍根的指環》的面紗》(The Perfect Wagnerite: A Commentary on the Nibelung’s Ring)以獨特角度探討華格納的著名鉅作,可稱是樂評中的精品。
今日提到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許多人都會將他和納粹聯想再一起。然則,稍加留意即可發現,華格納去世時,納粹還不知在哪裡。因此,華格納由於是希特勒的偶像,其作品被猶太人全面拒絕的現象固然是華格納的不幸,卻也反映出華格納不僅對其後的音樂或歌劇有重要影響,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歐洲文化發展中,如文學、繪畫等等,亦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無論在音樂生涯或私生活上,華格納的一生均可說是起起落落,多采多姿,他最引人注目的歌劇創作應屬需要演出四晚的《尼貝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 一般習以 Ring, 《指環》簡稱之)。該作品由開始構思致完成首演,前後歷經廿餘年(請參考書後附錄);這廿餘年亦是華格納生命裡最動盪的時期。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三日,拜魯特音樂節首次運作,以搬演全本《指環》揭幕,華格納一生的理想終於實現,亦寫下歌劇史上空前的一頁。
一八九八年,蕭伯納以英國讀者為對象所寫的《華格納寓言》初版發行;此時,距離《指環》全劇首演不過廿二年,而華格納辭世雖已有十五年,但是,當時的歐洲藝文界,無論好惡,均還沉浸在華格納刮起的旋風裡。在如此氛圍中,蕭伯納卻能以其個人的敏銳觀察,結合《指環》的特殊創作過程,以及華格納的人生經歷,自歐洲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的變動、資本主義、馬克斯主義,以及革命風潮等等社會背景出發,詮釋《指環》的劇情變化及劇中人物,揭開作品的神話面紗,回歸現實社會。即以全書的前半部為例,表面看來,似乎僅止於敘述劇情,但是蕭伯納的敘述方式清楚地展現了他的社會關懷及思考;也唯有他能將《萊茵的黃金》裡,各家爭相奪取指環的劇情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相結合,鋪陳出驚人的詮釋。讀者不妨先自行讀讀《萊茵的黃金》劇本,再閱讀蕭伯納的說法,即可對蕭伯納的思路一窺端倪。
雖然書中充滿了社會主義的思考,蕭伯納依舊清楚地呈現了他個人對歌劇的理解:音樂是歌劇的中心。字裡行間,蕭伯納展露了個人的音樂認知,亦毫不保留地呈現他個人對十九世紀多位歌劇大師的褒貶。必須一提的是,在蕭伯納成書的時代,對歌劇的研究和認知遠不如今日,因此蕭伯納的個人好惡,並不能反映這些大師在歌劇史上的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出發點都是源自於對音樂的討論,若拋開個人好惡不論,實可從中看出蕭伯納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成為英國重要樂評人的原因所在。
蕭伯納寫該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無疑在於希望英國亦能發展出類似的音樂文化;這一份關懷與期待,於第四版前言(1922年)以及自〈舊音樂與新音樂〉以後的文章中,清楚地顯露出來。該書初版至今雖已經過百年,《指環》之各種詮釋更是層出不窮,但是蕭伯納在全書中所流露出的社會、文化與藝術關懷,雖是針對當時的英國而發,然而證諸國內現況,依舊有許多值得借鏡及思考之處;這亦是編者與譯者當初決定將本書譯介予國人的出發點之一。
如前所述,雖是音樂評論,但蕭伯納文字的文學氣息依然濃厚。卻也正因如此,翻譯本書實係對譯者的一大考驗。兩位譯者林筱青和曾文英的譯筆雖異,卻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了蕭伯納的特殊風味:一語多關、嘲諷但不失關懷、談音樂亦涉及文化及其他藝術等等。為能讓國內讀者對相關之背景有基本認識,譯者及編者加上了許多屬於資訊上的註釋,期能帶給讀者對當時整體文化的體會。基本上,註釋若未註明,均出自譯者或編者;少數蕭伯納原有的註腳,則特別註明為【蕭伯納註】。
中譯本書名「尼貝龍根的指環──完美的華格納寓言」並非原英文書名之直譯,而係以原書名為出發點,就全書內容、蕭伯納之訴求,以及國內讀者對華格納和與其相關之複雜藝術文化背景的認知,做綜合考量後所得到的結果,希冀能夠藉著書名的變奏,提供讀者閱讀的方向。
閱讀本書,不僅可將其當做對《指環》之簡介,排除對該作的畏懼感,還可將其當做一部文學作品或文化評論來看待,在閱讀的同時,或能引發讀者與蕭伯納之間的對話,自行對音樂及文化進行思考,則更能體會蕭伯納於生前,在每一版序言裡的語重心長。
羅基敏
二○○○年七月
倫敦至拜魯特途中
初版序言
此書是針對華格納重要作品《指環》所做的評論,希望能對那些抓不到華格納音樂精髓,卻又滿腔熱情的華格納迷們有些幫助。他們雖然無法理解佛旦進退兩難的處境,但對若干顢頇之士的輕蔑態度不以為然,當這些人大肆批評佛旦所言盡是些言不及義的荒謬事情時,他們甚至會氣得火冒三丈。不過,就算以狗對主人般的忠誠來追隨華格納,至多也僅能碰觸到少數基本概念,分享些粗淺的好惡、情感,但對於其他方面就只能崇拜仰望,卻不知從何體會,這談不上是華格納主義(Wagnerism)。話說回來,若沒有共同理念在大師與徒弟之間維繫著,也就不可能會有什麼持續的發展,很可惜的,現在大家對於華格納在一八四八年間革命思想的瞭解,在這些英美紳士音樂愛好者的教育或生活經驗裡,付之闕如,因為他們總是政治上的騎牆份子,而且幾乎不和革命者往來。所以,早期將華格納的數本小冊子和散文翻譯成英文的作品,都受限於不良翻譯而淪為荒謬至極、扭曲原意的產物,完全不知所云。現在,我們終於有一個翻譯版本,它不僅是詮釋精闢的上乘譯作。更晉身為優秀文學作品之列:原因並非是其譯者阿斯頓.艾利斯(Ashton Ellis)的德文造詣比之前的譯者好,而是他知道如何掌握華格納的精神與理念,這些是前人怎麼也想不過的。
我對本書最大的期望,即希望能加入某些傳統英國人最可能缺少的東西。就像當初華格納與政治結緣一般,那些東西是我在音樂路上的偶拾與領悟,不但使音樂成為我年輕歲月中所學最多的一門知識,遠甚於其它的事物,也從此撒下了往後我對革命學派產生興趣的政治種子。如此的結合在英國並平常見;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似乎是唯一同時能就音樂與政治加以深入探討的人。因此,在音樂專業樂評和革命政治哲學著作之外,我僅在此大膽附上個人的淺見。
於彼特福,亨德黑,1898
蕭伯納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