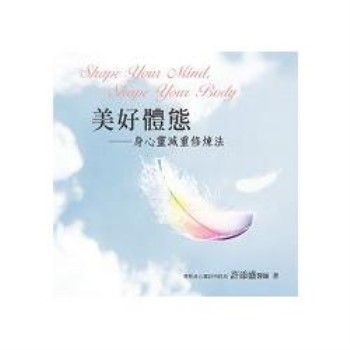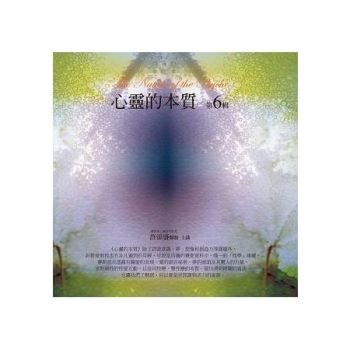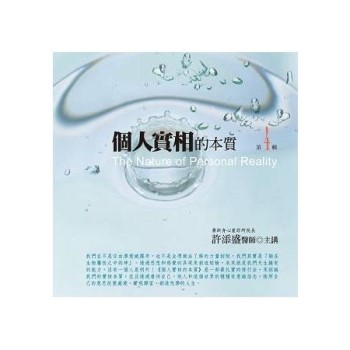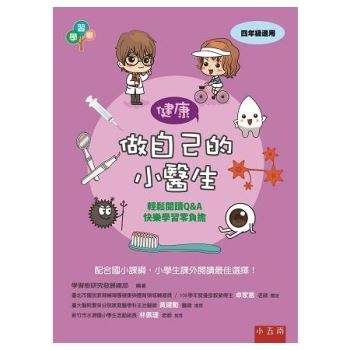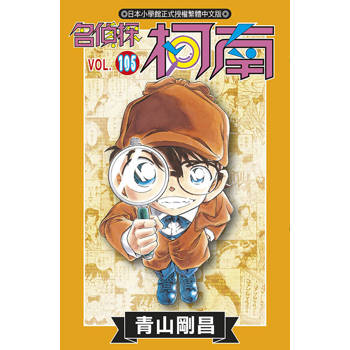作者序
一個成熟的思想總是揉雜著個人偏好與社會文化而形成的整體性呈現,幾無可能以類似成本歸屬的手法一一追溯思想的確切泉源,因此,要求給出確切的思想來源,是不切實際的偽學術手法。再者,思想真確性最終的檢證標準是人類的直觀,而非能否在文本體系中獲得支撐。以引證其它論述充為論題自身的真確性依據,將會陷入論題依靠論題的無窮遞迴。
這是一本關於哲學的論述,但它的目的並非是要教導哲學。由於哲學的學習無法僅僅透過閱讀哲學典籍並模仿哲學語詞即可完成,故,即算理解本書的內容,也無法清楚地回答是否已經理解了哲學。雖然能否真正理解哲學始終是一個無法給出答案的問題,但能否理解某一位哲學家的思想,卻是可能給出判別的,也就是:要能真正理解哲學家的思想,必須曾經有過與他相同的哲學困惑。如果未曾與他有過那樣的困惑,則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對你而言自始就不曾存在,既然困惑不曾存在,就難以理解何以需要有那樣的解答。
本書圍繞著我自身的關懷──【世界有無盡頭?如有,止於何處?】──而展開。在此,必須明確地提及兩位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與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對我的思想啟迪的重要性。當理解我之後,會發現,在很大的程度上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行的。
探討世界的邊界即是展現哲學的重要功能──「揭示人類直觀可能的先天形式及其所能伸展的範圍」。當它被揭示後,會發現哲學所能提供給人們的是多麼地少。然而,由於直觀條件的存在,使得認識與實在間是否一致?困擾著人們,古往今來吸引著無數的哲人及宗師不斷地試圖超克它們以達天人合一的涅槃境地。不幸的是,無數豪情萬丈的才子英雄在面對這堵頑牆後,最終總是嘆息而歸!至今仍是人類無可完成的大業。
「我的認知得以伸展的界限即是我的世界的界限」,這就是哲學上的「我」。即便知道有著那一堵高牆難以爬越,但人們卻總有著想衝破認識界限的自然傾向的衝動,欲求到達彼岸的真實世界。正是這種傾向標誌著人性中的道德光輝,因此,凡涉及經由認識通往本體的著述,與其說是一部哲學,不如說是一部倫理學,如能理解這點,即不難看出本書是一本倫理學的著作,固然在終局上你不會感覺到它有談論到任何傳統倫理的問題。
認識的界限一旦被尋得,則世界的盡頭就被找到了;世界的盡頭一旦被找到,那麼,學海無涯的深層含義──學無止盡的印象來自無法掌握大千變幻的現象所致──即被彰顯。
對世界盡頭的探究給予生命的意義在於:知所不知,不知所知。
林綠常
2013年6月1日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