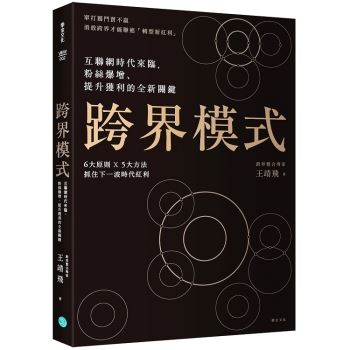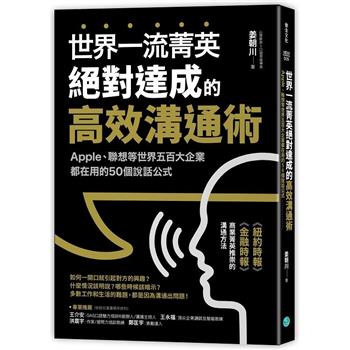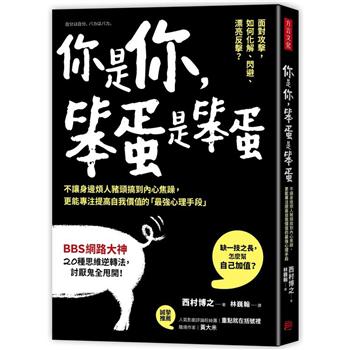2008年11月6日,他們集結在行政院衝撞集遊法,有人叫他們「野草莓」。
2014年3月18日,他們攻進立法院要求退回服貿,這次他們成了「太陽花」。
這本書是野草莓和太陽花
為了這個時代的精神而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
為什麼是關鍵字?這是新世代解讀新世代的社會力分析,於是我們決定要從新世代認知社會的模式出發,來展開我們的討論。在網路成為青年世代的生活方式之後,關鍵字就是他們思考與理解社會的方法。看到一個詞彙之後,透過搜尋引擎找來的資訊,對事物獲得不同層次的了解,找到定義、特質、相關敘事,再經過超連結,找到觀念的外延,這就是網路世代建構知識體系的方式。
這些關鍵字,同時具體而微地呈現他們對社會最真實的感受。年輕人之所以對這些辭彙朗朗上口,甚至形成風潮,是因為這些詞彙在同一世代、乃至於整個社會之中,具有高度的共識性,與大眾的經驗相互符應,以致一被丟到網路上,即能獲得廣泛的共鳴,傳頌千里。
但關鍵字又怎麼變成關「賤」字?「賤」既是貧賤的賤,也是作賤的賤。關賤字接近市井街坊的俚俗用語,而非體面堂皇的論述語言,這些詞彙的使用,凸顯了年輕世代在主客觀情勢的失落下,對於所有一表正經的事物失卻信任,寧可採取玩世不恭的姿態。犬儒背後,藏有滿滿的憤怒。
每一個關賤字都呈現了人民如何淪落為賤,以致深感憤慨,同時積蓄反抗與改革的動能。透過關賤字,我們期望能看見這個時代、這個世代及其不滿,找出「賤之何以為賤」,更要探問「何能不賤」,從反作用力尋找社會力,以及台灣的出路可能在哪裡。
延伸閱讀
《秩序繽紛的年代》
《八輕遊台灣》
《反造城市》
《第三種中國想像》
《厄運之地》(以上皆左岸出版)
《崩世代》(群學)
作者簡介:
■策劃:台灣教授協會
■總審稿:何明修(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主編:丁允恭(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
■撰稿
江昺崙: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
吳駿盛: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畢
林邑軒:台大社研所博士班
林彥彤: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紹興學程
林彥瑜:台大政治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雙學位
林飛帆:台大政治學研究所
陳以箴:成大工業設計系,零貳社前社長
陳宗延:台大醫學系、社會學系雙主修,台大勞工社社長
廖偉翔:成大醫學系、政治系輔系,《公醫時代》創始成員
作者序
策劃者序
發現當下台灣社會力
張信堂(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回顧1970年代初,美國尼克森政府為了解決越戰問題以及推動「聯中抗俄」政策,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導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處境岌岌可危。當時接班態勢明顯的蔣經國,則是在「四二四刺蔣案」與「保釣運動」後,藉由各種「革新」或「保台」言論以營造其改革形象。
面對讓人焦慮不安的變動時局,張俊宏、張紹文、包弈洪、許信良等台灣青年,在1971年10月的《大學雜誌》發表〈台灣社會力分析〉,希望「喚醒大家愛自己所能愛的社會,關心自己可以關心的人群,了解他們的需要,開發他們的人力,共同來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引自張俊宏,《我的沈思與奮鬥》,1977)
其後,歷經「美麗島事件」(1979)、「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解除戒嚴(1987),以至於1990年代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台灣的「社會力」終於迫使「黨國獨裁體制」發生變化,願意進行總統直接民選。民主化的浪潮甚至讓長期壟斷台灣政經資源的中國國民黨,於2000年總統大選時讓出政權,淪為在野黨。
當馬英九代表中國國民黨於2008年贏得總統大選再度執政後,在其「化獨漸統」的信仰下,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傾中政策,與中國擴大交流,例如開放中國人士來台工作,強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服貿協議、自經區等經貿協定。與此同時,油電雙漲帶動物價上漲,受薪階級的薪資卻停滯於十多年前的水準;打房完全沒有成效,房價高到年輕世代永遠買不起房子;GDP的成長有限,所得分配卻越來越不均。台灣人民對馬英九執政的不滿意度持續攀高,從46.2%(2008)飆至69.6%(2013)。
經過了四十幾年,台灣青年再度面對讓人焦慮不安的大環境,他們這一代又將如何分析台灣的「社會力」呢?
***
2013年初我「回鍋」擔任台灣教授協會(台教會)秘書長,向新任會長呂忠津、副會長許文堂提出由台教會主辦一場「台灣社會力分析」研討會的構想,承他們兩位贊同,並委由我協調籌備事宜。
一月下旬我出席由獨立青年陣線主辦、台灣教授協會協辦的冬令營,剛好遇到前來營隊進行專題演講的吳介民(當時任教於清大社會所)、何明修(台大社會系)兩位老師。我當面邀請兩位老師共同策畫「台灣社會力分析」研討會,他們也爽快應允,何明修並建議邀請作家丁允恭參與策畫。營隊結束前,我們敲定了研討會將以年輕世代為主要撰稿者,何明修則負責邀約研討會的參與人選。
籌備期間(3月~9月)共開了七次會議,先後確定了研討會主題、文稿的撰述方向與撰稿者等事宜。經過幾個月來熱烈的討論與協力合作,終於在2013年10月5日假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行「2013年台灣社會力分析──閱讀世代關賤字」研討會。
本書便是該次研討會的論文集結。能夠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何明修老師、吳介民老師和丁允恭先生在百忙之中參與策畫、審稿和校訂等繁瑣工作。
其次要感謝這些優秀的年輕執筆者,沒有他們的認真研究,就沒有本書的誕生。
最後要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執委會與秘書處同仁的全心全力支援,讓本次研討會的舉辦與本書的出版圓滿完成。
總審稿序
學運前夕的青年世代速寫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教授)
2014年春天,為了抗議《服務貿易協議》強行闖關,青年學生佔領了立法院。就如同春雷喚起了在土壤中沉睡的生命,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社會已經被徹底翻轉過了,再也回不去以往的寂靜與漠然。
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一場本來看似隨時要被驅離逮捕的公民不服從行動,可以在議場內苦撐二十四天,最後換得國會議長的政治承諾,得以「光榮出關」?為什麼有好幾百位醫生、律師願意放下私事,陪同青年學生一同輪班佔領立法院?是哪一種精神的感召,激發出無限的創意與靈感,使得藝術專業者進行「文化干擾」,視覺創意人士用「設計翻轉社會」,電腦高手「用鍵盤拆政府」?從後山到金門,反服貿遊行在街頭登場;從南到北,有一度全國的國民黨地方黨部與民眾服務站都被民眾包圍。無論三三○大遊行的參與規模是主辦單位宣稱的五十萬人,亦是警方有特殊計算方式所指認出的十一萬人,那無疑是台灣史上最盛大的集會活動。在當晚的凱道上,當林飛帆帶領群眾高喊「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無疑地,一個新的政治世代已經誔生。
的確,2014年就是台灣的「1968年」。在青年熱血沸騰的年代中,理想主義釋放出無所畏懼的力量,想像與現實的界限被打破了,一切都成為是有可能的。也只有在這場集體亢奮中,我們才重新發現,並且更真實感受到串連起我們彼此的共同連帶,也激發出深藏在我們身上的各種潛能,讓我們敢於去從事以往再三卻步的事。
從野草莓到太陽花
促成3月18日當晚學生衝入立法院的原因,並不只是前一天服貿審查的「半分忠」鬧劇,那至多只是引爆的導火線。過去幾年來,青年學生已經在街頭上橫衝直撞,挑戰他們所看到的各種不公不義之事。
回顧台灣的學生運動史,在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之後,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學生所主導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2008年11月,為了抗議中國特使陳雲林訪台期間的警方執法過當,全台大學生發起了野草莓運動,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靜坐抗議。他們提出三點訴求,要求(一)總統、行政院長道歉,(二)警政署長、國安局長下台,(三)修改集會遊行法。在馬政府不理不睬的因應下,野草莓運動後來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一直到隔年一月才正式落幕。在當時,三項訴求都沒有達成,一直到2014年3月21日(也就是反服貿學生已經佔領立法院三日後),大法官會議才釋憲認定,集會遊行法對室外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採許可制是違憲的規定。
儘管野草莓運動看似是失敗的,但是卻預示了新一波的學生行動風潮。學生在之前的一個普遍態度就是厭惡政治,不想要接觸政治人物,覺得兩黨都一樣爛,公共事務很難激發出他們的熱情。在野草莓興起之前,許多校園異議性社團已經停止活動,學運幹部都是透過PTT的版面動員,沒有事先的信任基礎。在野草莓學運之後,一批新的學運幹部浮現,他們陸續參與後續各式各樣抗爭,不斷地磨練論述與動員的能力。早在2012年底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已經出現了明星級的學運領袖,形成了全國規模的人際關係。
在野草莓學運動之後,各大校園紛紛出現新的異議性社團,例如成大的零貳社、清大的基進筆記社、中山的放狗社、中正的牧夫們社、陽明的有意思社等。原先已經停擺的傳統異議性社團也重新登場,例如台大的勞工社與濁水溪社、東海的人間工作坊等。再加上網路社交媒體的風行(臉書是在2008年才開始中文化),一個彼此密切連繫、能夠迅速行動的學生運動社群已經形成。
仔細觀察,2008年以降,學生參與的社運議題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首先是關於公平正義的議題,例如士林王家、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南鐵東移的拆遷與都更爭議,涉及土地徵收與開發的國光石化、大埔案、美麗灣,弱勢勞工的抗爭,如華隆罷工、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這些議題都呈現了戲劇化的對立,一方是有政府撐腰的大財團,另一方則是孤苦無援的弱勢居民。在這些大衛對抗巨人的戰役中,學生義無反顧站在弱勢者的陣營,很多時候,也是由於他們的介入,才扭轉了原先不利的情況,甚至取得最終的勝利。這顯示,有相當多學生已經看破了「拼經濟」的迷思,發展主義所帶來的並不是普遍的福祉提升,而是不折不扣的掠奪窮人、圖利富人。
另一類議題則是涉及中國因素對於既有生活方式的衝擊。在野草莓學運中,學生感受的不滿是,為何陳雲林來訪,路上的中華民國國旗要被隱藏起來,但是平常他們卻可以拿同樣的旗幟為國家代表隊加油?同樣地,在2011年底出現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起初只侷限於少數學者,到了2012年夏天之所以激發學生的關切,是因為旺中集團假借「走路工事件」揚言控告在臉書轉貼的陳為廷。當中國因素干涉青年學生使用臉書的自由,直接導致了大規模的學生抗爭風潮。
回到這次引發太陽花學運的服貿協議,從2013年6月21日兩岸兩會在上海正式簽定之後,就出現許多反對與質疑的聲音。對於青年學生而言,這一方面是公平正義的議題,因為大財團有可能受益,但是犧牲的卻是中小企業,同時這也是中國因素的問題,意味著兩岸進一步的經濟整合。換言之,正是由於同時觸及了近年來兩條學生運動關心的主軸,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才會激發出廣泛的學生與年輕世代的參與。
年輕世代的心靈圖像
收錄在這本合輯的文章,最早發表於2013年10月5日,一場由台灣教授協會所舉辦的研討會。當時服貿協議仍在立法院進行公聽會的程序,三天之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就在凱道上發起抗爭。透過這九篇「關賤字」,我們可窺見年輕世代的世界觀,理解他們在發動佔領立法院前夕,如何經歷與感知台灣社會。在不同程度上,九位作者都參與了太陽花之前的各種青年抗議活動;在這場學運中,他們也分別扮演了從總指揮、海外動員、後勤支援等的角色。理所當然,他們的觀點並不代表目前年輕人的平均值;事實上,正由於他們屬於有批判思考、獨立論述能力的那一群,他們所共同呈現出來的台灣圖像,講出了同年齡層的心聲,也因此,他們的訴求有可能成為這個世代的共同行動。
仔細閱讀這九篇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若干共同的線索。首先,他們是一群具有強烈世代意識(generation consciousness)的青年人,七八年級生明確感受到,他們將來不會再走前一代人走過的軌跡。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所有時期的青年人都會浮現他們的世代意識。在很多時候,年輕人只具有年紀意識,他們與前一輩人的差別只是比較晚出生,接下來他們要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樣的。從〈白海豚〉、〈22K〉、〈帝寶〉三篇文章中,一個共同主軸就是年輕人認為他們的機會被剝奪了。在經濟上,他們受到低薪化與高房價的雙重壓迫,二十幾前年林強高唱的「阮欲來去台北打拼,啥物攏不驚」,如今已經無法想像。面對各種掠奪土地與資源的開發案,年輕人的感受是「青年環境不正義」,他們的不滿就是來自於滿目瘡痍的環境,將是由他們來承受。
其次,他們也發展出與上個世代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們的價值觀更開放,較少承擔了先前的成見。從這群年輕世代開始懂事以來,原住民已經在政治上獲得正名,儘管仍在社會與經濟上處於被邊緣化的地位。因此,他們不需要像上一個世代,需要努力掙脫漢人殖民主義的遺毒,重新學習如何「把原住民當人看」。同樣地,對於稍微年長一點的世代,中國的威脅是文攻加武嚇,例如1996年的導彈危機與2000年朱鎔基「搞台獨沒有好下場」的警告。但是對於年輕的一代,中國因素已經跨越了海峽中線,直接進入本土社會,具體展現在學校中的「陸生」、風景區的「陸客」,以及台北動物園的貓熊。奇特的是,更加緊密的兩岸交流並沒有帶來威脅感的降低,反而使得新世代的中國圖像碎片化,無法拼湊出一個整體的全貌。最後,儘管當前的執政者試圖修改課綱,消除學生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理解,但是青年行動者卻很認真看待轉型正義的課題。他們反對校園中的「蔣公」銅像,用音樂會紀念二二八事件。上一個世代處於分裂的狀態,迫害者忙於掩飾大規模人權侵犯的罪狀,受害者則是要求討回公道,還原真相。但是這群年輕人卻是以和解共生為出發點,希望透過不同群體的生命故事進行對話,來達成相互理解的可能。
網際網路與移動通訊是在1990年代末期才開始開普及,年輕世代可以說是所謂的「數位原生民」(digital natives),他們很難想像要準備零錢打公用電話、在圖書館用紙卡查書、在校園門口排隊看入學考試榜單的年代。更迅速即時與無遠弗屆的資訊流動,也形塑了一種直言不諱、直白明快的語言風格,他們不能容忍難以啟齒、遮遮掩掩的禁忌,特別厭惡口是心非的道德偽善。當政客用「看報紙才知道」的遁詞來逃避公眾的質問,他們覺得這是外星人的回覆,他們因此偏好「打臉文」,直接揭露言行不一的公眾人物。「天龍人」一詞的出現,就是為了要指認出某個具有霸權地位的文化評斷標準,使得中南部的本省人受到歧視待遇。這明明是一個日常生活經常遇到的現象,主流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卻視若無睹,彷彿提到這個詞就是要撕裂台灣,破壞族群和諧。事實上,特意隠蔽歧視的現實,就是讓歧視更加恆久化,這一點青年世代看得很清楚。在過去,主流媒體代表最權威的訊息來源,其專業形象為社會大眾所共認;如今,年輕人的實際感受是,PTT八卦版或是名人的臉書專頁,居然會成為電視台所報導的「獨家新聞」!於是「腥聞」、「霉體」、「妓者」等貶損性辭彙成為流行,意味著青年世代看穿了主流媒體的空洞與虛無。
最後,這一代的年輕人享有多元自我實現的管道。有些人企圖仿傚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召喚「全台灣的魯蛇們團結起來」,也些人選擇從沉重的社會現實逃逸,沉浸於自己建築起來的「小確幸」世界。事實上,成為一個正港的「文青」是一件要時時提高警覺的自我修練之道,一方面要區隔出「假文青」的拙劣仿傚,另一方面還得躲避「反文青」的民粹挑釁。
太陽花世代的下一步
總結來說,台灣目前的青年人具有明顯的世代意識,他們自認為是屬於機會被剝奪的一群。他們少有上一代的成見與歧視,直白明快是他們的表達風格,而且他們也享有更多元的生活方式之選擇。很顯然,這些世代特色都展現在太陽花學運。這不是一場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運動,它拋棄了傳統「忠君愛國」的文化脚本,是從年輕人日常生活文化汲取文化元素,例如各種kuso、反串、反諷等的語言表達形式。儘管議場內的指揮系統是太陽花學運的靈魂,但是議場外各種自發性形成的次團體與活動,真正展現出這個世代年輕人的創意與不受拘束的自由心靈。
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是高度戲劇化的儀式,象徵太陽花世代的政治成年禮。在1971年,許信良、張俊宏等人用《台灣社會力分析》一書宣告了戰後新生代的誔生,在接下來的七○年代,他們開創了知識份子的公共領域,催生了黨外運動,撼動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同樣地,太陽花世代也是承擔了他們所要解決的時代任務。面臨政治民主的失能與倒退,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日益顯著的中國因素,目前的政治領導者沒有展現願景與視野,也無法提出解決因應之道。很快地,這些挑戰將落在太陽花世代身上,而他們獨特的世代經驗與世界觀,將會是引導台灣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導言
閱讀世代關賤字
丁允恭(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
當前台灣社會力分析
1971年,由許信良、張俊宏等人,於大學雜誌發表「台灣社會力分析」系列文章,引起台灣社會普遍的關注。這一系列社會力分析,事後來看,其內容與主張或許進步性有限,所造成的影響多少也不無疑問,但卻具有相當的先驅意義,甚至在某些人的眼中,成為更之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中,重要的初步嘗試之一。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力分析」在戒嚴時代的台灣開啟了、或者說是引入了一個範式,即「沒有調查、沒有發言」,它告訴我們:在進行社會改革以前,必須先對社會進行了解與描述。
現在,面對眼前的社會,我們也想做點什麼。於是,我們開始探索在2013年的當下,屬於我們這個世代、這個時代的台灣社會力分析。我們要問:橫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樣的台灣?其中潛伏著怎樣的社會力?在眼下的這個時代,我們要如何去挖掘、整理社會問題的面貌,並且加以解析?
進行整個分析之前,我們必須選擇一條路徑摸索而上。經過反覆的討論後,我們企圖透過解讀、展開在年輕世代的言說間最為流行的網路關鍵字,來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為什麼是關鍵字
為什麼是關鍵字?這要從時代與世代的特殊性來看。
這是新世代解讀新世代的社會力分析,我們決定要從新世代認知社會的模式出發,開展我們的討論。這甚至是一種思考模式上的差異。好比說過去的社會力分析,像是某種改革的地圖或是航海圖,而我們現在所找的是google map。
「關鍵字」的概念,雖然早於網路時代即已存在,但是到了網路誕生、頻寬加大,瀏覽器成為主流工具,同時網路使用成為庶民日常必需之後,「關鍵字」就不再只是圖書館學的術語,而是路人皆知的用語。
進一步聚焦到青年世代。網路並不是這個世代的新興工具而已,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本身就是這個世代。因為這樣,關鍵字更成為新世代思考與理解社會的方法:看到一個詞彙,然後上奇摩知識家丟出問題,或是到google與wikipedia自己做資料探勘。透過搜尋引擎的資訊管道,對事物獲得不同層次的了解,找到定義、特質、相關敘事,再經過超連結,找到觀念的外延,這就是網路世代建構知識體系的方式。關鍵字彼此之間的超連結,也會形成概念的展開、延伸,並在網路的言論空間上,形成下一次發揮、改作的文本。
另一方面,在高速運轉、資訊爆量的社會裡面,將訊息進行篩選、整理、簡化、次序化,創作所謂「懶人包」,成為新世代形成觀念的重要工具。關鍵字再加上懶人包,成為新世代描述世界的慣行方式。這樣的懶人包或許正如其名,失之簡略與疏懶,但卻直捷地表達了新世代的概念操作。我們的工作,就是透過對關鍵字的解析,把這一個個懶人包展開、深掘,看見背後的社會圖像。
這些關鍵字往往是微小化的世代論述,具體而微地呈現年輕人對社會最真實的感受。我們也都知道,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產物,並非單一或少數的個體可以發明、可以改變。年輕人之所以對這些詞彙朗朗上口,甚至形成風潮,是因為這些詞彙在同一世代、乃至於整個社會之中,具有高度的共識性,與大眾的經驗相互符應,所以一旦被丟出,即能獲得廣泛的共鳴,進而傳頌千里。
我們更期待,透過使用這些詞彙,進入新世代普遍的語境,讓年輕人們在使用這些詞彙的同時,對自己的處境以及想像進行反思,隨後採取行動。相信這樣,能讓我們的討論結果,產生更加廣大的影響與擴散。
關鍵字又如何變成關「賤」字
進一步我們要問:關鍵字又怎麼變成了關「賤」字?「賤」是貧賤的賤,也是作賤的賤。
我們所選取的關鍵字,都是充滿嘲諷、戲謔的負面用語,主要源自PTT等青年世代熱門的網路論壇。就像作為「loser」諧音的「魯蛇」,這樣的字眼在網路上風行,既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作為一種能指,既指向台灣社會目前客觀的貧窮、失能、缺乏機會,也指向青年世代主觀上的自我感覺不良好。
這些關賤字接近於市井街坊慣用的俚俗用語,而非體面堂皇的論述語言。使用這些詞彙,凸顯了年輕世代在主客觀情勢的失落下,對於所有一表正經的事物失卻信任,而寧可採取玩世不恭的姿態。犬儒背後,往往藏有滿滿的憤怒。
讓我們舉一些關賤字的例子來看看。
譬如說「22K」,從一個教育部的社會新鮮人就業輔導政策,變成網路上借代整個青年勞動貧窮化的關賤字,我們所看見的是:向下看齊的薪資政策、cost-down的產業發展、與階級流動功能喪失的教育體系,為年輕人標下低廉的價格/價值。22K這個數字,就是青年的集體自我認知:賤人、下流社會化,亦即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魯蛇」。甚至,這些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的問題,還引動青年世代的焦慮,轉化成為內部的歧視排序,成為網路上流行的「戰學校」、「戰科系」,還有像「到國立真遠」這樣的負面標籤。
與它對應的另一個關賤字是「小確幸」。為什麼一個來自日本輕文學的詞彙,會在台灣造成遠比日本本土更廣大的效應?為什麼它會成了年輕人所追尋的美好境界?而如果它是一種被認可的生活方式,為什麼網路上又會嘲諷地列出「文青的一百項指標」?當追求偉大夢想已成為不切實際的神話,賣雞排開咖啡店的小夢想又真的能確切實現嗎?小確幸固然夠小,但因此就能夠「確」、能夠「幸」嗎?這是另尋一種天堂入口,還是抱頭鼠竄的出口?
又譬如說「天龍人」作為一個常用於譏笑嘲諷他人的關賤字,我們所看到的是:這個國家缺乏發展正義,造成南北、地域、城鄉、族群的落差,也因此成為語言、投票行為、區域發展想像,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分野,以致在網路上應運而生「戰南北」的話題。而一龍還有一龍龍,天龍國中還有更細緻的階序存在,就像之前郭冠英聲稱「住到低級區域南港」,所引發的再一次爭議新聞,正是這種綜合矛盾的奇特反諷。
又譬如說,我們可以從「426」這個指涉中國人的貶義詞彙如何應用與背後所帶有的情緒,來探討兩岸關係的轉變演進,對不同時代與不同世代,造成什麼樣的心理與社會效應?包括我們對中國人的看法或想像,有什麼樣的變化?像是從國民黨反共教育下歷經大煉鋼苦難的同胞,一躍而成滿手鈔票的陳光標?又像是從布滿沿海的幾千顆導彈,變成塞滿六合夜市的幾萬個陸客?一個「26」,各自表述,然而這表述卻關係到國家認同的邊界何在,以及對中國的想像為何。
許多關賤字反映出台灣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爭議。譬如記者變成了「妓者」,從記錄的「記」變成了娼妓的「妓」,顯示在新聞倫理的崩壞下,過去被稱為無冕王的記者失去了閱聽者的信任,社會形象轉趨敗壞。我們要問的是,除了個體的職業倫理要求以外,新聞工作者是否也如同台灣其他產業的勞動者,往往因為來自企業主的高壓,扭曲了本身的勞動文化?而在商業置入橫行、媒體壟斷猖狂的爭議下,這樣的情況是否有變本加厲?
又像是「帝寶」,從一個豪宅建案的名稱,轉變成為階級妒恨的出口、代稱炫富者的關賤字。這是否反映了台灣幾近瘋狂的土地投機炒作,不僅像黑洞一樣吞噬了經濟發展的動能、擴大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同時也構成嚴重的住房問題,讓青年視購屋為不可能的夢想?台灣近年四處烽火的土地開發爭議,與這樣的土地炒作無法割離關係。
還有「蔣公」這個詞彙,本來在民主轉型後,已經慢慢消失於新世代記憶之中,但在前獨裁政黨重新執政後,對民主體制的尊重程度每下愈況,一切彷彿蔣氏父子復辟,一度成為敝屣的銅像,又再度在高堂上受到敬拜。一場荒謬的「蔣公設計獎」,引發網路上排山倒海的嘲弄,讓蔣公重新登上網路關賤字,也讓新世代感受到台灣民主化前的荒謬場景。對於戒嚴時代的歷史問題,我們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檢討與評價?民主的價值是否有因此而確立?當政府再度走上獨裁暴政之路,我們的人民是否能夠起而加以抵禦?因為王金平關說案所引發的監聽風暴,正是最好的試金石。
有些名人光怪陸離的發言,不但引起新聞爭議,也轉化成為社群網路上的重要關賤句,像吳敦義的「白海豚會轉彎」,或像馬英九的「我把你當人看」。前者凸顯出當局對原住民尊嚴的輕賤、後者則顯現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中,環境價值的被賤視。透過這些統治者失言所轉變成的關賤字,我們看到的是,無論是民族間的正義,或是環境的正義,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如此匱乏,亟待補完。
從本書的每一個關賤字,我們看到了人民主客觀上淪落為賤,因而深感憤慨,也積蓄反抗與改革的動能。透過這些關賤字,我們期望能看見這個時代、這個世代及其不滿,找出「賤之何以為賤」,更要探問「何能不賤」,從反作用力尋找社會力,以及苦悶台灣出路的可能所在。
策劃者序
發現當下台灣社會力
張信堂(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回顧1970年代初,美國尼克森政府為了解決越戰問題以及推動「聯中抗俄」政策,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導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處境岌岌可危。當時接班態勢明顯的蔣經國,則是在「四二四刺蔣案」與「保釣運動」後,藉由各種「革新」或「保台」言論以營造其改革形象。
面對讓人焦慮不安的變動時局,張俊宏、張紹文、包弈洪、許信良等台灣青年,在1971年10月的《大學雜誌》發表〈台灣社會力分析〉,希望「喚醒大家愛自己所能愛的社會,關心自己可以關心的人群,了解他...
目錄
策劃序 張信堂(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總審稿序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導言 丁允恭(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
【小確幸】……………………………………………………………………陳宗延
小而真確的幸福,可以是寒夜裡一杯熱茶的生活體驗,也可以是人與人間微小的溫情。在整體青年就業環境惡化的情勢下,概念進一步延伸,成為把握大不幸裡面的些微希望的時代精神。
【22K】……………………………………………………………………吳駿盛
政府每月提供給企業的補助金額,用以雇用社會新鮮人到職場實習。網路上以此指稱在勞動市場上失敗的競爭者。大部分的情況下,這並不是拿來嘲笑他人,而是用以集體性的自嘲,呈現一種絕望的世代氛圍。
【帝寶】……………………………………………………………………林彥彤
台北市仁愛路上前中廣所在地釋出後,興建名為「帝寶」的住宅社區,因為地價變成天價,於是成為全國豪宅的標竿。自此,帝寶成了誇富與仇富的主戰場,還有全國形象不良有錢人的主舞台。
【腥聞霉體妓者】…………………………………………………………林飛帆
網路上所慣用的「霉體」、「妓者」,就是媒體與記者的諧音,從過去的第四權、無冕王,淪落為今日不堪的字眼,反映出媒體產業社會形象的江河日下。然而他們的權力卻未曾削弱。
【白海豚】……………………………………………………………………江昺崙
即使國光石化建廠填海,原本迴游路徑被阻斷的白海豚也會自動轉彎。這是現任副總統吳敦義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所提出的動物行為學學說。不過,最後轉彎的是興建國光石化的政策,以致我們沒有機會驗證此一假說。
【天龍人】……………………………………………………………………廖偉翔
一種身分界定:原本是地域上的,作為具有優越感的台北人的代稱。而後轉化為階級上的,指稱社經階級頂端的既得利益者,與「藍血貴族」、「溫拿」等概念重疊。由天龍人衍生出「天龍國」,指稱作為首都的台北市。
【把你當人看】………………………………………………………………陳以箴
馬英九「失言錄」一例,除了語言上的荒謬外,更指向我們社會裡面根深柢固的歧視,並化為種種實質的壓迫。不被當人看的人,不是只有當天在場的原住民而已;而不把人當人看的,更不只是馬英九而已。
【426】……………………………………………………………………林邑軒
對中國人帶有蔑視意味的稱呼,取台語「死阿六仔」的諧音,是兩岸逐漸開放互動以後的產物,一如「大陸妹」的稱呼,取代了過去戒嚴時期只有「大陸同胞」與「共匪」的官式想像。
【蔣公】……………………………………………………………………林彥瑜
威權時代對於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蔣介石的官式敬稱,民主化以後逐漸隱沒,政黨二次輪替後又還朝復活。隨著蔣公銅像遷移爭議與文建會「台灣設計蔣」風波,移除「蔣公」成為台灣實踐轉型正義的一項未完成工程。
策劃序 張信堂(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總審稿序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導言 丁允恭(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
【小確幸】……………………………………………………………………陳宗延
小而真確的幸福,可以是寒夜裡一杯熱茶的生活體驗,也可以是人與人間微小的溫情。在整體青年就業環境惡化的情勢下,概念進一步延伸,成為把握大不幸裡面的些微希望的時代精神。
【22K】……………………………………………………………………吳駿盛
政府每月提供給企業的補助金額,用以雇用社會新鮮人到職場實習。網路上以...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