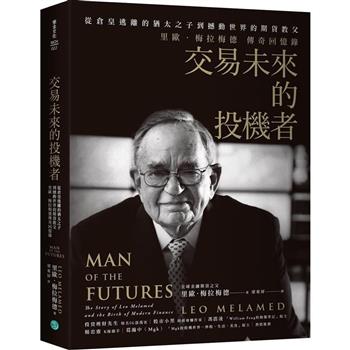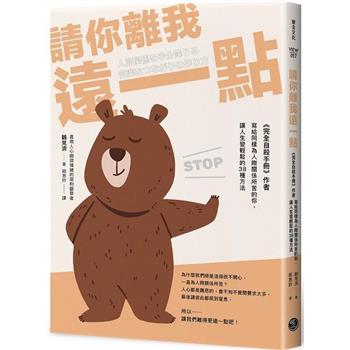如果你不為愛賭博,
還要為什麼賭?
if you're not going to gamble on love,
what should you gamble on?
考據莎士比亞佚失劇本,當代頂尖劇作家全新創作
哈佛大學全球戲劇交流計畫,在地改編跨國演出
據傳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一齣情節取材自《吉訶德先生傳》的劇作,名為《卡丹紐》,但原作早已佚失。2008年,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當今英美學界莎學大師、2012普立茲獎得主葛林布萊,以及知名百老匯劇作家查爾斯•密,合作將這個故事改編成美國現代話劇,在美國上演。之後哈佛大學更推出跨國的「卡丹紐計畫」,從日本到巴西,在十一個國家以不同語言、多元形式改編上演。
2013年7月,中文戲曲版由彭鏡禧、陳芳編劇,李寶春導演,陳長燕、李侑軒、朱錦榮主演,為這場文化流動實驗的壯舉,畫下完美的句點!
卡丹紐計畫網址:http://www.fas.harvard.edu/~cardenio/
劇情簡介:
卡丹紐和盧仙妲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在尚未徵得雙方父親允諾婚事前,卡丹紐就被迫離家,到一個權貴的宮廷服侍,成了貴族之子斐南度的親密好友。
斐南度曾以結婚為餌,誘姦過出身卑賤的德若苔,而今反悔;為了躲避德若苔,就隨卡丹紐返鄉。在那裡,不負責任的貴族之子立刻愛上了盧仙妲。斐南度藉故支開他的朋友卡丹紐,向盧仙妲的父親提親;盧仙妲的父母樂於高攀,遂不顧女兒反對,斷然答應這門婚事。
極度失望的盧仙妲寫信給卡丹紐,他急忙趕回。抵達時,卻只能從簾幕後面目擊結婚典禮。他看見所愛之人伸出手來應許嫁給給奸詐的斐南度,便絕望地衝出現場。他沒有看到盧仙妲在那最重要的一刻暈倒了。在她的緊身胸衣裡發現一張字條,宣稱她要刺殺自己。於是,斐南度勃然大怒,氣極奔出。盧仙妲則逃到一間修女院。
對這些後續發展毫不知情的卡丹紐棄絕了文明,一如荒野中的李爾王,像瘋子般遊蕩於席厄拉山脈。於此同時,被始亂終棄的德若苔聽說斐南度和盧仙妲的婚姻無效,就出去尋找他。她跟居里雅及其他許多莎士比亞的女主角一樣,打扮成男孩子,然而這項權宜之計並無法保護德若苔。她為了免遭姦污,把侵犯者推落山崖。之後她也逃到席厄拉山脈。
六個月過去。斐南度發現盧仙妲在修院,就劫持了她。卡丹紐和德若苔在山間偶遇;德若苔告訴他,盧仙妲在字條裡宣告自己因為已經許身卡丹紐,所以不能嫁給斐南度。卡丹紐因而重新燃起希望,神智也恢復清醒。斐南度和被挾持的盧仙妲也恰巧來到同一家客棧。德若苔責備斐南度不該如此待她,斐南度羞愧之餘,答應娶她為妻,讓卡丹紐得到盧仙妲。皆大歡喜。
產品特色
1. 由國際頂尖莎劇研究專家及知名百老匯劇作家,根據莎士比亞佚失劇本全新創作,並由台灣莎劇專家彭鏡禧教授中譯,是所有關注戲劇的讀者必讀佳作。
2. 由哈佛大學支持的跨國改編「卡丹紐計畫」,已在全球十一個國家上演,台灣是最後一站,意義非凡。
3. 2013年7月原作劇本英漢對照版本Cardenio《卡丹紐》、彭鏡禧及陳芳改編的中文戲曲版本《背叛》(附英文翻譯)同時出版,並由文化大學戲劇學系製作演出,葛林布萊教授並專程來台演講、觀戲,為台灣戲劇界留下跨國合作演出的精采紀錄。
作者簡介:
葛林布萊 Stephen Greenblatt
當代重要文學評論家、理論家及學者,於歷史、文化研究、文藝復興研究及莎士比亞研究著作宏富,咸認是相關領域的頂尖專家。近作《轉向:世界如何變為現代》榮獲2011年非文學類組美國國家圖書獎,以及2012年一般非文學類組普立茲獎。
An influential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 theorist and scholar, Stephen Greenblatt has written and edited numerous books and articles relevant to new historicism, the study of culture, Renaissance studies and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leading expert in these fields. His most recent work 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won the 2011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Nonfiction and 2012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查爾斯‧密 Charles Mee
美國知名劇作家,曾榮獲美國藝文學術院終身成就獎。著有劇作數十種,其中不乏具開創性與實驗性的作品。他深信「沒有所謂原創劇本」,因此設置了「(再)書寫計畫」網站,提供許多自己的文本供創作者免費改編之用──但不得僅是翻譯。
The recipient of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Charles L. Mee has written many plays, including Big Love, True Love, First Love, bobrauschenbergamerica, Orestes 2.0, Trojan Women: A Love Story, Summertime, and Wintertime. Believing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original play,” he has started “ the (re)making project” (http://www.charlesmee.org/about.shtml), offering many a text for free adaptation.
譯者簡介:
彭鏡禧
現任臺大名譽教授、輔仁大學客座教授、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曾獲第一屆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及散文翻譯第一名、中國文藝協會翻譯獎、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榮銜、臺灣翻譯學會榮譽會員榮銜。研究領域為莎士比亞、文學翻譯、跨文化戲劇。編、著、譯作品約四十種。
A Shakespearean scholar, Ching-Hsi Perng has to his credit many books, includ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Hamlet,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nd Measure for Measure. He has co-authored (with Fang Chen) Bond and Measure, Measur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adapted respectively from Merchant and Measure.
章節試閱
【劇本摘錄】
劇中人物表
安塞摩 (ANSELMO) 甫結婚的新郎
威威(WILL) 伴郎;安塞摩的好友
卡蜜拉(CAMILA) 安塞摩的新娘
艾德蒙(EDMUND) 賓客;伴娘莎莉的丈夫
莎莉(SALLY) 伴娘
多麗(DORIS) 卡密拉的姊姊
席夢妮妲(SIMONETTA) 管家;廚師梅可瑞的妻子
露宜莎(LUISA) 安塞摩的媽媽
阿福瑞(ALFRED) 安塞摩的爸爸
素珊娜(SUSANA) 職業演員;安塞摩、威威、莎莉等的大學朋友
如迪(RUDI) 木匠;阿爾巴尼亞難民
梅可瑞(MELCHIORE) 廚師;席夢妮妲的丈夫
幕啟前,
觀眾席的燈漸暗,我們聽見:
吉他彈奏出
Antoine Francisque (c. 1570–1604) 的〈長笛三舞曲〉庫倫特舞曲,
止歇於幕啟後不久。
我們處於
溫布里亞
一座石造農家前的石頭露台上。
橄欖樹
群花
葡萄藤。
舒適的戶外座椅散置於露台。
屋內傳來宴會的聲音。
(威威和安塞摩出現,手握香檳酒杯)
威威:何其完美的婚禮,安塞摩!
完美極了!
你知道嗎,
你是我認識最幸運的人了
能娶到你太太這樣的女人
美麗
溫柔
這麼溫柔
而且聰明
而且充滿生命力
(靜默)
安塞摩:對。
威威(笑):難道不對嗎?
安塞摩:你知道嗎,說來瘋癲,
但我懷疑她是不是愛我。
威威:她是不是……什麼?
(又笑)
的確瘋癲!
安塞摩:我知道。
可是
我揮不掉這個念頭。
我是說:
我怎麼能確定她愛我?
人怎麼可能建立感情結構的穩定基礎?
我怎樣才能在這裡有把握,
在我生命的最中心?
威威:安塞摩!
安塞摩:你要知道,威威,
她年輕,她衝動,率性──
我是說
這些特質很吸引人
這些特質使我一頭為她傾倒
而更重要的是
這些特質使她為我傾倒。
約會一次半加上兩通電話長談,
一次談的是羅斯科 ,另一次談的是德西達 ,
我就說:「妳嫁給我好嗎?」
她就莫名其妙地說「好。」
可是我又想:
她這些個特質將來會不會使她突然又愛上別人?
威威:安塞摩。
安塞摩:我就是沒法子擺脫這個苦苦糾纏著我
不肯放的念頭。
威威:什麼念頭?
安塞摩:我想她會對我不忠實。
(靜默;
之後威威笑起來)
威威:你神經病。
她愛你。
我沒見過有誰愛一個人
像她那麼愛你。
她就是那種人
一個絕對忠實的人她就是那樣
而且她對你的愛會天長地久。
我見過的人多了,
你可以看出
這位愛你的是個忠實的人。
沒有人比你更幸運了。
安塞摩:對。
威威:當然對,我一直認為
你聰明透頂,
你學習的智力這麼高強。
安塞摩:拜託。
威威:可是,也許因此使你有點像牛頓。
安塞摩:牛頓?
威威:以薩‧牛頓 。
有人說,他的頭腦總是動得太快
所以他早上要起床的時候
得先在床沿坐上
兩三個小時
把頭腦理清了才下床。
你,
你這個人
被你自己──有這麼點──過熱的智力
搞昏了頭。
也許你只是有一點
過份地愛分析。
安塞摩:對這件事沒有過份。
威威:正是對這件事過份。
安塞摩:而且如果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威威:我是……
安塞摩:你就會幫助我。
威威:我會幫助你。
安塞摩:你會?
威威:會。
安塞摩:不顧一切。
威威:不顧一切。
安塞摩:那就為我做這件事
看看你能不能引誘我太太
這樣我就知道可不可以信得過她。
【劇本摘錄】
劇中人物表
安塞摩 (ANSELMO) 甫結婚的新郎
威威(WILL) 伴郎;安塞摩的好友
卡蜜拉(CAMILA) 安塞摩的新娘
艾德蒙(EDMUND) 賓客;伴娘莎莉的丈夫
莎莉(SALLY) 伴娘
多麗(DORIS) 卡密拉的姊姊
席夢妮妲(SIMONETTA) 管家;廚師梅可瑞的妻子
露宜莎(LUISA) 安塞摩的媽媽
阿福瑞(ALFRED) 安塞摩的爸爸
素珊娜(SUSANA) 職業演員;安塞摩、威威、莎莉等的大學朋友
如迪(RUDI) 木匠;阿爾巴尼亞難民
梅可瑞(MELCHIORE) 廚師;席夢妮妲的丈夫
幕啟前,
觀眾席的燈漸暗,我們...
作者序
【譯後記】
再見《卡丹紐》
彭鏡禧
沉寂數百年後,《卡丹紐》重現江湖!譯完這齣頗有特色的劇作,覺得它的流動有幾點值得一記。
首先是這齣戲的創作概念緣起。作者之一葛林布萊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也是當今文學、文化研究方面的重量級學者。根據哈佛「卡丹紐計畫」網站(http://www.fas.harvard.edu/~cardenio/index.html)的說明,他企圖藉這齣戲探討(或印證)他的「文化流動性」(cultural mobility)理論。戲劇「原作」有它創作的背景,受到原文化、劇種的種種制約;當它跨越到另外一種時空,也就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時候,會產生怎樣的質變?這是有趣的研究課題。這齣戲已經在十一個國家以不同版本演出,許多相關資料也掛在前述網站上。能夠透過中文翻譯,並據以改編為傳統戲曲版,加入這一跨國實驗,應是極有意義的事。
查爾斯.密是美國當代劇作家,曾獲美國藝文學術院終身成就獎。深信「沒有所謂原創劇本」的他,設置了「(再)創造計畫」(“the (re)making project”)網站(http://www.charlesmee.org/about.shtml),免費提供許多自己的文本讓創作者自由改編──但不得僅僅是翻譯。這是文化流動的實踐,與葛林布萊的理念不謀而合。兩人合作改編《卡丹紐》這齣「莎士比亞佚失的一齣戲」,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粗略比較這兩齣戲,已可看到跨文化之後產生的驚人差異。原作主角卡丹紐和盧仙妲深愛對方,歷經種種艱險,才能重逢,見證了愛情的堅貞。來到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新郎和新娘相識不久,只經過「約會一次半加上兩通電話長談,一次談的是羅斯科,另一次談的是德西達」,就結了婚。大喜之日,新郎竟要他的伴郎誘惑自己妻子,以確定她是否真心愛他。這場速食婚姻果然經不起考驗,在喜宴之後就宣告結束;新郎安塞摩和新娘卡密拉都沒有通過測試:男的發現自己愛的是另一個女人;伴郎和新娘假戲真作,談起戀愛。卡密拉甚至鼓勵他的「前夫」追尋真愛:
當你找到了
你相信會天長地久的愛
你就不再有選擇權。
又說:
因為如果你不為愛賭博,
還要為什麼賭?
這番話正是她自己的心聲。因此兩人可以很快原諒對方,雙方算是頗有風度地分手,也是現代文明的「進步」現象。
在寫作技巧上,《卡丹紐》師法莎士比亞之處不少。安塞摩測試卡密拉,用的方法是戲中戲的演出,而戲中戲正是莎翁拿手好戲之一。在莎劇《哈姆雷》裡,哈姆雷王子為了捕捉叔父(國王)的良心,精心策畫了一齣戲,結果固然成功,卻也暴露了自己的意圖。《卡丹紐》的戲中戲演的不是別的,乃是「莎士比亞佚失的《卡丹紐》」!
阿爾巴尼亞難民如迪是戲裡一個逗趣的角色,活像《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極端自負的匠人霸臀(Bottom)的翻版。如迪不滿意自己被安排的角色,又想要搶別人的角色,害得導演連哄帶騙好不容易才搞定他。但一心想演獨角戲的他,最後還是如願以償,以戲中戲的內容,自行加演了一場戲中戲之外(應該說是另一場戲中戲)的精彩演出。光憑這一點,他就勝過霸臀不止一籌了。更何況,身為木匠的如迪,對舞台結構還有一套理論,講究簡單、平衡、穩固。這套理論,其實也可以運用於人生──包括愛情與婚姻,間接呼應了本劇的主題。劇作家讓工匠說出簡單的大道理,明顯諷刺(美國)高級知識分子的盲與茫:戲裡除了老一輩(也比較傳統)的阿福瑞和露宜莎(安塞摩的父母),所有來自美國的年輕人不是離婚就是有外遇。
大家敬酒祝福新人的時候,如迪也要求獻上阿爾巴尼亞祝婚詞:「雖然法律沒有『強制勞動』的條款,所有被判刑的人都送到『死亡礦坑』,去採挖鉻和黃鐵礦,在開敞的濕地……男孩轉大人,大人倏乎早死──那些定讞自殺的」。把男女婚媾說成男人的「強制勞動」刑罰,礦坑和濕地比喻女陰,結婚成了自殺行為。相對於其他人「愛河永浴」之類的陳腔濫調,這樣的葷笑話雖然不登大雅之堂,卻可能更符合實際。聽眾聽了目瞪口呆,或許因為聽不懂阿爾巴尼亞語,也或許被內容嚇壞了。這在莎劇其實早有先例。在純情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裡,莎士比亞讓羅密歐的朋友開黃腔,讓朱麗葉的奶媽追憶她丈夫當年對娃娃朱麗葉說的性交指涉,無非表明劇作家認為性愛乃是婚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遠從美國帶來「莎劇」《卡丹紐》的阿福瑞和露宜莎是劇中的長者,也像戲劇教授,特別對表演方法有強烈的意見。露宜莎鄙視
單單靠著佛洛依德心理學的老規則
那些個薄弱、簡化的見解
說明人之為人
好像我們
只是童年時期家庭動力的生物
而不包括
我們的社會
歷史和文化
這分明是新歷史主義宗師的化身。阿福瑞則逐字引用哈姆雷對戲班子的教訓,要求演員念臺詞要
在舌頭上輕輕說出:
如果你們扯著嗓門吼叫,像很多演員那樣,
我還不如讓街頭發布消息的來念我那幾行。
也不要用手過分地在空中揮舞,
如此這般;
一切都要中規中矩;
因為處在感情的洪流、暴雨、
乃至可以說是,旋風當中,
必須練就並生成不慍不火的功夫,
顯得平順穩當。
當觀眾抱怨戲不好看的時候,阿福瑞老實不客氣地教訓他們,要大家尊重劇作家:「承認也許劇作家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無論你們想法如何,他可能都已經想過……為什麼你們的看法會勝過他的?」而且,
說到個人喜愛
就像我爸爸常說的
「品味者,無可爭論者也。」
跟莎士比亞一樣,他們也論及戲劇與人生的關係。威威和卡蜜拉在戲中戲裡忘情深吻,冷眼旁觀的多麗指出兩人必定已經相愛,才能有如此逼真的表演。阿福瑞提醒大家:「這是大家常犯的錯誤──把他們在舞台上所見當作事實。」
露宜莎: 戲劇是非常逼真的藝術
會把我們不知不覺捲入其中。
阿福瑞: 然而,這是藝術。
露宜莎: 這不是人生。
但是,至少在這齣戲裡,藝術生動地反映了人生,莎士比亞的哈姆雷說過:
演戲的目的……好比是舉起鏡子反映自然;顯示出美德的真貌、卑賤的原形,讓當代的人看到自己的百態。……
旨哉斯言!
朋友背叛、奪友之妻的故事,無論中外自古有之。大膽把自己的女人交付朋友照顧的,不乏以悲劇收束者。《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的Claudio就慨嘆:
凡事都可交託你的朋友,
唯獨愛情必須自己保守。
Friendship is constant in all other things
Save in the office and affairs of love.
《卡丹紐》戲中戲裡,盧仙妲警告卡丹紐說:
以前沒有朋友背叛的事嗎?
小心哪,卡丹紐:愛情不可代理。
Is there no Instance of a Friend turn'd false?
Take Heed of That: no Love by Proxy, Cardenio.
因此,戲中戲和主戲的背叛主題互相呼應。只是由於時空的移轉、文化的變遷,劇中人物的反應與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說到背叛,作品的改編會不會是對原作的背叛?文學翻譯界有一句老生常談,認為翻譯像女人:忠實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實。改編乃是對原作的一種演繹,廣義說來,也可算為翻譯。它的對象是當代的讀者、觀眾,而這些人,跟他們的作者(改編者)一樣,受制於自己的時空、文化。無怪乎查爾斯‧密要說:「當然是文化先書寫了我們,我們才書寫自己的故事。」然則改編者改動原作,乃屬必要,不僅算不得背叛,反而要視為忠實──忠實於自己的時代、忠實於自己的文化、忠實於自己的洞見。
《卡丹紐》的故事從賽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在他之前想必還有前身──到莎士比亞和福雷徹,到奚額寶(Lewis Theobald),到葛林布萊和查爾斯‧密,到後者的十二種跨文化改編演繹,以及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2011年的新版等,多不勝數。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各個都不相同。與其說這些作品背叛原作,不如說是對「原作」的禮敬。而無論背叛或禮敬,都無關宏旨:葛林布萊深信莎士比亞不僅經常改寫他人的作品,也預期自己的作品同樣會被人改寫。今日我們再見《卡丹紐》,他日若又重逢於另一時空、場景,也無須訝異。真正重要的是:改編作品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即使莎士比亞並不在意,改編者仍須嚴肅以對。
【作者序】
莎士比亞佚失的一齣戲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許多作品,即使出自最偉大的作家,都已失傳,沒有留下蛛絲馬跡。埃司基勒斯(Aeschylus)的八、九十齣劇作,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約一百二十齣劇作,只各留下七種;尤瑞匹迪斯(Euripides)和艾瑞斯妥芬尼斯(Aristophanes)稍好一些:前者九十二齣留下十八齣;後者四十三齣留下十一齣。當然,他們都是 2500 年前古代希臘戲劇家。愈是接近我們的時代,重要作家的多數作品就愈有機會流傳下來。
至於活在 1564 到 1616 年間的莎士比亞,他的作品流傳更為複雜,因為他似乎對自己劇作的出版不感興趣,也沒有參與。不過他的名聲太響亮了,所以現知他的作品中,有一半在他生前印行過──大眾不僅樂意買票看他的戲,也樂意付錢讀他的劇本──其他作品則在他死後七年,由約翰‧何明斯(John Heminges)和亨利‧康斗(Henry Condell)這兩位友人兼演員夥伴精編出版(即「第一對開本」)。除了收入這部集子的劇作外,現代學術界只添加了一齣戲──一部叫做《兩貴親》(Two Noble Kinsmen)的晚期作品,是莎士比亞和後輩同事約翰‧福雷徹(John Fletcher)合寫的。
出道之初,莎士比亞最早期的幾個劇本是和一兩位當代作家共同執筆的。雖然團隊合作是戲劇的本質,但大部分冠上莎士比亞之名的作品似乎是他的獨立創作,至少他是主筆者。直到寫作生涯的晚期,他才又與人合寫;顯然他擇定了約翰‧福雷徹作為主要合作者及接班人。莎士比亞跟他合寫了《兩貴親》、一齣原名《都是真的》(All Is True)的歷史劇(現在通稱《亨利八世》[Henry VIII]),以及今已佚失的第三齣戲。
那齣戲叫做《卡丹紐》(Cardenio)。國王財務大臣檔案中,有這齣戲在 1613 年 5 月 20 日及 6 月 8 日各演出一場的記錄,註記了付款給何明斯。 1653年,書商亨福瑞‧莫斯理(Humphrey Moseley)在書業公會記錄簿(Sationer’s Register)──這是所有即將出版的作品都必須登錄的正式文書──登錄了「卡丹紐傳。福雷徹先生與莎士比亞著」。因此這齣戲毫無疑問曾經演出,而且起碼也曾公告周知其出版意圖。
莎士比亞和福雷徹的《卡丹紐》沒有一本傳世。失傳的理由並不清楚,但絲毫不令人訝異:十六、十七世紀的劇本,只有一小部份保留下來。當年沒有保存出版品的機制──沒有中央政府的收藏處──而大學圖書館員和私人藏書家不會蒐集當代劇本。儘管莎士比亞生前已頗負盛名,卻也要到十八世紀才被人狂熱崇拜到珍惜他生活和作品遺留下的點點滴滴,而這時候許多資料都已經亡佚,包括《卡丹紐》。
1728年,身兼劇作家、詩人、企業家的路易‧奚額寶(Lewis Theobald)宣布,他找到了莎士比亞─福雷徹的佚本劇作。奚額寶甚至還宣稱,他握有手稿三份之多,其中之一「有六十年以上的歷史,是知名老牌提詞人黨斯(Downes)先生親手所抄;據我獲得的可靠資訊,它早先屬於大名鼎鼎的貝德騰(Betterton)先生所有,而他有意公之於世。」奚額寶聲明,他在都儒里道(Drury Lane)成功演出的劇作《雙重背叛;又名,悲慘情人》(Double Falsehood; or, The Distressed Lovers)便是以這些手稿為底本。《雙重背叛》的戲文曾經發行,也流傳下來,然而據稱是它所本的珍貴手稿卻沒有倖存。
雖然奚額寶自己編輯過莎士比亞作品,雖然他也熟識當代其他莎士比亞編者及學者,但他卻不曾給任何人看過那些手稿,讓它們接受個別檢閱或認證。如此,難免啟人疑竇,認為他所謂對《卡丹紐》有重要發現的說法乃是個騙局,是為了上演他自己那齣戲所宣傳的花招。他自稱擁有的那些手稿假如確曾存在,則他過世後,即會成為科芬園劇場(Covent Garden Playhouse)的財產,而這個劇場,連同它的一切書籍文件,1808年完全毀於祝融之災。
當然,《雙重背叛》沒有十七世紀早期的印記,卻多的是奚額寶當時的思維與風格。只憑這一點並不能說它跟莎士比亞和福雷徹的劇本毫無關連,因為十八世紀早期的習慣是改寫伊莉莎白與詹姆斯一世時期的劇作,包括莎士比亞的,使之符合當代觀念。《雙重背叛》的文本曾經有人仔仔細細檢驗過,尋找跡證,看是否多多少少源於更早的手稿,也有一些高明的學者相信他們確實發現了這種痕跡。然而許多其他學者依然存疑,所以結果至多是尚無定論。
莎士比亞和福雷徹的戲劇情節顯然取材自塞萬提斯(Cervantes)《吉訶德先生傳》(Don Quixote [1605])第一部裡以插曲方式敘述的卡丹紐故事。這兩位劇作家幾乎絕無可能讀過塞萬提斯傑出小說的西班牙文版,但《吉訶德先生傳》相當快速地由一位流亡在外的的天主教徒湯馬斯‧薛爾敦(Thomas Shelton)翻譯成英文。略經耽擱之後,薛爾敦的譯本於 1612 年出版;到了 1613 莎士比亞和福雷徹劇本首演那年,想必已經轟動了倫敦文壇。
令人既震撼又感動的是,英格蘭最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作家閱讀了西班牙最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作家,兩人相遇於生命將盡之際(非常奇妙,他們註定要在 1616 年 4 月的同一天過世)。畢竟,在《哈姆雷》(Hamlet)和《李爾王》(King Lear)等戲裡,莎士比亞曾經沉思過瘋顛的怪誕幽默與極度哀傷;所用的那種強烈專注的心思,在他同代人物中,唯有塞萬提斯可以比擬或勝出。
然而,這一重大文學邂逅的焦點並不在我們會預期的那位精神失常、輕易上當的拉曼查騎士,反而是如莎士比亞和福雷徹的劇名所示,在塞萬提斯小說裡面,大多數漫不經心的現代讀者難得有印象的一段插曲。卡丹紐故事和吉訶德先生及其跟班桑秋‧班薩(Sancho Panza)的冒險活動有一搭沒一搭地交織著,是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男性友誼與外遇的悲喜劇;從早期的《維容納二紳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到晚期的《兩貴親》,莎士比亞在寫作生涯中對這種故事始終興味盎然。
卡丹紐和盧仙妲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在尚未徵得雙方父親允諾婚事前,卡丹紐就被迫離家,到一個權貴的宮廷服侍,成了貴族之子斐南度的親密好友。斐南度曾以結婚為餌,誘姦過出身卑賤的德若苔,而今反悔;為了躲避德若苔,就隨卡丹紐返鄉。在那裡,不負責任的貴族之子立刻愛上了盧仙妲。斐南度藉故支開他的朋友卡丹紐,向盧仙妲的父親提親;盧仙妲的父母樂於高攀,遂不顧女兒反對,斷然答應這門婚事。
極度失望的盧仙妲寫信給卡丹紐,他急忙趕回。抵達時,卻只能從簾幕後面目擊結婚典禮。他看見所愛之人伸出手來應許嫁給給奸詐的斐南度,便絕望地衝出現場。他沒有看到盧仙妲在那最重要的一刻暈倒了。在她的緊身胸衣裡發現一張字條,宣稱她要刺殺自己。於是,斐南度勃然大怒,氣極奔出。盧仙妲則逃到一間修女院。
對這些後續發展毫不知情的卡丹紐棄絕了文明,一如荒野中的李爾王(Lear),像瘋子般遊蕩於席厄拉山脈。於此同時,被始亂終棄的德若苔聽說斐南度和盧仙妲的婚姻無效,就(像《維容納二紳士》裡的居里雅 [Julia] 一樣)出去尋找他。她跟居里雅及其他許多莎士比亞的女主角一樣,打扮成男孩子,然而這項權宜之計並無法保護德若苔。她為了免遭姦污,把侵犯者推落山崖。之後她也逃到席厄拉山脈。
六個月過去。斐南度發現盧仙妲在修院,就劫持了她。卡丹紐和德若苔在山間偶遇;德若苔告訴他,盧仙妲在字條裡宣告自己因為已經許身卡丹紐,所以不能嫁給斐南度。卡丹紐因而重新燃起希望,神智也恢復清醒。他們跟別人一同來到某客棧,裡面有一位神父在店主的書堆中找到一個故事,便大聲唸給眾人聽。這個故事敘述新婚的安塞摩(Anselmo)要求他最要好的朋友羅賽柳(Lothario)設法勾引自己妻子,以考驗她的貞潔。他的妻子和那朋友墜入情網,合謀欺騙丈夫;這場愛情糾葛的結局是人人都絕望而死。說書的插曲過後,斐南度和被挾持的盧仙妲也恰巧來到同一家客棧。德若苔責備斐南度不該如此待她 ,斐南度羞愧之餘,答應娶她為妻,讓卡丹紐得到盧仙妲。皆大歡喜。
這個故事梗概,莎士比亞和福雷徹明顯得自《吉訶德先生傳》,但這故事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擷取的程度。塞萬提斯把它和沉迷於俠情的武士之冒險犯難糾纏在一起;為了故事流暢,兩位英國劇作家勢必要解開極為複雜的線團。卡丹紐故事的橋段僅僅在吉訶德來到席厄拉山脈,決心為了愛上杜西妮亞(Dulcinea)而瘋狂之後的際遇空隙間,斷斷續續冒出來。
塞萬提斯以特有的神秘、刻意、自我指涉方式打斷敘事,根本沒有按照著故事先後次序呈現。兩位合作的英國編劇努力從塞萬提斯刻意製造的一團混亂中,梳理出清晰連貫的情節,想必覺得啼笑皆非。他們達成任務的唯一鐵證在於這齣佚失劇本的劇名──不叫《吉訶德先生傳》而叫《卡丹紐》──還有奚額寶十八世紀聲稱尋獲手稿的改編本。拉曼查騎士,以及神父朗讀的警世故事這類敘述中斷手法,在《雙重背叛》裡完全消失。留下來的是審判卡丹紐和盧仙妲這一段直白有力的轉述。
這樣的轉述可就是莎士比亞和福雷徹在1613年要提供給大眾的精髓嗎?事隔這麼久,加上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我們無法確知。我們能夠確知的是,莎士比亞經常改寫他人的作品,而他也預期自己的作品同樣會被人改寫。
(彭鏡禧 譯)
【譯後記】
再見《卡丹紐》
彭鏡禧
沉寂數百年後,《卡丹紐》重現江湖!譯完這齣頗有特色的劇作,覺得它的流動有幾點值得一記。
首先是這齣戲的創作概念緣起。作者之一葛林布萊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也是當今文學、文化研究方面的重量級學者。根據哈佛「卡丹紐計畫」網站(http://www.fas.harvard.edu/~cardenio/index.html)的說明,他企圖藉這齣戲探討(或印證)他的「文化流動性」(cultural mobility)理論。戲劇「原作」有它創作的背景,受到原文化、劇種的種種制約;當它跨越到另外一種時空,也就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時候,會產生怎樣的...
目錄
莎士比亞佚失的一齣戲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卡丹紐
劇中人物表
第一場
第二場
譯後記 彭鏡禧
Shakespeare’s Lost Play Stephen Greenblatt
Characters in the Play
CARDENIO
莎士比亞佚失的一齣戲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卡丹紐
劇中人物表
第一場
第二場
譯後記 彭鏡禧
Shakespeare’s Lost Play Stephen Greenblatt
Characters in the Play
CARDENIO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