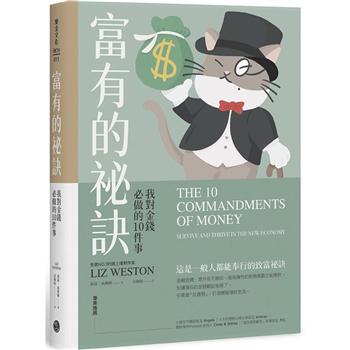我叫A子
我叫【A子】。大家在學校都這麼稱呼我。
我本人大約一個月前才知道這件事。也就是從去年第二學期的期末算起,連續缺席了好幾個月後,卻還是平安升上高中二年級的上學期開學典禮那天。
乘著刺痛皮膚的殘冬冷風,那名字就這麼悄悄地來到我身旁。至於這名字的由來,只要稍加推測就能輕易猜到,是出自談話節目報導我去冬天引發的那個事件時,主持人用來稱呼我的假名【A子小姐】。
雖然不能說完全不感到屈辱,但對我而言,這其實不算什麼壞事。畢竟因為那次事件而改變的,除了旁人對我的稱呼和目光外,也包括我自己。
那是非常巨大的變化。若說以前的我是個『多愁善感的愛哭鬼』,那麼現在的我應該可以用『冷靜而理性』來形容。
按照這邏輯,現在的我等於已經脫胎換骨,就心理衛生的層面來看反而是件好事。如此說來,現在的我其實正值人生的順風期,應該值得肯定才對。應該。
所以我決定成為【A子】,並以這個身分活下去……。
「──化野同學。」
時值五月初。那是在黃金週收假後的隔日,令人精神萎靡的一天即將進入尾聲、放學時發生的事。就在班會結束,我正收拾東西準備回家時,一個聲音忽然把我攔下。
「……」
抬頭一看,只見雪村老師站在眼前,臉上掛著一如往常的溫柔微笑。
【雪村純白】。為了替補春假時因交通事故而重傷離職的天本老師,學校臨時找來的女教師,專長是化學。年紀大約二十多歲,是個新人,同時也是我們班上的副班導。她的手腳修長、臉蛋也漂亮,微卷的頭髮長至背脊,平時總是穿著羊毛衣、襯衫和長裙那種露出度低的衣服;加上那溫柔的性格,整個人活脫就像童話裡的公主。實際上,校內學生私底下似乎也已經有人開始用【白雪】和【公主】之類的外號稱呼她。
儘管開學典禮後的班會時間才第一次向大家自我介紹,但早在當天班會結束時,她就已經被男女學生們團團包圍。真是了不起的凝聚力。不過那時候,當我站在人牆外遠遠眺望那副情景時,心裡卻油然升起一股強烈的感觸,深深領悟到自己跟她是完全不同的人種。直到今日,那種感覺依舊沒有絲毫改變。
「社團活動是從今天開始吧?讓我們一起加油喔,【化學社】……。」
「──欸?」
「咦?……妳沒聽說嗎?行事曆的確寫著是今天啊……我接任化學社指導老師的日子。」
「──沒聽說。」
話說我根本沒有收到通知。的確,黃金週後就是一年級生正式入社的時間,平常社團活動都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我還以為學校是為了隔離我才讓我加入化學社,所以應該沒打算讓我從事社團活動才對……原來如此,指導老師是她。雖說她的確是化學老師,但對新人而言,這等於是抽到下下籤。
「……這樣啊。其實這件事在連假不久前就敲定了。我應該早點告訴妳才對,對不起喔。」
看她一臉歉疚地道歉的樣子,我隨便應了聲「不,沒關係……」。
「……那個,所以說。我昨天去預定做為社團教室的第二理科準備室看了一下,裡面好像擺了很多沒在使用的雜物,還積了不少灰塵……因此我想趁今天打掃一下。等等我先回辦公室放個東西,然後再一起過去如何?」
雪村老師擅自決定今天的活動後,便立刻開始行動。莫非她真的想帶我進行社團活動?就憑她和那次事件後就被趕出社團的我……?因為校規規定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社團活動,而我也不能例外;所以校方才勉強把我編進社員數為零、即將廢社的【化學社】──這才是我入社的真相。難道她連這件事都不曉得……?如果是因為校方沒有說明的話,這就不是運氣問題,根本是惡劣的職場霸凌了。不過看來她好像只是單純沒發現而已?換言之,她的腦袋恐怕不怎麼聰明……。
不過隨便啦,反正對我而言,怎樣都無所謂……。
第二理科準備室似乎已有很長一段時間被當成倉庫使用。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甚至有學生在傳這裡有『幽靈出沒』。雖說我們學校有『校園七大不可思議』的傳聞,但是就我所知,故事中唯一有具體描述出幽靈本體的,就只有這間第二理科準備室和音樂教室兩處;出現在這裡的,是因為實驗疏忽而意外身亡的化學老師的幽靈,至於音樂教室的,則是在那裡自殺的女學生幽靈。
──不過,如果我是幽靈的話,完全不會想住在這種地方。
第二理科準備室實際上就是這種慘狀。簡直慘不忍睹。令人分不清是備品還是垃圾的成堆教材丟得亂七八糟,架子和桌上都積滿灰塵;窗簾和窗戶皆長年緊閉,空氣裡沉澱著陣陣霉味。總而言之,我們先把窗戶和窗簾通通打開來換氣,然後把有用的教材搬去第一理科準備室,不要的東西拿去垃圾場,將所有物品粗略分成兩類搬到外頭去。地板和置物架也用抹布擦過。如此整理過後,外觀總算稍微乾淨了些。反倒是我身上這件五月換季前穿的冬季制服上衣,濃茶色的布料一旦沾上灰塵馬上就能看出來,而且還很難清洗。讓我不禁懊悔了一陣,早知道在打掃前應該要先換上運動服才對。
「──啊。」
打掃到一半,雪村老師突然發現了某個東西,停下手邊的工作。
「嗚哇,真令人懷念……這東西,原來還留著啊……」
她一臉開心地用雙手撫摸一具玻璃箱,出神地盯著箱內的物體。放在箱內的,是一具跟小個子的我差不多高的人偶。光滑的頭頂、圓滾滾的眼睛、一身有點發黃卻依然十分白皙的肌膚──但卻一絲不掛。不僅如此,左半身的肌肉、血管、內臟、骨頭等全都裸露在外,老實說,一點都不可愛。
嘛,總而言之,這玩意兒就是所謂的【過期人體模型】。
「我啊,其實是這間學校的畢業生喔。當時這間教室還有老師在,以及這具人體模型……對了,妳有聽說嗎?它現在退休了沒呀?這個校園七大不可思議之一的【理科準備室會說話的人體模型】……」
面對興奮地不停丟出問題的雪村老師,我隨便「不曉得,大概吧。」地應了幾聲。我才不打算特意告訴她那跟我所知的怪談內容不一樣。這可不是因為我怕麻煩,那只是一半的原因。事實上,我對這件事所知的確不多。畢竟進入這所學校後一年又一個月以來,我完全沒有去調查校園怪談的美國時間。所以實際上也有可能只是我剛好沒聽說過這件事而已。
「這個就放這邊。」雪村老師說著把它移到窗邊,並將那噁心的醜臉轉向可以環視整間教室的方位。然後又從教室角落搬了張舊式的木製課桌椅,放在它正前方。
「化野同學就坐這裡吧。」
為什麼是那邊啊!總覺得好像感覺到些許惡意。不過算了,怎樣都無所謂。
於是之後我們繼續動手打掃。直到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時,窗外已經完全暗下來了。
「啊、糟糕。居然已經這麼晚了……」
雪村老師看看窗外,又看看手錶,然後慌慌張張地抱起幾件教具。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外面已經天黑了,等等我開車送妳回去吧。我先把這些東西拿回辦公室……」
「不,沒關係。我一個人回去就行了。」
搭電車從學校回去只要兩站。至於從學校到最近的車站,以及下車後到家裡的路程則需步行。不過無論哪段都不用十分鐘,再說打掃也沒有很累。況且就算鄉下的電車班數比較少,但現在離末班車發車的時間也還早。
「可是很危險耶,外面這麼黑──」
「沒問題的。一路上都有路燈,而且這附近也沒偏僻到哪去。」
「不,不行。還是我送妳。妳在這兒稍微等一下喔!」
雪村老師沒完沒了似地一面說著一面離開教室。見狀,我急忙出聲叫住她。
「老師!」
然後對停下腳步回過頭的她如此說道。
「可不可以請妳不要多管閒事?」
只見她「──咦?」地嚇了一跳,然後一臉困惑又戰戰兢兢地反問:「為什麼突然這麼說?」
「如果是我誤會的話,我向您道歉。我也知道自己這麼說或許非常失禮──可是請原諒我直言。老師最近總是刻意找機會找我交談,努力跟我套交情對不對?大概從開學典禮直到現在都是。雖然妳可能覺得這是副班導的責任,可我希望妳不要這麼做。」
「為什麼?」
雪村老師的嘴角擠出一絲有點勉強的微笑。
「因為完全沒有好處。不如說有害無益,只會讓老師的教師生涯沾上污點而已。」
「為什麼……妳會這麼認為?」
「妳應該聽過我的事才對?那就是原因,妳根本不該跟我扯上關係,打從一開始就是。我不曉得學校是用了什麼手段才把妳騙來當【化學社】的指導老師,但妳完全不需要這麼認真。只要隨便做做樣子就夠了。在我們彼此都不會受傷的範圍內。既然有空照顧我,不如把那些時間拿去幫助班上的人。我認為那樣會更有意義。」
「但妳也是班上的一份子啊。」
「不,不對。」我毫不猶豫地否定。
「請不要把我當成大家的一份子。我想班上的同學應該也沒人這麼想;就算真的有人搞不清楚狀況以為我是他們的夥伴,我也完全不認為自己跟他們是一夥的。所以妳不用勉強照顧我,請當我不存在就行了。」
從我口中聽到這些話,雪村老師似乎非常震驚。
「欸、欸欸,化野同學。為什麼妳要這麼說?拜託妳,以後別再說這種話了好不好……」
「……」
「……難不成,妳是在擔心我?怕自己給我添麻煩──妳是這麼想的嗎?可是我並沒有……」
「不是的。」
我再次堅定地否定。
「──我就實話實說好了。畢竟這對我們彼此都有好處。其實我或許是打從心底討厭妳的。雖然我也說不出原因,可大概從生理上就無法接受。光是看到妳的臉,我就煩躁得難以忍受。與其跟妳這種人搞好關係,我還寧願去跟那個人體模型交朋友。雖說沒什麼好處,但至少沒有壞處,況且對心理健康也比較有益。」
我單方面一股腦兒地吐完所有怨氣後,便一把抓起書包,逕自穿過傻在原地的雪村老師,開門走出教室,然後朝著校舍的大門大步離去。
剛剛的言行其實一點都不像平時的我;到底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過總覺得就是無法忍耐,結果一不小心就爆發了。
「──化野!」
正當我走到校舍門口、準備從鞋櫃裡拿出室外鞋時,一個聲音從背後傳來。
「──同學。」
我轉過身、斜眼一瞥。聲音的主人不知為何表情一僵,然後急忙補上「同學」兩個字。來者是名三十歲左右的男性,五官稍微有點印象。記得應該是今年新到任的美術老師。
「──妳要回去了?」
「是的。」
「這樣呀。那個,妳好像還有東西忘在美術教室……」
美術老師刻意語帶保留。
對他而言,這件事應該有點難以啟齒。
「不好意思。今天實在不太方便,我過幾天再去拿。」
「──是、是這樣啊。不好意思百忙中打擾妳。話說明天預定要舉辦迎新茶會,所以放學後美術教室裡都沒有人喔……」
……。
話剛出口,他立刻像是發現自己說錯話似的,低聲「啊……」了一聲。他的表情有些僵硬,目光刻意避開我的臉。
「謝謝您的用心。那麼我明天就過去把東西拿走。」
見到我深深低下頭道謝,他才「喔、喔喔……」地勉強回應,臉上總算露出安心的神情。
「那麼我就告辭了。」
我再次微微行禮,然後穿好鞋子,頭也不回地離開學校。
※
隔天放學後。距離社團活動開始的時間已經過了好一會兒,但社辦依然不見雪村老師的身影。
只要是感性正常的人類,在經過昨天的事情之後,應該任誰都不會想和剛大吵過一架的人在密室裡獨處──雖然這對異於常人的我而言不算什麼就是了。不過冷靜想想,當時我話可能真的說得有點太過分。但我也是為了彼此著想才選擇在一開始就清楚拒絕,因此並沒有什麼罪惡感,也沒打算反省。如果是正常人,現在或許正為此煩惱、後悔不已,痛苦得不得了才對。
「──好安靜。而且好清閒。太完美了。」
然而對我而言,這種能獨處的時間簡直就是神明賜予的恩惠。無時無刻都在沐浴在全校異樣目光下的我,從來沒想過能在這間學校內,擁有一間不必理會他人視線、自由享受清淨時光的庇護所。
因為實在幸福得無事可做,於是我轉頭打量了一圈周圍的環境。仔細觀察後,我才發現這間教室的裝潢風格十分古老,甚至到了詭異的程度。令人有種全校唯有這個空間被遺忘在過去的錯覺。
木板鋪成的地面每走一步便嘰軋作響。覆蓋牆面的木製櫥架上,只有一片薄薄的玻璃櫃門,感覺開關時稍微用點力就會碎裂;櫃內陳列著各種堆滿灰塵、不知名的骨頭和礦石、標本。天花板的兩盞日光燈一明一滅地閃爍,看著有點傷眼。
而其中最詭異的當屬這個──站在我眼前的人體模型。如果沒有這傢伙的話,教室裡的氣氛應該會完全不同吧?
從剛剛──應該說是從我坐下後開始,那傢伙就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這裡。
我不禁想起昨天對雪村老師說過的話,反過來盯著那人體模型瞧。
「──我在想什麼?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跟這種玩意兒做朋友啊?」
我喃喃自語了幾聲後便想移開目光……可就在此時。
『──幹嘛一直盯著別人看,很沒禮貌耶妳。』
──?
憑空傳來某人的說話聲。我抬頭張望了一下,不過想當然耳,教室裡除了我之外一個人也沒有。
正當我以為是自己的錯覺,視線再次飄回人體模型時……。
『喂。是我啦,我不就站在妳前面嗎?』
倏地,耳邊再次聽見人聲。那是一道彷彿在下水道深處悠然迴盪的獨特美聲。
我的前方除了人體模型外什麼也沒有。但聲音確實是從那方向傳來的──又過了幾秒鐘的靜默後,耳邊再次聽見那聲音……。
『喂,幹嘛無視我啊?我說的就是一副遊手好閒地坐在我正前方的椅子上,身材乾癟、小學生體型、有著一頭短髮和大大的眼睛,雖然五官還算工整但臉色卻像人偶一樣蒼白,脖子上圍著一條像恐怖分子才會戴的圍巾的妳啦。』
──看來對方好像是在對我說話,畢竟這裡除了我以外也沒有別人。儘管有點難以置信,但我現在似乎是被人體模型給搭訕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超現實的狀況。
『我說,妳叫啥名字?』
男人(?)突然不客氣地問。然而,我可不打算老實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人。
「在問別人的名號前,最好先報上自己的名字。」
『哦!妳還頗有常識的嘛,小妹妹。』
聽到我回嘴,男人(?)開心地笑了笑,然後報出自己的名字。
「我是【透】。請多指教啊。」
「請多指教……」
雖然我對他的名字其實並沒什麼興趣,但姑且還是點了個頭,算是回禮。
『好,那接下來換妳啦。』
「我叫【A子】。」
我迅速地回答了他的問題。
『姓啥?』
「沒有姓。」
『喂喂,這到底是不是妳的本名哪?』
「不,當然不是。」
『那妳幹嘛用那種像是義大利符號學者的名字?』
因為要從頭說明理由實在很麻煩,於是我只回了他一句「反正又沒有版權」。
「再說你還不也一樣用了假名?我才想問你,為什麼要用【透】這個名字?」
『妳‧猜‧啊。為什麼咧?有本事就猜猜看呀?』
【透】故作玄虛地把問題變成謎語,丟了回來。
「鬼才知道,難不成是因為左半邊的身體是透明的?」
『……啊 ……對對對,就是那樣。妳答對了。挺厲害的嘛。』
總覺得剛才他好像愣了一下……。
『──別在意別在意,別對那種小細節斤斤計較啦。話說我昨天聽到囉。妳啊,說了想當我的「朋友」是吧?』
我真笨,居然直到他口中吐出那單詞後才察覺他的真實身分。
「──妳是雪村老師?」
為什麼會沒想到呢。我是在昨天在這裡提到人體模型和那個詞語的。而當時這裡除了我之外,就只有雪村老師一個人而已。而從那時候的對話內容來推論的話,答案應該只有一個才對。
「哈啊?沒頭沒腦地胡說八道些什麼啊妳?我就是我,人體模型的【透】。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見到雪村仍死不承認、極力裝傻,我只好回她一句:「還在扯那種一下子就被拆穿的謊……」接著嘆口氣,認命地繼續陪她玩下去。
「人體模型一般是不會說話的。」
『只要活了超過二十年,人體模型的屁股就會裂成兩半,變得能夠說話喔。』
「屁股本來就是左右兩片好不好?妳是修練成精的人體模型嗎……拜託要編故事也編得好一點。雖然我不清楚妳用了什麼機關,但那種像變聲器的電子音,怎麼聽都不像是從生物口中發出來的。」
那很明顯是每季都會推出的警匪影集中常聽到的那種聲音。乍聽之下雖然像男性,不過最近的變聲技術那麼高明,讓女聲轉男聲也沒什麼不可能。
『哈啊啊?』他不滿地抗議。
『真要說的話,妳的嗓子不也像在卡拉OK狂歡一整夜後一樣奇怪嗎?』
「──卡拉OK?才不是,我的聲音本來就這樣。而且我的主治醫生也說過『妳的聲音很像我常去的酒吧的媽媽桑,很性感喔』。」
『什麼嘛,那不就是酒燒聲嗎?哪有女高中生會喝酒喝到燒聲的,瞎掰也要有個限度。』
「既然你不信,那要不要自己親眼看看?我沒說謊的證據……」
光用嘴巴說也無法理解,於是我把手指插入脖子上的圍巾,用力拉開。
『──!』
那裡留著一道巨大的縫合痕跡。他應該也看見了才對。雖然是數個月前的事件時留下的傷口,但因為中間經過好幾次手術,所以傷痕還依然清晰可見。
「因為傷到了聲帶,所以我的聲音這輩子都是這樣了。」
『……』
【透】一時間看似嚇到、啞口無言了一會兒,可沒過幾秒就又重新打開了話匣子。
『呃,抱歉啦,我不該隨便開玩笑的。不過老實說,妳以前到底是幹了什麼事呀?』
「殺人。」
『真的假的?』
「假的。」
『──妳這傢伙!別亂嚇人好不好?』
「話說回來雪村老師,妳也差不多該到此為止囉?我已經玩膩了,這種用玩偶扮家家酒的遊戲。」
『就跟妳說我不是雪村!』
雖然我試圖用言語逼她坦白一切, 可沒想到她還挺頑固的。
「既然如此,你到底是什麼人……」
『所以我就說我是【透】………………』
「……?」
喀啦喀啦喀啦……。
正納悶【透】的聲音為什麼像消風的氣球一樣愈變愈小時,教室入口的拉門突然打開了。我稍微嚇了一跳,迅速轉頭,卻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
「不好意思喔,我來晚了。」
雪村老師佇在門口,臉上擠出一抹僵硬的微笑。
………………。
「妳等很久了嗎?……呃呃,是這樣的。今天我想在開始社團活動前……哎、那個……化野…同學?」
我想自己現在大概正死命地盯著她瞧。或許是因為我的反應太奇怪,雪村老師小心翼翼地問了句「怎麼了?」。而我只能努力裝出冷靜的模樣。
「不,沒什麼。什麼事都沒有。一切都──」
『唷,我是【透】。請多指教!』
「──!」
就在這時,彷彿故意要打斷我一樣,一旁的【透】突然開口說話。
「──咦?」
雪村老師露出詫異的表情。
「剛剛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都沒有。」
「不……可是,感覺好像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是妳聽錯了。還是說妳也認為我的聲音就像在卡拉OK徹夜狂歡後一樣奇怪?」
「──哎?狂歡?咦咦?我根本沒說過那種……」
「我不想聽妳的藉口,總之今天請妳先離開。」
「不、可是我……接下來才要開始社團活動──」
我用兩手按著一臉困惑的雪村老師的背,將她往門口的方向──硬生生推出走廊。接著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關上拉門,隔著門板丟了一句「請妳今天先回去!」。她在門外叫著我的名字求我開門,但我迅速把門反鎖,讓她無法如願。然後又重複了一遍剛剛的台詞。儘管她仍舊在門外堅持了好一陣子,但最終還是死了心,拖著沉重的腳步聲離開。
──呼……。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遜斃了!瞧妳嚇得那副德行。』
就在我好不容易鬆了口氣時,那傢伙白癡似的笑聲響徹整間教室。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說妳,剛剛其實嚇得都快尿出來了吧?這是為了剛才的事報仇。』
「你究竟是什麼東西?說實話。」
『就告訴妳我是人體模型嘛。到底要我說幾次妳才懂啊。』
「那你搭訕我又有什麼目的?」
『我不是說了嗎,我是為了跟寂寞的妳當「朋友」而來的呀?』
我輕輕嘆了口氣。這傢伙根本沒法溝通,對話從剛剛開始就像鬼打牆一樣。
「可不可以麻煩你去別的地方玩校園七大不可思議的遊戲?我可不會像你期望地那般,做出亂吼亂叫或連滾帶爬地逃跑那種典型反應喔?」
『喂喂喂,妳這傢伙的反應也太冷漠了吧。最近的小鬼都是這副德行嗎?』
「不,我想只有我而已。如果是其他人的話,應該會對這種話題很有興趣。最近這裡剛好也正流行音樂教室的鋼琴如何如何的鬼故事。」
雖然不是直接聽來的,但之前偶然在教室聽人談論過這件事。
『啊啊,那個啊。明明教室裡沒有半個人,卻會聽到鋼琴聲的那個怪談是吧?據說好像是某個在音樂教室自殺的女學生的幽靈在作祟呢。』
「難不成那也是你的傑作?」
『喂喂,別把我跟那傢伙相提並論。兇手是那傢伙――是貝多芬幹的好事啦。』
他指的莫非是貼在音樂教室的牆壁上,一到夜晚眼睛就會發光、傳聞已久的那東西?我開口詢問後,他立刻答道『啊啊,就是他』。
『那傢伙也上了年紀,耳朵愈來愈不靈光了呢。住在樓上美術教室的布魯圖斯經常來抱怨鋼琴聲太吵,但那傢伙卻像完全沒聽到一樣,受不了……』
「──不,我想貝多芬的耳背應該是因為別的理由。」
真不曉得該從哪裡吐嘈起才好。不過老實說,這種事情怎樣都無所謂。
我抱著書包從椅子上起身。
『嗯?怎麼,這麼快就要回去了喔?難道有什麼急事嗎?』一發現我要離開,他就立刻語氣不滿地問。
「嗯。我想起自己還有事得去你說的美術教室一趟。去完之後就要直接回家。」
『是唷,真遺憾。那就替我跟布魯圖斯打聲招呼吧。』
「好。如果他也跟你一樣開口說話,我會記得大叫『連你也是嗎──!』的。」
我說完便轉開門鎖、推開拉門。正準備踏出教室時,背後又傳來他的聲音。
『哦哦,那就明天見啦!』
我沒有回答,直接關上拉門,頭也不回地離開教室。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柳田狐狗狸的圖書 |
 |
$ 109 ~ 234 | A子與(透)與社團時間。(全)
作者:柳田狐狗狸 / 譯者:ASATO 出版社: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28 語言:繁體書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A子與 (透)與社團時間。(全)
●第19回電擊小說大賞 金賞
●第3屆店員最愛輕小說大賞 得獎作品
●『奇諾之旅 the Beautiful World』作者 時雨澤惠一 強力推薦!!
我叫【A子】,我沒朋友。
因為半年前的事件而遭全班孤立的【A子】,某天在化學社的社辦邂逅了會說話的人體模型:【透】。【透】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某人在用變聲器說話似的,讓【A子】不禁開始懷疑起【透】的身分,【A子】雖然試著詢問【透】,但【透】卻不斷巧妙地閃避話題。就在此時,校內卻發生了女學生人體自燃的事件……。
由乖僻少女與會說話的人體模型交織而成的校園推理劇,就此揭開序幕!
作者簡介:
作者:柳田狐狗狸
現居京都府。基本上屬於無神論者,但痛苦時會毫不猶豫地求神拜佛的廢柴。最近經常向小說之神祈求作品的靈感……。
繪者:MACCO
新銳插畫家。曾在「niconico動畫」上投稿VOCALOID相關影片的插圖,博得了不小的人氣。最近正迷上臨摹。
TOP
章節試閱
我叫A子
我叫【A子】。大家在學校都這麼稱呼我。
我本人大約一個月前才知道這件事。也就是從去年第二學期的期末算起,連續缺席了好幾個月後,卻還是平安升上高中二年級的上學期開學典禮那天。
乘著刺痛皮膚的殘冬冷風,那名字就這麼悄悄地來到我身旁。至於這名字的由來,只要稍加推測就能輕易猜到,是出自談話節目報導我去冬天引發的那個事件時,主持人用來稱呼我的假名【A子小姐】。
雖然不能說完全不感到屈辱,但對我而言,這其實不算什麼壞事。畢竟因為那次事件而改變的,除了旁人對我的稱呼和目光外,也包括我自己。
那是非常巨...
我叫【A子】。大家在學校都這麼稱呼我。
我本人大約一個月前才知道這件事。也就是從去年第二學期的期末算起,連續缺席了好幾個月後,卻還是平安升上高中二年級的上學期開學典禮那天。
乘著刺痛皮膚的殘冬冷風,那名字就這麼悄悄地來到我身旁。至於這名字的由來,只要稍加推測就能輕易猜到,是出自談話節目報導我去冬天引發的那個事件時,主持人用來稱呼我的假名【A子小姐】。
雖然不能說完全不感到屈辱,但對我而言,這其實不算什麼壞事。畢竟因為那次事件而改變的,除了旁人對我的稱呼和目光外,也包括我自己。
那是非常巨...
»看全部
TOP
目錄
Contents
世界的中心
我叫A子
令人火大
你誰呀
就像打招呼一樣
紅外套
什麼樣的步驟
套用某人的話
阿基米德
勉勉強強
果然是你
我們
【主要登場人物】
Shigenori Karube
輕部重法
緋守警察署刑事課巡查部長。
只要邂逅的對象是女性,不問身分年齡一律上前搭訕的不良刑警。
Yuki Motogusa
素草有紀
學生會副會長。
偷溜進音樂教室彈琴時與A子邂逅。
平易近人的性格令他在男女生之間都極受歡迎。
Mashiro Yukimura
雪村純白
A子的副班導。
儘管外表十分成熟,性格卻意外傻氣?...
世界的中心
我叫A子
令人火大
你誰呀
就像打招呼一樣
紅外套
什麼樣的步驟
套用某人的話
阿基米德
勉勉強強
果然是你
我們
【主要登場人物】
Shigenori Karube
輕部重法
緋守警察署刑事課巡查部長。
只要邂逅的對象是女性,不問身分年齡一律上前搭訕的不良刑警。
Yuki Motogusa
素草有紀
學生會副會長。
偷溜進音樂教室彈琴時與A子邂逅。
平易近人的性格令他在男女生之間都極受歡迎。
Mashiro Yukimura
雪村純白
A子的副班導。
儘管外表十分成熟,性格卻意外傻氣?...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柳田狐狗狸 譯者: ASATO
- 出版社: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24 ISBN/ISSN:978986475079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寬 12.7 cm ×長 18.8 c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