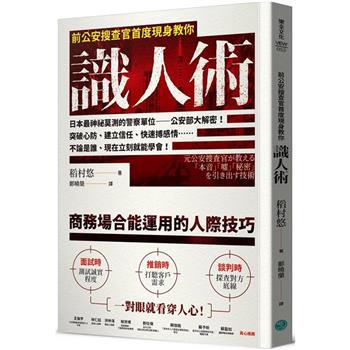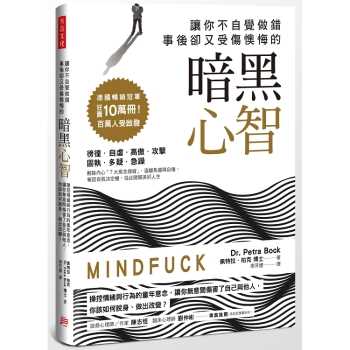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梁實秋等二十七位的圖書 |
 |
$ 100 ~ 270 | 天下散文選Ⅰ:1970~2010台灣(改版)
作者:梁實秋等二十七位,主編:焦桐,鍾怡雯,陳大為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0-07-2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14.8x20.5cm / 黑白 / 329頁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梁實秋,名治華,字實秋,號均默,以字行。另有筆名子佳、秋郎、程淑、希臘人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評論家、辭書學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寄籍浙江杭縣,出生於京師。
梁實秋,名治華,字實秋,號均默,以字行。另有筆名子佳、秋郎、程淑、希臘人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評論家、辭書學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寄籍浙江杭縣,出生於京師。一次看盡台灣最重要、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五十九位作家的作品。台灣近四十年的散文風貌,盡在書中。
《天下散文選》共有三冊,Ⅰ,Ⅱ冊的選文範疇在台灣。
在還沒有出現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台灣現代散文史》學術性論著之前,各種台灣現代散文選集便成為另類的台灣散文史藍圖。《天下散文選Ⅰ,Ⅱ:1970-2010台灣》的編選策略,即是透過一個隱形的散文史架構,精選出六十四篇台灣的散文佳作,從梁實秋(1901~1987)到黃信恩(1982~),跨越台灣現代散文創作的每一個世代,涵蓋各種重要的主題,讓讀者透過精彩的文本研讀,勾勒出台灣散文近四十年來的發展脈絡。
自一九七○年代以降,台灣散文進入多元發展的時期,從傳統的原鄉和懷舊主題、自然生態的書寫、佛法與哲理的闡釋、現代都市文明的觀察、社會亂象的批判、運動與旅行的記述、飲食文化的描述,到個人的神思與冥想。以這四十年作為選稿的時間跨度,足以呈現台灣現代散文最豐富的內容。
作者簡介:
梁實秋等二十七位。
編輯顧問
焦桐(1956~),詩人、作家、「二魚文化」事業、《飲食》雜誌創辦人。已出版著作包括詩集《青春標本》、《焦桐詩集:1980-1993》,及散文《在世界的邊緣》、《我的房事》、《暴食江湖》、《臺灣味道》,等等二十餘種,詩作被翻譯成英、日、法文多種在海外出版。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四十餘種。
鍾怡雯(1969~),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曾獲:中國時報散文首獎、聯合報散文首獎、九歌年度散文獎、星洲日報散文首獎及推薦獎等重要大獎。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豢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等十七部著作。
陳大為(1969~),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台北文學年金、聯合報新詩及散文首獎、中國時報新詩及散文評審獎、新聞局圖書金鼎獎等重要大獎。著有:詩集《再鴻門》、《盡是魅影的城國》,散文集《流動的身世》、《火鳳燎原的午後》,論文集《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等十九部著作。
蟹 梁實秋
看戲 琦君
添秋膘‧吃螃蟹‧炰烤涮 唐魯孫
鑰匙 羅蘭
小花與茶 張秀亞
紅頭繩兒 王鼎鈞
迷眼流金 王鼎鈞
大夥兒的舊情人 張拓蕪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催魂鈴 余光中
出門訪古早 逯耀東
潮州魚翅 ...
- 作者: 梁實秋等二十七位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7-29 ISBN/ISSN:9789862165898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