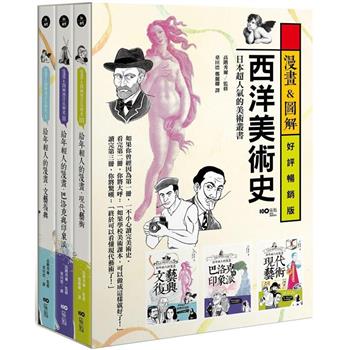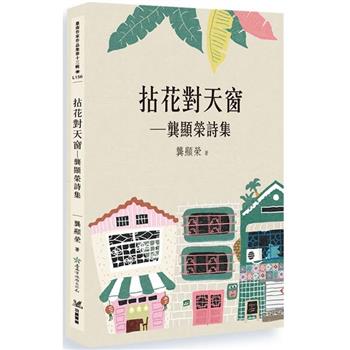上課的鐘聲響了,莫煩凡接過了一個勁度十足的球,比賽亦在四散入課室的學生嘈雜聲中結束。他為了發洩球癮,不太理會自己沒有穿鞋,雙腳因而有所損傷。他喘著氣,一跛一跛地走向唐尼。對方迎了出去,一雙眼睛帶點擔心的注視著他的腳。
雖然他們身披袈裟,但身分始終是半個旅客,所以當天他們在寺院中安排了日後的行程,出家的日子即將結束。
這座位於蒲甘近郊的寺院,範圍廣闊,唐尼與莫煩凡到處瀏覽。這裡將會成為他們的基地,意味著他們會在此還俗,結束緬甸的旅程。
唐尼走到寺院一處較高的地方,在鐘樓上示意莫煩凡他們將會遊歷的平原,只見遠處高高低低的佛塔,在紅土沙漠般的野外,露出了塔尖。
唐尼告訴莫煩凡︰「這裡有超過二千多座佛塔。」他指著一座較近較大的說︰「明早我們會登上這座塔看日出。」
蒲甘佛塔群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唐尼第一次踏足這裡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他告訴莫煩凡,早期這裡非常荒蕪,只有小村落與農家,大部分地方,類似澳洲艾斯石附近的沙漠,紅土上的佛塔,具有千多年的歷史。他又從那常帶備身邊的記事簿,抽出那手繪的名信片。紙質發黃了,四個角落已損破,明顯是幅兒童畫。他以欣賞的神態,把目光留在紙上一段時間,像在追憶甚麼似的,然後遞到莫煩凡手上。
「帥古寺(Shweguyi),建於一一三一年,由當時的國王建造,屬皇家祭祠的佛塔,是這裡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廟塔。我們會到這座塔頂看日落,那裡看夕陽的角度,我最為欣賞。」
中午時分,烈日當空,唐尼仍不厭其煩地帶著莫煩凡,到周圍附近的佛塔參觀,有些內面是空盪盪的,有些卻四方八面都供奉著神像,而部分神像更是驚人的巨大。每座塔都有編號,是最早期,由意大利及法國的考古學家與緬甸的歷史專家所編製。唐尼樂此不疲,津津樂道的每到一個新景點,便興奮雀躍地向莫煩凡「推介」。
他們由乾涸的河道,走出了柏油路,刺眼的光令他們不敢直視。兩人都把上身的袈裟騰出一部分,保護著被日曬的頭頂。烈日在長長的柏油路上,照出了一道白色耀眼的反光,像一條巨大的白蛇宛延起伏的邁向平原遠方。
牛車、頭頂貨物的婦人、自行車──統統在白光下變成黑影,一排排的在路中移上移落。唐尼不顧灼熱的陽光,站在路邊看著這出神入化的「光帶」,他更形容自己正欣賞一齣活生生的印尼皮影戲。這幅活動的畫,實在令唐尼太著迷了,他的雙腳,被燙熱的柏油路面蒸得不停地相互磨擦著腳背。莫煩凡因今早的球賽腳傷,一早套上了人字拖,他見唐尼「原地跳舞」,於是把自己腳下的一對鞋,放在唐尼腳邊,唐尼即時搖頭拒絕了。一輛卡車駛過,塵埃撲鼻,煩凡把頭上的袈裟拉下來,掩著鼻子。透過黃色的棉布,煩凡彷彿看到搖著身體的唐尼,已變成昔日玻璃糖紙下的尼尼,擺動上身,努力地彈琴。
這天他們提早回寺院休息,因為半夜裡,兩人便要出發到較遠的高塔看日出。
寺院早課前,兩個凍得瑟縮的和尚,帶備在路途中食用的乾糧,溜出廟宇,走到荒野上。
雖然雨季將近,但目前仍是沙丘處處,河堤乾涸;是夜沒有月光,但滿天低低的繁星,密集的罩盡地平線。那柔和的銀光,令起伏的沙丘,變成一幅幅杏色的天鵝絨;周邊被風吹到只懂朝著一個方向彎身的蘆葦,像一條巨大的羊毛圍巾,貼伏地掛在河堤。
今夜流星特別多,速度也很快,莫煩凡趁中途小休時,挨在蘆葦上看得入神。突然一束光芒較強的流星劃破天空。
「快快許願吧。」唐尼大聲疾呼。莫煩凡立刻把雙手合在一起,放到前胸,抬頭望著那高速的流星,滑向唐尼那方的天際。唐尼朝著流星極速奔向沙丘,伸手到流星消失在天邊的一點,手舞足蹈的嚷著︰「哈哈,我接到了你許願的流星,我知道了你內心的祕密,哈哈──」
莫煩凡二話不說,追了上沙丘,把唐尼撞跌,提著他的手,口中狂叫:「還給我,還給我。你不可能知道我的願望,更不可能了解我心中的祕密。」兩個大男人,摟作一團,從沙丘滾落河床。
兩人仰睡著,望著星空。沉默的河床,間中只有蘆葦與晚風的嘯嘯對話。唐尼側面望向莫煩凡,自言自言的他,低聲慢道:「但願──我是晚風,可以隨意走入──你的蘆葦叢。」對方依然沉默一直沒有反應。他那水汪汪的眼睛,仍然被漫天星光吸引著,沒有理會那句「晚風」送來的獨白。突然,莫煩凡側身背向唐尼。不久,莫煩凡起身,提著布袋走了。
高塔的金頂,在一粒黃光燈泡通宵照亮下,遠望已能看到那片金光閃閃的三角形。塔下四周,卻仍然是漆黑一片,只有星光引路。兩人太早到達目的地,周圍靜悄悄,觀看日出的時間也許尚早,遊人杳然,更顯得古塔的荒涼。
他們沿著塔邊外圍斜斜的石級爬上去,到了第一個平台,莫煩凡示意再繼續爬高一個看台。唐尼尾隨他的腳步,這道石級比下層的更加傾斜,兩人需要扶著旁邊的鋼管扶手。可能莫煩凡有點腳傷,加上梯級高,而梯面窄,他看來有點吃力,幾次提腳時,腳跟也差不多碰到唐尼的鼻尖。他在情急下,小腿碰到了級邊,他哼了一聲,痛得停了下來。鮮血在漆黑中,清晰地染在袈裟上。
過了一陣子,唐尼見莫煩凡動也不動,受傷的小腿令他僵住了。唐尼側首仰望,知道只要再上多兩級,便會到遠另一道觀景台,於是,他示意莫煩凡再慢慢爬上去。提腿也感覺吃力的莫煩凡,到了平台的時候,血已流到腳跟,他按捺不住,坐到石級頂的平台邊;唐尼仍留在石級上,見莫煩凡坐下了,堵塞著梯口,他微微張口喘氣的臉部,剛巧在那流著血的小腿前;唐尼掀開莫煩凡染血的袈裟,眼見鮮血在黑夜中,墨亮地流出來。他只向上望了莫煩凡一眼,小腿便已擁入他的懷中,雙脣已合在傷口上;他替傷口啜了兩口血,然後,毫無動靜地抱緊著小腿,嘴巴仍在傷口上。
熨熱的舌底,和暖了冰冷的傷口。莫煩凡舉頭望向遠方夜空,期待著一個永無曙光的黎明,情不自禁的手,輕撫了唐尼磨砂般的腦袋。他蓋上眼晴,在漆黑中,感受唐尼澎湃的心跳,按摩著自己麻木的小腿。在冷空氣裡,感受唐尼從鼻孔力喘而噴出的熱氣,有節奏地沿小腿而下,消散在腳背上。
灰藍的朝霞在高塔上飄過,天上開始淡吐微白。莫煩凡見唐尼嘴角有點血跡,他用袈裟以指尖慢慢替他清理。
「我替你塗上脣膏,現在你可以登台了。」
唐尼立刻爬上剩餘的兩級,張開雙臂,以豪邁的聲音,誇張地唱起意大利歌劇。
唱了幾句,他以手輕按小腹,像個紳士般,向台下左右敬禮,還鼓掌笑著自嘲︰「Bravo,Bravo──」莫煩凡一拐一拐的走到身邊,以手隨意束起染血的部分袈裟,扮作獻花。一時間,兩人的笑聲,已傳遍塔下每個角落,回音飄渺在縷縷朝霞間,過百成千的塔尖伸首在萬里天際,有如台下觀眾。
唐尼意猶未盡,拿出了牧童笛,遞給莫煩凡,對方微笑地搖了頭,唐尼又立刻吹出了一段拉威爾的玻莉維亞舞曲,弄得莫煩凡拍手不斷叫嚷︰「Bravo,Bravo──『海納百川』。」
接近破曉時分,遊人開始登塔了。兩人於是走到有利觀看的向東地位,一起倚在剝落的塔身上,冰冷的晨風從塔身彎角吹過來,莫煩凡挨近了唐尼旁邊。
地上仍然一片濛,時淡時濃的藍,轉眼間又化紫了。凝罩在樹梢頂的濃霧,只有偶然的農家炊煙,才能突破這層封鎖的濃濃煙幕。一絲絲、一縷縷,兩人看得定神。無言間,兩個和尚,看似心神一致;奈何彼此心竅成謎如霧,但求大家能夠變成那縷炊煙,衝破那道被心理障礙封鎖的紗幕。
「啲噠」聲令兩人同時分了神,一對年青的韓國情侶登上塔來,女的穿了時下流行的所謂韓版衣服,「啲噠」怪聲源自她腳下的一對涼鞋,鞋頭上貼著一堆向外兩邊伸展的白色雞毛。她粗魯的當她經過唐尼面前的時候,唐尼以手指向著自己赤腳的腳背,示意她在塔上不應套上鞋履。唐尼換來的,是這個女人的高傲目光,以及她故意的提腿,還從唐尼腳背跨過,惺忪回望一眼,繞道走過了兩人身處的狹窄平台。
唐尼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第一道穿透地平線的曙光,已經深深吸引著他。太陽還沒有升上來,天邊仍然泛著一片紅光。遠處一列低低的山巒下,伊洛瓦底江,由南至北,靜靜地伏在薄薄的霞霧下,偶爾那銀白的江面,隨著漸強的曙光,而泛映片片幻化的淡紅。
對岸江邊一處山峰上,明顯地出現了一座佛塔,底部白色基石,清晰可見。唐尼遙指那佛塔金頂,低聲跟莫煩凡耳語︰「看著太陽升上來時,第一道光會打在塔頂上,純金的塔尖會發出閃光,到時許的願會很靈驗。」步伐,令兩堆大雞毛刺目地繃跳著。
微風中,莫煩凡把耳朵更加靠近了唐尼的嘴邊,他喜歡在冷空氣中,感受從唐尼冒著蒸氣的嘴巴,斷續沖入耳孔的那股暖流。
莫煩凡極為享受那近乎沖入心底的感覺,他甜絲絲地微笑,向著唐尼說︰「今次我會直接出聲告訴你關於我許的願望,免得你又伸手去接那道金光。」他把視線向下望到塔底,繼續說︰「我絕不希望你會死在這裡。」
唐尼又掛上他那招牌式的苦笑︰「說真的,我將會許的願是與死有關乎;你知道我在這裡出世,所以,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深愛我的人能夠把我的骨灰,撒在那江面上。」他指著遠方宛延遼闊的伊洛瓦底江。
莫煩凡順著唐尼的指尖,望向前方。淡黃而有點刺眼的黃光中,一個一個橢圓形的黑影,由地平線慢慢上升。
「我曾想過,但自問有點虛榮。」莫煩凡停下來,望了一眼唐尼,繼續他那欲言又止的話︰「其實與你差不多,找一個深愛著自己的人,拖著手,到巴黎,登上艾菲爾塔。」
他再度停下來,望著七個浮沉的熱氣球,有的在江面略過,倒影與實物,形成了一個有趣的「8」字,有的在瀰漫著煙霞的塔尖間飄盪。莫煩凡指著一個飄得較近的熱氣球︰「上去,與愛人一齊乘上去,是我的最終願望。」
唐尼眨著雙眼搖頭︰「我畏高,只試過一次,在澳洲艾斯石,當時怕得要死。在我們出發到緬甸前一天,埃及樂蜀發生了熱氣球爆炸下墜事件,死了很多遊客。」
「我知道,當中有一對罹難的老夫婦。──當時有想過,如果,其中一個是我,見著火的氣球升得這麼快,我可能不會跳下來,會緊抱我老拍檔的身體,緊握著手,面部也緊貼,隨風吹,任火生,這種與深愛的人,接受用火洗禮最終結的一刻──挺浪漫。」莫煩凡臉色沉下來。
「不要說了,還是等一陣朝著光,你許你的願,我許我的。」唐尼設法調較著雙方的情緒。
「我還未說完,請給我一點時間,好嗎?」莫煩凡帶點央求的眼神,令唐尼瞪著他的大眼,點了一下頭。
「說到『愛』,我也弄得糊塗。起初很愛的一個人,隨著大家因生活而漸變的行為,因了解而顯露的性格,以及因相處而過去的時間,『愛』亦起了變化。」莫煩凡又來唏噓︰「更可怕的,就是心目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對象。你會恐懼自己不敢再重新去愛,但明顯而不能自制地,內心卻有愛的感覺。那種莫名奇妙的愛,有點可怕︰當內心接觸到突遇奇來而又甜絲絲的愛意,原來只是發自對方一個完全不經意的表示,那──簡直係『愛』得認真『要命』。」
遠方塔頂遲來的光,被雲層遮擋了。連番道理下,大家總算許了那事先張揚的願。彼此遲來的心領神會,雙方良知又可否曾被蒙蔽。
莫煩凡離開高塔的時候,突然感覺身心疲倦。可能漏夜趕路未眠、腳傷、甚而懷疑自己的說話詞不達意,令人產生誤解,總而言之,他目前的境況很糟,心力交瘁。
一聲尖叫,一個回頭,打破了一切的緘默。幾隻大雄雞,拖著黑色高撓的長尾,被兩個小孩力追趕著,沿途還有幾片「似曾相識」的白色雞毛遺落在路中。在彎角處,韓國女子正與另一隻更大的公雞掙扎著。公雞看來寧死也要「占據」「母雞涼鞋」似的,交配旺季了,眼前的景象看得唐尼在路邊「咯咯」大笑。
還是一個土著女孩,替韓國女子解了圍。她熟練地把公雞抱入懷中,並與剛才兩個追逐雞隻的男孩,走到旁邊的屋前攤檔。
大哥哥與他的年輕妻子開始擺檔,臉上塗著葉形檀香粉的妻子,正忙碌地推銷汗衣給觀看日出的遊客。汗衣上除了印有著名景點外,熱賣的還有過去一兩年間,訪問英美回國的昂山素姬。
唐尼與莫煩凡正在留意汗衣上昂山圖像之際,耳邊不斷傳來年輕女子推介紀念品,說這是昂山素姬的衣款、那是她最喜歡的顏色,一名女遊客打趣說︰「哪種衣扣是她常用的?」素姬氾濫了。
難怪的,唐尼細聲告訴一向不理政治的莫煩凡︰「昂山素姬六十七歲了,政府軟禁了她廿多年,在各方面來說,似乎她亦消耗殆盡、無能為力。政府唯有利用她現時在國際上剩餘的一點名氣,向外推銷一下緬甸的資源,希望一方面能夠改善落後了大半個世紀的經濟,另一方面是提高緬甸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是推銷,跟她一樣?」莫煩凡輕舉他的手指,向著年輕少婦。
「是,她賣汗衣;昂山,推銷血汗。」唐尼延續了莫煩凡的話題。
突然,唐尼拿起了一件手繪風格的汗衣,以他買賣畫作的專業,斷定了作畫人的風格。他立刻從布袋拿出了記事簿後頁的名信片。年輕女子看了,笑著指向旁邊蹲在屋前,正從小妹妹手上接過一隻隻雄雞關進籠裡的背向男人。他聽聞妻子叫喚,立即走到售賣汗衣旁邊的水果檔。
健碩的男人接過了唐尼手上的名信片,笑著說︰「是我小時候畫的,在帥古寺附近;爸媽的農田在那裡,我在田裡幫手種水果。」他指著檔口前的生果,笑得更加燦爛︰「那時在田邊閒時作畫,賣給遊客,幫補生計。」他又保持笑容地指向後面仍然圍攏雞籠的弟妹。
唐尼微笑著向莫煩凡說︰「他們從小到大,雖然生活清苦,但大家都很樂觀;這一點,從他們臉上時常掛著的笑容,就可知道。」
物歸原主,唐尼把名信片發還給他,作為留念。檔主禮貌地給唐尼送上兩個釋迦,唐尼還是付了錢,放下一個,自己提走了另一個。臨走道別時,唐尼瞄了名信片一眼,心內亦難捨地道別了這張身攜十多年,近乎破損發黃的紙張。
唐尼把熟透的釋迦分開,自己拿了一半在樹下與莫煩凡分享。唐尼把色澤鮮黑的種子從口中吐出,不為意間,竟被莫煩凡偷偷地一一拾起,放在掌心。然後,待唐尼不察覺的時候,他把種子小心地放入他的鮮綠色絲質小包內。
這天,寺院還安排了他們兩人到附近的琥珀嶺(Popa),他們更會在那裡的寺廟躭上一兩天。琥珀嶺是在群山包圍的山谷中央,突然冒起的一座筆直山峰,頂部建有一座有金塔的寺廟。寺院的基石有彩條橫間,基石正好完整地圍繞了山峰最峭的頂部懸崖一圈。金塔寺院與整座山峰的配合,遠看恰似另一個風格的迪士尼古堡。琥珀嶺歷史悠久,是著名的古代皇室御用寺廟,是歷朝歷代,每個國皇登基必到的祭天之地。
唐尼與莫煩凡在兩旁樹林的山路上漫步,從樹隙間隱約可見琥珀嶺。途中他們遇到汽車拋錨的過客、討吃的天真村童、還有在路邊候車的旅客,大家都各自打成一片。村童手中拿著食物、文具、肥皂、牙刷等,旅客們把身邊可用的日用品、又或者在下一站可以替自己補充的物資,都一一慷慨地送到貧困山中兒童的手上。對遊客而言,好一個既「心釋重負」,又身心痛快的旅程。
在路上,牧羊人在塵土飛揚中,趕緊把山羊群逐入矮樹林。第一場春夏交替的雨,終於豪邁地降落了。唐尼與莫煩凡走向一座紅色的涼亭,一群喧鬧地等候汽車經過時,追逐車尾討吃的小孩,竄奔的由亭內向外四散,各自回家避雨。
涼亭是木製的,紅色油漆大部分已剝落,露出了光滑的木紋。唐尼盤坐木板地,倚在亭柱,呆望亭邊地上被簷水打成的一列泥洞。莫煩凡發悶的望向琥珀嶺,手指像彈古箏般,撥著亭身圍欄上的水珠。
「還會好天嗎?剛才陽光還烈烈的,現在去了哪裡?」莫煩凡有點悶躁。他的視線由琥珀嶺的寺院彩條基石,轉到唐尼臉上︰「你猜倘若天色轉晴,天空會否出現彩虹。」
「可能吧,幹甚麼?又想來許多一個願?」唐尼建議著。
「嗯!」莫煩凡用有點像日本片集裡,那種演員慣用的、肯首確認式的回答。
唐尼由地板彈起來,環顧四方後,他選擇了地板上剝落紅漆最少的一片地方,拋下他袋中的孔雀藍詩集,然後,他要求莫煩凡把繡花包拿出來,把紫色綁繩與鮮綠色小包分開。莫煩凡恐怕唐尼看見包內的種子,於是要求私自處理這個行動,並按唐尼的要求把繩子與包包分開,放在詩集兩旁,而唐尼亦迅速在亭外摘下一片沾滿雨水的綠葉,拋在小包旁邊。
唐尼慢條斯理地走向莫煩凡身邊,拖著他的手,走向地板上最紅的一個角落,左顧右盼地回頭對著莫煩凡微笑。雖然沒有朝陽打在酒窩的臉上,但在那瞬間,莫煩凡卻看到了與唐尼第一次外出化緣時,經過溪澗上的石橋那一刻,唐尼在晨光中,向著他微笑的神采。
唐尼風度翩翩,一手依然緊拖著莫煩凡,另一隻手順著彎腰的方向,傾前「介紹」般向地上排成一列的東西一指,傾情地對莫煩凡說︰「這裡總共有七種顏色。」說時他還指向莫煩凡與自己身上的袈裟,以及他腳邊一片大紅地板︰「是我為你設計的彩虹,滿意嗎?一齊誠心許個願吧。」
莫煩凡若有所思地望著絲質小包,最後,他放下了唐尼的手,把包包拾起,繫上繩帶,放回自己的布袋內。
雨,依然下著。烈日後的雨水,蒸出了一份薄霧般的水氣,順著山風飄渺在樹林間。琥珀嶺不見了,哪來彩虹。
to be continued……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梅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 131 ~ 179 | 蒲甘夕戀【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梅逸 出版社:集夢坊 出版日期:2014-07-0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192頁/15*21cm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蒲甘夕戀
兩個男人,一段跨越四十年的情感
以澳門與緬甸為故事背景,交織出異地的同性火花……
澳門西灣海堤岸公園旁的孤兒院與小學隔著一條街相對,唐尼與莫煩凡的命運由此開始交會,卻不知是緣薄緣淺,一直未曾有過交集,直到兩人以計程車司機與乘客的身分相遇,他們的故事才得以繼續。
在唐尼的邀約下,兩人一同前往緬甸短暫出家順便觀光,在寺院只有彼此相伴的簡樸生活,與緬甸美景的催化下,感情與日俱增,幾乎要跨過禁忌界線,但兩個已婚男人、在異國身披袈裟,加上生長背景的懸殊,莫煩凡卻決定逃離……
書名兼篇名的「莫問我是誰」,可以是「莫問:『我是誰?』」也可以是「莫問我是誰。」前者是主角莫煩凡的掙扎獨白;後者則是對於這段情感的困惑與迷失。
本書以細膩且極具畫面感的寫作手法,描寫出介於「單戀」與「相戀」之間的模糊地帶,以及一位中年男子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感,所經歷的掙扎與迷惘,而書中描寫的緬甸風光,更為本書增添獨特風味。
作者簡介:
梅逸
來自香港,寫作多年,字字琢磨,擅長利用文字在讀者腦中推砌成一幅幅靜謐優美的畫面,特殊的描寫方式,讓文字躍於紙上,讓人有如觀看一場紙上電影。
章節試閱
上課的鐘聲響了,莫煩凡接過了一個勁度十足的球,比賽亦在四散入課室的學生嘈雜聲中結束。他為了發洩球癮,不太理會自己沒有穿鞋,雙腳因而有所損傷。他喘著氣,一跛一跛地走向唐尼。對方迎了出去,一雙眼睛帶點擔心的注視著他的腳。
雖然他們身披袈裟,但身分始終是半個旅客,所以當天他們在寺院中安排了日後的行程,出家的日子即將結束。
這座位於蒲甘近郊的寺院,範圍廣闊,唐尼與莫煩凡到處瀏覽。這裡將會成為他們的基地,意味著他們會在此還俗,結束緬甸的旅程。
唐尼走到寺院一處較高的地方,在鐘樓上示意莫煩凡他們將會遊歷的平...
雖然他們身披袈裟,但身分始終是半個旅客,所以當天他們在寺院中安排了日後的行程,出家的日子即將結束。
這座位於蒲甘近郊的寺院,範圍廣闊,唐尼與莫煩凡到處瀏覽。這裡將會成為他們的基地,意味著他們會在此還俗,結束緬甸的旅程。
唐尼走到寺院一處較高的地方,在鐘樓上示意莫煩凡他們將會遊歷的平...
»看全部
目錄
序幕
剃度
掛單
化緣
佛法
僧旅
身世
生日?
三個喪禮
流年似水
莫問我是誰
三盞燈之金石
三個願望
失落
命貢現身
奇遇玻璃宮
蒲甘夕戀
遺章、遺笛
剃度
掛單
化緣
佛法
僧旅
身世
生日?
三個喪禮
流年似水
莫問我是誰
三盞燈之金石
三個願望
失落
命貢現身
奇遇玻璃宮
蒲甘夕戀
遺章、遺笛
商品資料
- 作者: 梅逸
- 出版社: 集夢坊 出版日期:2014-07-02 ISBN/ISSN:978986901104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