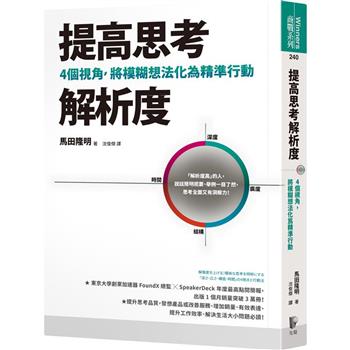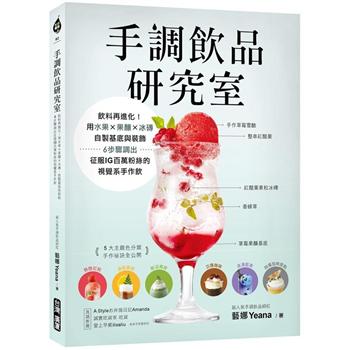透過地方耆老口述、貼布畫看日治時期未竟殖民村——豐田村的前世今生。動人心魄的百年敘事,花蓮的地方誌,臺灣的歷史註腳之一。
口述、貼布畫
土地與人的生命故事,
豐田村的前世今生,
臺灣族群的足跡。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社區工作者結晶。
「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那裡的人必定對它充滿感情;年輕人會透過這些故事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我是誰?將來或許有一天,他們為種種原因離開花蓮、離開東部、離開台灣……但是他們不會迷路,需要回家的時候,會知道方向。」
2018年的Unknown Asia Art Exchange OSAKA展覽,評審在216個亞洲各國的藝術參展者中,將「Kanoknuch Sillapawisawakul賞」頒發給來自台灣東部的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獎勵二十年來由兩代社區工作者,引領東部超過40個村落、近千名長輩用他們止不住顫抖的雙手,捏著小小塊的二手衣物碎布,沾著糨糊,一片一片創作自己的生命故事。關於戰爭的恐懼、貧困的滋味、女性處境、遷徙的足跡,以及對家人的思念、往者的追憶……一幅幅畫面,也凝固了東部各個時期的生活圖像。
豐田村曾是日本「未竟的殖民村」,加上後來的新移民,說豐田村是個不斷移出移入的聚落,一點也不為過,而透過這些「個人」生命經驗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集體」的豐田村誌,以及台灣東部發展史。
本書由貼布畫出發,配合長者的口述,將圍繞在豐田以及鄰近所發生的故事串連,顯現百年來人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樣貌與發展。不僅是地方誌,也是台灣史的註腳之一。
「或許,許多故事、許多豐田乃至臺灣的歷史之謎,終究還是會為歷史淹沒,永遠消失。但那都是我們這一片土地的前世。台灣的前世,比我們想像的還悠久,而臺灣這一片土地的今生,就從你認識她的此刻開始⋯⋯」
推薦——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須文蔚(詩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楊翠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劉克襄(作家)
劉秀美(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作者簡介:
楊富民
1992年生,東華大學華文所碩士班,社區工作者,專職社區營造與輔導、地方發展、青年培力以及地方文化與藝術工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講好花蓮故事,由豐田開始——
斑斕的工藝,素樸的文字,編織、縫合後山百年故事。
藝術敍事,鄉土情懷,歷史記憶,民間智慧,田野調查,庶民文學。
這是一本奇特而動人的地方誌,生命史。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看到書名的「村誌」二字,或許令部分讀者卻步,以為地方誌會充滿古奧難懂的歷史文獻、或是讀來枯澀無味,但《後山來去──豐田村誌》卻是一本打破上述刻板印象的作品。牛犁協會透過「藝術敘說」的方式,不只讓長輩們的口述歷史有了可供著力的起點,也讓記憶得以被視覺化,凝結在既繽紛又樸拙的「貼布畫」中。故事太多,無法一一盡錄,因此本書選擇透過幾位主要敘事者的經歷,串連起以豐田為圓心的歷史,再穿插若干結合貼布畫的簡短口述,相互交疊出這個「未竟的殖民村」的前世今生。它是關於一個村子的故事,也是關於戰爭、歷史、族群、女性、移動、婚姻、地方經濟……的故事。而這些動人的口述史所帶給我們的,毋寧是一個更重要的訊息:人的身分與認同,從來無法被化約在單一的符碼裡。
事實上,以貼布畫進行敘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種提醒。一個畫面,可以是一段經歷、一種身分、一個地點、一些物件;有些故事貫串了一輩子,有的則始終停格在某個時間點──畢竟,人們記憶與解釋歷史的方式各有不同,有自己面對及度過磨難的態度。看似明亮的用色,描述的可能是令人心驚的轟炸與創傷,較為黯淡的,也可能是雲淡風輕版的「我這樣過了一生」。若單憑視覺印象貼上標籤,就會忘了敘說的意義正在於圖文未必要相符,而是相互補充與「再發現」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若將一幅畫視為整體,湊近凝視,就會發現每個細節都來自不同的布料,有著殊異的紋理,任何單一元素,都無法充分呈現內裡的複雜性。《後山來去》的本身,無疑也是這樣一幅以豐田為主題的大型貼布畫,既反映出高度的時代共性,也訴說了獨一無二的生命敘事。——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楊富民是個固執的青年,從讀高中開始,他就守在一方小村,為長輩記錄故事,帶動阿公和阿媽製作貼布畫,從一個一個生命故事中,還原臺灣人流離、遷徙與苦難的歲月。透過他的努力,花蓮的長者參與了國際的畫展,有自己的三媽藝術節,製作專屬銀髮族的「山海襪」,召喚了一大批的青年朋友,建構花蓮社區創生的奇蹟。現在楊富民透過口述與貼布畫,完整還原了村頭的歷史,把記憶的詮釋權從官方奪回,交給創造時代的人們和土地,讀來令人震動!——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兩代社區工作者,行腳超過二十年,以藝術說故事,透過文字與貼布畫,多線敘事,多音交響。
從土地母體出發,循著地誌水文,以一則則生命故事,編織成一帖島嶼身世簿。二戰時期美軍空襲、家族鄰里合力蓋屋、發現寶玉的喜悅、女性在婚姻家庭與自我生命間的盤桓追索……所有故事,都與離家與返鄉的永恆辯證有關。
我們心中都有一處田水豐美的家園。這本書,是一張地圖,是一部導覽手冊,也是一個熱情的領航員,帶領我們返回自己的鄉土。——楊翠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緣自豐田小村鎮的交會,我和牛犁(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工作者都是多年老友,在許多社區事物也有多方的交流和切磋。上一代以自己在第一線實務操作的寶貴經驗,以及執著精神,經常補足我在偏遠鄉鎮的疏離。下一代則以年輕人的熱情和浪漫,創造諸多有趣的生活可能,拉近我跟鄉鎮青年的距離。
關心社造多年,有此巧合機運自是相當珍惜。在我的認知裡,牛犁本身的學習和摸索無疑也是許多臺灣社區的典範。本書的出現讓我隱隱感覺,那是他們積累許多豐沛經驗,渾然成熟的作品。透過長時田野的調查內涵,我們不只看到了豐田村的歷史,也更加清楚這個社區協會多年的努力,既從容又完整展現的斐然成績。 ──劉克襄(作家)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大轟炸、流徙、豐田玉,
他鄉還是故鄉。
苦難與美好共譜一世紀的豐田故事,
這是一本地方耆老以生命記憶拼貼的豐田,
是地方,是人,是情感,也是歷史!
花蓮因《後山來去》而耀眼,
豐田因它而飽滿。
走入時光隧道,
豐田歲月層層疊疊。
是那動人心魄的百年敘事。——劉秀美(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名人推薦:講好花蓮故事,由豐田開始——
斑斕的工藝,素樸的文字,編織、縫合後山百年故事。
藝術敍事,鄉土情懷,歷史記憶,民間智慧,田野調查,庶民文學。
這是一本奇特而動人的地方誌,生命史。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看到書名的「村誌」二字,或許令部分讀者卻步,以為地方誌會充滿古奧難懂的歷史文獻、或是讀來枯澀無味,但《後山來去──豐田村誌》卻是一本打破上述刻板印象的作品。牛犁協會透過「藝術敘說」的方式,不只讓長輩們的口述歷史有了可供著力的起點,也讓記憶...
章節試閱
大轟炸
米軍的大鳥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十月,米軍派出三千三百五十二架飛機轟炸台灣,若男因此十月過後停止了學業。那天「大鳥」飛過豐田,躲在溝底的若男看見了,三妹也看見了。三妹當時出門換生活物資,正從森本(今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一帶)走回大平(今壽豐鄉豐坪村)。戰爭越拖越長,生活裡如鹽、糖、米、醬油等開始管制,後來連火柴、木炭、蛋都是「切符制」,需要用票券兌換,連農業用肥料,衣著纖維產品也限量。
三妹的養父這時幫日本人做長工,沒辦法像其他漢人有土地耕種,可以偷偷藏作物,何況私藏作物,一旦被發現可會挨警察一頓棍打。養父的工錢還算可以,不過就算掙得再多也買不到吃的,幸好養父狩獵技術不錯,時常有一些收穫以度過斷炊的日子,只是打獵也得悄悄上山,設下陷阱,再悄悄查看。
空襲那一刻,她手捧著一袋配給米,正看著一班火車經過,車上載滿甘蔗與背著大包、小包行囊的人們。有人向她揮手,她於是把米放在地上也朝他們揮手,一直到火車遠去。回家路上,她故意彎進甘蔗園裡。她喜歡高高的甘蔗,一根根挺立在田地上,一叢叢茂密得像迷宮一般。趁附近工作的大人沒注意,竄行甘蔗園,左拐右繞,非常有趣,如果到頭來都沒被發現,更像是完成一項偉大的壯舉。但這天,甘蔗園才走到一半,依稀聽到嗚咿嗚咿的警報聲,遠遠近近就騷動起來。或許防空演習慣了,三妹一開始並不心慌,雖然有些緊張,但還是「按兵不動」。之前日本人也教大家《台灣防空讀本》,縱使空襲每個人都有工作,家家戶戶與左右鄰居分工合作,成年女性一部分協助年幼孩子躲避,一部分準備運水、撲火;成年男性工作更複雜,除了救火救災,還需隨時準備與敵軍戰鬥,唯有年紀小的兒童可以單純躲避。這些十一歲的三妹都懂。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先是看看附近有沒有日本警察,若沒有,就原地等待警報解除;若有,就依照《讀本》拿梯子、水桶,又或者掩護孩童進入防空洞⋯⋯甘蔗林遮擋了他們的身影,也遮蔽了他們的視線,誰都沒看到天際那幾個正在逐漸靠近的黑點,直到警報聲響換成震破耳膜的轟隆隆,抬頭一看,不得了,米軍的「大鳥」!三妹再也顧不得玩了,米袋一拋,逕找有人的地方跑去,跟著他們跑了起來。「大鳥」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三妹跟著逃的大人眼看跑不過飛機了,於是回頭猛地把她抱起、撲倒,緊緊摀住。
三妹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大鳥」已從他們頭上飛掠而去了。如今八十多歲的她還記得,同村阿姨緊緊抱著她,和她一樣全身顫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全世界在那一瞬間反而寂靜無聲。「大鳥」上的人盯著她,沒有任何表情,就這樣看著她,一眨眼也隨「大鳥」消失而去。
爆炸與機槍的聲響隔了好一會兒才傳來,她和阿姨幾乎等了有一世紀之久。站起身來,阿姨幫她拾起米袋,挑揀散落一地的米粒。走出蔗田,看見警察騎著單車遠遠趕過來,三妹沒忘記向他問好。警察前來教訓那些空襲時還佇在田邊的工人。這時,有人從火車站那兒跑來,一路喊著火車死人了。眾人於是紛紛拿起農具,一起往火車站奔去。
三妹回到家才知道,那天火車遭米軍掃射槍砲,車上沒有幾人生還。包括那些與她揮手道別的吧,他們真正的離開了。
日人大撤退
本願寺銅鐘
要回國了。但他們的家在這裡,國在海的那裡,回國就是離家。
戰敗的消息傳來,日本人提心吊膽,一開始盛傳夜裡台灣人將會有暴動,就連警察也告誡:「晚上早點睡,沒事不要開燈。」豐田自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全村通電以來,夜裡第一次完全陷入黑暗之中,連一小盞燭火也熄滅。
但,小松石夫依然堅持在傍晚點亮神社的石燈,因此,整條街、整座村,就只有神社這裡一光煢煢。點完燈,返家路上,望著街上一片漆黑,小松石夫還是不免有些害怕。想起父親在世時,曾向他說起日本移民初來乍到來,夜裡擔心可能會有原住民出草,大家輪流巡邏,因此也導致後來吉野村的建立。
當初,大家一心想著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根,村子裡的地神碑立於昭和十年(一九三五),上頭寫著「日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所有人都以為會在這兒千秋萬代,不料也才三四十年的光景就得離開了,真是異常諷刺。
小松石夫的父親,小松兼太郎曾在自己的《一代記》裡寫著他們如何來到這裡: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我(小松兼太郎)與臺灣總督府的官員檜垣直枝先生打好關係,提出前往官營移民村的意願,並獲得了錄取。六月五日動身啟程之時,在浦戶港搬運貨物的歸途當中,生了場病只得返家……來到台灣開墾的條件嚴格,不僅家世要清白,還要求家人必須得一起搬遷而來。最重要的是身體一定要健康,政府不希望讓人去到台灣開墾,卻要請更多的醫生去照顧他們。
同月的二十日我終於痊癒,從老家出發,於二十一日抵達神戶。在後藤旅館住一宿後,與認識的木下磯吉、德永榮次郎家族一起搭乘「備後丸」,於二十五日抵達基隆。傍晚,我與同行的人們在基隆港轉搭「小倉丸」,終於在二十六日來到花蓮港。出花蓮港沒多遠便是火車站,我們搭上火車,在當天正午十二點至豐田。歇息片刻,便立刻接受移民指導所的職員三浦先生的檢查。
當時我身上帶的現金共有兩百零八円整。三浦先生讓我們抽籤,分發土地與居住地,我分配到森本居住;雖然聽說那時候最好的特等土地是大平,但是來到新的地方、新的開始的這種興奮感仍是難以掩蓋。所以,總共經歷整整六天的路程,走過海路、陸路,我們落腳這裡──豐田。
趁三浦先生填寫資料時,得有餘裕觀看豐田。所在的車站,僅以四根竹子作為柱、四根竹子做為梁。上頭則以茅草鋪成當作屋頂,若雨勢大一些,底下的人們勢必淋得全身濕透。車站也沒有月台,人們上下車,就是火車停在那裡,大家自行爬上爬下。
遠遠近近只有一根電線杆,芒草、牧草長得比房屋還高。三浦先生將資料填寫完畢,開始介紹移民村,最後特別交代:「晚上因為擔心有原住民族的攻擊,實行宵禁,不得在夜裡點燈。」
小松石夫步出神社,回望隨風搖曳的燭光凌亂了鄰近的影子。他內心的難受非關敗戰,真正傷心的,是必須離開這片土地。父親手記裡,還寫著他們在這片土地上所經歷的種種,而那也是他的童年回憶啊⋯⋯他不禁嘆了氣,離開這片土地儼然背離了父親、背離自己的童年,離開了這裡他還會是誰。
《大正三年暴風雨記事》:
同年(大正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七日蓋起牆垣,大約十點左右,北風驟然吹起,不時有大暴風出現。風塵揚起,十二點時家屋已近全毀。接著下起雨來,就在家人一起逃出屋外的同時,房子瞬間崩塌,幸虧無人受傷危及生命。
同年總共發生七次颱風。八月十二日一場大雨,隔天便引來洪水。
二十九日又是大雨,隔天同樣一場洪水。
為了解決水災,宮浦西邊往下深掘了百間面積的土地,築起了土製堤防。
九月一日,由於水流會從森本部落元二組自宅的西邊侵入,便在同一個地方築起了土製堤防。這時的指揮官為高橋事務官、小笠原主幹及中渡邊巡查。高橋事務官等三人裸著上身用圓鍬努力地防止災害的發生,大坪部落的全體居民也一同為了防災而努力。
移民指導所送來飯糰招待大家。而後,水流暫時從我家地板下方流去。最後,土地受大水侵襲,導致全毀的地主有曾我部淺治、曾川定八、西村槌松……等十八人。
在森本部落東邊的特等地則有五人的土地不是全毀就是半毀。
這場暴風雨發生在豐田建村的第二年,整個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大家對重建完全喪失了信心,更何況繼續生活,雖然總督府撥下不少慰問金。他們毫無動力的聚集在小學校的劍道館避難,間或有人和移民指導所的官員起了爭執,他們想要回去了,指責官員欺騙自己的國人來到這裡,罔顧大家的生命安全。說好提供土地與房子,土地卻需要開荒,房子建了卻倒,甚至有人染病,死了沒得土葬、沒得緬懷,只能盡快火化,成了一罈子灰。
父親為日記題名「一代記」,小松石夫知道那是父親一直到臨終前抱持的心情——要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重建家族。早年回去的人不少,留下來的人不多,父親卻始終堅持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他氏子總代的身份,有責任與義務將天皇、天道諸神的餘蔭,在台灣建立庇佑世世代代的神靈之地。只是父親萬萬沒想到,一代記,就此不得不中斷了。
小松石夫默默走上參拜道,往鳥居方向走去。整個村落因宵禁一片黑暗,今日天上也不見星月,但小松石夫還是依稀看得見遠方鳥居的輪廓。雖然由水泥所建,不如木造來得精美,但卻是村子裡最堅固的建物。早期大家不明白台灣的氣候,一開始用木頭搭建嶄新、亮麗的鳥居,不到一年便腐爛毀壞,從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以來重建了好幾次,之後才改用水泥,成為當時除小學、移民指導所之外為數不多的水泥建物。
參拜道旁有十幾棵麵包樹,是由移民指導所與第一代村民共同栽種。父親曾說,這些麵包樹是村子的重要作物,當初日本政府從南洋帶回來的樹種,整個夏天一棵樹可以結上一兩百顆麵包果,撥開果實裡的籽煮湯,味道嘗起來像花生,果肉用來煮菜入湯,是番薯之外的選擇。暴風雨頻仍的那一年,一代們的作物少有撐過那個暑天,唯獨麵包樹上的果實卻在颱風後依然一個一個冒出來,比番薯還可靠。
走完參拜道進入神社之前,需先跨過一座小石橋,神社每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慶典就是從這裡開始。往裡邊走,可以看見一尊金太郎抱大鯉魚的雕像矗立在池子中央。第一代先輩中有許多人因瘧疾、風寒病逝,為祈求新生的孩子不會同遭厄運,大家便合力請人在神社建了金太郎像,期望出生在豐田的後代都可以像金太郎般健壯地長大。
只是戰敗了,這些都不再屬於他們的了。最後,神社、金太郎、鳥居,還有開村紀念碑——當初由台灣總督親筆題名,這些都只能留在原地,成為見證,見證他們曾在這裡的痕跡。帶不走的無可奈何,事實上,帶得走的,才是最煩惱的。小松石夫最煩惱的,就是擺在家裡的那口林田本願寺銅鐘。
父親小松兼太郎作為氏子總代,初來豐田便被指派為代理社掌,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正式成為社掌,花蓮港廳的三個官營移民村——吉野、豐田、林田,其中豐田神社即由他負責。當年豐田神社迎請御靈代可是件大事,整個花蓮港廳的大事。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三日,迎接御靈代的主幹林久松指揮,以及小松兼太郎等人代表前往花蓮港。隔日清晨前往海邊靜候,一同等候的還有花蓮港廳廳長飯田先生。
御靈代搭乘舞須丸號在當天已抵達花蓮港外海,轉搭小船進港。小船用白布包著,當時的鈴村主典兼任御靈樞奉守,捧著御靈代從小船下到碼頭。在場的所有人,包含花蓮港廳廳長以及廳長後方一行人,包括港廳所有官方單位的課長、各町長官與居民,以及各個巡查、氏子總代、吏代,有頭有臉的仕紳都到場,眾人神情無不莊嚴肅穆,一點言語都不敢發出。
正午十二點,眾人沿著碼頭一路走向火車站,塞滿了花蓮港廳最熱鬧的黑金通。這麼多人卻沒有造成交通阻礙,正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在行列之中。火車抵達豐田站,由小松石夫的父親將御靈代供奉上台車,飯田廳長走在前頭,一路前往移民指導所。沿路的居民不是隨行,便是在自家屋前恭候。
小松石夫當時年紀小,只記得熱鬧非凡。
父親過世,社掌這樣的職位理所當然由小松石夫繼承,除外還有林田村的林田本願寺,父親後來受村民請託成為本願寺的住持。戰爭爆發,小松石夫擔心本願寺成了米軍轟炸的目標,便將寺裡的銅鐘帶回家保管。這口銅鐘的意義重大,本願寺是佛教寺院,這口銅鐘主要的目的在於超度亡魂,戰爭期間往生者眾,鐘若遺失,便沒有辦法將各地亡魂引導去屬於他們的地方了。
不料,戰爭打得久,結束得快,作為敗戰國,小松石夫不僅來不及超度亡魂,還面臨被遣返日本的命運。他親眼見本願寺銅鐘鑄成,本以為銅鐘也會成為家族世代的責任,傳承父親、也傳承先輩開創這片土地的遺志,但眼前卻成了他最大的負擔。
他不免想過將銅鐘帶回日本,但回到日本,自己是否還會有神職者的身分,他無法確定,或許連敲銅鐘的資格都沒有,何況鐘上頭寫著「林田本願寺」,就代表了它屬於這裡、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們。另外,更現實的層面,是每個回日本的人只許攜帶一件不超過三十公斤的行李,以及一千元以內的現金,光是這口鐘,就可能就抵掉兩三個人的行李重量⋯⋯
小松石夫回到家,躺在榻榻米上,想著想著,意識也如同夜色般濃黑,走入夢鄉,他依稀正乘著船在太平洋上晃蕩,準備歸返那個素未謀面的祖國。
流徙
船過黑水溝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彭黃來二十一歲,住在廣東揭西縣五雲鎮流平村,村子裡人人都姓黃,是個客家村落。因為黃是村子裡的大姓,她的父親便將女兒的第二個名字加上母親的黃姓,以免孩子成長過程中,受村子裡其他孩子欺負。
對彭黃來而言,回憶在中國的那陣子,就像上個世紀的遠。人們猶沉浸在抗戰的勝利中,卻聽說又打起來了──共產黨與國民黨。雖然戰爭還沒蔓延到這裡,但村子裡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糟,大家再次回復到戰前的愁眉苦臉。
丈夫某天工作回家告訴彭黃來,聽說國民黨軍一路節節敗退,在西南的往西南跑、在東北的往東北跑,在東南的也往東南跑,不久就全部會經過這裡,戰爭一天比一天接近了。丈夫說:「再不走,將來國民黨、共產黨的軍隊過來,村子能不能保住不知道,倒是他或許會被軍隊抓去。」抗戰時國民黨的軍隊來到村子徵兵,丈夫的大哥,她的大伯作為長子,早早就加入軍隊,從此音訊全無,原以為勝利後哪天村口就會出現他的身影。
經丈夫這麼一說,彭黃來之後幾天都吊著心情,她幾次問丈夫:怎麼辦?怎麼辦?丈夫也看著她問:怎麼辦?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一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彭黃來一輩子沒念過書,是丈夫看了信,只聽他說了一句「是大哥」,之後神情像是煙火,一下明、一下暗。她急著問先生怎麼回事?
「去台灣吧。大哥信裡寫,他隨著部隊去到台灣接收,台灣好,荒蕪的土地很多,如今日本人也走了,土地更多。反正在廣東也是種田,到台灣為什麼不能種田?」
夫妻之間幾乎沒有爭執,雖然彭黃來這輩子連村子大門都沒出去過幾回。他們不等戰爭真的來臨,收拾幾天便啟程,帶著七歲的小叔,拎著行李,就這麼上路。走上幾天來到鄰近的海港汕頭,在汕頭待了三天,丈夫幾乎用盡所有錢財,終於尋覓到一艘可以將他們送去台灣的船。上了船,看著岸上萬頭攢動的碼頭,內心不免有些慶幸。不久,船在黑水溝上顛簸,他們接連四五天死去活來的吐,還得費心照顧七歲的小叔。但總算見到陸地,船上的人說到了高雄。
來到台灣的彭黃來與丈夫終於可以鬆懈下來了,渡過一道海,才真正感覺戰爭遠離著他們。他們在高雄歇息了兩天,丈夫上街問往花蓮的路怎麼走,那人問他走山不走山?先生問什麼差別?那人回答,山是原住民的。於是他們聽了那人的話,先往南去到屏東。他們沒有多餘的財資,搭趟船也幾乎耗盡所有。一路上省吃儉用,經過旅社也不敢停留,傍晚找寺院、廟宇或者土地公廟,與神明搭伙過上一宿。
「台灣人的心腸一直都好。」七八十歲的彭黃來至今仍是這樣說。那時候除了廟宇,走近村莊,村民看他們落魄又骯髒,卻從不嫌棄,常在他們背後叫喊著,要他們別再走了,讓他們在禾埕上、牛棚裡過一夜。
小叔年紀小,吃不了這樣的苦,常常在路上哭鬧。有回離開屏東進入台東,經過一處原住民部落,小叔怎麼樣都不肯走了,他們便把小叔背起來,只是小叔仍是不斷哭鬧,聞聲而來的居民說著他們聽不懂的語言,三步兩步跑到跟前,拎著兩包米,還有一串用細絲串起來的玉米,塞在他們手上。彭黃來開始相信,大伯信裡說的台灣好了,真的是好。本來與丈夫快沒勇氣再走下去,是沿路的人們給了他們繼續的力氣。只不過那樣的時代難有幸福的故事,一路上為了給自己弟弟吃飽、照顧妻子的丈夫,在抵達花蓮時,臉色一天比一天差,先開始下痢,然後渾身發冷。路是走不下去,彭黃來只得牽著小叔,讓先生掛在身上往前走。
來到大富村,好心的村人告訴她,丈夫恐怕是得了瘧疾,日本時代有藥也醫不了。彭黃來聽到覺得天像是坍了,她急著問那村人能夠如何?那村人搖搖頭,找醫生吧。於是她將部落給的那兩袋米剩下的一袋遞給村人,她哀求著問,幫她找醫生吧。村人仍是搖頭:這時節,醫生死的、失蹤的都有——醫生沒了。
那名村人讓彭黃來到他家田寮過一夜,勸她想好後事。彭黃來夜裡抱著丈夫與小叔哭泣,天明醒來,發現丈夫身軀已經冰冷、發僵了,再沒有呼吸。村人幫她將丈夫火化,見彭黃來孤家寡人帶著一個孩子,便介紹一當地國小老師家,讓她去當幫傭。
她年老了想起這件事情,說她這輩子似乎一直都趕不上哀傷,即使那時節她內心難過得無法形容,生活卻不讓她好好掉下眼淚,她還有小叔要養育,還有日子得過下去。她沒再去尋丈夫的大哥。幫忙的老師後來介紹她認識一名姓徐的先生,她知道帶著小叔在老師家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明白老師的薪水微薄,何況還要養上他們。於是她成了徐姓男子的小妾,徐家幾個孩子的小媽,隨他們來到豐田。
她看著小叔長大,把小叔當自己的孩子,直到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的那一場叫溫妮的颱風,把她的過去統統帶走。
颱風大得驚人,村子裡的屋子一間間吱嘎作響,夜裡不斷聽到有人在吶喊、驚叫。她與一群人守在大老婆的媳婦家,媳婦正要生產。外頭轟隆隆,有人說神社塌了、誰家塌了。小叔正值年輕力壯,早早跟著一群男丁出去幫忙。女人跟小孩在黑夜裡,耳邊除了風的呼嘯、房子的喘氣,還有媳婦生產的呻吟。漫漫長夜,都不知道怎麼過去的,直到一聲嬰兒的哭啼,眾人才回了神。天亮了,颱風逐漸停歇,有人說孩子一出生颱風便走,是個好兆頭,眾人於是才相視微笑、道賀。
家門被推開來,來的人先道了喜,許久才終於結結巴巴的說,彭黃來的小叔不見了,他們一行人在溪邊挖土堤引水,一陣大水沖來巨木撞向小叔,大夥兒來不及拉他一把,只見小叔被巨木擒著消失在黑夜中。
後來再沒人見過彭黃來的小叔,一片狼藉中也沒有人有多餘的力氣為別人哀悼。
大轟炸
米軍的大鳥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十月,米軍派出三千三百五十二架飛機轟炸台灣,若男因此十月過後停止了學業。那天「大鳥」飛過豐田,躲在溝底的若男看見了,三妹也看見了。三妹當時出門換生活物資,正從森本(今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一帶)走回大平(今壽豐鄉豐坪村)。戰爭越拖越長,生活裡如鹽、糖、米、醬油等開始管制,後來連火柴、木炭、蛋都是「切符制」,需要用票券兌換,連農業用肥料,衣著纖維產品也限量。
三妹的養父這時幫日本人做長工,沒辦法像其他漢人有土地耕種,可以偷偷藏作物,何況私藏作物,一旦被發現可會...
作者序
前言
這座島嶼過去漫長的一段時間,被國家、家國、國族意識以及和中國對抗的情境綁架,舉凡認同、歷史、族群、人民,幾乎都在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服務。直到這一代,我們才恍然想起這麼一個問題──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
自荷鄭時代以降,臺灣長期處於各種政治目的底下:荷蘭時代的航海據點,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哨站;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基地,以對抗另一個國族;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期望臺灣成為大清領土的海外屏障;日本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日本帝國主義開展;近代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以及進入解嚴,貌似成為當代美中關係下的無煙戰場。
將近五百年,臺灣已然成為一個為他國、他權存在的島嶼。雖然我們不斷宣稱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看似如此,真實的情況又如何?我們有「權」嗎?我們的「主體」又是什麼呢?這樣曖昧不明的臺灣,會是那個反共剿匪的臺灣嗎?還是更應該追溯到原住民文化的南島語族文明?又或者追索《馬關條約》?探詢日本投降的《終戰詔書》與《舊金山和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解答,每個人都能夠宣稱自己是臺灣人。這樣一個紛雜且眾聲喧嘩的島,正好是這五百年來結下的「果」。
然而,臺灣到底是什麼?答案看起來明確,臺灣就是臺灣,不是過去任何時期的臺灣,是當下、此刻,我們所居住的島嶼。不過這樣的回答仍然讓人心虛,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這才發現,我們竟然沒有能力為這座島嶼詮釋;我們這才發現,我們並沒有真正明白臺灣是什麼,甚至都不能夠肯定誰是臺灣人。
這本書試圖藉著微觀臺灣人的故事,讓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坦白的說,這本書並不會給任何一個人解答,因為臺灣也不會是這一本書,又或者一個東部足以代表。
故事來自於花蓮東部,一個名為豐田的小村莊。這一座小村莊,它除了是我這輩子的家,我至今未曾離開過的地方之外,它在整個臺灣史裡還有著特殊的一面。某個時間點、某種程度上,它純然是個移民村。這座小村在一九一三年由日本政府建立,近百年來,各地遷徙到此的人們,經歷了戰爭、天災、疾病,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最後重新出發,終於在這一片土地落地生根,成「家」、成「鄉」。
從這樣的一個小村宏觀整個臺灣社會,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整個臺灣的縮影。人們不斷在島內外移動,甚至在南島語族文化中、原住民的歷史中,也是不斷的移動,尋找新的故鄉,建立新的家園。
這本書的故事,是由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的社區工作者們,花費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蒐集,並以單純的口述歷史、史料調查和近期發掘的藝術敘說方式,擴大更多村民投入。它是一個由村民大家集結起來的村史、村誌。
口述的方式與過往有所不同,在於所謂的「藝術敘說」這一部分。它最早的起源,是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耆老雖然擁有故事,卻缺乏敘說能力,因此協會藉由藝術創作方式,刺激他們以圖像「描繪」個人的生命經驗,將過去的記憶用拼貼畫面呈現。於是這些豐田村的長輩們,用他們止不住顫抖的雙手,捏著小塊、碎片的二手衣物,沾著糨糊,一片一片黏貼在畫板上──也是接下來你會在書中看到的那些可愛、稚氣、樸拙的插圖。
截至今年(二〇一九),牛犁協會前前後後跑過了東部四十個社區,蒐集近千幅生命故事的「貼布畫」,有關於戰爭的恐懼、貧困的滋味、女性的為難、遷徙的足跡,以及對家人的思戀、往者的悼念……這些個人的血淚史,集結起來卻也是整個族群的遷移史與生命史。
這麼龐大的故事資料,到了撰寫成書的階段,難免面臨諸多取捨。令人感動的是,長輩們完全諒解我們的無奈,甚至認為他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件事情。他們渴望自己曾經走過的歲月,不會因此消失;渴望告訴後代,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渴望被人記得,生命被不同的方式流傳。
他們甚至渴望告訴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臺灣人──這座島嶼是你們、是他們、是我們的家。
這也是我從小在這座村莊感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客家族群、閩南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省族群,他們是我的朋友、是我在這片土地上的家人。我們許多時候並未真的細分他們是原住民、客家人,又或者如我是外省家庭。雖然知道,彼此會在習俗、信仰,略顯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同樣在這片土地上,互相照顧,與深愛對方。
與其說我希望藉這一本書,寫我們的村、寫我們的「臺灣」;倒不如說是這些長輩促使這件事情發生。他們知道,世代早該交替:過去因為社會環境、因為政治氛圍,許多未能說的事情,他們想趁還有餘力時告訴我們,這座島是如何成為我們的家。
前言
這座島嶼過去漫長的一段時間,被國家、家國、國族意識以及和中國對抗的情境綁架,舉凡認同、歷史、族群、人民,幾乎都在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服務。直到這一代,我們才恍然想起這麼一個問題──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
自荷鄭時代以降,臺灣長期處於各種政治目的底下:荷蘭時代的航海據點,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哨站;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基地,以對抗另一個國族;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期望臺灣成為大清領土的海外屏障;日本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日本帝國主義開展;近代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一...
目錄
一、 大轟炸
空襲警報
米軍的大鳥
二、 流徙
米棧村的養女
溝仔尾的香妹
本願寺銅鐘
不動明王
阿玉的綁腿布
三、 豐田玉
發現寶玉
失玉之後
四、 他鄉、故鄉
船過黑水溝
離家出走
想家
回「家」
新住民
一、 大轟炸
空襲警報
米軍的大鳥
二、 流徙
米棧村的養女
溝仔尾的香妹
本願寺銅鐘
不動明王
阿玉的綁腿布
三、 豐田玉
發現寶玉
失玉之後
四、 他鄉、故鄉
船過黑水溝
離家出走
想家
回「家」
新住民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