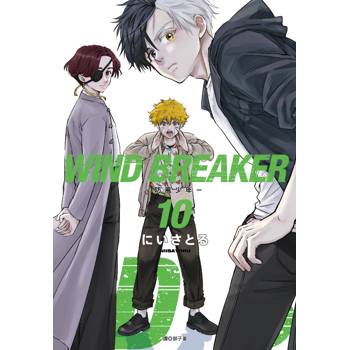台灣版序
承蒙小異出版的錯愛,拙著《趕屍傳奇》的繁體字版本即將在台灣等地出版發行,這對於我來說,自然是倍感高興,十分榮幸的。
《趕屍傳奇》正式動筆是二○○七年六月,在天涯社區的「蓮蓬鬼話」以及新浪、搜狐、騰訊等原創頻道進行連載,意想不到的是,點擊率一路?升。連載不到一個月,就有十幾家出版公司與我聯繫,意欲出版該書。書上市後,反響非常熱烈,銷售業績不俗。
中國大陸的恐怖小說創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起步較晚。但一旦起步,發展卻是非常迅速。優秀的恐怖小說作家脫穎而出,恐怖小說作品更是如過江之鯽,一時間,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在這樣一種紛繁的背景之下,怎樣才能夠獨樹一幟,也就成了希圖有所作為的恐怖小說作家的一個不得不好好思考的問題了。
我想,紮根屬於自己腳下這片土地,從這裡汲取養分,恐怕不能不說是一個好的選擇吧。基於這個考量,我把目光定位在神祕的湘西。
從出生到如今,我生活的這片地方,民國時,叫晃州,現在叫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縣,從地域概念上說,從屬於湘西。晃州也好,新晃也罷,都沒有幾個人知道。而它在古時,卻又可笑地聲名大振,因為,在唐宋時期,新晃曾兩度置縣名為夜郎。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為新晃的題詞是這樣的:「楚尾黔首夜郎根」。「夜郎自大」是一個令華人圈感到尷尬的詞語。從這個詞語中,便可知道,我腳下是一塊封閉且驕傲的地方。自古以來,湘西都流傳著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傳說,這裡聚集著侗族、苗族和土家族等土著少數民族,他們不但有自己的生活習性,還有不可示人的諸多的法術與禁忌,讓外人既覺得神祕,又覺得驚詫。我自己是侗族人,是伴著侗歌長大,浸淫在「叫魂」、「驅駭」、「放蠱」、「唱七姐」等有趣也有些驚懼的習俗的環境中長大的。做了多年的文字,我便想,何不就寫自己最熟悉而外人卻很陌生的湘西?於我自己,駕輕就熟,於讀者,又可滿足其對於詭異湘西的好奇之心?何況,寫自己家鄉的人事與鬼事,完全是信手拈來,甚覺輕鬆、親切。
於是,便初步定下了寫一個以湘西神祕文化為背景的系列懸疑恐怖小說。
現在,《趕屍傳奇》得到小異出版及責任編輯江怡瑩小姐的喜歡,於我,是一份意外的驚喜,但願於台灣讀者,也依然於是。
這是我的第一本在台灣出版的長篇小說,拙著能推薦給台灣的讀者檢閱,心下,又不免有些忐忑。從文多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也曾有一些小文在台灣的《中時晚報》、《自立晚報》刊發,那時起,我就有個想法,不僅僅是作一些小文以作在台灣的補白,而如果能夠有長篇小說在台灣出版,那將是我深感榮耀的事。如今,我的願望在小異出版及其責任編輯江怡瑩小姐的大力推介下得以實現,在此,請允許我向其表示衷心的感謝!
楊標
二○○八年六月
引子
太陽落入山背的一剎那,天,就像潮水一樣,鋪天蓋地的黑了下來。剛才還是人聲鼎沸,此刻,隨著黑暗的降臨,一下子就沉寂了。風從山埡口吹來,嗚嗚作響。在寨子中心的坪壩上,上千的人,上千雙眼睛,都盯著院壩中間的年輕女子。她端坐在用細篾織成的涼床上,頭低著,像一隻幸福的小羊羔,又像一隻等待宰割的小雞仔。那女子一身著紅,紅衣、紅褲、紅鞋,頭髮也用紅色的絲線紮著。三天後,是她出嫁的日子。這時,她的心裡,想的是她年輕英俊的情郎,還是她馬上就要面對的給她「開紅」的寨老?此刻,沒有人知道她的心思,也沒有人想那麼多,想多了,腦殼要痛,如果一不留神,想到了別處,還會惹得神靈不高興,怪罪下來,輕則三病兩痛,重則家破人亡。就是連她三天以後的丈夫,一樣不敢多想,要想,也就是祈求寨老稟承著神的旨意,把福祿財壽一古腦兒都賜予到他們那個紅紅火火的木屋裡,惠及他們的子子孫孫。
院壩邊緣,是寨老家那碩大的吊腳樓。這是全寨最大的吊腳樓,一共四層,比一般人家的多了一層。跑馬欄杆上,坐著一排人。坐在中間的就是寨老,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他目光肅穆地盯著院壩裡的人們,思緒很是渺遠。三個時辰後,他就要代替新郎行使給新娘開處的神聖使命。
「端公」肅然站立。他穿著紅色的法衣,一手執著一隻鏤了亮銀的牛角,一手執著包了熟銅皮子的法拐。端公的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因為,他的臉根本就沒有露出來。他的臉上戴著一副儺面具。儺面具是用上好的楠竹製成的,用朱砂、紅汞和著麝羊的血染成了紅色。整個紅色面具上,只有兩根白色的牙齒彎曲著,像兩個細小的月牙兒。面具的頂端是如火焰一般的頭髮,直立著,似乎要刺破那深不可測的天空。
端公把牛角湊到嘴上,一邊鼓起腮幫「嗚─嗚哇─嗚─嗚哇─」地吹著,一邊還把那法拐搖得叮叮地響成一片。牛角聲一短兩長,意味著法事正式開始。端公的徒弟雙手端著一只陶盆走到他的面前,單膝跪下,高高地舉起陶盆。只見端公把牛角掛在了自己的腰上,敲燃了火鐮,把陶盆裡的松明油點亮。那徒弟就把那陶盆放在院壩中。
端公再次將牛角吹了起來,這回,是一聲接一聲不歇氣地嗚嗚吹著。
連吹了三聲,那陶盆裡的火,便越發地旺了起來。
這時,人們一人手裡執著一把松明柴棒,排著隊,走到陶盆前,把那松明柴棒默默地伸到陶盆裡,點燃後再圍到院壩邊上。於是,滿院壩裡一片燈火通明。
端公的徒弟把端公身邊的豬皮大鼓咚咚咚地擂了起來,鼓聲雄渾激越,壓住了那呼呼的山風。端公走到場地的中間,左手高舉過頭,拇指與中指相連,捏了一個連心訣,高聲叫道:「讓神聖的火燃起來,讓神明的光亮起來,讓鮮豔的血飆出來!」
鑼、鈸、鼓、罄一齊敲響,上千的人吼叫著,一起聚攏來,圍著那紅衣女子和陶盆興奮地跟著端公一起喊叫:「讓神聖的火燃起來,讓神明的光亮起來,讓鮮豔的血飆出來!」
端公翻起了跟斗,人們圍繞著端公呼呼地舞動著火把,也狂熱地跳了起來,邊跳邊唱:
至高至敬的神啊,
我們把至美至賢的姑娘送給您;
至真至善的神啊,
我們把至鮮至香的初血獻給您,獻給您,
我們把至鮮至香的初血獻給您,獻給您,
我們把至鮮至香的初血獻給您,獻給您……
第一章
龍溪鎮又死人了
1
民國二十二年秋天,罕見的大霧如一團一團的棉花,翻翻滾滾地把整個龍溪鎮摀得嚴嚴實實。
「砰!」
鐵炮的聲音。又聽到了鐵炮的聲音。
小鎮上大凡紅白喜事,都免不了要放鞭炮。而鐵炮,只有在有特別或重大的事情時才放,因為它火力十足,那響聲足可以讓一個鎮的窨子屋都會微微地晃動,也足可以把沒有來得及摀住耳朵的孩子們一瞬間震得腦殼一片空白,然後耳朵裡才傳來一片嗡嗡的怪叫之聲。
聽聲音,是雜家院子那邊傳過來的。
呆呆地站在窗前的舒要根,眼瞅著湧進窗子裡來的霧罩,剛剛還感慨著好大的霧啊,就聽到了鐵炮的響聲。他眼前的那一團白紗般的霧氣,似乎也嚇了一跳,劇烈地搖擺了一下柔若無骨的身子,便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掌給劈成了碎片,飄飄搖搖地四散開去。舒要根的心裡不禁一緊,暗道一聲「不好」,就伸出食指把竹篾窗簾的環扣輕輕地一撥拉,那窗簾便像斷了線的風箏,嘩啦一聲掉了下來。房間裡一下子暗了。
這是入秋以來,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裡,龍溪鎮上第四次響起鐵炮的聲音了。也就是說,小小的龍溪鎮上,二十多天裡,死了四個人!
舒要根四十二歲,大腹便便,紅光敷面,一看就知道是有家有財的人。他在龍溪鎮上開著一家綢緞鋪,叫「昌祥永綢緞鋪」,生意一向興隆。他樂善好施,為人和氣,對錢財看得輕,對人情看得重,是龍溪鎮上的商會會長。
舒要根對正在抹著烏木桌子的傭人說:「柳媽,我要出去一下。」
柳媽直起腰,說:「好的,老爺。」
柳媽走到內室的門邊,對裡面說:「老爺要出去了。」
太太睡在床上,淡淡地說:「嗯。」
於是,柳媽才跨入太太的臥室,打開紅油漆衣櫥,把舒要根的外套取了出來,走出屋,輕輕地把房門帶上。
柳媽到舒家已有十多年了,這十多年來,老爺和太太對她很好,並不把她當下人看待。老爺和太太雖然不像別的夫妻那樣吵吵鬧鬧,但也不像有的夫妻那樣和和睦睦,一直是平平淡淡、冷冷清清的。自從少爺舒小節一年前去了烘江師範讀書之後,老爺就搬到另一間房睡去了,而他的衣服仍然放在太太的臥室裡。他要換衣服,也從不自己到太太的臥室裡去,而是叫柳媽拿出來。老爺與太太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磕磕絆絆,作為下人,她自然不好問,凡事都裝作不曉得,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舒要根穿上夾層長袍,外面再罩了一件青羽綾馬褂,想了想,還是把那頂絳色小緞帽戴到頭上,這才不疾不徐地下了樓,穿過天井,出了門。
柳媽這時才想起老爺還沒有吃過早飯,就喚了一聲:「老爺,您的參湯還沒喝呢。」
舒要根並沒有回頭,只是舉起右手,擺了擺,走了。
龍溪鎮又死了人,他不能不去看看。一個街坊叫他一聲,他竟然腳下一軟,差點跌倒。那人趕忙扶住了他,雙眼卻是很奇怪地盯著他的臉龐,不知道他怎麼會差點兒滾著。舒要根點點頭,急急忙忙地掙脫那人的攙扶,往雜家院子走去。他心裡隱隱約約地感覺得到,這人,再死下去,下一個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了。剛才,也就是正好想到這裡,才嚇得腳桿子打滑。
2
雜家院子在正街,拐個彎,沿一條不長的小巷走進去,就到了。這裡住著三十多戶人家,有楊、朱、鍾、劉、陳等姓氏,因為姓氏雜,就叫作雜家院子。
舒要根走進院子。院子不大,擠滿了人,顯得更窄小。院子中央擺著一張竹床,竹床上有一具屍體,屍體上面蓋著白布單。他正想問那躺在竹床上的是哪個,就看到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穿著青布衣服,手裡舞動著一張手帕,呼天搶地的在竹床邊哭:「你這死鬼,話都不吭一聲,甩下我們孤兒寡母,講走就走了……」
原來是開粉館的陳鬍子的老婆,那麼躺在竹床上的就是陳鬍子了。
舒要根按禮節勸慰陳妻:「人死不能復生,走的走了,留下來的還是要好好過的,莫哭壞了身體,吃虧的還是自己。」
陳妻平時是不敢得罪舒要根的,此時可以不顧禮節,可以無視老幼尊卑,可以不應付家親內戚,眼下最要緊的事,是把心腔裡裝著的怨恨和委屈都釋放出來,否則會出大事的。因為對意外事故的不堪承受和對未來的絕望,陳妻像是被抽了筋一樣,全身無力,如一只青色布袋掛在案板邊緣,因為長久的哭泣,她的臉好像腫脹了許多,五官也比平時擴大了些,根本不像平時那個笑咪咪、低眉順眼的女人。此刻她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抹著,正眼都不看一眼舒要根,繼續著她的哭訴:「嗯,呀,你個背時挨萬刀的……」馬上意識到自己的男人真是挨刀死的,有些忌諱,便轉移了話題。
「會長,唉,你看這……」一個管事的老頭過來,跟舒要根打招呼。
舒要根臉色陰沉,沒回話,也不用裝笑臉,走上前去,把白布單輕輕地揭開了一角。舒要根又是一驚。陳鬍子和前面死的那四個人一樣,眼睛都是睜開著的,瞪得溜圓,透著驚恐和委屈。他伸出手,把陳鬍子的眼皮往下抹,竟然一點作用都沒有。那眼皮看起來和活人的差不了多少,柔軟且有彈性,而實際上,手一接觸,那眼皮卻是冰硬的,非但沒有彈性,還像是石頭雕成的一樣,彷彿有點硌手。唯一讓舒要根感到那眼皮和活人相似的地方是,陳鬍子似乎也在用勁,用他的眼皮抗拒著你的力氣。你越想往下合攏他的眼皮,他就越是要往上睜得更大。稍稍地僵持了一會兒,舒要根就放棄了他的努力。他不知道,如果霸蠻地和陳鬍子較勁,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對於接下來出現的不可知的境況,舒要根心裡虛得慌。這個把月來發生的事,已經讓他心力交瘁了。蓋上白布單時,他聽到了一聲輕微的嘆息聲從布單下面隱隱發出。聲音似有似無的,他不敢肯定,也不敢再看,不再停留,離開屍體,朝人多的地方走去,只感覺後頸窩裡像被吹進了一絲涼氣,寒冷至極。
「會長,裡面請吧。」老頭把舒要根請進廂屋裡坐下。一個女孩兒端了一盆熱水放在桌上,請他擦臉。舒要根擰乾了毛巾,意思地擦了一下,那女孩就把臉盆端出去了,然後,再拿了些點心、茶水擺在他面前,退了出去。
老頭坐下來,把陳鬍子的死因慢慢地講給舒要根聽。
3
「陳鬍子粉館」開在雜家院子靠大街的拐角上,是龍溪鎮最有名的一家粉館。粉館共有三層樓,一層樓做廚房,二、三層樓都是餐廳。他的生意好,不獨是面朝舞水河,坐在樓上可以一覽舞水四時風光,更是因為他的手藝獨特,粉的味道好,惹來眾多嘴饞的人。他請了五個幫手,一天到黑都還忙不過來。
這陳鬍子有個脾氣,他製作「臊子」(作料)時,誰也不准看,哪怕是自己的老婆也不允許。每天晚上打烊之後,等那些幫工們回家了,他就把所有的房門都關好,一個人在廚房裡配料。這也難怪,開粉館關鍵在臊子,臊子不好吃,粉做得再好,也不會有人光顧的。陳鬍子保護自己的臊子配方,就像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
粉館因為生意太過興隆,人手總是不夠,陳鬍子不得不又收了一個小夥計。那個夥計才十六七歲,是鄉下的,沒地方住。陳鬍子看他人長得也還憨厚,加上年紀還小,想必不會有那些花花腸子,就同意了讓他住到店子裡,反正這店子也要有個人看守。陳鬍子沒想到的是,小夥計人雖小,卻是很伶俐,面相雖憨,卻是鬼得很。他住在二樓一間堆放雜物的屋子。沒過多久,他就悄悄地把樓板鑿了一個小洞,等到陳鬍子關緊了所有的門窗開始配臊子時,他就趴在樓板上,從那一眼小小的孔洞中,看陳鬍子配料。
昨天逢十九,龍溪鎮趕場,粉館一直忙到天黑透了才打烊。等大夥兒在粉館裡吃了夜飯,收拾洗刷之後,快到半夜了。陳鬍子自己也累得夠戧,想回家休息了,但想到第二天的臊子不夠了,還是強打起精神,關了門窗,去配料。
小夥計脫了鞋子,輕手輕腳地下了床,趴在樓板上,把那一雙小眼睛貼到孔洞上,看陳鬍子配料。
陳鬍子的腦頂心禿得厲害,幾乎是寸草不生,在燭光的照射下,光溜溜的。只見他打開櫥櫃,把五香、胡椒、花椒粉還有老醋等一二十樣東西一一擺放在桌子上,然後,他像是發現有人在他的背後一樣,突然反過身來看,等確信並沒有人時,才把案板下面的一塊五花豬肉扯出來,把剔骨刀高高地舉起,正要一刀砍下去時,那手竟然就停了下來,在他的頭頂上一動不動了。一口菸的時辰後,陳鬍子猛然一個轉身,揮舞著剔骨刀像劃一個個橫「8」字一樣,來來回回地舞動著,嘴裡還哼哼唧唧地叫道:「我砍死你,我砍死你,我砍砍砍!」
小夥計看到這一幕,感到莫名其妙,以為那是陳鬍子家祖傳下來的什麼法事。不一會兒,他就知道自己錯了。只見陳鬍子舞了一陣之後,眼睛就像看到了什麼令他十分駭異的東西一樣,瞪得溜圓,連眼珠子都快要鼓出來了,剛才的那種勇猛孔武的神態也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害怕和恐怖。他低了聲,擺著手,說:「莫過來,你莫過來……」一邊說一邊連連後退,等退到了牆壁邊,再也沒有退路了,他跪下來,可憐巴巴地哭道:「那不能怪我啊,那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矩啊……」這時,他拿著剔骨刀的手像是被一雙無形的手死死地捏住了一樣,反轉過來,對著自己敞開的肚子狠狠地插了進去,血就噗地一下像水一樣射了出來。陳鬍子啊地叫了一聲,短促而尖銳。他沒有停止手上的動作,而是兩隻手都捏住了刀把,共同用力,把那剔骨刀上下左右地攪動起來,肚子裡那被鮮血染紅了的腸子就骨碌骨碌地流了出來……
小夥計嚇傻了,呆在樓板上,想動,動不了;想喊,喊不出聲。好一陣,才像是從睡夢中醒過來一樣,拉開門,往樓下衝去。樓梯上很暗,加上驚慌,他一腳踏空,骨碌骨碌地滾下去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楊標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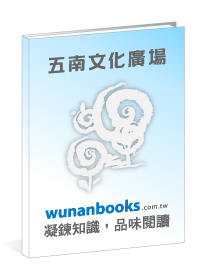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
$ 110 ~ 238 | 趕屍傳奇
作者:楊標 出版社:小異出版 出版日期:2008-07-2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68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楊標
楊標,字廷瞻,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民籍,明朝政治人物。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趕屍傳奇
揭開詭異湘西趕屍禁忌的驚人內幕!
她的臉龐掩隱在濃密的頭髮中,露出巴掌大的一片白色來,
仿如剝了皮的雞蛋,細膩,潔白。
在這麼黑的夜晚,她的臉竟然是那麼白,像是被水泡了許久。
頭髮上,還有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淌,滴答、滴答,
甚至還聞到了一股特別的腥味。
那隻沒被頭髮遮掩的眼睛,竟然沒有瞳仁,
也和她的臉一樣,全是慘白的。
靈鴨寨,神壇上躺著一個全身著紅的女子,她是人們獻給「瑪神」的禮物。
龍溪鎮,砰的一聲炮響猶如喪鐘,將人們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二十年前,靈鴉寨所有二十歲以上的男人,都參加了一個儀式。現在,凡是參加了那個儀式的男人,一個接著一個死光……
英俊的趕屍匠終日與屍體為伍,卻又註定一生與女人無緣;妖豔的草蠱女幽居山野,竟並有兩個半人半鬼的丈夫。
美麗的湘西女子,堅不可摧的古老風俗,神祕的趕屍行當,駭人的巫蠱之術,這一切交織碰撞出的,將是一段炫目又驚心的動人傳奇!
作者簡介:
楊標
七月初七生,湘西人,侗族漢子,憑藉《趕屍傳奇》聞名網路文學界,自出道以來,所向盡數披靡,贏得海內外fans無數,被奉為湘土恐怖小說第一人。從小就生活在湘西的大山深處,浸淫在湘西文化的氛圍裡,耳濡目染,感同身受,湘西的人和事,處處都充滿了迥異於其他地方的特點,詭異、魔幻、神祕……尤其關於趕屍的傳說,更是花樣百出,精彩無比。
曾經是一個純粹的人,做著純文學,現在是一個凡俗的人,寫著俗文字。喜歡打字,自稱打手。曾獲《人民日報》、《民族文學》、《湖南文學》等獎項,其小說和散文還散見於《中國時報》、《自立晚報》、《國語日報》、《星島日報》等香港、台灣報刊。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昨日重現》。系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TOP
章節試閱
台灣版序
承蒙小異出版的錯愛,拙著《趕屍傳奇》的繁體字版本即將在台灣等地出版發行,這對於我來說,自然是倍感高興,十分榮幸的。
《趕屍傳奇》正式動筆是二○○七年六月,在天涯社區的「蓮蓬鬼話」以及新浪、搜狐、騰訊等原創頻道進行連載,意想不到的是,點擊率一路?升。連載不到一個月,就有十幾家出版公司與我聯繫,意欲出版該書。書上市後,反響非常熱烈,銷售業績不俗。
中國大陸的恐怖小說創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起步較晚。但一旦起步,發展卻是非常迅速。優秀的恐怖小說作家脫穎而出,恐怖小說作品更是如過江之鯽,一時間,令...
承蒙小異出版的錯愛,拙著《趕屍傳奇》的繁體字版本即將在台灣等地出版發行,這對於我來說,自然是倍感高興,十分榮幸的。
《趕屍傳奇》正式動筆是二○○七年六月,在天涯社區的「蓮蓬鬼話」以及新浪、搜狐、騰訊等原創頻道進行連載,意想不到的是,點擊率一路?升。連載不到一個月,就有十幾家出版公司與我聯繫,意欲出版該書。書上市後,反響非常熱烈,銷售業績不俗。
中國大陸的恐怖小說創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起步較晚。但一旦起步,發展卻是非常迅速。優秀的恐怖小說作家脫穎而出,恐怖小說作品更是如過江之鯽,一時間,令...
»看全部
TOP
目錄
引子
第一章 龍溪鎮又死人了
第二章 孤獨的趕屍匠
第三章 瑪神的使者
第四章 被貓帶走的屍體
第五章 開棺
第六章 來歷不明的算命人
第七章 「母子」情深
第八章 咒蠱墊
第九章 往事並不如煙
第十章 飯養人,歌養心
第十一章 背叛
第十二章 瑪神的懲罰
第十三章 喜神店
第十四章 月光下的活屍
第十五章 殭屍大戰
第一章 龍溪鎮又死人了
第二章 孤獨的趕屍匠
第三章 瑪神的使者
第四章 被貓帶走的屍體
第五章 開棺
第六章 來歷不明的算命人
第七章 「母子」情深
第八章 咒蠱墊
第九章 往事並不如煙
第十章 飯養人,歌養心
第十一章 背叛
第十二章 瑪神的懲罰
第十三章 喜神店
第十四章 月光下的活屍
第十五章 殭屍大戰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楊標
- 出版社: 小異 出版日期:2008-08-01 ISBN/ISSN:97898682174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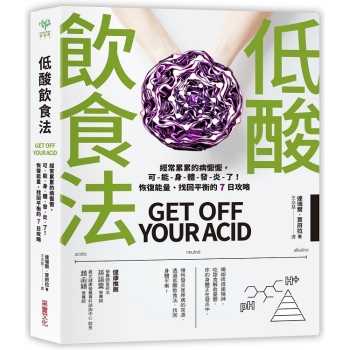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41/2014150562736/2014150562736m.jpg?Q=e3fc9)




![114年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資格考通關寶典[教師資格考] 114年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資格考通關寶典[教師資格考]](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18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