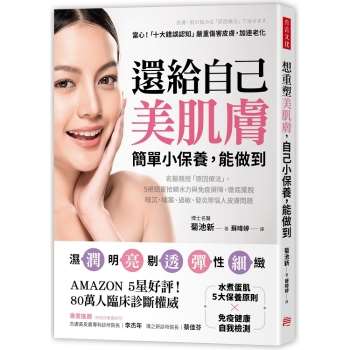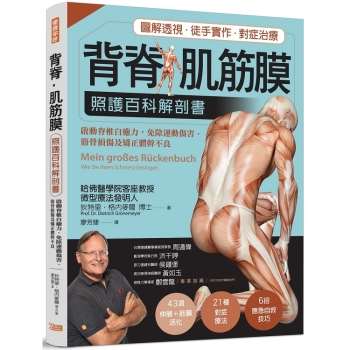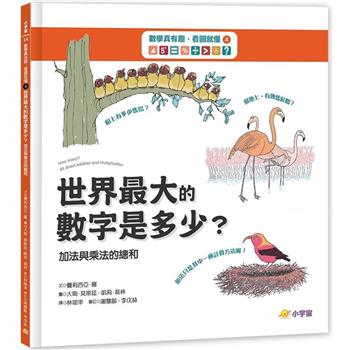我是迷失於通幽曲徑的人,厭倦了
石頭於陰影中身裹銅黃,厭倦了
杯裡的茴香酒,還有檸檬片
一次是酸,一次是陰差陽錯的虛名
複述、翻卷,拿著地圖
一顆橄欖樹在帕提農神廟的呢喃
石頭於陰影中身裹銅黃,厭倦了
杯裡的茴香酒,還有檸檬片
一次是酸,一次是陰差陽錯的虛名
複述、翻卷,拿著地圖
一顆橄欖樹在帕提農神廟的呢喃
─〈不如說雅典的秩序〉(節選)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各自述說著,而無人知曉。
楊沐子以詩詮釋了各個城市的地域文化與生活,一種奔放,隨心所欲的聲音;
將詩與城市的角落結合,將感性與知性揉合──開啟、打破城市的樣貌與聲音。
頑劣,荒謬,趣味。
肢解文化和文化之間的差異秩序,切入現實各個角落,進行抒情和假戲劇性的實驗性創作。
女詩人楊沐子將四十首挑戰自我,不受任何約束的詩,
塑造一種冷與熱相互衝突的快感,延滯既定的意義的社會形態,讓詩句們自行構成對立批判……
本書特色
★四十首挑戰自我,將城市揉合成一首首不受任何約束的詩
★抒情和假戲劇性的實驗性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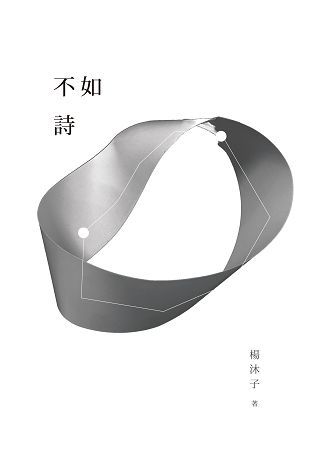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