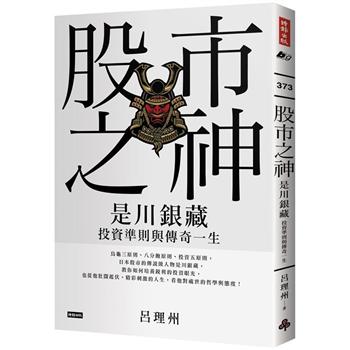章一 小雪
我的生辰是在深秋,今年格外的冷,容城已經落過雪了。我原本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翹了功課,卻沒躲過家裡頭那個望子成龍的老爹,還是被趕去了郊外的壁雍。他也不想想,龍生龍鳳生鳳,儘管他們都說我長了張聰明伶俐的臉,可我畢竟是他的嫡親兒子,就算馮平章活過來親自教我,我也成不了什麼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家,最多便是得了蒙在鼓裡的路人幾個羨豔欽佩的目光——喏,那將來可是太學院的太學生,馮幻馮平章的門生。
他們豈會知道,是我爹暗裡使了大錢把我塞進去的,若是教馮平章知曉,不知會不會從棺材裡氣得跳起來。
我月前就看中了家裡布莊那塊上好的織錦,早早量了身盼星星盼月亮地挨到今日好不容易穿上身,一出門就被蕭瑟的秋風吹去了三魂七魄,這越發讓我想念起了家裡的地暖銅爐、駝絨毛毯和羊奶茶,我哆哆嗦嗦地轉頭,瞧見阿縝身上穿著單薄的灰色長袍束著腰帶若無其事地走在我的外邊替我擋掉些寒風。他只比我大一個月,卻比我高了兩個頭,那張英俊卻不自知的臉被風吹得紅彤彤的,嘴唇乾燥得起皮,終於察覺到我在看他,扭過頭眨著眼毫無顧忌地同我對視著。
「少爺,你冷嗎?」
他雖看起來有些遲鈍,卻總是很能體察出我細微的情緒,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傢伙大部分時候是在裝傻充愣。說得文雅點兒,那叫大智若愚。他們高大的外表具有欺騙性,常常令人覺得他們愚笨好欺,除此之外大概也同他們伽戎人這數百年一直都被欺辱奴役有關。不過,當今大爃皇帝就是伽戎人,所以他們早就都被除了奴籍,分了土地,地位卓越,早就不可與昔日為奴時同日而語了,只是我想不通阿縝為什麼不願離開我家,偏還要跟著我,以至於我們全家每每見他都有些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告到官府吃不了兜著走。
可阿縝像是什麼也不懂,我叫他走,他的臉色慘白如蠟紙,以為是我不要他了。他會睜著那雙眼珠子比我們要淺一些的大眼睛可憐兮兮地凝視著我,叫我於心不忍,仿佛真是我要將他掃地出門一般。
我常常同他說,本少爺將他留下來冒了很大的風險,叫他得時刻記得我的好。他堅定地點頭,發誓這一生都要跟著我、待我好,我欣然,又覺得阿縝到底還是不夠聰明伶俐,三言兩語就被哄騙著許給了我終身。我不由擔心了起來,覺得他這傻乎乎的樣子,將來若是出府了自負營生被人騙了可怎麼辦。
他好不容易留下自然是對我比以前越發言聽計從,體貼呵護,更不可能仗著此刻翻身作主的身份有半點跋扈要將過去的種種全都報復回來。只是我家不能再將他當奴僕看待,讓我同他拜了義兄弟,他依舊跟著我。
他倒也不客氣,大大方方地同我結拜了,從此便跟著我一同去學堂,雖然他的腦袋對讀書習字一竅不通,拳腳上卻很有一套,打遍十里八鄉未曾遇到敵手,後來索性就跟著我家護院的武師師傅學習槍棍了。
只是這一夕之間他身分的驟然改變令家中不少年輕丫鬟對他殷勤許多,讓我有些莫名不悅,我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可他卻一如既往地容忍著我。
「冷。」
我話音剛落下,他便解開了自己的袍子,要往我身上罩,我大驚失色,呵斥道:「你裡頭就剩下兩件裡衣,是想凍死嗎?!」
他巴愣著看著我,臉上的表情困惑不解,我半口氣沒吐出來,連忙上前幫他把衣襟拉好,「我不想去學堂了。」
他想了想,「嗯」了一聲,「不想去就不去。」
聽了他這話兒,我心裡頓時舒暢了許多,果然只有阿縝說話做事最襯我的心意。
時辰尚早,那些勾欄妓館還未開張,就連酒樓飯館也是大門緊閉。我帶著阿縝在鬧市街上蹓躂了一圈,這會兒真是冷清極了,我剛剛提起的興奮勁又被這每年深秋從東泠濟川入侵的寒風打得七零八落。
「那有座茶樓開著。」阿縝冷不丁地開口說道。
我皺了皺眉,把目光移了過去,心裡有些悶悶不樂,本少爺大壽就只能坐在那破破爛爛的茶館裡喝茶聽那不入流的小曲兒嗎?可想歸想,我還是架不住那帶著無孔不入的風往我衣領袖口裡鑽,連跺了兩下腳,帶著阿縝朝茶館走去。
就在我仰頭挺胸走近茶館的時候,阿縝突然輕輕扯了我一把,迅速擋在了我的身前,停下了腳步,我在他身後踮起腳目光越過他寬厚的肩頭落在一個可疑的男人身上。他正靠著門柱半躺在那欄杆上,身上黛色的袍子有些舊,被洗得發白。
他同這暮秋灰白的古城融為一體,像是被寒風裹挾的灰芥落在這西津千百年來無論如何都無法耕種始終荒頹的土地上,生長在那兒,也死在那兒。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楚危的圖書 |
 |
$ 210 ~ 380 | 西有鹿鳴
作者:楚危 出版社:留守番工作室 出版日期:2017-10-28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西有鹿鳴
養尊處優的布莊少爺鹿鳴,一夕之間忽然失去了一切,厄運接連而來。
那段再平凡不過的生活、那些再平凡不過的家人陪伴、那座再平凡不過的老城,在被流放到冰天雪地裡的鹿鳴眼中,已如海市蜃樓般虛幻。
能讓他緊握最後一絲生存希望的,只有從小一同長大的奴僕霍縝,
然而顛沛流離之中,鹿鳴也無從得知霍縝究竟身在何方。
「究竟什麼時候還能再見到我的阿縝?」
那個名叫無情的命運卻也慈悲,在最潦倒的時候看見最真的情感,患難中,他們開出最美的花朵。
留守番年度徵稿驚艷之作──《西有鹿鳴》
作者簡介:
楚危,手速成謎,摸魚時500,截稿時6000;葉公好貓,雲養吸貓,生性怕狗,尤懼泰迪;現耽古耽都愛,愛兩情相悅,也喜求而不得。信箱:wennky@outlook.com
TOP
章節試閱
章一 小雪
我的生辰是在深秋,今年格外的冷,容城已經落過雪了。我原本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翹了功課,卻沒躲過家裡頭那個望子成龍的老爹,還是被趕去了郊外的壁雍。他也不想想,龍生龍鳳生鳳,儘管他們都說我長了張聰明伶俐的臉,可我畢竟是他的嫡親兒子,就算馮平章活過來親自教我,我也成不了什麼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家,最多便是得了蒙在鼓裡的路人幾個羨豔欽佩的目光——喏,那將來可是太學院的太學生,馮幻馮平章的門生。
他們豈會知道,是我爹暗裡使了大錢把我塞進去的,若是教馮平章知曉,不知會不會從棺材裡氣得跳起來。
我月前就...
我的生辰是在深秋,今年格外的冷,容城已經落過雪了。我原本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翹了功課,卻沒躲過家裡頭那個望子成龍的老爹,還是被趕去了郊外的壁雍。他也不想想,龍生龍鳳生鳳,儘管他們都說我長了張聰明伶俐的臉,可我畢竟是他的嫡親兒子,就算馮平章活過來親自教我,我也成不了什麼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家,最多便是得了蒙在鼓裡的路人幾個羨豔欽佩的目光——喏,那將來可是太學院的太學生,馮幻馮平章的門生。
他們豈會知道,是我爹暗裡使了大錢把我塞進去的,若是教馮平章知曉,不知會不會從棺材裡氣得跳起來。
我月前就...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楚危
- 出版社: 留守番工作室 出版日期:2017-10-28 ISBN/ISSN:97898693941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6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高:20mm
- 類別: 中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