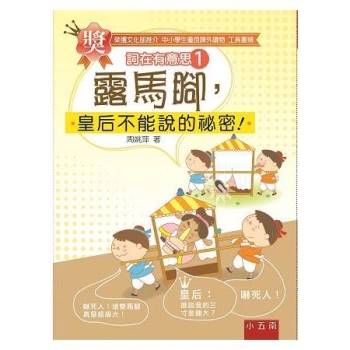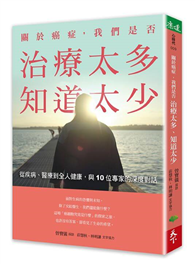序
我讀櫺曦◎博弈
櫺曦在《自體感官》裡有一詩是〈我們談詩,不談感情〉,耐人尋思,詩怎麼能不談感情呢?這首詩,開始是這樣的:「詩集裡躲隻蠍子」,詩結尾則說:
一度以為自己是隻蠍子
然而,當被翻閱
開始,我螫向一段不算短的
懷念
難道是感情螫人?或更怕的是自己螫了自己,近詩情怯,至痛如冷不防的蠍螫。對於詩人而言,隔一段時間再看自己所寫的詩時,曾經投入的情感又回來敲著心門,以為死矣卻未僵直的悸動,這種回憶所引起的刺痛,是詩者那曾幻化為詩句描述的分身,靈魂,又出現眼前,似曾相識的回螫。詩裡一句「透明分身或靈魂搬運」,讓我想起有位詩人曾言,當讀到一首詩而有頭蓋骨被掀開的觸動,我就知道那是真詩。這螫的概念在這本詩集內亦出現於〈影〉,〈囈病持續〉,與〈出版〉數詩中。在〈天亮〉一詩中,也有「詩的談論不再激情」一語,似乎不談感情,談則不再激情;
詩的談論不再激情───
你是我,你在白格內看我
儘管爬行牆與牆間,你的臉
有我的臉
而「你是我,你在白格內看我」,自體與字體在這裡似有了暗示,你的臉與我的臉有了重疊。
櫺曦的這本詩集並不易讀,有極深的個人情感描述方式在裡頭,也跳出傳統的詩審美,幾乎是寫給創作者看的,交流的,其中思想飄忽,詞語豐富,少因循舊語,語句多有暗示,和比喻性的詩語言是有些區隔的;但也正是這些吸引人。詩人的詩有「詩句換日線」(〈天亮〉),「末頁皺了一條∕換日線」(〈出版〉),似乎詩人常夜行,詩句如地球是旋轉的,或許在黑夜換日的時候來讀,更有體會;但行到無腳印之處,我也擔心後頭是否有尋荒的拓客。知識上來說,若不向異處探索,有什麼可以進步的呢?故樂於──亦覺榮幸──為短文略述閱讀所得。
1. 詩句可另成詩題
這樣的情形,意味著詩句是有啟發性的,觸動人想像的;而想像是脫韁野馬,甚至不在原詩的草原上奔跑。比如〈島旅〉的「闔眼的路燈是兀立撐傘的耆老」,再比如〈天亮〉裡的「蠹魚與言鳥」,〈讀我的感官〉裡的「過於抵抗的感官」,〈熱血與懶懶〉裡的「平行不比垂直討喜」,或〈詩.兩棲〉裡的「傳統外皮中裸超現實的骨」都能讓人另有想像。櫺曦與文字維持的關係是矛盾的,似愛但總是有哀愁的;如「如何對文字∕不設防」,「就讓文字的銳利割破我喉嚨」,「文字反射在黑色屏風上」,「文字裡的黑潮」,「文字沼澤適逢秋味」,「裸裎的文字」或「是否那文字也能纏綿?」
一直到讀到〈曖昧期〉裡的
我們很有默契的
翻出愛情
便如同一棵樹上開滿了花等待結果
我竟生出「才放下心」的感受。
在讀完〈讀信〉,〈翻信〉,〈郵戳〉諸詩後,不由即筆致詩人如下:
《無聲的字幕》
斑駁的地址
郵差許久未曾經過
破損的窗
漏出遺世的眼神
詩人棲居在格子裡
無聲的語言在
無色的圖畫下
一個個詩人的輪廓
時代彈爆的強光
落印在負片上
我經過一格小鎮
不見藍衫子
我走到一格山野
蘆葦說著去年
這入骨的情感,不在皮肉上;櫺曦詩者辛苦了。
2. 性的意識
性可說是體變化的開端,也是潛伏在成年人意識裡最主要的自體本能念頭,這本詩集裡巧妙地把性意識融入比喻與暗示,並賦予自體的新意義,構成了一部份的自「體」感官,因此文字「自體」與人的身體器官的意義聯繫也因此豐富了起來,有一個平行意識的貫穿感官。這與哲學上的自體與感官的定義是不同的。下面我摘句一些具有性意識的例子,排列以方式如下:
詩題:句∕句∕……
無聲的人們:獨自手淫語言∕獨自飯菜
島內哭泣:有千萬隻觸手∕分別猥褻海岸∕路的盡頭是時間的腳趾∕意識在裡邊泅泳
啖腸論:送入嘴裡∕洞房∕枕在後腦的牙
骨人:將史料點向每一個空虛穴位
援女:我曾從那隙縫裡找尋∕解離的青春字詞∕除了跨(跨)下所藏匿的信仰
一夜晴:不如多買幾個蘋果∕等待夜黑∕許多體液經紫外線照射後竟無情
郵戳:齒狀花排擠你的青春∕臉,處女不再
不只沉默的艦隊:魚貫著 尾隨∕輿論∕這棟宅體的裡外∕皆是補強∕在這棟過於龐大的艦隊裡∕各自尋找可親吻的女體∕交媾,為這抹自由尋找∕繁衍的道路
油畫.Ⅱ:蛋黃 讓倘佯給釣了上
油畫.Ⅲ:你是幻想的口吻,在∕我的季節裡∕捉 迷藏
油畫.Ⅳ:意識的死因∕不單純於∕空白的繪布上
油畫.Ⅴ:夜的腋下騷癢
入睡:許多隻羔羊∕都躲著∕都躲在你的闔眼
層玻璃:幾種果汁裸泳在不外遇的泉區∕細微的掙扎在毛孔裡立現∕切線上滿住你的懷念
葬花:花瓣掉落的方式似高樓大廈解體∕哭泣聲不過爾爾抽∕噎也只是一種反射
尋夢的男子:就寫些麥穗的隱事
相反:便讓我銳利得∕切開你豐腴的外表∕在情緒上種一棵樹∕許多背離者都脫逃到鏡外
咖啡潛讀:失速墜毀一片∕未經世事的土地
囈病持續:囈病已不是口水舔舐∕解決在於把洞填補
逐波:我們輪流開往潮汐∕他睡在我的眉尖
靈魂錯落:安靜得∕擁入名為虹的夾層中
天亮:天亮以後∕我們需將蠹魚與言鳥放行
性的意識出現在詩裡可算是當代詩的一個特有的現象。能夠言之有義,自肉體的到心靈的,自小我的到大我的,自社會的到文化的,以性為體,以體為鑰,開啟了解當代詩情的另一篇,這是前輩詩人少寫的,也是這本詩集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地方。
3. 自體感官的延伸
在輯七〈短印記〉的短詩選中,我看到了詠物詩的轉變,或以物為自體,或以感官入物;那自體的陳述,期待感官的邂逅。如〈購物袋〉一詩,說的何嘗不是詩?鬧字就像個手推車,裡面裝著「市」;鬧字有何嘗不是腦,詩人推著它;鬥字又比如有雙耳,產生字形的聯想暗示;則,再回顧〈側耳〉那詩,就更有意思了。(《說文解字》:鬧,不靜也。從市鬥。)
〈購物袋〉
雙耳
倒折成舊的手推車
置放,鬧鬧鬧的
感
官
氛圍
重覆
使用
耳是自體,也是感官,在這本詩集裡多次出現,已構成一個母題意識,令詩人所〈致無聲的人們〉也要〈側耳〉來「傾聽遠方的要來未來的停滯」,這是詩者的心聲吧。
於是,折下兩片耳朵
裝上
倏地消失在
巨
大
夜
空
這本詩集,語言形式是不落俗套的,讓我借用〈天亮〉詩中的句式:不落俗套的語言形式是□□,我喜歡;)
詩無法說盡,甚至說近,我的短文所及於其他讀者與作者是次體的,個人的。讀者放空自己,接著進入詩集,跟隨著櫺曦的詩,進行一趟自體感官之旅,那麼,承認你所感受到的,那便是屬於你的自體感官。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