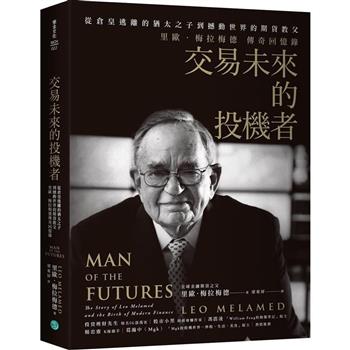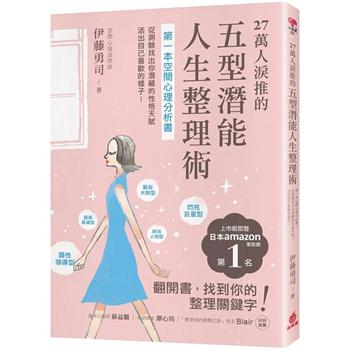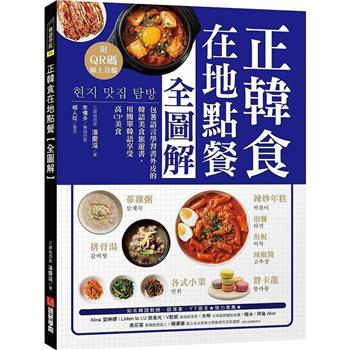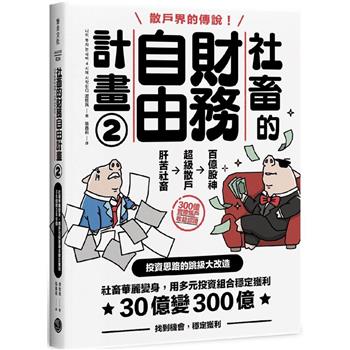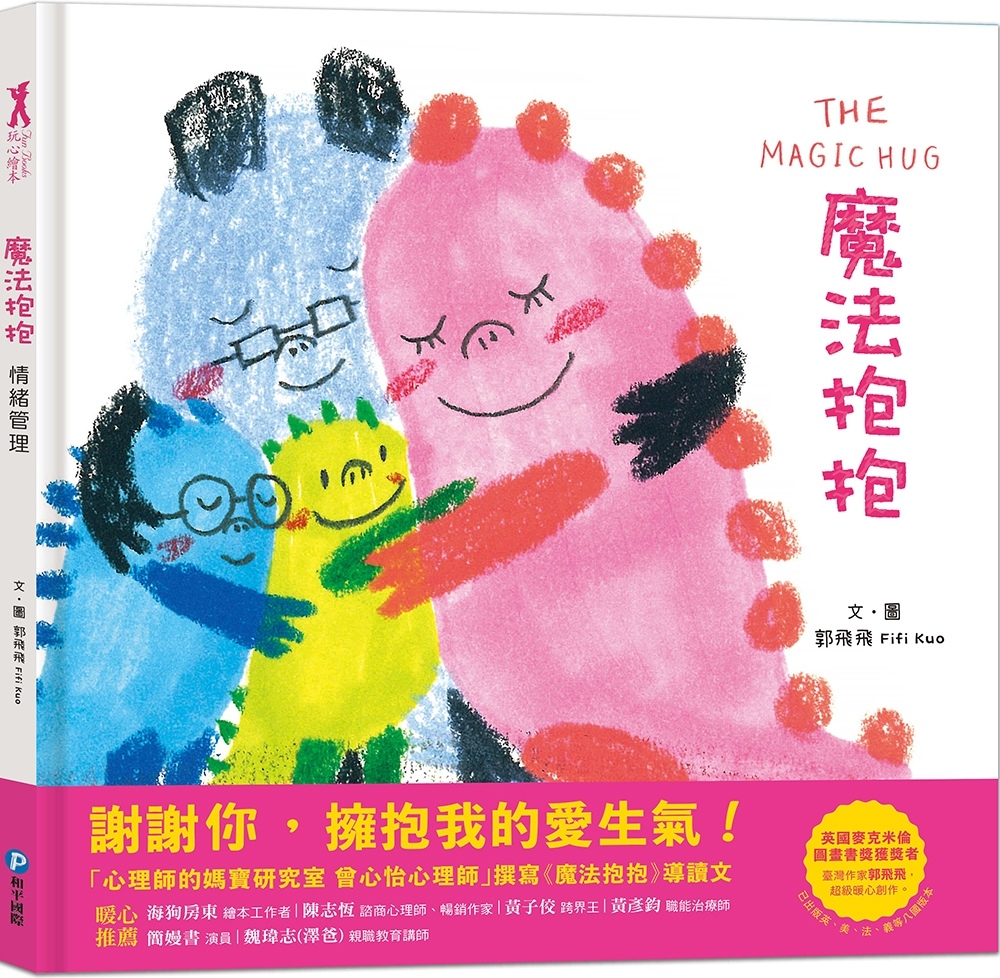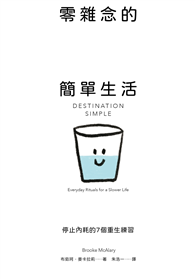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歐文.馬修斯的圖書 |
 |
$ 441 電子書 |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
作者:歐文.馬修斯,Owen Matthews / 譯者:Zhou Jian 出版社:今周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4-24 語言:中文 |
 |
$ 388 ~ 554 |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
作者:歐文.馬修斯(Owen Matthews) / 譯者:Zhou Jian 出版社:今周刊 出版日期:2025-04-2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76頁 / 14.8 x 21 x 2.6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馬修斯
|
 卡爾·馮·馬齊烏斯,是德國植物學家和探險家。
卡爾·馮·馬齊烏斯,是德國植物學家和探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