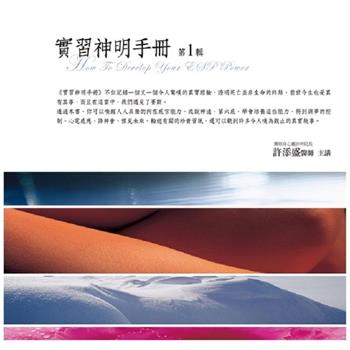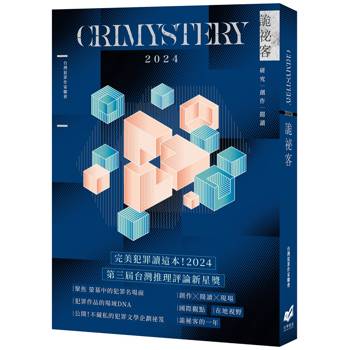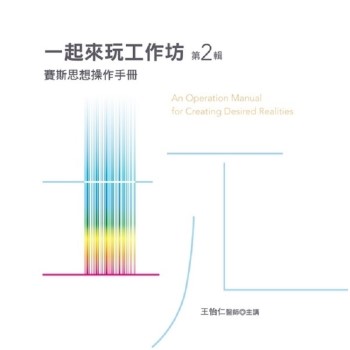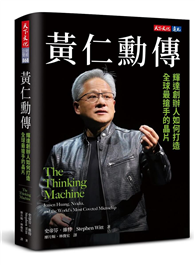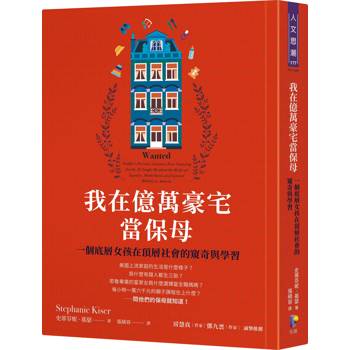序一
陪著你走
我的丈夫卓斌,他寫成了這本自傳式的《活在激流中:如煙足跡》,平時他專注於自己診所的業務,很少花時間在娛樂或看其他書籍,他卻自己學電腦,利用它來寫作,我從旁看他自學,難怪他常常笑我學甚麼也要找老師去學校。
我和他認識已四十多年,雖然也是同一醫學院畢業,先後只差兩年,不過在學校時是素未謀面。因緣際會,逃離暴政,回來香港。為了追回失去的時間,巧合在同一間和同一班的英語夜校補習,那時我已是一個三歲孩子的母親,他是一個受異性垂青的男士。
當年英國統治香港,非英聯邦畢業的專業人士,受盡社會歧視,受盡當地同業排擠,我曾經想當護士不能,當幼兒老師不能,謀生困難。後蒙卓斌引薦在柴灣的教會診所工作,因而也逐漸的互相瞭解。
在他的工作蒸蒸日上的時候,他作了換上別人不會作的決定,要去外國尋找他的希望,不滿足沒有尊嚴賺得來的金錢,他,終於可說是做到了,也帶動了他的家庭成員移居外國的機會。還有最大的受惠者,自然是我了。1972年,他做了另一個出人意表的決定,寫了一封信給我的父兄,提出希望和我結婚,互相扶持,互相照應,自此也改變了我的下半生,在我驚喜之餘,深佩他義無反顧向前的毅力。
如果以賺得的金錢多少來論成敗,他算不上成功,不過他回顧和我數十年來走過的日子,以及見著他的親人,在西半球過著較安穩的生活,他對自己曾經所作的付出,他感到比得到財富更大的滿足。
李愛勤‧2005年10月
序二
在洛杉磯至廣州的航班上
在洛杉磯至廣州的航班上,一口氣讀了歐陽先生的《活在激流中:如煙足跡》。一路回憶逝去的往事,眼角竟不自覺地滲出了淚水。書中描述的許多生活場景,人物故事,都是我輩所曾經歷,感同身受,百感交集,徹夜未眠,「沉重」二字不但躍然紙上,亦始終擠壓著讀者的神經。
那些充滿激盪的往事,雖然在人們的記憶中漸已遠去,但在歐陽先生筆下,卻依舊如此的鮮活逼真,猶在眼前活現。
傷過也罷,傲然也罷,重拾這段辛酸,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如同將經已癒合的傷口再次撕開般的讓人掙紮與難受,歐陽先生以其個人的經歷,為後人再次翻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
對中華民族而言,過去的百年,是一段災難深重的百年;對中國人而言,過去的一個甲子,同樣烙著沉重的傷痕印記。
或許有人認為,在不幸的年代,歷盡浩劫者比比皆是,這並不稀奇,不錯,比此益苦之人數不勝數。然而,從娓娓道來的每一樁小事中,都仿佛看到了一股凜然不屈的正氣與傳統中國讀書人的錚錚傲骨,百折不撓、自強不息,這不正是今天不少人所欠缺的嗎?
或許我們無法改變世界,甚至在無奈中苟且偷生,向現實低首,在磨難中消沉,成了自我交代最好的下臺階。從香港─廣州─昆明,再由湛江─香港─英國─美國─回到香港,我們可從字裡行間中看到一位歷經半個世紀,縱橫太平洋東西兩岸,為追尋夢想而不辭勞苦、孜孜不倦的行者身影,其中的艱辛雖不為人知,而其執著前行的身軀,無意間不知感染了多少後來人。
如果說救世行醫是個人的追夢,而對親情的承擔,則令讀者觸到了歐陽先生冷峻外表下的鐵漢柔情。在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今天,這份濃濃的親情,又顯得是那麼珍貴,沁人心脾、暖懷至深。
《活在激流中:如煙足跡》快讀完了,飛機徐徐降落白雲機場。凝望著窗外彌漫的濃霾,輕輕把書合上,閉目冥想……腦中在回放著這位慈祥的長者在慢慢訴說往事,沒有刻意的宕蕩刺激,也沒有出人意表的驚天一霎,我卻在這湲湲長流中似乎知曉了一點歐陽先生的心事,亦從中好像悟到些什麼?
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心中喃喃自語:翻過了這頁,但願從今國泰民安,步出機場,朝著海關走去……
翛然‧2014年3月
作者序
我生於1931年,正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那一年,響起了炮聲後的第十天。
1937年我六歲的時候,日本進一步的侵略,在北京製造了「七七盧溝橋」事件,引起了全面的抗日戰爭,這段時間,我的家庭生活在香港,仍然過著太平日子,直至1941年日本進攻香港,生活才受戰爭的影響,也就是說,我十歲前是過得安逸。
1945年戰爭是停止了,環境好不了多少,對外的戰爭雖然停止,硝煙未散,便是國共內戰,打了四年的內戰結束了,卻是帶來前所未有的災劫。
數十年來,大多數的中國人,海內或海外的,或多或少受到牽動,而我卻是很幸運的其中一個能夠較早離開風暴中心。在《活在激流中:如煙足跡》中,雖也反影了一些上一世紀中國的坷坎,不過我在這方面的經歷,相比於那些已傳世的,中國自1949年以後那些泣鬼神的往事,只是毫不顯眼的浮光掠影,只給自己留下記憶而已。
歐陽卓斌‧2005年10月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