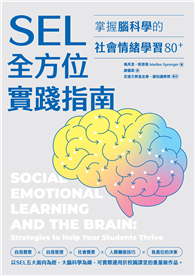昏君當國、奸臣當道、忠臣難當,
國家多難、禍國殃民、浮雲蔽日,
昏君、奸臣、忠臣構成一個解不開的結。
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芸芸眾生,攘攘諸官,模樣都差不多,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
奸臣們會說: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會說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殺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面相專家則說可根據一個人的相貌舉止來判斷,一般奸臣大多有個「狼顧」之相。這種說法影響最大,所以科舉取士後授官之前要經目測一關。這不是選美,而是剔醜,即留下「國」字、「田」字臉形者,排斥那些臉形像「申」、「甲」、「由」字者。
受此影響,戲曲、小說中的奸臣都被臉譜化,從而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奸臣一出場便可認出,總之誰醜誰就是奸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忠奸抗衡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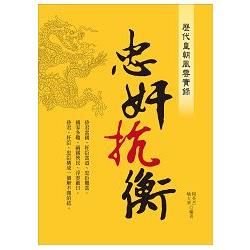 |
$ 196 ~ 252 |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忠奸抗衡【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楊英杰、喻大華 編著 出版社:大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9-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72頁/17*23cm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歷代皇朝風雲實錄:忠奸抗衡
內容簡介
序
前言
忠奸是父老相傳代代不忘的話題,更是小說、戲曲家描寫的對象,同時,其中的一些問題千百年來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政治家和史學家。
比如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芸芸眾生,攘攘諸官,模樣都差不多,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於是奸臣們會說: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會說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殺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面相專家則說可根據一個人的相貌舉止來判斷,一般奸臣大多有個「狼顧」之相。這種說法影響最大,所以科舉取士後授官之前要經目測一關。這不是選美,而是剔醜,即留下「國」字、「田」字臉形者,排斥那些臉形像「申」、「甲」、「由」字者。受此影響,戲曲、小說中的奸臣都被臉譜化,從而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奸臣一出場便可認出,總之,誰醜誰就是奸臣。
其實,若僅就相貌而言並加以打分的話,奸臣的分數肯定會高出忠臣。試想一個讓人一見就生厭的獐頭鼠目者怎會輕易討得君主的好感,從而獵取高位、得售其奸呢?據史書記載,很多奸臣都是儀表出眾,相貌堂堂,舉止非凡。如楊素、蔡京、耶律乙辛、阿合馬、嚴嵩等人,當然也有例外,王莽就是一個,但這類奸臣為數極少,並且能以其他長處來彌補這一缺欠。
奸臣們不僅相貌好,而且往往身懷「絕技」。普遍具備的就是表演才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口才極好,又恰到好處。捅你一刀之前能拉著你的手誠懇地為你出謀劃策,捅完之後還能抹幾把淚水。除此之外又各有所長:比如秦末的趙高深通法律;北宋的蔡京名列翰林,又是大名鼎鼎的畫家、書法家;南宋的秦檜曾中進士,頗有文采;明朝大奸嚴嵩詩文書法造詣也很高,這類例子不勝枚舉。筆者曾經設想,假若他們生在今天,或許其中很多人會成為影視明星、書畫家的。
古人云:大奸似忠,這也是奸臣的一個特點。他們以種種方式表達對國家、君主、同僚的忠誠和信義,並且往往也確有些忠信的實跡:或有功於社稷,或報德於同僚,從而得到從上到下的普遍好感,才得以占據高位,禍國害人。假若他們中途身死,未得施展其奸,其中有些人如王莽、楊素等將在歷史上留下無可挑剔的忠臣、功臣形象。
奸臣們還具備一個特點,一般頗具才幹。如楊素輔佐隋文帝統一天下,軍功赫赫,為一代名將,而且下筆成章,文詞華麗,可謂是文武全才。又如北宋神宗以後變法派與保守派互鬥,雙方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但不論哪派得勢,都要任用蔡京,就是因為他有才幹,他能辦成別人辦不成的事。總之,奸臣辦事幹練,能量過人,凡奸佞之徒,沒有一個是笨蛋。
由此可見,奸臣本來具備成為名臣的素質,但他們為何沒有成為名臣、忠臣,反倒成了奸臣呢?
其一,從主觀上來說,他們本是一些品德低下的小人。他們唯利是圖,為此不僅可以出賣靈魂,甚至可以殺妻烹子,拋宗棄祖;他們不講信念,反復無常,投機鑽營;他們嫉賢妒能,心理變態,百般排斥;他們陰險狡詐,虛偽成性,不以真面目示人;他們生性狠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由於有這些主觀因素,一旦客觀條件具備,便為所欲為,大售其奸。
其二,昏君當國是奸臣產生的客觀條件,並且是關鍵性的條件,對此有必要深加討論。
提起昏君,人們往往會想到劉阿斗、晉惠帝一類的白痴,這固然可以算作昏君的一種,但人數極少,並不典型。再一類就是玩物喪志,不謀其政者,如南唐後主李煜擅琴棋書畫,尤長於填詞,宋徽宗好書畫,明世宗崇道等。按說這類帝王天資不低,所好也不算低級,但中國帝王獨攬大權,國事繁重自不待言,即使全力以赴,猶恐不周,何暇及此?他們以此為專業,治國反倒成了業餘的,難免有奸臣投其所好,竊取大權。這類帝王人數不是太多,但也屢見不鮮,應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昏君。
最典型的昏君是兩個極端:一類是有治國之心而無治國之才,能力經驗均顯不足,這類君主容易為奸臣所控制,並在奸臣的引導下更加昏庸;二類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一意孤行。這類君主自以為是天下最聰明者,所以聽不得逆耳忠言。於是奸邪小人因之而進,先是投其所好,百依百順,騙取信任,獵取高位,然後挾天子之威風,打擊異己,禍國害民,為所欲為。這兩類典型的昏君在中國昏君中比重最大,他們或是被奸臣所控制,或是被蒙蔽,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為奸臣的產生負全責。因為無論奸臣勢力多麼強大,也超不過君主;無論君主多麼軟弱,只要他們起而除奸,天下自會有人起而響應。奸臣的垮台,相當多是由君主翻臉造成的,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品德低下的主觀因素是奸臣產生的動機,而昏君當國便為實現這種動機提供了全部條件,所以昏君奸臣是緊密聯繫著的概念。
那麼昏君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體制問題,即君主專制體制為昏君產生提供了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並不是說所有君主都是昏君,而是說只要有這種體制,就必然會有昏君。
其一,君位世襲制很容易造成昏君。一般說來,開國帝王都面臨著嚴峻的局面,這實際上是個優勝劣敗的競爭過程,競爭的勝利者即開國皇帝往往具有一些常人不備的特殊品格,為政治國是比較賢明的,並且能影響到一個王朝的頭幾代皇帝。再則如果皇帝有很多兒子(可能是幾十個)可供選擇,並且他又善於選擇的話,那麼下一代皇帝也會較為賢明。但畢竟開國皇帝每朝只有一位,而其他君主又多不善於選擇繼承人或無法選擇(兒子太少或只有一個),那麼下一代君主的賢愚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加之國家承平之時,皇子長在深宮,於民生飢苦、國家大政一概沒有體驗,一旦登極,茫然無措,很容易被奸臣迷惑,從而成為昏君。
其二,皇權至高無上,為昏君為所欲為提供了條件。帝王與大多數人一樣,在品格上往往是高尚與邪惡並存,並且年輕的帝王還有可塑性。但帝王的顧忌很少,他要為非作歹,非常容易,臣子大概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搬出「天」來嚇阻帝王,日食是一種警告,地震又是一種警告,祖廟失火表明祖先的憤怒等;再就是「極言直諫」,即直接向皇帝剖析利害,希望獲得採納。然而一旦皇帝既不在乎上天,又拒絕臣屬勸諫時,他就像一匹脫韁之馬,在人民的身軀上奔騰踏躍,無人可以制止,大小官員除了關門飲泣,在紙上哀求外,別無他法。
在這種體制下,昏君奸臣兩惡相濟,為所欲為。值國家承平之際,奸臣導君為惡,揮霍浪費;值國家多難之際,奸臣排斥忠良,製造內訌;值國家傾覆之際,奸臣或弒君篡位,或賣國投敵;至於魚肉人民,貪污肥私更是奸臣的普遍類型。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弄虛作假,欺上壓下,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栽贓陷害,軟硬兼施,種種手段不一而足。
但是,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只是昏君奸臣的世界,黑暗中也有光明,忠臣就是封建社會中的光明之一,是古代社會中精英的一種。
和奸臣不同,一則原則上說忠臣的產生不應有什麼前提,忠於國家、恪盡職守,勤政愛民,按儒家道德規範為人為官,就應算是忠臣。這類人數極多,但人們往往稱之為「名臣」、「循吏」、「良吏」,而不稱之為忠臣。二則忠臣似乎什麼人都可以當,哪怕是太監、宮女,甚至乞丐,只要在王朝覆滅時能一死以殉,就是忠臣。但這類「忠臣」並不為人重視,加之也不太合於今天的價值觀念,故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典型的忠臣其產生在事實上是需要有前提的,如昏君當國、奸臣當道、國家多難,並且往往是這三個前提同時存在。
典型的忠臣有如下品格:他們忠於國家、君主、信念,為此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他們為人剛直,不媚君主,直言敢諫;他們疾惡如仇,不畏權勢,不計後果,敢於鬥爭;他們為人誠實,不搞陰謀,不事欺騙,表裡如一;他們重義輕利,愛民如子,不事聚斂。而且他們往往又是能臣、功臣,並因此而身居高位,也因此而成為昏君奸臣的迫害對象。
忠臣的結局大多是悲慘的:他們有的血灑疆場;有的一生坎坷,備受迫害;更悲慘的是被誣以謀反,死在他所忠於的政權屠刀之下。正因如此,數千年來人們在為他們傾瀉了江河般熱淚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深思,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為何忠臣永遠是犧牲者呢?
忠臣的對手是奸臣,而奸臣的靠山是皇帝,沒有昏君,何來奸臣?而有了昏君,忠臣又怎能鬥過奸臣。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專制社會,忠臣的結局只能如此,這點很好理解。但問題是忠臣往往也掌握著很大的權力或擁有很大的勢力,如岳飛就掌握著一支令敵人喪膽的數十萬人的勁旅,他們為什麼不奮起反擊呢?這只能用今人難以理解的古代道德去解釋。一則他們都有一種以身許國的獻身精神,他們重視生命的價值而不重視生命的短長,失敗以至犧牲性命對他們來說並不可怕,甚至他們之中會有人視此為達到不朽的途徑。再則,從古代做人講究信義的原則出發,他們不去搞陰謀,他們相信正義的力量,相信即使君主不能為其洗去冤情,那麼還有千秋史評。最後,在當時的觀念中,他的權力、軍隊甚至生命都是屬於君主的,若以此對抗君主,便是亂臣賊子,這違反了他們畢生為之奮鬥的信念,是寧死也不會去做的,所以,忠臣的信念也決定了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做犧牲者。今天看來,他們因此而喪失了事業、生命、家庭,難免給人迂腐的印象,他們的忠誠之中也確實有愚忠的成分。但不能以此來否定其忠誠的價值,因為這不僅體現著誠實、獻身、捨生取義的高尚品格,而且也是忠臣征服人們心靈的主要原因。試想,岳飛起兵相抗,固然可以保住生命,甚至還可能實現收復中原的理想,但人們會怎樣看待他呢?人們會不會因此而對秦檜產生另一種印象?因為秦檜說他要謀反並未說錯。
也許有人還會問:忠臣不能搞些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嗎?遇事圓滑些,隨和些?回答是肯定的:絕對不能。歷史上確實有一類政治家,他們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由此而保住了自己並使國家免受了更大損失。這類人只可稱為「名臣」而稱不上忠臣,因為忠臣講究「知行合一」,明知是錯的就絕不附和,一定要起而反對。例如海瑞上疏,觸怒皇帝,犯了死罪,多虧徐階從中調和,免他不死,並委以重任,但海瑞重新上台後,立即把打擊矛頭指向徐階,因為他發現徐階家族有霸人田產、橫行鄉里的劣跡。應該承認,這是一種良好的品格,但在封建官場中卻顯得不近人情,從而也注定了忠臣坎坷、失敗的命運。
忠臣不僅講究知行合一,還講究不可為而為之。文天祥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為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血灑揚州,為的是向垂死的故國盡臣子的最後一份力量。這就好比父親病危,做兒子的明知不可救也要盡力去救。體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精神,並且可以取得人格、信念上的勝利,但在事實上卻注定是失敗者、犧牲者。
忠臣是犧牲者,是悲劇性的人物,但他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不僅以高尚的人格征服了千萬人的心靈,並且使自己得到了永生。他們的英靈成了中華之魂,這中華魂是激勵仁人志士奮進的精神動力,是支撐中華民族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支柱,從這個意義說,他們又是勝利者。
歷史上的忠臣、奸臣、昏君早已成為過去,但他們的言行事蹟卻是一部永遠也讀不完的書,發人深思。我們撰寫《忠奸抗衡》一書的目的,也正是在於透過抨擊禍國殃民的奸臣賊子、庸主昏君,頌揚公忠體國的賢能忠臣,給人們啟迪。
中國古代的忠臣、奸臣形形色色,他們之間的鬥爭錯綜複雜。本書以容易引起現代人共鳴的經典人物、典型事件作為選擇標準。在撰寫中,我們探索著用一種較新的筆法寫作,以增強趣味性、可讀性和啟迪的作用。
本書的寫作,除了引用歷代史料外,還借鑒了史學界同行專家的研究成果,限於體例,未能一一註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撰寫過程中,始終得到中國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魏鑒勳教授、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同仁的具體指導。於此一併致以謝意。
本書是我們同心合作的結晶。其中《魂兮歸來》、《大漢之旌》、《大隋巨奸》、《烽火長安》、《遼東忠魂》為楊英杰撰寫;前言及《北國宮變》、《天日昭昭》、《浩氣丹心》、《元初奸佞》、《熱血千秋》、《青天海瑞》、《大明孤忠》為喻大華撰寫;《千秋功業》為謝春山撰寫。最後由楊英杰統稿。
本書難免有許多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忠奸是父老相傳代代不忘的話題,更是小說、戲曲家描寫的對象,同時,其中的一些問題千百年來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政治家和史學家。
比如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芸芸眾生,攘攘諸官,模樣都差不多,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於是奸臣們會說: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會說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殺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面相專家則說可根據一個人的相貌舉止來判斷,一般奸臣大多有個「狼顧」之相。這種說法影響最大,所以科舉取士後授官之前要經目測一關。這不是選美,而是剔醜,即留下「國」字、「田」字臉形者,排斥那些臉形像「申」、「甲」、「由」字者。受此影響,戲曲、小說中的奸臣都被臉譜化,從而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奸臣一出場便可認出,總之,誰醜誰就是奸臣。
其實,若僅就相貌而言並加以打分的話,奸臣的分數肯定會高出忠臣。試想一個讓人一見就生厭的獐頭鼠目者怎會輕易討得君主的好感,從而獵取高位、得售其奸呢?據史書記載,很多奸臣都是儀表出眾,相貌堂堂,舉止非凡。如楊素、蔡京、耶律乙辛、阿合馬、嚴嵩等人,當然也有例外,王莽就是一個,但這類奸臣為數極少,並且能以其他長處來彌補這一缺欠。
奸臣們不僅相貌好,而且往往身懷「絕技」。普遍具備的就是表演才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口才極好,又恰到好處。捅你一刀之前能拉著你的手誠懇地為你出謀劃策,捅完之後還能抹幾把淚水。除此之外又各有所長:比如秦末的趙高深通法律;北宋的蔡京名列翰林,又是大名鼎鼎的畫家、書法家;南宋的秦檜曾中進士,頗有文采;明朝大奸嚴嵩詩文書法造詣也很高,這類例子不勝枚舉。筆者曾經設想,假若他們生在今天,或許其中很多人會成為影視明星、書畫家的。
古人云:大奸似忠,這也是奸臣的一個特點。他們以種種方式表達對國家、君主、同僚的忠誠和信義,並且往往也確有些忠信的實跡:或有功於社稷,或報德於同僚,從而得到從上到下的普遍好感,才得以占據高位,禍國害人。假若他們中途身死,未得施展其奸,其中有些人如王莽、楊素等將在歷史上留下無可挑剔的忠臣、功臣形象。
奸臣們還具備一個特點,一般頗具才幹。如楊素輔佐隋文帝統一天下,軍功赫赫,為一代名將,而且下筆成章,文詞華麗,可謂是文武全才。又如北宋神宗以後變法派與保守派互鬥,雙方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但不論哪派得勢,都要任用蔡京,就是因為他有才幹,他能辦成別人辦不成的事。總之,奸臣辦事幹練,能量過人,凡奸佞之徒,沒有一個是笨蛋。
由此可見,奸臣本來具備成為名臣的素質,但他們為何沒有成為名臣、忠臣,反倒成了奸臣呢?
其一,從主觀上來說,他們本是一些品德低下的小人。他們唯利是圖,為此不僅可以出賣靈魂,甚至可以殺妻烹子,拋宗棄祖;他們不講信念,反復無常,投機鑽營;他們嫉賢妒能,心理變態,百般排斥;他們陰險狡詐,虛偽成性,不以真面目示人;他們生性狠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由於有這些主觀因素,一旦客觀條件具備,便為所欲為,大售其奸。
其二,昏君當國是奸臣產生的客觀條件,並且是關鍵性的條件,對此有必要深加討論。
提起昏君,人們往往會想到劉阿斗、晉惠帝一類的白痴,這固然可以算作昏君的一種,但人數極少,並不典型。再一類就是玩物喪志,不謀其政者,如南唐後主李煜擅琴棋書畫,尤長於填詞,宋徽宗好書畫,明世宗崇道等。按說這類帝王天資不低,所好也不算低級,但中國帝王獨攬大權,國事繁重自不待言,即使全力以赴,猶恐不周,何暇及此?他們以此為專業,治國反倒成了業餘的,難免有奸臣投其所好,竊取大權。這類帝王人數不是太多,但也屢見不鮮,應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昏君。
最典型的昏君是兩個極端:一類是有治國之心而無治國之才,能力經驗均顯不足,這類君主容易為奸臣所控制,並在奸臣的引導下更加昏庸;二類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一意孤行。這類君主自以為是天下最聰明者,所以聽不得逆耳忠言。於是奸邪小人因之而進,先是投其所好,百依百順,騙取信任,獵取高位,然後挾天子之威風,打擊異己,禍國害民,為所欲為。這兩類典型的昏君在中國昏君中比重最大,他們或是被奸臣所控制,或是被蒙蔽,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為奸臣的產生負全責。因為無論奸臣勢力多麼強大,也超不過君主;無論君主多麼軟弱,只要他們起而除奸,天下自會有人起而響應。奸臣的垮台,相當多是由君主翻臉造成的,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品德低下的主觀因素是奸臣產生的動機,而昏君當國便為實現這種動機提供了全部條件,所以昏君奸臣是緊密聯繫著的概念。
那麼昏君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體制問題,即君主專制體制為昏君產生提供了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並不是說所有君主都是昏君,而是說只要有這種體制,就必然會有昏君。
其一,君位世襲制很容易造成昏君。一般說來,開國帝王都面臨著嚴峻的局面,這實際上是個優勝劣敗的競爭過程,競爭的勝利者即開國皇帝往往具有一些常人不備的特殊品格,為政治國是比較賢明的,並且能影響到一個王朝的頭幾代皇帝。再則如果皇帝有很多兒子(可能是幾十個)可供選擇,並且他又善於選擇的話,那麼下一代皇帝也會較為賢明。但畢竟開國皇帝每朝只有一位,而其他君主又多不善於選擇繼承人或無法選擇(兒子太少或只有一個),那麼下一代君主的賢愚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加之國家承平之時,皇子長在深宮,於民生飢苦、國家大政一概沒有體驗,一旦登極,茫然無措,很容易被奸臣迷惑,從而成為昏君。
其二,皇權至高無上,為昏君為所欲為提供了條件。帝王與大多數人一樣,在品格上往往是高尚與邪惡並存,並且年輕的帝王還有可塑性。但帝王的顧忌很少,他要為非作歹,非常容易,臣子大概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搬出「天」來嚇阻帝王,日食是一種警告,地震又是一種警告,祖廟失火表明祖先的憤怒等;再就是「極言直諫」,即直接向皇帝剖析利害,希望獲得採納。然而一旦皇帝既不在乎上天,又拒絕臣屬勸諫時,他就像一匹脫韁之馬,在人民的身軀上奔騰踏躍,無人可以制止,大小官員除了關門飲泣,在紙上哀求外,別無他法。
在這種體制下,昏君奸臣兩惡相濟,為所欲為。值國家承平之際,奸臣導君為惡,揮霍浪費;值國家多難之際,奸臣排斥忠良,製造內訌;值國家傾覆之際,奸臣或弒君篡位,或賣國投敵;至於魚肉人民,貪污肥私更是奸臣的普遍類型。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弄虛作假,欺上壓下,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栽贓陷害,軟硬兼施,種種手段不一而足。
但是,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只是昏君奸臣的世界,黑暗中也有光明,忠臣就是封建社會中的光明之一,是古代社會中精英的一種。
和奸臣不同,一則原則上說忠臣的產生不應有什麼前提,忠於國家、恪盡職守,勤政愛民,按儒家道德規範為人為官,就應算是忠臣。這類人數極多,但人們往往稱之為「名臣」、「循吏」、「良吏」,而不稱之為忠臣。二則忠臣似乎什麼人都可以當,哪怕是太監、宮女,甚至乞丐,只要在王朝覆滅時能一死以殉,就是忠臣。但這類「忠臣」並不為人重視,加之也不太合於今天的價值觀念,故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典型的忠臣其產生在事實上是需要有前提的,如昏君當國、奸臣當道、國家多難,並且往往是這三個前提同時存在。
典型的忠臣有如下品格:他們忠於國家、君主、信念,為此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他們為人剛直,不媚君主,直言敢諫;他們疾惡如仇,不畏權勢,不計後果,敢於鬥爭;他們為人誠實,不搞陰謀,不事欺騙,表裡如一;他們重義輕利,愛民如子,不事聚斂。而且他們往往又是能臣、功臣,並因此而身居高位,也因此而成為昏君奸臣的迫害對象。
忠臣的結局大多是悲慘的:他們有的血灑疆場;有的一生坎坷,備受迫害;更悲慘的是被誣以謀反,死在他所忠於的政權屠刀之下。正因如此,數千年來人們在為他們傾瀉了江河般熱淚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深思,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為何忠臣永遠是犧牲者呢?
忠臣的對手是奸臣,而奸臣的靠山是皇帝,沒有昏君,何來奸臣?而有了昏君,忠臣又怎能鬥過奸臣。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專制社會,忠臣的結局只能如此,這點很好理解。但問題是忠臣往往也掌握著很大的權力或擁有很大的勢力,如岳飛就掌握著一支令敵人喪膽的數十萬人的勁旅,他們為什麼不奮起反擊呢?這只能用今人難以理解的古代道德去解釋。一則他們都有一種以身許國的獻身精神,他們重視生命的價值而不重視生命的短長,失敗以至犧牲性命對他們來說並不可怕,甚至他們之中會有人視此為達到不朽的途徑。再則,從古代做人講究信義的原則出發,他們不去搞陰謀,他們相信正義的力量,相信即使君主不能為其洗去冤情,那麼還有千秋史評。最後,在當時的觀念中,他的權力、軍隊甚至生命都是屬於君主的,若以此對抗君主,便是亂臣賊子,這違反了他們畢生為之奮鬥的信念,是寧死也不會去做的,所以,忠臣的信念也決定了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做犧牲者。今天看來,他們因此而喪失了事業、生命、家庭,難免給人迂腐的印象,他們的忠誠之中也確實有愚忠的成分。但不能以此來否定其忠誠的價值,因為這不僅體現著誠實、獻身、捨生取義的高尚品格,而且也是忠臣征服人們心靈的主要原因。試想,岳飛起兵相抗,固然可以保住生命,甚至還可能實現收復中原的理想,但人們會怎樣看待他呢?人們會不會因此而對秦檜產生另一種印象?因為秦檜說他要謀反並未說錯。
也許有人還會問:忠臣不能搞些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嗎?遇事圓滑些,隨和些?回答是肯定的:絕對不能。歷史上確實有一類政治家,他們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由此而保住了自己並使國家免受了更大損失。這類人只可稱為「名臣」而稱不上忠臣,因為忠臣講究「知行合一」,明知是錯的就絕不附和,一定要起而反對。例如海瑞上疏,觸怒皇帝,犯了死罪,多虧徐階從中調和,免他不死,並委以重任,但海瑞重新上台後,立即把打擊矛頭指向徐階,因為他發現徐階家族有霸人田產、橫行鄉里的劣跡。應該承認,這是一種良好的品格,但在封建官場中卻顯得不近人情,從而也注定了忠臣坎坷、失敗的命運。
忠臣不僅講究知行合一,還講究不可為而為之。文天祥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為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血灑揚州,為的是向垂死的故國盡臣子的最後一份力量。這就好比父親病危,做兒子的明知不可救也要盡力去救。體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精神,並且可以取得人格、信念上的勝利,但在事實上卻注定是失敗者、犧牲者。
忠臣是犧牲者,是悲劇性的人物,但他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不僅以高尚的人格征服了千萬人的心靈,並且使自己得到了永生。他們的英靈成了中華之魂,這中華魂是激勵仁人志士奮進的精神動力,是支撐中華民族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支柱,從這個意義說,他們又是勝利者。
歷史上的忠臣、奸臣、昏君早已成為過去,但他們的言行事蹟卻是一部永遠也讀不完的書,發人深思。我們撰寫《忠奸抗衡》一書的目的,也正是在於透過抨擊禍國殃民的奸臣賊子、庸主昏君,頌揚公忠體國的賢能忠臣,給人們啟迪。
中國古代的忠臣、奸臣形形色色,他們之間的鬥爭錯綜複雜。本書以容易引起現代人共鳴的經典人物、典型事件作為選擇標準。在撰寫中,我們探索著用一種較新的筆法寫作,以增強趣味性、可讀性和啟迪的作用。
本書的寫作,除了引用歷代史料外,還借鑒了史學界同行專家的研究成果,限於體例,未能一一註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撰寫過程中,始終得到中國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魏鑒勳教授、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同仁的具體指導。於此一併致以謝意。
本書是我們同心合作的結晶。其中《魂兮歸來》、《大漢之旌》、《大隋巨奸》、《烽火長安》、《遼東忠魂》為楊英杰撰寫;前言及《北國宮變》、《天日昭昭》、《浩氣丹心》、《元初奸佞》、《熱血千秋》、《青天海瑞》、《大明孤忠》為喻大華撰寫;《千秋功業》為謝春山撰寫。最後由楊英杰統稿。
本書難免有許多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