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二十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黃進興
作者簡介: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
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章節試閱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十九世紀方號稱係「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萊歐(Clio)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榮銜;蓋自啟蒙運動之後,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主導了學術的發展。2 反觀十九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尚在孕育當中、嗷嗷待哺。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英國代言人艾克頓(Lord Acton,1834-1902)為例,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
又說:
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
艾氏的觀點乃是歷史學派回應新興社會科學共通的說詞,例如,蘭克學派在法國的追隨者—賽格諾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也適時刊行了《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s sociales, 1901)強力推銷社會科學應採用歷史方法,而遭致「方法論帝國主義」(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之譏。
顯然對艾氏和塞氏而言,歷史的思考遠溢於具體的歷史知識。他們的說詞復傳達了下列兩項訊息:其一,在世紀之交,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足以振翅長飛。要知十九世紀裡,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無不有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無一例外。但他們言說的時間點,適是其他學科趨於圓熟自信、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
約略其時(1880s-1890s),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對內則是蘭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 1856-1915)和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對決,前者標榜文化史,以寬廣的研究取向、結盟其他學科,對抗專注政治史、制度史的蘭克學派;7 對外,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代表歷史學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於忍無可忍之際,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緬格(Carl Menger, 1840-1921)百般的挑釁。雙方纏鬥多時,牽連甚廣,直迄二十世紀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時代,方告落幕;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
值此風雲變化的分水嶺,艾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餘威,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社會學」(sociology)有利。而蘭布希特又另外主張「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這點,連蘭克學派的欽茲(Otto Hintze, 1861-1940),都咸表認同。他發現晚近新開發的經濟史、社會史皆非系出同門(傳統的史學),而是來自新興的經濟學。迄此,連蘭克學派的集大成者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於其史學方法論鉅著的晚期修訂版,都不得不引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且承認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時風易勢,由此可以窺見。尤其邁入二十世紀初期,史學仿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節節敗退、割地賠款。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道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國以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為首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他亟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盟,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而魯賓遜之所以稱謂「社會科學」為「新盟友」,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魯賓遜發覺,即使是當今最了不起、學識淵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竟連「冰河期」(ice age)或「圖騰」(totemism)均聞所未聞,遑論其他閉塞不敏的傳統史家了。此事宛如民初名家錢穆遭受「不通龜甲文,奈何靦顏講上古史」之譏。又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一度懷疑甲骨文是騙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難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最終亦非得屈服時勢,私下取閱甲骨文。
對應地,該時在中國承西學遺緒者,便是梁啟超(1873-1929)的「新史學」。梁氏坦承:「史學,若嚴格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乍聽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嘗不可解作梁氏企圖將中國史學擺脫傳統「四部」之學的糾纏,進而加盟西學的陣營。這種覺醒不止限於個別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變革。在教學上,1920年起,北京大學史學系即明訂「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於必修科」。
而留美歸國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不遺餘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從他對魯賓遜《新史學》的譯文中求索。《新史學》裡有一小段話恰可作為答案,何氏是這樣翻譯的:
歷史能否進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
合,不去仇視他們。
這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於評斷乾嘉時期的章學誠(1738-1801)與當今史家的高下時,呂氏如是評道:
他(章學誠)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現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沉寂多時而晚近方才當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呂氏之見,其史學造詣較諸現代史學,仍未免略遜一籌。其故無他,現代史學的進步實拜別種科學之賜。而在諸多科學之中,社會科學尤為「史學的根基」。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靈格(Johan Huizinga, 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貶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只因渠無法取資當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以闡釋希臘文明的特質。東西兩相輝映,真是件無獨有偶的趣事!
事後回顧,自魯賓遜以降,史學門戶大開,社會科學長驅直入史學領域,坐收漁翁之利。況且時值社會更革,歷史的實用性遂受到無比的重視,在美國致有「進步史學」(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稱。在歐洲,則是由「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擔綱,其與「社會科學」有近乎天衣無縫的結合。年鑑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夫雷(Lucien Febvre, 1878-1956)及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均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會學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勸勉學生「放棄史學,而改習法律、攻讀考古學位,或學德文與其他」,而且該學派非常重視「比較方法」和「量化技術」。
但是,上述魯賓遜等這般標榜「新史學」者,卻未曾意識到「社會科學」與「史學」潛在的緊張性,似乎仍以「輔助科學」的模式去理解「社會科學」;他們不僅從未覺察出「社會科學」存有鯨吞蠶食的野心,並且無緣目睹日後馬克思唯物史觀對史學入主出奴的態勢。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馬克思史學宰制中國大陸史學多年,已廣為人知。同時,帶有鮮明目的論色彩的「近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亦席捲西方及臺灣史學界對歷史進程的解釋,使得中、西史學只能朝同一目標邁進:「普遍的(西方)合理性」。
簡之,二十世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結構論」(structuralism)側重系統的分析,時間因素不受到重視,歷史的縱深與變遷遂不得突顯。社會科學則是以喧賓奪主之姿出現,因此,受其影響的歷史分析,自然缺乏歷史感。該時的史學則呈現「歷史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狀態。
尤其在一九六○年代,「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顯學,以布浩士.史基納(Burrhus F. Skinner, 1904-1990)的「行為心理學」作為表率,他大肆推廣及宣揚「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並非人類行為的科學,而是那類科學的哲學」,一時鼓動風潮,造成另番社會科學的變革。而史學界大力鼓吹運用「行為科學」者,無過於伯克豪爾(Robert F. Berkhofer, Jr., 1931-2012),他的《以行為進路進行歷史分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乙書,曾流行一時。伯氏將該書獻給「我的歷史女神」(To my Clio),別有開展另一頁「新史學」的意味。其實,無論倡導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結盟,或後來奉行為科學為師,均不脫史學科學化的窠臼。居間,伯克豪爾尤為激進,他主張當前的史學問題不在於該否援用社會科學,而是如何去運用它。他說:
人作為分析的單元,只能透過某些概念架構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類行為的知識,其他史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他又斬釘截鐵地表示:
此時此刻,「行為主義」(behaviorism)提供史學研究最佳的答案,因為她汲取了人類行為的嶄新知識。換言之,史學必須借重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加上科學哲學裡方法論的自覺。
遵此,
史家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服務,便是挖掘事實,⋯⋯供給正確、可靠的事實。
另方面,史家又必須藉著指涉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方得尋得事實。是故,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實的供給者。而史學的最終下場,只能將詮釋權拱手讓給社會科學而淪落為資料服務的副手,更不被容許置喙理論的創新。換言之,史學與社會科學僅存有單向的主從關係。
尤有過之,復經紛至沓來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禮,傳統的歷史概念已被解構得體無完膚。美國的懷特(Hayden White, b. 1928)甚至明言:
毋論「歷史」(“history”)僅是被視為「過去」(“the past”)、或攸關過去的文獻記載、或者經由專業史家所考訂攸關過去的信史;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特別的「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
這種觀點對十九世紀末葉曾經宣稱「歷史是其它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頓,純是茫然無解的。
況且,社會科學的流行步調變化萬千,稍縱即逝。一九五○年代的史家,建議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韋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會學,社會、文化、象徵人類學,古典、凱因斯(Keynes)、新馬克思的經濟學,佛羅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學」。一九七○年代的史家,則鼓勵我們取資「紀茲(Geertz)的文化人類學、傅柯(Foucault)的論述理論、德希達(Derrida)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構主義、塞素(de Saussure)的符號學、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論、傑克遜(Jakobson)的詩學」,睽隔未為久遠,所列科目已全然相異,令史家目眩神搖,無所適從。
是故,中、西史學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恓恓惶惶,無所安頓。這由一九二○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兩岸史家(尤其大陸)幾乎是言必稱馬克斯、韋伯的地步。值得警惕的,當一九六○年代末葉,西方史家正熱烈擁抱社會學時,社會學界卻開始質疑起本門學科的信度;這種危機意識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它學科,令得滿懷虛心、登門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會科學」為實,史家在感到絕望之餘,遂捨實就虛,一股躍進「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亟盼遁入後現代主義的空門,一了百了。殊不知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終的輪迴。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十九世紀方號稱係「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
作者序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略有交代。容可挪之為背景知識。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啟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 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6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則是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況愈下、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鑑。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箇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一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需特別感謝中研院陳盈靜女士不憚其煩的協助。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勉,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
目錄
自序
1.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2. 從普遍史到世界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
3.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4.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
5.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辯——一個虛構的「假議題」
6.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趨勢——「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
7. 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
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9.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
10.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王冕之死
11. 章學誠的遇與未遇
12. 論儒教的俗世性格——李紱的〈原教〉談起
13.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
附錄 從現代學術反觀古典政教——黃進興院士訪談錄
自序
1.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2. 從普遍史到世界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
3.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
4.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
5.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辯——一個虛構的「假議題」
6.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趨勢——「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
7. 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
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9.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
10.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王冕之死
11. 章學誠的遇與未遇
12. 論儒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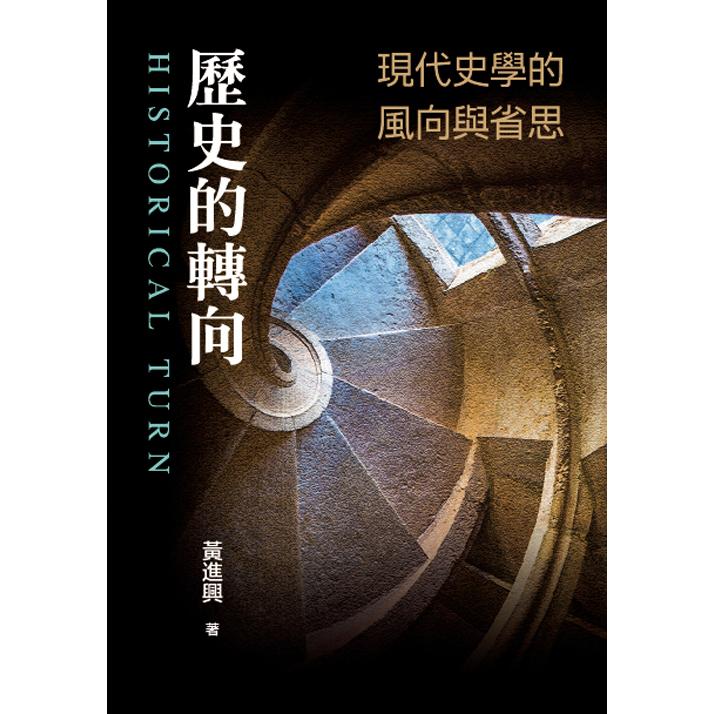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