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我多年來熱衷的領域可稱之為場所社會學。就因為這份熱忱,讓我注意到人們如何實際體驗社會關係,包含相當親近與非常遠距的社會關係,以及兩者如何相互影響。但因為「場所」並不是清楚而明顯的實體,顯而易見的這種關注並非來自經驗主義。如果不致力於探討主要理論,就無法理解場所。若欲理解看似簡單的場所社會關係和場所消費,就必須加入許多複雜的社會理論。的確,幾乎所有主要的社會和文化理論,總與某種「場所」的解釋相關。然而,這些理論卻未解釋場所的多樣化,因為它們並未涵蓋時間社會學及空間社會學、社會環境和物質環境間的關係,還有實物消費和自然與人造環境消費之間的相互依賴等。
因此,我想在本書建立三個論述:第一個論述是了解場所是複雜的理論和實證工作,需要一系列創新技術和調查方法;第二個論述是大部分社會理論都未能依照需求處理場所的本質問題,因為這些理論不知如何處理時間、空間與自然;第三個論述是至少部分場所是「被消費的」,對這種消費模式的分析研究並不多,而且多牽涉到人類感官的範疇。
本書書名為《消費場所》(Consuming Places),這個標題意欲表達四項主張:第一,人們逐漸把場所重新建構成消費中心,成為商品與服務被比較、估價、購買和使用的脈絡;第二,就概念上來說,場所本身是被消費的(consumed),尤其在視覺層面上。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為遊客和當地人提供各式各樣的顧客服務;第三,場所實際上確實是被消耗的(consumed)。場所因為具備某項特質(工業、歷史、建築物、文學、環境),所以人們覺得它地位重要,不過這些特質也會隨著經年累月的使用而逐漸枯竭、消滅或耗盡。第四,場所可能會吸引(consume)一個人的認同,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成為名符其實的令人著迷(all-consuming)之所。這對遊客、對當地人,或對兩者而言皆是如此。如此的場所認同感,可能產生多重的在地熱情、社會和政治運動、保護協會、一再前往的旅遊模式、享受四處漫步的樂趣等等。論及消費∕場所關係,上述四個面向所揭示的矛盾和模稜兩可,正是本書探討的重點(場所與消費的相關探討參閱Sack 1993)。
場所的理論分析日新月異,這亦是我關注的面相,尤其是「重新建構」(reconstructing)此一概念。使用「重新建構」一詞,正說明了1970年代末以降,學界理解場所的方式出現重大改變。有兩大現象造成此一轉變: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世界各地經濟急遽轉變;與此同時,政治經濟學取向再度活躍於社會科學領域,這兩個現象迫使學界必須就場所瞬息萬變的經濟基礎,展開研究和理論化的工作。我將在本章節後續部分,詳細討論那肇始於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一改我們對場所的理解之理論轉移。1980年代中晚期,人們開始意識到,政治與文化實乃建構場所和場所經驗最核心的一環,因而重新建構一詞的意涵也隨之變易。我個人特別關注場所消費,尤其在視覺層面上,並試圖把某些商品與服務消費的分析概念,連結到場所消費上。
之所以轉向文化,是受到兩個概念上的轉變所刺激:第一,研究者開始注意到人們對於場所的理解,不單只是被賦予的,實際上是由文化建構而成的。第二,研究焦點轉而處理文化變遷的經濟基礎,並關注我曾在他處提出的「符號經濟」(economy of signs)(Lash and Urry 1994)。這也導致使許多研究開始重視所謂的文化產業--藝術、觀光、休閒——文化產業如今已成為各地經濟、文化急遽改變的關鍵因素。
就在這些革新概念發展之際,我們對於社會和自然兩者關係的認知也有了些微改變。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的學問,過去,社會學立論的大前提是,社會和自然彼此截然有別。如此的觀念其實透露出改造自然的想法,甚至還把自然概念化成應受人類、社會馴化與支配的不自由領域。不過近年來,將自然視為就在那裡(out there)且應受控制和支配的觀念,卻同遭學術和實務層面的批判(同樣參閱Lash and Urry 1994: 第十一章)。特別是環境保護運動已然改變我們對於自然的理解,而近年諸多新興構想認為自然同時涵蓋了社會和自然環境,其共通特點即是「整體的自然」(integral nature)。
本章的重點,我應當擺在鑽研多年的時、空議題上(參閱Urry 1981b; Gregory and Urry 1985)。本章我將會指出,時空議題在當代社會學理論本應舉足輕重,可然而實情並非如此。二十世紀社會理論史,就某些方面而言,係一部時空議題意外缺席的歷史。不過我也會指出,時空議題不盡然一片空白。四處突圍的時間與空間論點,試圖破除原有的看法,這些既有概念一再清楚界定出立基在與無涉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社會,向來被當作從內部自行生成,有它們各自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受時間、空間所囿。此外,每個社會自成一格、互不往來,社會的界限幾乎等同於民族國家的疆界,舉凡規範共識、結構衝突或策略行為,在概念上多半被當作社會內部運作的過程。除卻都市及鄉村社會學,學界很少去正視社會內部空間彼此分化、區隔的過程。因此,二十世紀社會學研究的焦點多半側重在獨立的社會體系,認為社會結構不因空間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很少認真分析各式各樣的社會時間(social times),更無視場所和組織在重要意義上而言,其實是有時效的。
已有論者指出,學界對空間的忽視更甚於時間。索雅(Soja)提到,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的三、四十年間,全世界接二連三發生重大的技術、文化變革,影響深遠,徹底翻轉當代生活的空間基礎(spatial underpinnings)(1989),這些變革包括電報機、電話、X光、電影、收音機、腳踏車、內燃機、飛機、護照、摩天樓、相對論、立體派、意識流小說和精神分析(另可參閱 Kern 1983)。但索雅卻認為,這些變革多半未能從當時的社會理論裡反映出來。因為有關空間變革的討論全劃歸到另一門獨立學科領域之下,也就是日漸趨向實證主義的地理學。地理學把學門界線劃得涇渭分明,謹守明確的學術分工。索雅因而推論,有一種歷史意識銘刻在社會理論之內,導致「歷史的『想像』似乎可以消弭地理的想像」(1989: 323)。如此的歷史想像,儘管可從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便能見到端倪,不過相對而言,社會學對於下列議題依然無動於衷:明確時間的重要,尤其是社會關係因時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以及特定社會結構之內,其實包含著不同的社會時間。
本章第一部分,我將扼要摘錄一些二十世紀早期關於時間和空間的著作;第二部分,我將敘述是什麼促成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整個時間和空間觀念的改變,使得空間和時間因素更廣泛地被應用於社會學和社會理論;最後一部分,我將分析1980年代稱為「時空」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計畫之興起。闡述的焦點會放在幾本重要著作上,這些著作皆採納學者從事社會結構與文化過程相關研究時,應當確認時間與空間這樣的觀點,亦接受時間和空間既是權力的本質,亦是衝擊社會結構與文化過程的內在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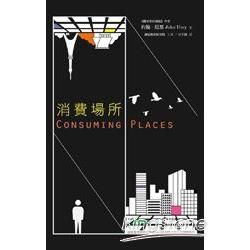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