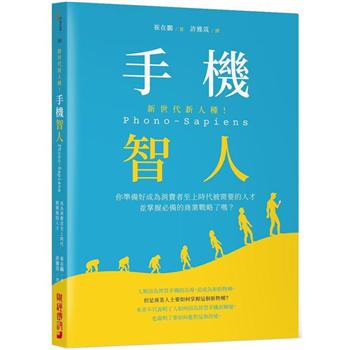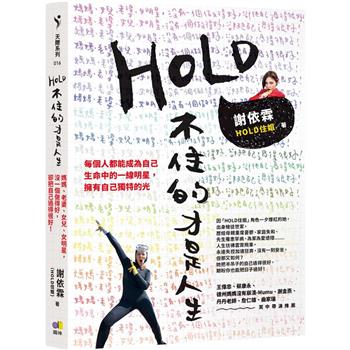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美國:世界首都 Estados Unidos: El capital|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因為你不會相信有多久的」。她以前有固定的工作,兩個女兒長大也離開各自組成家庭了,她的老公也先她一步離開了,而她有著一些錢,還有很多時光要打發,所以來這跟其他義工一起煮飯,每星期一三五,「為了神的榮耀」。她的社區廚房辦了五年了,它位在教會的一個寬敞、乾淨且無裝潢的地下室。她提到上帝時,聽來像是不再期待祂伸出援手,但卻仍祈求恩助一樣。
「為什麼只有那三天開?」
「因為那些日子剛好是其他社區廚房不開的時候,我們發現那些可憐的人在那幾天沒得吃……」
珊德拉女士指的可憐的人是一群五十幾個男人(都是男的),幾乎都是墨西哥裔的,幾乎都是中年或老年人。他們坐在兩張寬長的桌子兩邊,前方放著一個盛滿豐盛的蔬菜、雞肉、飯和鹹豆泥的盤子。大部份住在附近,少數住在家裡。多數流落街頭,在某個被遺棄的角落,一輛舊車裡,在橋下。或當冬天來時,在哪個流浪漢之家,那過一夜就得離開的地方。他們有大半天在十字架傳教會的教堂屋簷下渡過:九點喝一杯咖啡和吃個甜甜圈,十點聽傳教,十一點吃午餐。
「是啊,這裡大部份來的是墨西哥人,但還有其他國家的,拉美裔或非拉美人。深褐色的、白色的、咖啡色的,什麼人都有。」
珊德拉女士說完,然後看我是否聽懂了她所說的有關咖啡色的嘲弄話。
為宗教帶來更多的好處是:如果不是因為這樣,誰還會要來?更多宗教上的用途是:如果他們不來,那會怎樣?
巴爾多羅門(Baldomero)說他叫貝托(Beto),又說他出門後通常會到那街角,找人聽他訴苦。在那街角有「第二號絕望的吶喊」:「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戒酒匿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幫助你戒酒和戒毒」、「若希望不再受苦打這電話」等資訊。
「您認為我叫巴爾多羅門,但這兒大家都叫我貝托。」
貝托是個矮小、消瘦、黑皮膚、骨頭突出,六十幾歲的男人。他說他之前工作了很多年,負責庭院園藝。
還說他有個家庭,有三個好孩子。
「最小的還是個正式公民呢。」
他用那加勒比海地區的口音這麼說,為的是要強調他兒子是美國人,因為他是在這出生的,在芝加哥的一個郊區出生的。可是因為酒精他自己失去了一切:酒精逼他幹了所有他自己不會想幹的事,讓他遠離了家人,遠離了上帝,讓他沒工作。又說他現在想辦法回歸到原來的生活道路上,但為時有點晚了,他說,所以流落街頭。他說的「那個地方」(out there),指著街頭的那一角落,又說他的家人不願意再見到他,因為他對他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見不得人的事,我傷害了他們。」
「你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
那是只有我知道的事,他說。又說人生還剩什麼:過日子,這裡開的時候來吃飯,晚上找個地方過夜,有時候喝個幾杯,不然人生還剩什麼? 他問我,為了要聽我說「對,你說的沒錯」,而我閉著嘴。
宗教是人們的娛樂。
現在超市裡播放著那昆比亞舞曲(cumbia),唱著愛情和愛惜這美麗人生的那類歌。在十字架傳教會的地下室裡,窮人們低著頭吃著。在一個角落有五或六個年輕人叫著,說笑著。沿著較遠的牆壁有一個櫃子,唯一的一個:「我是生命的麵包,靠向我的永遠也不會挨餓。」
「他們像那些,怎麼說……那字西班牙文怎麼說?」
珊德拉女士問,想著她想說的那個詞:
「他們稱為流浪漢的,可憐的傢伙們。」
她終於找到了。之後,有一個食客跟我說,貝托的一個女兒自殺了。有些人說,那是因為他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什麼樣的事?」
「她不想做的事。」
他說,然後安靜下來。
貝托的人生充滿錯誤:他沉淪下去,卻沒辦法再爬起。那些陷下去的邊緣人的貧窮:
「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我最懷念那些植物。「那個地方」是很難種什麼植物的。我試過了,但撐不久,我想「那個地方」是沒辦法的。只要我還沒有失去我的手感就好,如果我失去了它,我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很多人以為來這兒的只有流浪漢。說真的,我想很多人寧願這麼認為。這樣他們會覺得心安點。」
大衛‧克勞福(David Crawford),「食品供給主任」,他的名片上是這樣寫的,他在「公正耕耘」(A Just Harvest)工作,那是一家由多個宗教團體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大衛是黑人,蓄有幾根很長的頭髮並花俏地結在他光禿的頭頂上,留著稀疏的鬍鬚,穿一件寬鬆的上衣和緊繃的高領,細長的領帶。大衛用那美式機關槍的方式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把字句噴出來,且沒有歇息的跡象。
「這樣比較簡單:大家說得很清楚,他們是流浪漢,體系外的傢伙們。所以不是體系的錯,是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這裡您看到的都是有地方住的,但問題是錢不夠支付所有的開銷:有房租要付,還有健保費、醫藥費,然後沒錢買吃的,所以只能來這。這裡什麼人都有,來的人各個不同,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人生的。他們的共通點是沒錢買食物,而這是確實的:只要能避免,沒有任何人會想來這些地方的。」
想像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個人的過去而淪落到這地步,是比較容易的。用一個表述來架構他們的人生:他們是流蕩的,一個瘋子、酒鬼,染有毒癮,他們墮落了。由於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不去或鮮少質疑一個來社區廚房取食的他者,所處的社會環境。
「公正耕耘」在芝加哥的另一邊,地鐵往北的最後一站。那是個黑人社區,有些偏僻,當夜幕降臨,街燈不怎麼明亮。但這個機構的建築很乾淨,有充足的照明、寬大的窗戶,有一間牆壁畫滿蝴蝶、鸚鵡、星球和火山,孩子牽著手,充滿鮮艷色彩的壁畫的大廳。有三十幾張可坐四到六個人的桌子,整齊地排列著,很乾淨,鋪著潔淨的塑膠桌布保護著;而在大廳的另一邊有一些置放菜餚的大桌子。這邊有黑人、拉美人、白人;有小孩、老人、男人和女人。沒人向他們問什麼資料,如果想吃飯,他們就把名字登記在一張紙上,找一個托盤。大衛說,這裡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三分之一的退休族,和三分之一有工作,但不夠家用及買食物的家庭。
「有可能有人有工作卻還是花不起菜錢?」
「當然,那些是暫時性的工作,打掃家庭和辦公室,在廉價酒吧當服務生,搬運或卸貨工的。有時可能一個星期內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有工作,領取八元的最低時薪,那這樣每個星期可能就能領到一百五十或兩百美元。在一個最便宜的房屋月租至少五百或六百美元的地方,還有交通費、醫藥費、衣服,你算算看吧:他們拿什麼買吃的?「公正耕耘」在這佇立了三十年,但最近三、四年,接受服務的人數增加許多。每天下午所準備給兩百個人的食物裡,一個小時內就清光了,乾淨俐落。大衛也說,他們的食物很健康且富營養,給他們一些肉類,好的蛋白質食品,蔬菜、沙拉、水果、麵包,所有一餐所需的營養均衡都顧全了。我們最不希望他們覺得我們提供次等的食物:沒有人是次等人士,也沒有人吃著次等飲食的。
大衛說著,然後再看我一次:
「那你呢,不想吃點什麼嗎?」
貝緹(Betty)有六十幾歲,白色短髮,有不透明的藍色眼珠,少了幾顆牙齒,且有一個像熨斗板那般挺直的背。她用一個助行器走路,不過她住得不太遠,離這約七或八個巷口。她說她剛來這時是因為喜歡吃飯時有伴,又說現在她想可能是這樣,或不一定如此。無論如何,她就是不願意說她來這是為了吃慈善分發的食物。但現在她知道,如果沒這家社區廚房,這社區會出很多問題的。
「我老公七年前去世的。我有時覺得他很幸運能先走一步,不需要這樣過日子。而且我們向來是認真繳稅的公民呢。」
貝提的先生一生在房地產公司做財務管理,做會計那類的。十五年前帶著一份微薄退休金退休,足以讓他們倆過活。隨著時間,交易所的交易變化讓他們的退休金縮小到貝緹幾乎付不起房租。
「每一年我的女兒會請我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走走,她住那。可以的話,也會寄點錢給我,但幾乎不多,可憐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貝緹又說她不希望造成她女兒的負擔,但看來真像一場騙局,過了這麼大半生,居然現在變成其他人的負擔。然後她問我打哪來的,我說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啊,那那邊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還是只有在美國?」
「我們盡量讓他們感到,來這不需要感到羞愧, 他們不過是在行使他們的權利罷了,每個人都有吃食飽足的權利。」
大衛說,但人們經常沒辦法撫平那羞愧感:
「您知道嗎,那是幾十年來被灌輸的一種觀念,認為來到這些地方是種恥辱,代表嚴重失敗的那般。如果美國政府羞於承認國內有飢餓的人民,且看看那些可憐的男人和女人是否能夠不感到羞愧?」
有個六十幾歲的黑人男性,很瘦,一副落魄樣,穿著一件非常寬大,印著歐巴馬臉龐的黑白襯衫。
「所以您喜歡歐巴馬執政?」
「我?我為什麼?」
「您穿的襯衫。」
「啊,是啊,別人送的,我就拿來穿。」
那男人牙齒僅剩幾顆,無力的眼神,兩手托著餐盤,不怎麼想聊天的樣子。
「但您喜歡嗎?」
「那是我喜歡的一張臉。」
「我就在問這,為什麼?」
「因為他經常都在笑,跟我一樣。」
「那你還會再投他一次嗎?」
「不,幹嘛?他當總統後我還是這般樣。一切都沒什麼改變。」
在一個角落的告示板張貼了很多廣告,場所的規定,還有一張不太大的海報:「讓華爾街還債」。大衛跟我解釋這不是他們貼的,這只是給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一個空間。這份海報是團體「全國人民行動」(National People's Action)貼的。在很多的規定和說明裡面,「公正耕耘」標示了一個他們的不妥協:他們不收受政府補助。他們接受來自個人的、私人機構的、教會的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捐助,但從不接受政府的協助。
「但在我的國家裡有很多人飢餓,非常多的人。」
大衛說。因此他希望有所貢獻,這是為何他們做這些的原因。
「我們希望能像幫助任何鄰居一般去幫助這些人。」
「任何一個鄰居?」
「是,任何一個。任何一個鄰居都該知道他和他的每一個鄰居都有飽足的權利,且如果一個鄰居沒得吃,則要想辦法幫助他;如果沒有幫助他,就有著跟飢餓本身一樣的過錯,更何況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糧食富足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該盡一份力的,不論何處,不論何人。那是我們認為的,那如果您不贊成……」
「我嗎?」
「好吧,您或任何人。」
這比較依然令人嫌惡:跟尼日或孟加拉的窮人比起來,這些絕對是享有特權的一群。
但是前述的窮人不在身邊讓他們可以比。
該要討論貧窮這概念,其相對性。飢餓是絕對的貧窮,但這裡的情形是相對的貧窮,而他們卻把這稱為飢餓。相對性是個哲學性的辯論:我們到底能夠或願意或應該容忍多少的不平等?
相反的,絕對的貧窮看來是被下述這些人,排除於這個辯論之外的:那些認為一個人尚可活在遠低於其可接受的環境之下,而當這些外在因素,讓此人必須要在自然發生之前就死去,他們也會感到一點不舒服的人。
就讓他們餓死吧。
「但是吃東西這回事不應該像一場每日的戰鬥,對吧?這裡是美國耶。」
迪克(Dick)戴著一副無框的眼鏡,修齊的頭髮,留著山羊鬍,厚厚的下巴贅肉,一件淺藍色的襯衫,一邊的袖子繡上美國國旗,很像郵局員工的制服。迪克五十幾歲,有個大肚子,像是兩人份的那般大。
「不,我從來沒在郵局上過班,這件衣服是我在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二手店買的。我在一家卡車公司上班,在倉儲部門,本來都好好的,可是他們關了,現在找工作非常的難。誰要僱用我這年紀的?」
迪克說,他本來就認識來「公正耕耘」這些地方領食物的人,但他從沒想過他自己居然也有來這的 一天。
「我有時候還會做點捐助。我不懂,真的不懂,怎麼事情會走到這地步……」
迪克喜歡聊天,且呼吸困難:
「我吸太多煙了,還好現在煙變貴了……」
迪克說他每天吃起司通心粉,還有一個一美元四十九分的罐頭,如果可以,還配上一瓶啤酒。
「但我能怎麼辦?我領食物券,可每星期拿不到四十美元。每星期我只有四十元能花,四十元我可以幹嘛啊?」
又說所以他每天下午都來「公正耕耘」,至少來這讓他胖胖的,吃飽飽的。他是這麼說的:胖胖的,吃飽飽的。
「現在他們說什麼肥胖很不好,影響健康,我知道的是,胖子從不會因飢餓而死。可能因其他原因死掉,但絕不會是飢餓。」
迪克說著,然後起身,這是個很複雜的動作。他拿著拋棄式紙盤,盤子還留有一些剩餘的飯粒和兩整塊麵包。他帶到垃圾桶丟進去,我知道我不該,但我不禁想到那些剩菜不知能餵食多少個在印度比哈爾的、在蘇丹的人。比較,我們都知道的。
9.
食品架上滿是各種鮮艷的色彩:紅色、藍色、黃色,都是原色系的。食物架上印著微笑著的老虎、小獅子、松鼠、鸚鵡、雞、狗、貓,微笑著的明星,有成就的運動員送上一堆像雪團一般白的螺旋狀的多穀物早餐,多種形狀,多種口味的:蜂蜜、水果、核桃、肉桂、巧克力。另為了讓孩子們回復健康,也在包裝盒上畫著一杯滿溢的牛奶。一位體型像兩個甚至三個女人那般胖的女士,一頭蓬鬆散亂的金髮,碧藍的眼珠,一件深粉紅色慢跑褲。她拿著一盒寫著Trix的早餐穀片,上面還畫著一隻兔子。一副懷疑樣,她重新把盒子放回去。那肥胖的女士很吃地推著一台不太滿的推車往前走。她氣喘吁吁地走的,行動極為緩慢,雙腿不停的碰撞,看來不太能支撐她的重量。
「不好意思,我拿不到上面的那一盒。」
那盒應該是她拿得到的(超商可不想讓消費者錯過消費的任何機會)但那位太太拿不到。
「這便宜得多了,知道吧?」
我幫她拿一盒沒有圖畫的早餐盒,上面寫著「健康得不得了」的廣告詞。女士看一看,向我道謝,放入她的推車裡,繼續氣喘吁吁地走。在她的推車裡有一包超市品牌的麵條,兩打蛋,三包奶油麵包,六罐起司通心麵罐頭,其他種類的罐頭,兩卷廚房用紙巾,一盒家用洗衣粉,兩盒果膠和待放烤箱加熱的蛋糕,三公斤糖,兩盒香草冰淇淋,一罐兩公升的美乃滋,三盒各十二條的香腸,一隻死的雞。
「我的孩子也喜歡吃這些。」
這位女士名叫瑪瑞絲卡(Mareshka):她說她叫瑪瑞絲卡,又向我抱歉剛剛要我幫她拿那一盒,但也說她的身體實在是負荷不了了。我不敢問她負荷不了什麼,但她說她經常來「全家一元」(Family Dollar)買東西,「全家」是賓漢頓(Binghamton)旗下最便宜的超市。然後瑪瑞斯卡看我一下,用那深沉的眼神看我,帶著一絲哀怨的說著,好像我問她另一個問題般,那我最想問的一題。
「我不窮,我有工作的。我什麼人都不求的。我們從來什麼都不求人的。」
之後,瑪瑞絲卡走出了超市,在半遺棄的灰色人行道上。那「我們」就是她的上幾代。之後她跟我說,她的曾祖父母一百年前從波蘭移民過來,因為這兒有工作,所以他們留在這。
「可憐啊,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現在過的模樣。」
「你不會因他們選了這麼糟糕的地方定居感到生氣嗎?」
「我還怪他們什麼啊,可憐的老傢伙們。至少死的時候是安穩的,不需要面對這些。我想我寧願這麼想。」
賓漢頓(Binghamton)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離市中心約三個鐘頭車程:離全球權力中心僅三個小時。距離白人拓荒者驅走印地安人,然後一個白人獨佔著這全部的年代已超過兩百年了。威廉‧賓漢頓(William Binghamton)先生買下了這片土地,且掛上他的大名。這裡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個很繁華的地區,非常具潛力,這一區能接到部分出海的港口。然後西元一八五〇年火車出現,工業開始興盛,移民潮蜂擁而至,銅板聲響清脆的碰撞。賓漢頓在那些日子的重要性,讓這一區蓋了美國第一所治療酒精上癮的療護中心——紐約州戒癮庇護所(New York State Inebriate Asylum)。之後波蘭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陸續進駐,那些創造美國的移民,創造了一段輝煌時期。
他們將之稱為機會之谷:城市不斷的擴張,開始蓋起虛幻而不實的漂亮房子,橋樑、教會、公園,還有那IBM企業。繼二次大戰後,賓漢頓達到城市發展的巔峰:在這發明了模擬飛行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 company)在這製造武器,軍事監視設備類的尖端科技武器是他們的專長。但冷戰的結束,讓他們的生意大打折扣;當攻擊共產黨不再是賺大錢的生意,工廠一一倒閉,或遷到更適合經營的地方。因一個特殊的詩學正義的情況,在打贏這場戰役後賓漢頓城失去了工作、人民、希望;現在,這個城市比一百年前的人口還要少:若包括其郊區的居民頂多只有二十五萬人,而且每四個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
現在,賓漢頓最好的房屋變成了一間間的小銀行、大型殯儀館、各式各樣的教堂,他們的重點可清楚了,賓漢頓的購物區在城市外圍,一個像鬼城的中心,破舊的街道,被遺棄的住宅,二流的大學,和一份宣示「全美國僅餘的一百五十個旋轉木馬,其中的六個就在此市」的驕傲。這城市的消息不時也上報:比如說,西元二〇〇九年四月,一個自越戰退役的軍人走進位於前線街(Front Street)的美國公民協會(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射殺了十四個人。或去年,當蓋洛普(Gallup)在這城市進行民調,發現這裡是全國有最多悲觀人士居住的地方,或是天空最為髒污的城市。或根據最新數據,將這城市列為全國前三名有肥胖人士的城市之一:超過該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的居民。
西方文明可是超級肥胖的:脂肪多、油膩且粗壯。
未來當字典定義這些詞彙時,肥胖(obesity)的意義將為應受到譴責的肥大,具有危險性的。
瑪瑞絲卡的祖父曾經營一家香腸店,自製自售。他的父親不想碰這麼多肉,所以到IBM公司當工人。當賓漢頓城的工廠逐一關閉時,他只好回去接家業,他感到很悶,生意也很快就瓦解掉。瑪瑞絲卡當時已經三十歲了,已經結婚並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試著開一家美髮店,但沒成功。她的先生是公車司機, 他們就這樣想辦法生活。
「那時那銀行的女人說服了我們。她說什麼我們能夠買一個房子,還比租金更便宜。那不是真的,她說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但我們想要相信她。」
他們買了一棟六萬美元的房屋,銀行貸款給他們,而且很漂亮呢。她跟我說,你沒看到,是那種小木屋的,還有後院、前廊、兩層樓、三個臥室,非常可愛。她說著,然後臉沉了下來。因為她先生在西元二〇〇八年去世,剛好是那一年,而她一個人沒辦法繼續支付房貸,所以銀行收回了房屋。
「對啊,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
她跟我說,而我不知道是否該問他是否也很肥胖。她看著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沒錯,他沒好好照顧自己,但至少還能再活久一點,對吧?一定可以的。」
現在瑪瑞絲卡幫一個表姐管理一家店。賣啤酒、香菸、報紙、彩票、小零嘴,每月領兩千美元。她的三個孩子介於十三到二十一歲間。
「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吃的。你叫我拿什麼給他們?」
「妳領那樣的薪水難道沒資格申請補助,食物券什麼的?」
「是,權力我有,可沒意願。我不想。我能夠維生,不想任何人送給我什麼。我是個美國人。」
「我是美國人(I'm American)」,她說,
好似那幾乎代表一切。
幾年前美國政府將一種特殊疾病放在前鋒的焦點位置:肥胖。
開始懼怕這疾病是近幾年來最極端的文化轉變。好幾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的社會裡,身為胖子是種奢侈:能夠吃到多餘的份量,在自己的身軀裡浪費那財富,並有所炫耀,這是另一種權力的展示。
甚至才幾十年前,肥胖是個不容置疑的富有表徵。那些肚皮快要把戴有金鍊條、隨身錶的外衣撐破的皇室、大官、教皇、財閥們,那些戴著帽子的豐腴女士們,或歌舞劇的女演員們,都用那些脂肪當作她們的獎賞。 在一個當勞動讓身軀瘦下來的年代,一個肥胖的身軀是一種不事塵勞的炫耀。在一個當吃食是種特權的時代,一個吃得到想吃的,並且吃得比需要的還要多的身軀,是一個令人想要展示的體態。但之後,肥胖開始退流行。首先,反主流文化的年輕人視其為資產階級的象徵。隨後,資產階級者認為他們也該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靜態的工作讓人肥胖,運動需要花錢和運用自由的時間,他們該要展示一個充滿纖肌和有運動性的身軀了。然而把肥胖視為疾病是還不到二十五年歷史的。
而當然啦,有錢人因此也不再是肥胖的了。
一般說來這有那麼點可惜。我們認為肥胖是被暴露在外的個人缺失:一個沒辦法充分掌握自己身軀來變瘦,無法控制身體的人。但是,逐漸的,這也形成了社會歸屬的訊號,只不過是社會的另一個極端肥胖越來越是個貧窮的象徵。
醫師們歸咎肥胖為心臟血管疾病和其死亡,部分的癌症,以及那項文明病——糖尿病大增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想要精確的界定它,使用「身高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的公式:一個人的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這指數介於二十五到三十之間,則這個人超重;若超過三十,則那個人是肥胖的。
這標準是嚴苛的:我,一百八十五公分高,重九十公斤,有輕微的超重,BMI值為二十六點二。雖如此,我依然是在多數拉丁美洲男性的平均值之下:二十六點七。若是肥胖,則應該要重一百零三公斤。
以這樣的嚴格計算方式,就不難接受全球有十五億超重的人口;肥胖人口則佔其中的三分之一:五億人。這些數據造成了一個很值得注目的現象:世界是如此的扭曲,居然讓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的,飢餓和胖子的人數差不多。且,不論是默許或明示,一些人缺乏的食物被另一些人拿走了:胖子吃著飢餓的人沒得吃的。
聽來像是對幾乎所有事情一種還不賴的解釋,但就像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樣,這不是真的。
「他們說我們需要吃健康的。誰哪有錢去買健康的食物?要有錢才買得起那些蔬菜和水果……」
「那您喜歡吃那些蔬果?」
「說真的嗎?要說真的嗎?」
「好吧,既然我們都在……」
「說真的我不喜歡。我知道該要吃那些其他的,可我也知道沒辦法,錢不夠買。你們也可以跟我說這些對我不好,但我喜歡。我的人生有夠多的苦楚了,還要再一天到晚想我該要吃什麼的,甚至連安穩的吃我喜歡的都不行。」
「那您不擔心孩子?」
「我的孩子已經夠大了,他們能夠開始自己找吃的。我沒辦法再有什麼影響力了。」
「您的孩子身材瘦嗎?」
瑪瑞絲卡用一種嫌惡和怨恨的眼神看我,然後微笑。
這不是真的:肥胖是富有國家的飢餓。在不太貧窮也不太富有的國家裡,肥胖的人是營養不當的人,是最貧窮的人。在這些國家裡營養不當是由欠缺變為過多,由食物的欠缺轉為垃圾食物的過剩。那些貧窮國家裡營養不良的窮人是在於吃得少,無法發展他們的身軀和腦力;那些富有國家的窮人是在於吃太多廉價垃圾食品(油脂、糖分、鹽分)而發展出了不成比例的身軀。
這不是飢餓的反面:這與飢餓成雙成對。
不平等就是如此體現的。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沈倩宇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66 ~ 504 | 飢餓:從孟買到芝加哥,全球糧食體系崩壞的現場紀實
作者:馬丁‧卡巴洛斯 / 譯者:沈倩宇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5-11-11 語言:繁體/中文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1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飢餓:從孟買到芝加哥,全球糧食體系崩壞的現場紀實
▍這是個食物資源最豐富,卻最飢餓的年代|失控的糧食分配正義第一手紀實 ▍
這個時代,不再有因匱乏而造成的飢餓,因為飢餓是人們的貪婪所造成。
食物供給系統的失衡、糧食浪費帶的無盡揮霍,讓「吃的不公」惡化蔓延……
//她沒選擇過她的未來,沒想過她的人生有可能和現在截然不同。
她從沒想過,或許她能夠擁有毋需擔心明天是否還有食物吃的人生。//
據估全球每年可生產能餵飽約一百二十億人口的糧食,這將近是全球人口的兩倍,那為何時至二十一世紀的現今──這有史以來生產最多糧食的時代,仍有超過十億以上的人們正忍受著飢餓或為營養不良所苦,諷刺的是,在糧食浪費帶上竟也有超過十億的肥胖及過重人口同時存在!
每一年,約三百多萬的孩童因飢餓相關的疾病而死亡,而同樣的疾病對一個有充足營養和健全醫療資源的孩子而言,並不會構成大礙,這樣的惡況居然發生在糧食資源過剩的地球上,這不是宿命,一個因飢餓而死亡的孩子是個被謀殺的孩子。
▍是誰在挨餓?又是誰在製造飢餓? ▍
我們都知道肚子餓是怎麼回事,也習慣了這種感受,生活中沒有比肚子餓這件事更為平常的事了。不過,對我們許多人而言,距離「真正的飢餓」實際上卻再也遙遠不過。
為了瞭解飢餓,為了訴說飢餓的故事,卡巴洛斯走遍印度、孟加拉、尼日、南蘇丹、馬達加斯加、阿根廷以及美國等地深入探訪紀錄,在這些地方,他遇到了很多因乾旱天災、戰爭動亂、極端貧窮、社會邊緣化,或甚至糧食市場的投機炒作等種種原因,而飽受飢餓煎熬的人們。作者筆下的故事,屬於飢餓的人們,這些處於極度惡劣環境並想方設法減緩飢餓感的人們,也屬於那些利用食物進行投機生意和政治盤算,而造成如此飢餓景況的人們。
▍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因為飢餓而吹響了革命的號角,當年因飢餓興起的革命,至今兩百年後卻仍在上演。▍
自古以來,飢餓是促成社會改革、科技進步、革命和反革命的動力。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比它更重要,更深遠地影響人類發展進程,也沒有一場病疫或一場戰爭比它殺戮了更多的人。至今尚無一場瘟疫像飢餓一般,如此致命,但卻又如此容易避免。
書中將一一揭示全球「飢餓」的成因,怎麼樣的運作機制讓超過十億人吃不到其基本所需?這是世界秩序下無可避免的宿命?有能力者怠惰和拖延的結果?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獨門生意?一個正被解決中的問題?還是全體人類文明的失敗?
本書的內容也許會因太過真實而令人感到不適,也許大家能夠感同深受,作者筆鋒直指問題核心,不迴避去觸碰痛處,意欲掀起一場關於「食物分配正義」的全民革新運動!
聯名推薦──────────────
卡巴洛斯帶領我們綜觀全球,探查原因錯縱複雜的飢餓問題,筆鋒犀利直指核心,卻又不失溫暖關懷。而書中結尾「必須採取行動」的訴求,更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多年來透過「飢餓三十」關心飢餓議題的持續行動相呼應。面對這關乎生命氣息存留的大事,我們絕對不能冷漠以待!──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龔天行
暢銷作家|大S、知名演員|張鈞甯、知名導演|戴立忍、綠色陣線執行長|吳東傑、香港記者及《剩食》作者|陳曉蕾、台灣農村陣線秘書長|蔡培慧
◎衝擊性十足,內容深具實用價值,見聞廣博靈通。──尚‧齊格勒(Jean Ziegler)|前任聯合國糧食權利問題特別調查員、法國著名飢餓議題學者
◎本書除了是部關於「人類最大之失敗」的報導作品外,也是對於記者本業的一大反思:為何,為了什麼目的,一個記者當了記者;又為何,為了什麼目的,他們做出了報導。就本書而言,其所報導的是悲慘,那數之不盡的悲慘。──雷伊拉‧蓋瑞羅|《國家報》
◎一本怪異、獨特、暴力,且不可或缺的書。卡巴洛斯此一作品具有令人難忘的強烈力道。──安東尼‧路卡斯|《世界報》
◎本書教人驚嘆,渾身不快,但又迷人。它一拳即擊倒了我們如此舒適的文明。──娜莉雅‧艾斯顧爾|《先鋒報》
◎一本我認為會變得非常重要的書。一本大家都缺少的書。──阿古斯丁‧費南德斯‧馬優|《世界報》
◎再沒比這更傑出的作品了!──耶穌‧費雷|《真理報》
◎幾可確認這將是二○一五年最棒的一本書!──李嘉鐸‧馬丁尼斯‧優卡|《地平線》
◎一個嚴酷又令人熱血澎湃的報導。──《共和報》
作者簡介:
馬丁‧卡巴洛斯(Martín Caparrós)
西元1957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法國巴黎取得歷史碩士學位,曾旅居馬德里和紐約,辦過書籍雜誌與美食雜誌,翻譯過伏爾泰、莎翁和格維多(Quevedo)的作品。曾榮獲星球文學獎(Premio Planeta)、艾拉德小說文學獎(Herralde de Novela)、西班牙皇家國際新聞獎 (Internacional de Periodismo Rey de España)、古根漢基金獎(Guggenheim Fellowship)。種過一棵檸檬樹,有一個兒子,也出版過幾本著作。最新著作包括小說Comí(暫譯:《我食也》),以及探討美食的Entre dientes(暫譯:《唇舌之間》)。
譯者簡介:
沈倩宇
輔大英美文學系學士,亞利桑那大學公共衛生碩士。旅居中南美及北美州多年,曾與墨西哥非法居留身份居民共事,以及祕魯貧民窟青少年生活和研習等。熱心於社會與公共議題,現於非營利單位服務,同時身兼自由譯者。
TOP
章節試閱
|美國:世界首都 Estados Unidos: El capital|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緣起 Los principios|
1.
我看著這三個女人,持續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外婆、一個母親和一個舅媽。那母親和舅媽緩慢地收拾放在醫院折疊床旁邊的兩個塑膠盤、三根湯匙、一個燻黑的小鍋子,還有那綠色的桶子,然後交給外婆。當這位媽媽和舅媽將被單、兩三件小小的襯衫收在一塊棕梠葉墊子,讓舅媽撐在頭上時,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但我接下來看到的光景讓我全身發軟:舅媽將身子往前傾趨向折疊床,抱起了孩子,將那小小身驅撐在半空中,用很怪異的表情看著──一種很驚訝,又感到極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然後將他放在媽媽的背上...
1.
我看著這三個女人,持續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外婆、一個母親和一個舅媽。那母親和舅媽緩慢地收拾放在醫院折疊床旁邊的兩個塑膠盤、三根湯匙、一個燻黑的小鍋子,還有那綠色的桶子,然後交給外婆。當這位媽媽和舅媽將被單、兩三件小小的襯衫收在一塊棕梠葉墊子,讓舅媽撐在頭上時,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但我接下來看到的光景讓我全身發軟:舅媽將身子往前傾趨向折疊床,抱起了孩子,將那小小身驅撐在半空中,用很怪異的表情看著──一種很驚訝,又感到極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然後將他放在媽媽的背上...
»看全部
TOP
目錄
緣起
尼日:造成飢餓的制度
關於飢餓-1:人類的起源
印度:傳統的皈依
關於飢餓-2:人們的雙手和生產
孟加拉: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關於飢餓-3:貧窮,以及更多的飢餓人口
美國:世界首都
關於飢餓-4:不平等的分配體系規則
阿根廷:在垃圾堆上討生活
關於飢餓-5:真正看清慈善這回事
南蘇丹:最後誕生的國家
關於飢餓-6:當飢餓成為一種比喻
馬達加斯加:被掠奪的新殖民地
寫在最後
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謝辭
延伸閱讀
尼日:造成飢餓的制度
關於飢餓-1:人類的起源
印度:傳統的皈依
關於飢餓-2:人們的雙手和生產
孟加拉: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關於飢餓-3:貧窮,以及更多的飢餓人口
美國:世界首都
關於飢餓-4:不平等的分配體系規則
阿根廷:在垃圾堆上討生活
關於飢餓-5:真正看清慈善這回事
南蘇丹:最後誕生的國家
關於飢餓-6:當飢餓成為一種比喻
馬達加斯加:被掠奪的新殖民地
寫在最後
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謝辭
延伸閱讀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馬丁‧卡巴洛斯 譯者: 沈倩宇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11 ISBN/ISSN:97895713643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88頁 開數:14.8x21.0 cm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