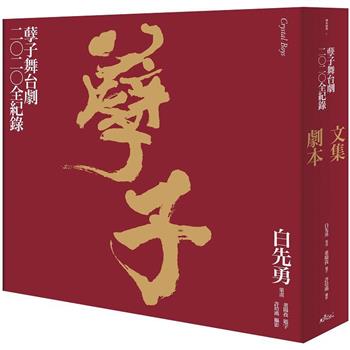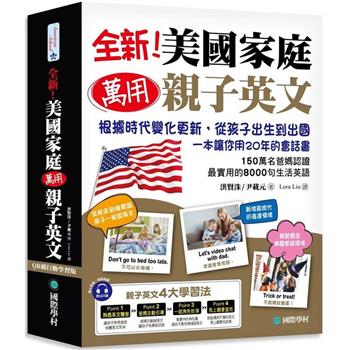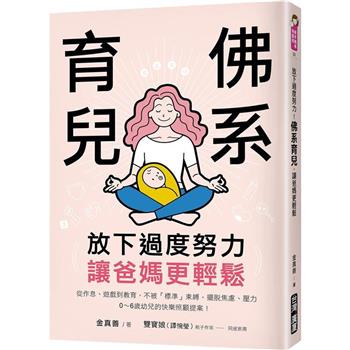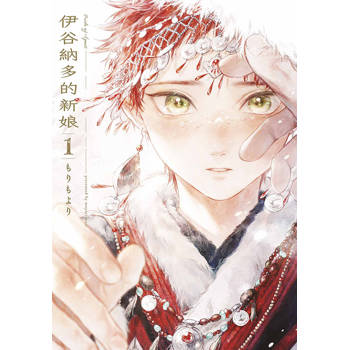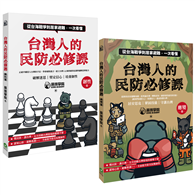1861年
蘇慧廉是以接棒者的身份於1883年初春來到溫州,因為他的前任李華慶 (Robert Inkerman Exley)病逝了。
蘇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於英格蘭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我後來到英國,才知道哈利法克斯在英人眼中並不是一個好地方。這座城市最有名的可能是以城市名命名的哈利法克斯銀行,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不過在前不久爆發的金融海嘯中飽受重創。
蘇慧廉出生的這一年,中國人稱為辛酉年,也稱咸豐十一年。是年八月,咸豐皇帝病逝於熱河,六歲的同治繼位。他的生母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從此走向權力中心。在二十六歲的慈禧當政的同年,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走向美國的權力中心,他開啟的是北美洲的一個新紀元。
同治在位的十三年,身居紫禁城的小皇帝與慈禧都不知道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了林肯完成美國的統一外,德意志與義大利也都在這一時期完成了統一。這些國家在統一後便開始國內的大建設,並由此迎來經濟的大發展。史家發現,同治之前,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大國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便增加了美、德、意。這種變化,對中國而言,不僅面對的世界大不一樣,而且是更加困難了。
起初,我只是因蘇慧廉生於1861年才關注這個貌似平常的年份。但當一些資料、史料在這一年交彙時,我看到了大歷史中充滿詭譎的安排,以及歷史通向未來必然的路徑。
與蘇慧廉同齡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寫道:
我今晨坐在窗前,
世界如一個路人似的,
停留了一會,
向我點點頭又走過去了。
模糊的蘇慧廉
蘇慧廉的英文名為William Edward Soothill,直譯的話,應叫他「威廉‧愛德華」,亦有人譯為「蘇威廉」、「蘇熙洵」、「蕭塞爾」、「蘇慈爾」、「蘇赫爾」、「蘇惠廉」、「蘇特爾」、「蘇維伊」等。 這些不同的譯法為我們後來探索他的歷史足跡,增添了諸多不便。
關於蘇慧廉早年的材料很少,我至今還只能勾勒出一個粗線條的輪廓:
他出生於一個貧寒的家庭,其祖父曾陷入一場官司,從此家道中落。 蘇慧廉的父親叫威廉•蘇西爾(William Soothill,1836-1893),是個普通的工人,從事布料、原材料的染色、壓制工作。 蘇慧廉的母親叫瑪格麗特(Margaret Ashworth,1840-1919),1858年嫁給蘇慧廉的父親後,先後為他生了十二個孩子,六男六女,老大就是蘇慧廉。 蘇慧廉的父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工作之餘為所在的教會從事佈道工作。父親的信仰及言傳身教後來改變了蘇慧廉一生的志業。蘇慧廉有一個叫艾爾弗雷德(Alfred Soothill,1863-1926)的弟弟後來也成了牧師,1885年開始傳道,並長期擔任阿什維爾學校(Ashville College)校長。創立於1877年的阿什維爾學校今天仍在招生,是英格蘭北部哈羅蓋特鎮(Harrogate)最古老的私立學校。
來華前蘇慧廉沒有經過大學的教育,他的學校生涯只到十二歲。學校畢業後即進入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因為他起初的想法是做個律師。後來改變初衷,除了家庭的信仰外,據說還因聽聞一個傳教士在非洲冒險宣教的故事。這位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遣往東非的傳教士叫查理斯•紐(Charles New),同時也是個探險家,曾於1871年徒步登上乞力馬札羅山,並成功穿越雪線。蘇慧廉年輕、激情的內心一時因這個故事充滿夢想與渴望。
蘇慧廉從此有了去異域傳教的想法。為了獲得更多的神學知識,蘇慧廉去曼徹斯特的神學院進修。他自學法語與拉丁語,並通過里茲市(Leeds)的入學考試。
僅看這些背景,很難想像,這個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職業規劃還漂移不定的年輕人後來會有驚人的成就,不論是在傳教領域,還是學術領域。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蘇慧廉自小就非常勤奮。據他妻子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回憶,蘇慧廉年輕時經常在書房裡讀書直到半夜,天亮後又早早起床,接受老師的教誨。蘇慧廉自己在回憶錄中也說小時候曾因為能背《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而獲獎。《聖經新約》中的《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很長,有三十九節,這可從側面說明他既勤奮又天賦甚高。
我一直不知道蘇慧廉的長相,直至2007年底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書架上看見《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 一書。這本大陸稀見的港版書收錄了胡適很多的舊照,其中一張是中英庚款委員會赴華代表團的合影。我當時已開始蘇慧廉資料的收集,這張攝於1926年的舊照讓我驀然發現,右邊第一人即是蘇慧廉。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正面的蘇慧廉。
以前溫州歷史寫到蘇慧廉時,總會用一張他戴帽的照片。這張照片來自他傳教回憶錄第三章中的一張插圖。在這張題為《在路上》的黑白照片裡,一個穿著白色洋裝、戴著圓形帽子的白衣男子坐在山轎上。照片中的人物是中景,帽沿讓原本不大的臉顯得更加模糊。路熙說這個白衣男子就是蘇慧廉。蘇慧廉一直就以這樣的形象留在溫州過去百年的歷史裡。
如果沒有夏鼐(字作銘,1910-1985),溫州人可能連這張模糊的照片都沒有。夏鼐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溫州人。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在北京西單市場一舊書攤發現了兩本與溫州有關的英文書——《中國傳教紀事》 與 《中國紀行》 。前者1907年出版於倫敦,作者是蘇慧廉;後者1931年出版,作者是蘇慧廉的夫人蘇路熙。夏鼐知道蘇慧廉,他早年留學英倫,一次去牛津遊學,還邂逅了蘇慧廉的女兒。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溫州曾向夏鼐借閱這兩書,以撰寫文史資料。在時任溫州市圖書館館長梅冷生與夏鼐的通信中,保留了當時借閱、擬譯、催還的記錄。雖經數次催還,但它們終沒有回到夏鼐的書房,直至他1985年去世。
這兩本英文回憶錄今天保存在溫州圖書館善本書庫裡,成為近幾十年來溫州人瞭解蘇慧廉及其溫州事工的唯一來源。
呼召
蘇路熙在《中國紀行》 一書中這樣寫道:
一天夜闌人靜的時候,他合上書本,為了消遣,他翻了翻手頭邊的一本雜誌。這本雜誌上說正在招募一個年輕人去溫州接替另一個年輕人。蘇慧廉這時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那一個人」。
當時是1881年夏天,英國偕我公會 派駐溫州的唯一一位傳教士李華慶剛剛去世。
「溫州失去了唯一的傳教士之後,差會(Missions)只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尋找另一個。1881年春季的時候,筆者曾被里茲和布拉德福德(Bradford)教區提名為牧師候選人。不過,在隨即召開的年度會議上,通過了當年不招收新牧師的決議——那也是唯一的一年。這消息好比晴天霹靂,他只能靜靜地求學以待來年。現在尋求接替李華慶牧師人選的工作以呼籲信的形式展開,上面用委婉的措辭表示很少有人能比前任更優秀。」蘇慧廉1906年離開溫州時,寫下這段當年赴華的因緣。
蘇慧廉相信這是上帝在呼召他,與差會無關,他於是跪下來禱告:「主,我願意去,但除了中國,除了中國!」
為什麼除了中國?「因為傳教士居然到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面前出售一個純粹的理論,這個理論不能給他們帶來現世的利益。」蘇慧廉後來這樣解釋。
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英國人眼裡,中國是片太過陌生的土地。
大約二十五年以前,有一位能幹的牧師,被稱為「神學博士」,因為他多年前曾榮獲這一學位,當他聽到我要去中國,就連忙勸我不要去,如果我一定要當傳教士,那就去日本,因為比起「骯髒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相處令人愉快得多了。
蘇慧廉儘管報了名,但他還在幻想,如果報名不被接納,那他就可以不去中國。他知道還有個志願者也在競爭這個職位,這是他內心的一線希望。但蘇慧廉最後還是被選中了,他終於無路可逃。
儘管這並非我的本願,但這是命運的安排。從那一天起,我就沒有為接受這一命運而後悔過。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沈迦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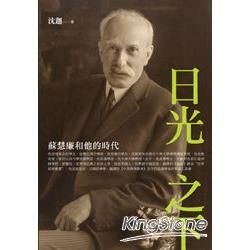 |
$ 521 ~ 594 | 日光之下: 蘇慧廉和他的時代
作者:沈迦 出版社:新銳文創(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12-12-1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10頁 / 16*23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
從十九到二十世紀,有超過二十萬名來自英語國家的青年人,帶著《聖經》及上帝的使命,前往世界各地傳播福音。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這個幾被中國人遺忘的名字,是其中的一員。
本書作者跨越三大洲,沿著傳主百年前走過的道路,尋找歷史深處的蛛絲馬跡。通過爬梳史料,結合數十位後人的口述訪談,並數度前往英倫閱讀教會檔案,歷時六年,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還原了一生都與中國關聯的這位「中國通」的生平。這部傳記既遵循學術規範,又以一嘯百吟的筆觸,寫出了中國近代史的一詠三歎。
作者簡介:
沈迦
1969年出生於浙江溫州。浙江大學文學碩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曾任職溫州日報社,現為上海能近公益基金會理事。著有《文化人換筆》《普通人——甲乙堂收藏劄記》《夏承燾致謝玉岑手劄箋釋》等。
章節試閱
1861年
蘇慧廉是以接棒者的身份於1883年初春來到溫州,因為他的前任李華慶 (Robert Inkerman Exley)病逝了。
蘇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於英格蘭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我後來到英國,才知道哈利法克斯在英人眼中並不是一個好地方。這座城市最有名的可能是以城市名命名的哈利法克斯銀行,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不過在前不久爆發的金融海嘯中飽受重創。
蘇慧廉出生的這一年,中國人稱為辛酉年,也稱咸豐十一年。是年八月,咸豐皇帝病逝於熱河,六歲的同治繼位。他的生母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從此走向權...
蘇慧廉是以接棒者的身份於1883年初春來到溫州,因為他的前任李華慶 (Robert Inkerman Exley)病逝了。
蘇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於英格蘭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我後來到英國,才知道哈利法克斯在英人眼中並不是一個好地方。這座城市最有名的可能是以城市名命名的哈利法克斯銀行,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不過在前不久爆發的金融海嘯中飽受重創。
蘇慧廉出生的這一年,中國人稱為辛酉年,也稱咸豐十一年。是年八月,咸豐皇帝病逝於熱河,六歲的同治繼位。他的生母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從此走向權...
»看全部
作者序
自序: 千萬里,我追尋著你
還很小的時候,我就跟隨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這本書裡將屢屢提到的溫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圓柱,非常醒目。小時聽教堂裡的老人說,大柱子是從英國運來的。於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國人將這些高達十餘米的木頭不遠萬里運到小城溫州?
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那時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溫州日報》做副刊編輯,因工作的關係獲知溫州市圖書館善本書庫裡有兩本外國傳教士撰寫的回憶錄。因是英文寫的,鮮有人知道書裡到底記錄了什麼。1999年底,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報社組織「百年溫州...
還很小的時候,我就跟隨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這本書裡將屢屢提到的溫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圓柱,非常醒目。小時聽教堂裡的老人說,大柱子是從英國運來的。於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國人將這些高達十餘米的木頭不遠萬里運到小城溫州?
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那時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溫州日報》做副刊編輯,因工作的關係獲知溫州市圖書館善本書庫裡有兩本外國傳教士撰寫的回憶錄。因是英文寫的,鮮有人知道書裡到底記錄了什麼。1999年底,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報社組織「百年溫州...
»看全部
目錄
自序:千萬里,我追尋著你
主要人物
小引
第一章 陌生人 (1861-1890)
第一節 溫州城裡的陌生人
第二節 那時溫州
第三節 蘇慧廉來了
第四節 甲申教案
第五節 荒野玫瑰
第六節 第一個十年
第二章 客卿(1891-1900)
第一節 新十年的開端
第二節 回英述職
第三節 楓林迷局
第四節 定理醫院
第五節 戊戌
第六節 世紀之交
第三章 初熟(1901-1906)
第一節 或明或暗的新世紀
第二節 藝文學堂
第三節 開學大典
第四節 女性的天空
第五節 溫州醫事
第六...
主要人物
小引
第一章 陌生人 (1861-1890)
第一節 溫州城裡的陌生人
第二節 那時溫州
第三節 蘇慧廉來了
第四節 甲申教案
第五節 荒野玫瑰
第六節 第一個十年
第二章 客卿(1891-1900)
第一節 新十年的開端
第二節 回英述職
第三節 楓林迷局
第四節 定理醫院
第五節 戊戌
第六節 世紀之交
第三章 初熟(1901-1906)
第一節 或明或暗的新世紀
第二節 藝文學堂
第三節 開學大典
第四節 女性的天空
第五節 溫州醫事
第六...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迦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12-16 ISBN/ISSN:978986591526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0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基督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