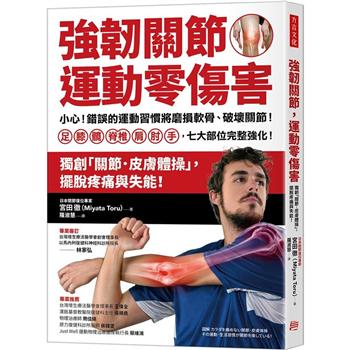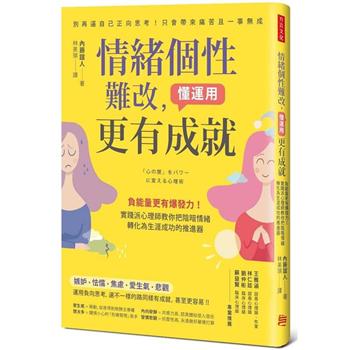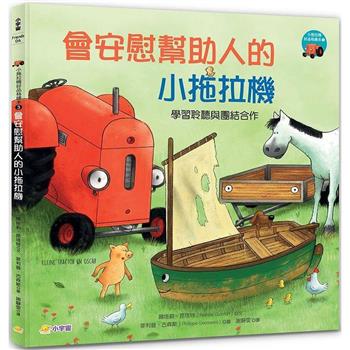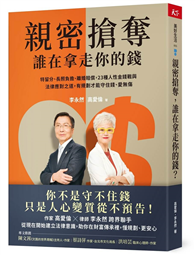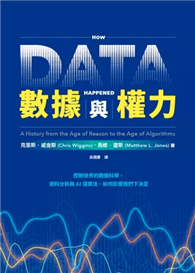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法比歐.史塔西的圖書 |
 |
$ 66 ~ 246 | 卓別林的最後一支舞
作者:法比歐.史塔西(Fabio Stassi) / 譯者:陳澄和 出版社:愛米粒 出版日期:2013-10-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0頁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像劍一般的光芒劃破黑暗。光芒從一個盒子射出,然後擴散,慢慢地在大廳裡劃出兩條完美的對角線……單是這樣已經很有看頭,你可以什麼都不懂地站在那裡看著:煙霧、還有光芒,光裡面盡是塵埃,此外別無它物,微小的粒子懸浮在空氣中,時而升高,時而下降,時而模仿宇宙的萬物,相互追逐、嬉戲……」
故事開始讀到彷彿卓別林徐徐告白的文字,有他鍾愛電影螢幕下人物閃動而生的光影,而他的故事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被記錄下來,與真實人生相互輝映。他已經預告了讀者:「這是為聖誕夜準備的一部滑稽黑白片。是鋸屑、淚水與笑聲世界中的一部浪漫啞劇。」即便故事內容不是喜劇中常見的歡鬧輕鬆情節,這位喜劇泰斗還是希望他的觀眾更或是他的親生兒子,能了解並認識他跌宕又充滿驚奇的「流浪漢」人生。
年輕的卓別林也形容自己就像鐵路,充滿壯志豪雲的氣概,他人無法企及的成功渴望。變動的世代,工業科技日新月異,無聲電影無疑是最新奇的娛樂,而渴望成功的卓別林,再歷經無數的失敗與成功之後,終站上大銀幕的舞台,貼上小鬍子、拿起柺杖、戴著高帽子,扮演衝突性極高又困難詮釋的角色,例如搖身變成一個紳士與乞丐、荒謬與正經、爆笑卻又心酸的角色,那就是他永垂不朽的「流浪漢」形象,使觀眾永遠難忘。
故事開始的發生時間設定於 1971 年的耶誕節,當時卓別林已值八十二高齡,垂垂老矣如他,在洋溢幸福和喜氣的節日裡,竟然見到了死神。原來,死神正準備來帶走他,可是卓別林的小兒子克里斯多夫年紀還小,喜劇泰斗盼望能看著兒子長大,便與死神立下約定:只要他能博得死神一笑,便能多得一年壽命。
把握剩餘存活時間的卓別林,寫出一封封書信給親生兒子,多是人生的冒險遭遇,在馬戲團裡工作的時光,也多有著墨,後來做過不一樣的工作,也有詳細描寫。人生晚年的表演他獻給死神,也奮力 紀錄下人生光景分享給其親兒。卓別林面對死亡雖然深感恐懼,然而他明白生命的價值餘韻留長。
作者簡介
法比歐.史塔西Fabio Stassi
現年五十歲,在羅馬大學 的東方研究圖書館上班,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說,都是在通勤的火車上完成的,曾榮獲義大利許多大獎,並被翻譯成德文和葡萄牙文。「卓別林的最後一支舞」(暫 名)是他第四部長篇,2012年10月義大利正式出版之前,就已在法蘭克福書展引起轟動,共賣出13種語文的翻譯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