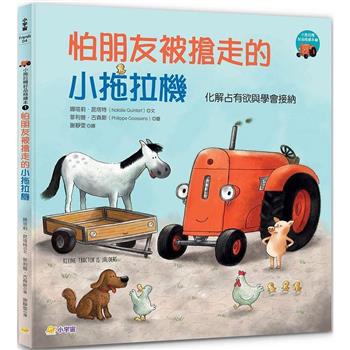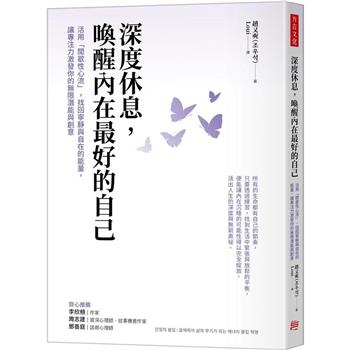暴力不會消失,它只是改變面貌。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暴力的世界裡,即便我們的祖先為了躲避暴力加諸在身體上的痛苦,制定了各式各樣的制度與文化,企圖遏阻暴力的發生與蔓延。然而,這些制度與文化卻又變身成為另外一種暴力形式──或許是肢體對峙的衝突暴力;或許是警察與軍隊的合法暴力;也或許是語言與媒體的隱形暴力。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暴力形式當中,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都在自覺與不自覺的狀況下參與其中,成為暴力的合夥人。
到底什麼是暴力?暴力的樣貌又是如何呈現?本書詳述了暴力發生的各種元素與條件,並為我們揭開暴力不為人知的黑色帷幕。
作者簡介:
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
一九五二年出生,主修社會學、哲學與政治學。任教於德國哥廷根大學,並於該校講授社會學。另一本著作:《恐怖的秩序:集中營》(Die Ordnung des Terrors:Das Konzentrationslager)於一九九三年由S.費雪出版社發行。
譯者簡介:
邱慈貞
台灣苗栗人,輔仁大學德文研究所碩士。喜歡閱讀、戲劇,視翻譯為轉換文字的「另一種再創作」。
譯有長篇偵探小說《集體殺人村》、《別在我心靈上打耳光》、《魔法莉莉:大鬧校園》、《魔法莉莉:烏龍魔法》、《小偵探阿基:足球大賽風雲》等系列兒童書,以及《安徒生日記》(合譯),《世界名船事典》(合譯)與《女情人們》(審訂)。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暴力與人類歷史相始終。本書回顧、細數、分析暴力的發展、樣態和影響,讀來怵目驚心,發人深省。暴力如果是恆久必然的存在,那麼小自個人、社會,大至國際,我們如何才能與暴力「和平」共處,便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課題。──女書店創辦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蘇芊玲暴力遊戲、暴力電影為何總大熱賣?這本書告訴你答案!虐待、刑求、武器、戰爭、大屠殺總在人類史層出不窮,因為暴力來自潛能與文化,是人性天生動力。在殺戮中享受權力與快感,看弱者無助呻吟,戰爭、暴力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人的內心既已為暴力預留天地,此刻,單靠法律與道德不夠,讓我們放開雙手面對暴力,我們的任務不是讓它任意奔流到世上來,而是在心中、在文化、在歷史裡與之奮戰。──資深媒體工作者簡余晏暴力是權力行使中最赤裸也是最極端的形式之一。權力無所不在,暴力也如影隨形,小至個體,大至國家,都不免行使暴力;不只是當下暴力橫行,揆之歷史,無不斑斑在目。如此重大的課題,可惜缺乏深入結構及於普遍面的研究,渥爾剛.索夫斯基的這本書,正是解開暴力的鑰匙,值得一讀。──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暴力是沒有理由的,它不祇存在古代的野蠻時期,也存在現代國家的體制中。暴力切割生命的延續性,使活下來的人喪失信心,無法忘懷恐懼的經驗。所謂根絕刑求。廢止死刑與避免大屠殺,有其本質上的困難,但這也是吾人必須不斷追求的目標。──人權律師、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魏千峯
名人推薦:暴力與人類歷史相始終。本書回顧、細數、分析暴力的發展、樣態和影響,讀來怵目驚心,發人深省。暴力如果是恆久必然的存在,那麼小自個人、社會,大至國際,我們如何才能與暴力「和平」共處,便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課題。──女書店創辦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蘇芊玲暴力遊戲、暴力電影為何總大熱賣?這本書告訴你答案!虐待、刑求、武器、戰爭、大屠殺總在人類史層出不窮,因為暴力來自潛能與文化,是人性天生動力。在殺戮中享受權力與快感,看弱者無助呻吟,戰爭、暴力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人的內心既已為暴力預留天地...
章節試閱
第六章 觀眾
一位早期基督教的奧古斯丁弩斯教父(Augustinus),在他的「告解」中詳細報導了暴力的試煉:那位勉強從「馬戲團表演」的魅力回過神來的朋友兼學生阿里比斯(Alypius),原本到羅馬來研讀法律,也就是在這兒,「他不自覺地,也讓人無法理解地,陷入對古羅馬競技表演的莫名狂熱中。儘管他原本對此抱著排斥和厭惡的態度,但是就在吃飯的時間,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些朋友和同學。這些友人們極力邀請他,雖然他一開始堅決反對並且抗拒,但最後還是屈服在友人們『善意的暴力』之下,一起跟到露天劇場,因為那幾天正好有「殘暴和恐怖」的表演。阿里比斯對朋友說:『就算你們真的把我的人拖去了,但是你們能強迫我的精神和眼睛去看表演嗎?就算我的人真的到場,我也不會看表演,那就表示其實我戰勝了你們和表演。』
他的朋友讓他把話講完後,還是堅持帶他去看表演,因為他們想知道,阿里比斯的決心是不是真的能實現。他們進場找到空位坐下來,就發現整個劇場早已充滿狂暴的歡樂氣氛。阿里比斯閉上眼睛,阻止自己的精神參與這種殘暴的行為。要是他也能把耳朵關上就好了!接下來怎麼樣呢?場內的競技進行時,在場觀眾突然同時發出恐怖的驚叫,把阿里比斯嚇了一跳,使得他被自己的好奇心說服(或者是屈服),告訴自己也許可以把眼睛張開,像個高高在上的主人一樣,冷眼嘲弄這一切。此時他的心靈所受到的傷害比身體的創傷還要嚴重,心中想看的念頭使他抱怨是因為群眾的叫喊使得他這樣做。叫聲穿透他的耳朵,攻破內心的防備。
很可能他那大膽(而不是勇敢)的神識受到衝擊,從原先高高在上的地方掉下來。只要他原先對自己有多自信,那麼他現在就有多軟弱。……因為只要他一看見血,野蠻的渴望就會滲透他,那麼他就再也無法把頭轉開,好像被場面定住一般,接收了憤怒,並且毫不自覺地對這種野蠻的競技感到滿足、陶醉在殘忍的樂趣之中。現在他已經不再是還沒進場之前的那個『他』,而是群眾當中的一份子,他加入群眾,成為帶他來競技場的那些朋友的『真正同伴』!接下來會如何呢?他開始觀賞、尖叫、狂熱,並且還把瘋狂帶回家裡,這種狂熱不僅迫使他下次再與這群『同好』回來競技場,還會讓他化被動為主動,去找尋其他同好。」
儘管抱持著厭惡和抗拒的態度,暴力的狂熱還是佔領阿里比斯這個觀眾的感官、耳朵、眼睛和心靈。因為被群眾的激動所吸引,造成內心防衛的崩潰。血腥的場面引發激動、樂趣和興奮,讓他這個觀眾沈迷在殘暴中。奧古斯丁弩斯教父鉅細靡遺的描述這種改變,真正吸引觀眾的其實並不單單是群眾的叫喊、集體情緒的感染,還包括暴力本身!暴力就像是毒藥一般,奧古斯丁弩斯不是在描述一個無可救藥的性侵害者,阿里比斯不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和沒有個性的年輕人,他不是沒有基本道德觀。他用盡一切力氣想抵擋誘惑,誰知誘惑竟然比他還強大。血腥慶典的狂亂鼓舞了他,使那些道德教條突然瞬間消失。
因為這種改變實在太徹底了,以致於它的影響力直到活動結束後還會繼續存在。這名觀眾回家時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他已經嚐過鮮血,現在他想要再看看更多更多的血腥,就是這種欲望把他再度帶回競技場中。我們不能斷言這種改變只會發生在缺乏文明風俗和不夠穩重的群眾身上,類似的觀眾不只出現在古羅馬競技場,應該說凡是暴力發生的地方,觀眾就離它不遠。在吊死犯人的絞刑台邊、燒死異教徒或女巫的火刑柴堆旁邊、把刺客五馬分屍的廣場上,都可以看見觀眾的身影。
我們可以在重刑犯的牢房門口、憤怒的群眾中、叫囂著要把犯人當眾殺死的人口中,看見「他」(觀眾)的身影;也可以在迫害行動展開後,衝入受害者家裡的一大群民眾當中認出「他」來;還可以在血腥的動物競技或者運動比賽的觀禮台上發現「他」;還有播放恐怖電影的電影院,以及轉播戰爭圖片的電視螢幕前看見「他」。暴力的觀眾不可能絕跡,不論是單獨或者和其他人一起,觀眾就跟他關注的暴力一樣,無所不在。
觀眾都在做什麼?是什麼原因把他帶到事發現場?觀眾出現的原因不能只從個人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他是一種普遍性的角色,他的行為是一種動機明確的集體過程,他的心靈受到事件吸引,他的感官在尋求刺激和轟動的消息。觀眾之間有一種直接的、相互刺激的關係,要想理解他們的態度和反應就不能忽略暴力的影響力。先來談不參與其中的「置身事外者」:他快步地走過事發現場,甚至還把眼睛撇向另一邊。置身事外者不會觀看事件,他只專注於自己要走的路。他不想注意那些「也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不會去參與,而且還會想辦法從內心徹底擺脫這個事件。
我們不能把這種態度錯認為無知,置身事外者絕對不是毫無概念,他很清楚自己應該知道什麼,如果他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他不想知道的。
也就是說,他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他已經不想再深入瞭解什麼了。為了這個目的,置身事外者還準備了許多防護措施。因此他那種保持距離、出於道德立場的冷漠態度,絕對是想當然爾的舉動。不參與事件的冷漠態度必須抵擋吸引力,還要讓感覺遲鈍。他的作法是:讓暴力與他無關,他武裝自己,克制自己,讓自己遠離暴力場面,以便抵擋內心那股不由自主的衝動,去看那些讓人忽視的事物。如何讓自己變得遲鈍又冷漠,並不是先決條件,其實那是「主動去採取的被動態度」的結果。因為所謂的「什麼都不做」、「快速離開」、「撇開目光」等都是一種措施,「置若罔聞,視而不見」其實都是一種行動,只要暴力的力度愈強硬,「把防護網嚴密拉開、把所有外在事物阻隔在視線之外」的防衛措施就愈費力。我們可以試著把置身事外者的愚昧歸咎為歷史變遷,或者當時的社會狀況。
但是態度冷漠其實早就是社會化的原則,(社會)團體化原本就經常意味著距離和隔絕,創造差異、拉起界線並確切分隔。每一個群體都會被一個冷漠的區域包圍,只會偶爾對外展現些微的注意力。對於在此區域定居的外來同胞,內部的權利義務並不適用於他們,他們的命運雖然偶爾引起注意,但是他們仍然屬於另一個「遙遠的世界」,一個沒有人負責的世界。他們只會「短暫地」成為參與、幫助或引發同理心的對象。道德和團結意識只達到這個團體的邊界,那樣可以減少大眾的注意力,然而真正的日常道德並不會完全遵守這種實際又理性的普遍原則,道德只會「認真地」停留在「親近世界」中。別處發生的暴力只要不威脅到自己就與他無關,由此看來,他的冷漠恰好符合共同生活圈的差異和隔絕。
對感受的抗拒加強了群體界線,讓人可以免於羞愧、罪惡和無助。一個什麼都感受不到的人,就可以免於受到良心的譴責。他不需要自責,省掉作為目擊證人的許多不快。一個無視暴力的人,可以克服內心的波濤洶湧,也避免了厭惡和恐懼:例如對於暴力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害怕,對於擔心自己無法抵擋禁忌吸引力的害怕;還有對於鼓舞自己參與其中的邪惡動機的害怕。只要穿上冷漠的盔甲,就可以把侵略和恐懼排除在外。冷漠讓觀眾保持原來的面貌,他快步離開,然後毫無困難的繼續過自己的日子。
他把暴力場面擱在一旁,對他絲毫沒有造成影響,這並不是冷血;置身事外者還沒有達到像「專注的旁觀者」那種冷酷無情,那種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態度,以及對準目標的專注眼神。因為冷血的人不會對任何事情感到震驚,因為他正忙著「全神貫注的觀察」;相反的,冷漠者只在意避開「他不想看見的事物」。他內心早已麻木、遲鈍,並且隨時保持滴水不漏的戒備狀態。任何事情對他來說都一樣,災難對他來說,只是背後的一點聲響罷了。
至於「關心」、或者有時候應該稱之為「好奇」的觀眾就不同了:這種人也不會置身事「內」,但是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消息、謠言、新聞等,他就會趕緊跑到暴力發生地點,他不會抗拒暴力,反而會鎖定暴力作為目標。對他來說這種行為與知識、新知無關,吸引他的是那種不尋常的刺激、恐懼、熱鬧的野蠻演出。那些關心的人想要「適度的」親身體驗一下,他帶著行家的眼光評鑑這場戲:包括這個劊子手的工藝品,那個戰士的武藝。同理心或者同情心對他而言是陌生的,他不會把自己帶入受害者的處境當中,他人的疼痛發生時只會稍微觸動他,他不會感到氣憤,也不會失去理智。
他的身體不會制止他,也不會鼓舞他,他的態度很冷靜,但並不是徹底的冰冷。雖然他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但是一位關心的觀眾並不是完全沒有感覺。他聚精會神地在「看戲」:他四處環顧,還把目光落在其他觀眾身上。他保持一貫自主的眼神,一個不受暴力影響的眼神,他覺得興味盎然,身歷其境,但是並沒有介入事件當中。他還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神經不能控制他,他的感官無法誘導他,「內部」和「外在」處處界線分明。讓他感到激動的是他會採取保留的態度,讓自己與興奮的狂潮保持距離。等到其他人的狂熱褪去之後,那就是他離開的時候。
冷漠可以把事件隔離,至於關心的觀眾則要靠自己的力量與事件隔離。在一群瘋狂的群眾中,他會為自己找尋一個安全的位置,一個可以對抗群眾衝動力量的制高點。因為一個專注的旁觀者,和一個興奮的觀眾之間的距離真的很短,隱藏在面具般冷酷眼神的背後,是一份矛盾、複雜的情感:是身為觀眾的興致勃勃,還有讓人又愛又怕的那種恐怖的樂趣。究竟是什麼樣的吸引力讓旁觀者就算努力控制自己,還是會想盡辦法靠近事發現場?原因絕對不只是單純地對於「與平淡的日常生活不同」所產生的好奇而已;更不會只是感官意識對事件所接收到的趣味而已。
讓觀眾激動的,其實就是暴力。暴力讓人厭惡、讓人害怕、但卻又吸引人也讓人歡愉。受害者的抽搐和叫喊雖然引發短暫的驚駭、短暫的噁心,還有引發對自己生命的擔心,不過這些反應都是輕微的,離全身發抖的恐慌還有很大的距離。受到暴力侵害的並不是觀眾,而是受害者。觀眾一邊感到恐懼,同時也在享受自己的安全感。那種害怕的情緒摻雜了放鬆和滿足,也是一種無懼的幸福。這時候觀眾感受到一種罕見的心靈狀態:他覺得自己很勇敢,能夠和讓人害怕的人一較長短。
恐懼所引發的「樂趣」通常源自於自身的安全狀態,清楚理解自己根本不用與恐懼正面衝突。也因為這個理由,使得受害者和觀眾之間形成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除非觀眾開始同情受害者,對他產生認同,到那個時候他就會失去驕傲的態度和內心的篤定。暴力如此殘忍,刑求如此殘暴,但是對於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言,那都不過是一場戲。他看見的「痛苦」,並不是他自身的痛苦,因為良心不安和道德虧歉而產生的同理心,只會暫時出現,不過我們不能把這種態度與同情相混淆。同情心乃從「所有的人都是平等,都應該給予幫助」的觀點出發,這種認知對一位旁觀者來說,可說是前所未聞的。通常觀眾會偏愛行為者(施暴者),因為吸引觀眾的是行為,而不是受害者的痛苦。
觀眾淺薄的同理心與對行為者的欽佩(對於他強大的力量、強勢的主導態度)相重疊。旁觀者感受到自己那種「想要與行為者分享強大力量」的渴望,他讚嘆行為者製造的痛苦,因為旁觀者沒有權力去做。不過,雖然他如此尊崇暴力,但是他的恐懼並沒有完全褪去,暴力很可能突如其來地發生在圍觀者身上:只要行為者一個轉身、一個眼神、一個引人注意的叫喊、一個劈砍,都可能讓暴力瞬間在群眾中發酵。因為觀眾發現暴力越界了,所以他的恐懼更不可能消除了。於是他陷入恐懼、樂趣、吸引力所糾結的內心掙扎中,只有接下來群眾的瘋狂才能解救他。
情緒亢奮的觀眾沒有餘力理會一個旁觀者內心的矛盾,他不斷鼓掌、往前衝,還不斷鼓譟。他對暴力歡呼,假如行為者表現的稍微遲疑,觀眾就會為他打氣,要求他為觀眾呈獻殘暴的折磨手段。這時候觀眾不再只是「遠觀」的群眾,而是盡可能地「置身事內」。他們緊緊圍住競技場,不願意放過任何細節。行為者的熱情似乎已經傳達到觀眾身上,一開始還站在一旁與殺戮的吸引力,以及自己的抗拒互相拉鋸的人,這時候顯然已經陷入暴力的「暴風圈」。驚訝與驚嚇都已經消失無蹤,害羞變成歡呼、意猶未盡的亢奮,進而轉化成親身參與的動力。
「看別人受苦很有趣,讓別人受苦,樂趣更高!」群眾的歡呼聲不僅針對血腥的表演,也針對內心矛盾的化解。在快樂沖昏頭的狀態下,觀眾的心理終於找到了空間,他心中的恐懼好像被抹去了一般。受害者痛苦的哀嚎被群眾的歡呼和吼叫聲掩蓋過去,觀眾在徹底認同行為者的過程中,戰勝了內心的恐懼;在忘我的投入中,戰勝了自己。群眾的亢奮不止回饋了暴力,也解放了內心那股擋不住的力量,以及對恐懼的經驗。觀眾之所以要求暴力,要求恐懼死亡,其實目的就是要享受最後戰勝一切(戰勝恐懼)的快樂。他們用超越自我界線、以及自我態度的轉變來展現對暴力的尊重。
所謂的狂歡絕不能容許任何失望,吸引力和亢奮需要不斷的、新的養分,以免讓人再度陷入矛盾的心態當中。觀眾要求看到新的刑求手段和新的受害者,要見到大量湧出的鮮血,場上沒有一個戰士可以免除一死,殺戮的慶典需要的是殘暴。假如受害者太早「掛了」,或者直接下跪求饒,那麼觀眾就會反感、抱怨,甚至鄙視他。激動的觀眾會開始揶揄、辱罵、叫囂,並且要求把受害者的頭砍下來。還有,假如上演的「戲碼」出現重複,觀眾也會大聲要求換新。他們不能忍受一點冷場或者沈悶,否則就會強烈抗議。
羅馬哲學家塞內加(Seneca,譯註:西元前四年至西元前六十五年,羅馬斯多噶派哲學家和政治家,為一世紀最卓越的思想家和作家。)在寫給盧齊利馬斯(Lucilius,譯註:西元前一百八十年至西元前一百零二年,羅馬斯多噶派哲學家與諷刺作家。)的第七封信中(第一份公開批評古羅馬戰士競技機構的文獻),如此描述著:「我似乎陷入一種午間的恍惚,竟然對樂趣、玩笑和放鬆產生期待,想藉由看見別人流血讓自己的眼睛消除疲勞。結果正好相反:先前所有的戲弄與挑釁都還算是一種慈悲,現在喜劇結束了,接著上演的是一場典型的謀殺。
那些人手無寸鐵,沒有絲毫自衛能力,只能用身體去承受外力的打擊,徒手向敵人戳去──絕大部分的競技戰士都「喜歡」採取這種方式。他們怎麼能不「喜歡」這種方式呢?他們根本沒有頭盔、盾牌可以抵擋武器。為什麼需要鎧甲?為什麼需要擊劍技術?這些東西只會延緩死亡發生而已。大清早就先把人丟給獅子和熊進行廝殺,到了中午再把人丟給他的觀眾。善戰好殺者就找實力接近的人與他對抗,不過勝利的一方沒有辦法享受接下來的血腥屠殺。
整場競技最後會在戰士死亡後結束,群眾拿著火把和刀劍進場,這個過程會在休息時間發生。『有些人根本就是在幹搶劫殺人的勾當。』那又怎樣呢?死掉的人本來就是殺人犯,所以這是他應得的報應。至於你這個一旁的可憐人又得到什麼呢?『殺害、踢打、火焚!為什麼他那麼害怕鋒利的刀劍呢?為什麼他殺人的手法那麼溫和呢?為什麼他那麼不情願赴死呢?群眾好似一條鞭子,揮向他的傷口,他應該用順從的胸膛承受所有的鞭打和劍擊才對呀!』但是有人把我的想像打斷了:『據說有人把死者的喉嚨割斷了,好讓現場能夠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必須從當時的氣氛來解讀這段插曲,對群眾的罪惡、野蠻的遊戲,以及好殺的行為提出警告。它點出旁觀者的震驚、以行家自居的自負,以及對大多數群眾原始本能的輕視。這些「有水準的人」想看到的是戰鬥中的「靈魂原則」:擊劍技術和競技運動的緊張刺激,而不是野蠻的屠殺。他是來享受和聊天的,他要體會的是那種輕微的顫抖和害怕,並不是要陶醉在殺人的行為當中。他期待的是沒有威脅的決鬥,並且還要能從中發現殘暴的樂趣。這些「有水準的人」既冷靜又小心,他知道保護自己,知道如何壓制罪惡感,也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
他從來不會暴怒,外在衝擊只會擦傷他的表皮而已。對他來說,感官上受到的驚訝並非狂熱,還在高度判斷力的掌控範圍內。至於其他群眾只認得直接的感官刺激,他們對血腥的喜好無法平息,旁觀者以理智築起來的防衛範圍,早就被處於狂熱情緒中的群眾拋諸腦後。亢奮讓群眾遠離持續增強的恐懼,他們的情感得到澄清,也讓他們從對立矛盾的感覺中得到解脫。群眾併吞個人,個人也融入群眾的行動中。我們必須詳細解釋這種融合的過程,不能把它與文化批評所認定的「平均主義者」(Vermassung)相提並論。這段融合的過程與認同或適應無涉,也與個人的神聖結局(死亡)無關。
雖然過程只是針對暴力的「演出場景」,但是觀眾的融合卻十分深入,直達每個人的皮膚和毛髮,以及身體和靈魂。群眾的集體情緒是一股自動的力量,一個獨立不可抵擋的力量,它侵入人體,讓人毫無察覺就順從於它,變成一種個人既有的態度。一開始觀眾還會集體行動,一聽到消息之後,他們立刻從四面八方、各個角落跑來。消息宛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不需要任何人的號令,幾分鐘之內,他們就擠滿廣場。原先只有屈指可數的群眾,接著變成幾十個人,然後變成好幾百人。
凡是正好在附近的,全部都趕過來了。要是事先知道詳細時間的人,也會不辭辛苦的長途跋涉,期望能及時趕到事發現場。探討這些觀眾的出身背景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們聚集在斷頭台台下或者競技場中,每個人都可以來看熱鬧,這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無關,決定權在於誰剛好碰上這個天大的偶發事件。暴力已經在等待大家了,死亡與每個人都有關,人人都想看到暴力和死亡。這些觀眾是一個暫時性的匿名社會群體,只是偶然與吸引注意力的事件相連結,這個社會群體只是透過暴力表演而存在,暴力製造了它的觀眾,成了觀眾中的焦點。
這些觀眾當中並沒有領導人,也不是接到什麼命令,更沒有人指揮他們的行動。巷子和門廊到處都是嘈雜的叫喊,態度遲疑者還會被人要求一同前往。很多人還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什麼事,就開始拔腿狂奔;也有些人一開始還猶豫不決,但最後還是加入人潮。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這些看熱鬧的人群推向事發地點,一股獨特的吸引力鼓動了人群,讓他們互相跟從。彼此相互感染(模仿)的過程讓人克服了個人心中的保留態度和防備心,他們之所以跑過來,是因為其他人也同樣往這裡跑。
比較重要的是,一定有什麼稀奇的事情要發生,就在那裡,就是人潮要去的地方,這個熱鬧一定不可以錯過!引發並增強這種吸引力的只是數字,一種多數的力量。參與的人愈多,它的吸引力就愈大;同樣的,只要吸引力愈大,來的人數也就會愈多。沒有人願意錯過好戲,人人都想要到場,於是每個人都在引誘另一個人,吸引他們也到現場去。這個行動不需要決定,也不需要考慮,多數群眾的吸引力已經在潛意識生效,每個人都想一同去暴力之地。
觀眾到達事發地點之後就會各自分散,如果那裡規劃了座位和號碼,那麼群眾還會遵守秩序規範。如果空間非常狹小,就會發生推擠,就會擠得水洩不通。聚集的人愈多,人數爆滿的時間愈快。群眾開始為了包廂位置而發生爭執,好奇心最強的人開始往前擠,用手肘把擋在路上的人撞開,並且制止後面的人繼續擠過來;其他人開始靠攏,擋在前面,以確保得到較好的視野。親臨現場是他們所有的目的,但是臨場感也只有在愈靠近暴力的地方才有辦法感受。於是人群中出現鬥毆、競爭、對抗。
他們只是想要看見被押往刑場的人犯,盡可能親身感受到斷頭台的刀片落在人犯頭上那種震撼。行刑還沒開始,氣氛就已經高漲,緊張情緒升高,觀眾不耐煩的等待行刑。慢慢地,所有人都想爭取最好的位置,觀眾開始推擠,他們肩並肩站著往前眺望。群眾都在尋求一種「身體上的親近」──一種集體的擁擠親密感。雖然互不認識,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存在,每個人都想跟別人一樣,跟其他全部的人一樣。人類與他人保持距離的習慣,在這個時候突然被破壞,大家緊貼在一起,變成一種莫名的親密感。
社會結構中彼此區隔的角色和階級,領域、財產和命運,已經在群體中消失。這種親密從個人的存在壓力(社會壓力)、對個人的壓迫和恐懼中解脫出來。群眾之間的差異被弭平了,同時也減輕個人的罪惡和羞愧感。這時候人人都是一樣的,別人跟他本人一樣,與自己同樣貼近。我們不應該低估這種平等狀態的狂熱,這種狂熱與相互感染和影響無關。這種融合有一個明確的肢體觀點,這種貼近感很重要,在一般的社會交流中很少發生。群眾的顫動和動力直接傳導到身體反應,他們用盡全身的力量大聲叫喊、伸長脖子、高舉雙臂,並且渾身發熱,歡呼聲讓他從座位上跳起來,他發出前所未有的叫聲,與橫掃競技場的的聲音風暴合而為一。
有些人已經感覺自己突然身處「快樂合唱團」,從座位上再度站起來,根本沒發現自己到底為何會變成其中一員?群眾的行為牽動個人,讓人達到忘我的境界。身體的界線似乎消除了,自我已經瓦解,激動的節奏、情緒的起伏、期待的不安、釋放後的爆發,全都深入身體的每個毛細孔,這種身體上的改變經常被忽視。有人說這時候群眾關閉了理智和良知,啟動了原始的本能。這種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群眾的力量包含感覺和感受,狂亂讓他忘了自己,他貪婪地接收變換的氣氛,跟別人一樣喊叫,如果有人喊著報復,他也高聲喊著復仇;假如因為鼓掌而滿場沸騰,他也會為英雄行徑鼓掌。
他自己就是群眾,就是控制整個氣氛的情緒。就在他與團體一起行動的時候,他也造就了集體情緒的力量。他做別人做的事,讓自己跟其他人一樣;藉由感受和發現其他人的感受與發現,讓他融入其他人當中。這時候,孤單已經離他而去,他不再是那個他,他已經忘了自己是什麼樣子了。他樂意讓自己被群眾併吞,這樣他就可以不必做自己,群眾把他這個「個人」從自我當中解放出來。觀眾會影響暴力的進展,他們觀看並評論行為者,有時候群眾的目光還會讓行為者感到不安。不過他並不需要害怕,因為群眾並不是可能起訴他,並且與他為敵的目擊證人。
就算是默默待在一邊興致濃厚的旁觀者,也都是偷偷站在行為者那一邊的。他不會阻止行為者,也不會阻擋他的路,既不會反對,也不會抗議。
旁觀者任由暴力發展,他的沈默好像無言的認證。關於同意和反對之間有一個絕對的差異:反對需要一個明確的聲明、清楚的表達,但是贊同就不需要。因此,沈默就是一種同意,沈默的多數確保了暴力的領域,只要觀眾無言的站在一旁,施暴者就可以不受影響繼續行動,他不需害怕任何侵犯,受害者也不能奢望任何幫助。
只要群眾當中發生一些風吹草動,對暴力而言就是一種新的動力。行為者和觀眾彼此都很興奮,群眾的鼓掌鼓勵了行為者、煽動他,鞭策他繼續向前。假如他缺少活力,不夠專注或殘暴,就立刻會被譏諷和輕視。然而,掌聲和叫喊引發殘暴,接下來的惡行也會升高群眾的狂熱。亂喊的群眾本身就是破壞勢力,也就是說,暴力創造了它的觀眾,而觀眾同時也製造了新的暴力。現在施暴者好比觀眾的代言人,他只做觀眾希望他做的事,他向觀眾展示,讓觀眾知道,可以要求他做什麼。因此暴力變成一種想法,變成一種表演,讓觀眾從中認出自己的倒影:行為者就像觀眾,觀眾也跟他一樣。
行為者具體實現了觀眾的願望,執行觀眾的指令,現在真正的劊子手不再是他,而是觀眾。觀眾認同行為者,因為他做的事是觀眾不敢做的,他擁有觀眾渴望的所有力量,他成了委託他、鼓勵他的觀眾的一部分,他們把他從群體當中分離出來,又再度接納他,還把他看成偶像。觀眾在他身上發現自己,他成了混亂團體中的重點,成了觀眾力量、以及征服意志的根源。觀眾在暴力中慶祝戰勝自己的勝利,而他們的要求往往超越實際的殘忍,因為群眾只是在事件旁邊圍觀,所以他們比自己親自下手執行血腥行為還要極端,其心態就好比膽小的人偏偏又愛大叫,出風頭一樣。
有些觀眾根本按捺不住,他們想要一起動手,假如馬路上沒有封鎖線的話,他們會往前衝,擠進競技場中,抓起木條動手打人。群眾的這種行動把施暴者和觀眾一起帶入不受拘束的自由領域,行動和觀眾之間的分界線已經被拆除了。通常觀眾會和勝利者站在同一邊,為勝利者歡呼和鼓掌,從他身上進而崇拜起自己。勝利者得到象徵勝利的棕櫚葉,得到獎金和皇冠。至於那位倒下的戰鬥者,雖然他丟棄盾牌伸出左手的一隻手指請求寬恕,卻得不到仁慈對待。觀眾鄙視一個貪生怕死之徒,挨打的人無法博得同情,他只會招惹怒氣和憤恨。
勝利的最高權力會如何看待一個搖尾乞憐的膽小鬼呢?這個人只會玷污觀眾好不容易得到的勝利;他只會提醒我們對死亡的畏懼,這可是觀眾才剛克服的恐懼,這時候無助感只會召來反效果。倒下的人就應該被打,被刑求,被殺──這就是群眾當作判決基礎的野蠻原則。失敗的人會被排擠,從人類世界除名,他應該永遠消失才對。穿著跟商業神墨丘利(Merkur),或者地獄擺渡人加隆(Charon)同樣長袍的運屍工人,他們的任務是把死人抬出場外。他們先用炙熱的鐵塊檢查那些「死人」是不是還有生命跡象,如果有人還在做垂死掙扎,那麼他們就會讓他徹底死去。假如有人撐過這場致命的戰鬥,展現了勇敢和鬥志,就會得到尊敬,甚至佩服,群眾對這種人會大方地讓他活下來。
在古羅馬競技場時代有一種有名的風俗──戰鬥最後由觀眾來做死刑判決。雖然形式上的判決權握在觀眾中的最高階級──羅馬皇帝手中,拇指豎起意味著「生」,拇指往下意味著「死」,但是競技場中的決定主導權其實不是皇帝,而是觀眾,因為沒有一位君主敢公開反對群眾的意見,他一定會認真的注意揮動的手帕,聆聽眾人的呼叫以及最大聲的叫喊。最後,群眾做出關於生或死的判決,觀眾既是法官也是劊子手。他們決定命運、允諾仁慈、並且指揮暴力的最後一個行動。
第六章 觀眾一位早期基督教的奧古斯丁弩斯教父(Augustinus),在他的「告解」中詳細報導了暴力的試煉:那位勉強從「馬戲團表演」的魅力回過神來的朋友兼學生阿里比斯(Alypius),原本到羅馬來研讀法律,也就是在這兒,「他不自覺地,也讓人無法理解地,陷入對古羅馬競技表演的莫名狂熱中。儘管他原本對此抱著排斥和厭惡的態度,但是就在吃飯的時間,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些朋友和同學。這些友人們極力邀請他,雖然他一開始堅決反對並且抗拒,但最後還是屈服在友人們『善意的暴力』之下,一起跟到露天劇場,因為那幾天正好有「殘暴和恐怖...
目錄
第一章 秩序與暴力
第二章 武器
第三章 暴力與激情
第四章 暴力、害怕與疼痛
第五章 刑求
第六章 觀眾
第七章 處決
第八章 戰鬥
第九章 圍捕與逃亡
第十章 大屠殺
第十一章 物的破壞
第十二章 文化與暴力
跋──謝辭
第一章 秩序與暴力
第二章 武器
第三章 暴力與激情
第四章 暴力、害怕與疼痛
第五章 刑求
第六章 觀眾
第七章 處決
第八章 戰鬥
第九章 圍捕與逃亡
第十章 大屠殺
第十一章 物的破壞
第十二章 文化與暴力
跋──謝辭

 共
共  索夫是法國加爾省的一個市鎮,位於該省西部,屬於勒維岡區。該市鎮總面積31.56平方公里,2009年時的人口為1880人。
索夫是法國加爾省的一個市鎮,位於該省西部,屬於勒維岡區。該市鎮總面積31.56平方公里,2009年時的人口為18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