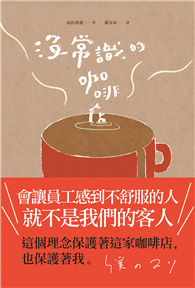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溧灡的圖書 |
 |
$ 196 ~ 252 | 傀儡戲法【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溧灡 出版社: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0-25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傀儡戲法
「我不過是自己的傀儡,永世不滅。所以,我可以陪你,直到你不要我⋯⋯」
傀儡師蘇聆音在海岸徘徊,日復一日,都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
終有一日,在起伏浪濤中遇到古老神祕的鮫人—美麗而強大的安泠,他對自己有著異常執著,訴說那些被遺忘的過往愛語,卻得不到回應。
出於利用,蘇聆音用身體交換了一年為期的契約,他想算計安泠,卻沒想過會先付出巨大代價。
波光粼粼中,一次次歡愛讓這場契約變質了,自詡冷靜的蘇聆音面對安泠的強勢獨占,甚至是挖心明志的覺悟逐漸動搖,而此時傀儡師家族爭權的陰毒內幕,別有所圖的算計聯姻,比洶湧大海更加不可測的暗潮,終將在兩人之間埋下未知的命運分歧⋯⋯
前世今生的糾纏與詛咒,只希望最終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作者介紹
溧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