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海耶克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最顯著的特徵是:知識貴族的精神。他的身教與言教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在尚未進入這個過程之前,當然有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追求知識(或曰追求真理)是艱難的。在這個過程中,你如不認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求知識嗎?追求知識有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用英文來講,可以intellectual autonomy來表達。這種知性活動不受外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勢力的干擾,也不會為了趕時髦而從事這種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有所發現,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誤解、曲解,也只能堅持下去。這裏也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堅持下去的問題。
這種在知識領域之內追求知識的人,如果獲得了重大的、原創的發現,他當然深感知性的喜悅,卻不會產生恃才傲物、自鳴得意的心態。因為他是在追求知識,不是在追求虛榮;何況知識邊疆的擴展,使他面對的是知識邊疆以外的無知領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築在別人的努力所積累的知識之上,即使他的最具原創性的發現──例如,他發現(在法治之下的)市場經濟是產生、保存、協調、流通與增益知識的最佳機制──也間接與他的師承有關,與奧國學派經濟學和蘇格蘭啟蒙傳統有關;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歸屬。1999年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舉辦的紀念海耶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系列演講會上,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Gary Becker先生曾說:僅就哈氏在經濟學領域之內的貢獻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寫過那一篇發表此一重大發現的論文,就足以稱謂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那篇論文是於1945年9月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譯作“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著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 1948﹞。)
另外,他永遠是以開放的心靈、知性的好奇心,面對別人的意見,樂意接受別人對他的啟發(如上世紀50年代,他的思想頗受博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識論的影響,便是顯例)。對於別人的批評,他當作是刺激他反思他的思想的材料。對於別人的誤解,甚至惡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別人在知識上的盲點,所以無從產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帶給他知性的喜悅,卻不會產生知性的傲慢,當然也與孤芳自賞之類的偏狹心態無涉。海耶克先生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發現,另一方面卻又以開放的心靈面對別人的不同意見;此種“堅持”與“開放”,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因為一切是以忠於知性的追尋為準。
這種遵循理知的召喚與指引的人格素質,展示着——用韋伯的話來說──知識貴族的精神。知識貴族,不是甚麼社會貴族,也不是經濟貴族。知識貴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數人做得到的──在“諸神戰爭”的現代性文化中,始終堅持忠於知性神明而無懼於其他神祇的精神。
海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殷海光先生語)。不過,凡是跟他長期接觸過的人都會感覺到,他實際上是一個內心熾熱,具有強烈道德感的人。當他談到自由的意義,以及自由被誤解的時候,雖然語調仍然嚴謹,但常常會血脈賁張,臉龐通紅。然而,他卻那樣習於自律,而且做得那樣自然,那樣毫不矯揉造作。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他這樣的風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養,雖然在道德上他確是一位謙謙君子,而是強烈的知性生活的結果。知識是他的終極價值,追求知識賦予他生命的意義。這樣發自內心的知性追尋,把作為一種志業的學術活動提升到具有高貴和尊嚴的生命層次。
由於西方現代社會和文化已經出現了深刻的危機,產生了種種價值的混淆,這種精神在許多西方學者和知識分子身上已經很難見到了。
殷海光先生的身教與言教的最顯著的特徵則是: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同胞的苦難與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已。他會盡一己之力以言論介入公共事務,希望能夠指出在公共領域之內的諸多問題的解救之道。這種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極、不氣餒、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靜思,也不玩世不恭(那樣的表現當然也有;不過,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另外一個殷先生的精神特徵是:在政治權力與社會及經濟勢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獨立與真誠。這種公共領域之內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資源。
不過,在他的心靈中,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產生了轉化,因為他畢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洗禮。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籬(家族、地方、學校、黨派、種族、國家)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個人主義的特質。(這裏所指謂的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體主義而言。它是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與“安那其”〔anarchistic,無政府〕個人主義不同。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並不反對國家的存在,毋寧主張國家需要存在與發展,國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陳獨秀在1914年所說,“保障權利,共謀幸福”。)
殷海光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他卻反對“本能的愛國主義”。他的早年性格中確有狂飆的一面,但卻歸宗於真正具有獨立性的自律。正因為他的關懷具有超越性,所以他更能使它落實到具有普遍意義的,不可取代、不可化約的個人價值(th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與個人(每個人)的尊嚴與發展之上。(這裏所說的個人價值,不是英文中的“value”,而是“worth”。中文在這方面,不夠細緻,不夠分殊,所以“worth”和“value”都只能用“價值”兩字譯出。因此,我在這裏談到殷先生所堅持的個人價值時,需要用“不可取代、不可化約”來說明它的特殊意義。)
林毓生
導讀
一紙風行
1944年3月和9月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聲名大噪,也同時令他聲名狼藉。
這本書讓海耶克聲名大噪,是因為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總編輯Bruce Caldwell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35萬冊以上。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一大原因是此書美國版出版後不久,美國的《讀者文摘》即決定把它的摘要轉載,並且替其書會出版和發行摘要的單行本。Caldwell表示,《讀者文摘》當時的發行量約在875萬冊左右,因此據估計《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單行本最終印行了超過100萬份。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論雖然很具爭議,但它的主張在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營一致的重視,致使海耶克的這本書洛陽紙貴,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海耶克最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就華語世界而言,戰後台灣,在海耶克的首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1953年便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他選譯的《到奴役之路》。中國大陸對海耶克的著作也很重視。本書譯者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在1958年便翻譯了海耶克早期的純經濟學著作《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務印書館在1962年也出版了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為內部發行而翻譯的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說這本書使海耶克聲名大噪,我想是絕不為過。畢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不過,這本書同時也使海耶克在一些學術圈子內變得聲名狼藉。
海耶克在撰寫這本書時,大概也有類似的顧慮。在原書的前言中,海耶克一開始便說他有責任解釋清楚,為何作為一個專業經濟學者的他,要寫這本很具爭議的政治書。海耶克的解釋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似乎作用不大,因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海耶克放棄了嚴謹的經濟科學的研究,不務正業地去當政治評論員。一些經濟學者甚至認為,海耶克由於在1930年代跟主導經濟學的凱恩斯在相關的經濟理論辯論中敗陣,因此轉而投身到經濟學領域以外的地方去。不管如何,在戰後當海耶克希望離開他任教多年的倫敦政經學院,轉投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時,即是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多方努力下,芝大的經濟系都不聘用海耶克。最終他只能加入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
在經濟學界以外,一些重要的學者對海耶克這部書也不以為然。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1945年在閱讀《通向奴役之路》時,以“可怕”(awful) 來形容海耶克。哲學家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當時寫信給海耶克的好友波普爾(Karl Popper)時,引用左派人士所說的“反動”(reactionary)來形容海耶克的觀點。政治學者Herman Finer更撰寫了一本《通向反動的道路》(The Road to Reaction)來反駁海耶克。
不過,今天離《通向奴役之路》首次出版已70多年了,人們看來還在繼續閱讀和出版這本書,繼續研究海耶克的思想。究竟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劃時代的意義
讀者如果單是細讀《通向奴役之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海耶克對極權政治鞭辟入裏的批評。海耶克在這本書中,很希望澄清當時他認為的兩大流行的誤解。首先就是西方知識界普遍以為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沒落時的極端反撲,其政治性質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南轅北轍的。其次,不少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體下,政府通過理性規劃來節制自由市場的“盲動”以達致社會公義的結果是既可取又可行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它剛發表的那個時代,其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試圖糾正上述這兩大流行的誤解。
海耶克對當時這兩個流行的“誤解”有強烈的看法,是和他在20世紀頭四十年前後在歐洲的德語社會和英語社會長期生活和研究比較有關的。1931年以前,年輕的海耶克主要在說德語的維也納生活、讀書和工作,並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役,學術上則主要承繼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自由市場和主觀價值理論。他在成長時有一段時間曾經受到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所吸引,但他看到不少原先是服膺社會主義思想的德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一戰敗戰後逐步走上擁抱納粹主義及其極權手段的道路。他們開始醒覺到,儘管在納粹德國興起前社會主義黨人和納粹黨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不斷,但他們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如果推到其根本處,是極其相似的會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
因此,當他在1931年移居英國到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後,對英國溫和社會主義者普遍認為納粹主義的興起,是經濟大蕭條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窮途末路式的極端反撲這一類觀點大不以為然。海耶克認為,西歐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如果頭腦清醒地作出反省的話,理應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政府管控市場和進行中央規劃的主張,如果要有效而徹底推行的話,免不了要在政治上實施種種侵害個人自由的舉措,最終和納粹德國一樣走上全權統治的道路。海耶克相信,英國的工黨和社會民主派缺乏這種認識和體會,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自己年青時在德語世界的經歷,另一方面也因為英國的自由和法治傳統很強大,使這些左傾思想的人士誤以為就是加強政府管控也不礙事。加上二戰期間,戰爭的動員需要已使大家對政府集中規劃習以為常,海耶克因此覺得更有必要對此“誤解”進行批判。
把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連結起來,海耶克的用意其實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和所推行的暴政,如果簡單地把責任完全歸結到德國人的民族性或納粹主義身上,那便是無視了德國文化同屬是歐洲的共同文化的一部分這一事實,也忽視了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會產生極權的可能。海耶克在撰寫《通向奴役之路》時,已預期盟軍最終將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因此,如何在戰後的秩序重建中,面對根本而真正造成極權暴政的因由,更好地認識、重塑和維護自由文明所賴以茁壯的思想資源和相關的制度傳統等,便是頭等重要的事。釐清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關係和澄清上述的“誤解”,正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一大任務。
在學理上論說清楚為何維護個人自由跟維護自發的社會秩序是分不開的,以及為何不應該盲目迷信理性萬能,以為理性規劃的制度必然可以取代,或優於社會上自發的調協制度(如市場、普通法、道德習俗等),正是海耶克澄清上述“誤解”的依據。他認為依靠政府干預市場以達致某種通過一些抽象推理預先假定的平等或公義結果,不但會破壞人類長期自發互動中累積下來的社會協調機制,更會直接干犯個人自由。在現代複雜的社會中,由於對社會互動協調的知識是散落分佈在社會不同角落的個人身上的,因此在缺乏例如自由價格這類自發形成的機制的情況下,中央式的理性規劃根本不可能盡知相關而瞬息萬變的資訊,至使干預往往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使當權者為求目的,不斷加強干預的力度和範圍,一步步迫近全權的暴政。這便是海耶克為甚麼不同意經濟平等可以和政治自由共容,並在《通向奴役之路》對英國工黨及其理論領袖拉斯基(Harold Laski)當時提出的工業國有化主張不斷作出批評的理由。
換言之,《通向奴役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視和引起廣泛的爭議,在當時是因為海耶克尖銳地對進步知識界達成的一些重大共識提出了異議。而這本書和海耶克的思想至今仍舊在學界和知識界備受關注,是因為海耶克的立論根據,其實是針對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高度推崇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作根本性的批評,認為唯理主義錯誤的以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到所有人類的認知範疇之上,盲目相信理性設計本身在方方面面都優於傳統智慧或實踐經驗的累積,任何不合理性標準或理性不及的東西都是比理性低劣的事物,理應被理性淘汰。海耶克相信,現代的唯理主義是對理性的濫用。這種濫用並不單局限在例如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政治意識形態上,而是廣泛地存在於近現代歐洲文明的某些強大的思想資源之中,不斷地挑戰着歐洲文明中的自由傳統。因此,對海耶克思想的關注超越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空,也超越了冷戰的年代,因為他的理論、批判和對理性、自由等根本問題的反省,對歐洲文明和現代性到了今天還是有相關的意義,其立場觀點仍舊有啟發性,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現在還在閱讀和討論他的著作。
《通向奴役之路》是海耶克第一本非專業經濟學的著作。我們與其說他從此放棄了嚴謹的經濟學分析,不務正業地從事政治評論,不如說《通向奴役之路》標誌着海耶克突破經濟學的局限,認識到要充分、深入而全面了解社會的種種秩序和現代人的處境,稱職的思想家必須同時要進入政治學、法理學、思想史、哲學心理學、方法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作出跨學科的研究。在此以後,海耶克在這些方面先後發表的一流著作,確立了他成為其中一位20世紀西方思想大家的地位。從今天這個角度看來,《通向奴役之路》使海耶克聲名大噪,遠多於聲名狼藉了。
海耶克與中國自由主義
海耶克的思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些方面發揮着關鍵的影響。近年這一點愈來愈受到華文學界的關注。周德偉、夏道平、殷海光都是在上世紀50–80年代的台灣,通過譯作和著作,有力地推介海耶克思想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林毓生同時是殷海光和海耶克的學生,在周、夏、殷這一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基礎上,於70年代、80年代,以至現在,進一步深化和推動海耶克服膺的古典自由主義如何與中國傳統開展對話,希望通過“創造性轉化”的方式,把中國傳統中可以和值得改造或重組的東西,變成有利的文化資源,使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和制度,可以在中華文化的環境下生根成長。
自從清末嚴復等開始引進西方的自由思想到中國來之後,中國自由主義雖然一直受到來自傳統的衛道思想和來自社會主義式的革命思想的雙重夾擊,但通過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胡適等人的努力,一直以來還算得上是五四運動之後,在中國思想界中一股重要的思潮。但到了1949年之後,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大陸有三十年可以說是踟躕不前。在這段期間,通過海耶克思想對台灣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使中國大陸的思想界在到了改革開放政策出現之後,從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那裏再次有機會承傳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命脈。
我看到最早以一整篇的篇幅來討論海耶克對中國自由主義影響的論文,是1992年熊自健發表的〈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觀熊自健這篇文章認為,海耶克對殷、夏、周幾位台灣自由主義者在思想方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海耶克的自由經濟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台灣自由主義者以為“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可以同時並存的看法。第二,通過海耶克在《自由的憲章》等鉅著的分析,台灣自由主義者大大加強了對自由的價值、自由條件的保持、自由與法治的關係等認識。第三,通過海耶克對真偽個人主義的辨識和對自由主義倫理基礎的探索,台灣自由主義者開始毫不含糊地提出“把人當人”這種“康正的個人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根據。
張世保在〈“拉斯基”還是“海耶克”?──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激進與保守〉,以及林建剛在〈從拉斯基到海耶克:胡適思想變遷中的西學〉中以一些具體的例子,進一步闡述了中國自由主義者如何從戰前服膺同樣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的拉斯基的社會民主派的“經濟平等”主張,轉而到在戰後接受了與拉斯基針鋒相對的海耶克的“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是不能並立的論述。張世保的文章也指出了因為受了海耶克的文明演化思想的感染,中國自由主義者從反中國文化的激進立場,轉而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本身,為中國自由主義在這方面促成了一大轉向。
海耶克的理論除了影響到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作出思想上的改變之外,到了80–90年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陸知識分子身上,海耶克這本《通向奴役之路》,帶來的卻是印證了預言般的震撼。
目前在中國大陸思想界很活躍的秋風進一步提到在這方面海耶克理論的雙重意義。首先,海耶克基於有限理性的英式自由思想,開展出對文明演化的解釋,指出了在文明內的制度和傳統做法往往並非是個人理性或設計意圖所造成的結果;人類文明中的大多數實踐知識也是體現在那些不能以理論知識或語言完全闡明的理性不及的制度和習慣做法之中。這些制度和做法雖然行之有效,卻不一定能為人所意識到或以理性語言完全演繹出來。這些做法多是包含着長時間累積下來但卻不能明言的豐富經驗和判斷。而我們去跟從這些制度和做法賴以構成的規則,正是文明得以運作之道。要創新改變,依這樣的思路推演,也只得在邊際上進行和採用內在的批評,靠同一文明內被廣為接受的做法作為標準,修正文明內在當下產生爭議的做法。如果我們以為可以有一外在於相關文明的理性標準全面地建構全盤的改革,來取代這些傳統做法,那就犯上了理性致命的自負。
秋風認為,有了對有限理性的認識,自由主義者便應放下全盤改革的虛妄,轉而於局部制度性改革的努力,尤其應在憲政制度上尋求一漸進的改變。他說:“在周德偉的思想典範刺激下,過去幾年中,我一直尋找現代中國思想和政治的中道傳統。在清末立憲者、張君勱、陳寅恪、周德偉、現代新儒家等等看似相互沒有關係的人物和思潮之間,存在着內在而深刻的關聯。我將他們概括為“現代中國的保守—憲政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他稱這是中道的自由主義,因為“與之相比,激進革命傳統固然是‘歧出’,因其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在文化上趨向於單純的破壞。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偏激,這一點與革命傳統相同;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軟弱無力,這一點又讓它敗給革命。保守—憲政主義傳統則保持了自由的革命的中道。”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憲政改革的範疇伸延到政府的公共和財經政策的檢討和芻議,我相信夏道平在1950年代開始在台灣輿論界中在這方面依據海耶克式的自由主義提出的觀點和建議,和秋風論及的中道自由主義是有共通點的。夏道平之後的吳惠林和謝宗林在台灣這方面的努力,正是這傳統的延續。
要全面充分地檢視海耶克對戰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影響,是一項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和理論研究中很值得去做的計劃。除了上述提到1950─80年代海耶克對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之外,海耶克的思想對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在市場改革方面,和對大陸的自由思想的去激進化的保守轉向上也發揮很大作用。一些大陸知識分子,例如英年早逝的鄧正來曾經為了譯介海耶克的論說而閉關八年,翻譯和著述了幾百萬相關的文字,更是值得重視的努力。我希望日後有機會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
《通向奴役之路》
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前輩學人這本1962年《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譯本,大致而言,可說是高水平和準確之作。難怪後來中國大陸的一些譯本,也依據滕、朱兩位的翻譯而出版。比起殷海光1950年代在台灣的選譯本來說,這本1962年的譯本的水平和準確性我認為都是較優秀的。
這次我協助香港商務印書館編審滕維藻和朱宗風的《通向奴役之路》的譯本,基本上把原譯文保留了下來。其中我決定對譯文作出修正的內容,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原翻譯明顯的錯譯。例如“第二卷”錯譯成“第2章”,“博士”錯譯成“教授”等。第二類修正是一些學術上的專門修辭。如果滕、朱兩位當時的翻譯與現在的標準用法不合,而我認為現在的標準用法較準確的話,我也作出了修正。明顯的例如原譯文把海耶克原本的nationalism翻成“國家主義”,現在修正為“民族主義”。原譯文把democracy譯成“民主主義”,現在基本上修正為“民主”。第三類則是原譯文的翻譯對理解海耶克的思想會產生誤導,所以須把譯文修正過來或作出改善,以避免在理論上錯解了海耶克的思想。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海耶克在談到英式法治下的規則所具備的Formal的特質這一點。由於海耶克認為英式法治下相關的法和規則,主要是用來規範程序上的公正或個人受到保障的領域,而不是實質地為達到任何共同或具體目的而服務,因此,這類的法和規則相對於有實質指向性(substantive)的規則而言,其特質是形式性(formal)的。滕維藻和朱宗風的譯文在這方面通常都把海耶克原文中的formal rules或formal law譯成是“正式的規則”或“正式的法律”。但依照海耶克的思路,英國國會依照法治精神制定和通過的法規自然是“正式”的,但就其性質而言,這些法規應是“形式性”的而非具“實質指向性”的,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把滕、朱兩位的譯文從“正式”改為“形式”,以免對海耶克的理論產生誤讀。
上述三類的修正,我直接在原譯文中作出了修改,並沒有保留原譯文。另一類修改,則是海耶克的原文本身出錯的,滕、朱兩位的譯文因此也把原文的錯誤直譯了出來。在此,我在本書保留了原譯文,但在錯誤之處加上﹝編審按:﹞這括號,把正確的資料在括號中寫出來。這方面的修正,我主要得益於在此導言文首提及的Caldwell教授。他2007年為英文海耶克全集編輯The Road to Serfdom時,花了不少工夫把海耶克原文在資料上的一些錯誤改正了過來,我也趁這個機會在此譯文版本中把原文的錯誤指出來。
最後,原文和原譯文在此版本都採用了同頁註腳的方式紀錄了海耶克或譯者的註解,這一點我在本書保留了下來。這篇導言我也採用了同頁註腳的方式記錄我的註解。但在本書的原內文和翻譯本中,我作出編審註解時,則採用了文末註腳的方式,以資識別。
多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給我機會編審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翻譯的這本海耶克的小經典。這個版本餘下來的任何不足和錯漏,責任自然在我,望各位高明指正。
張楚勇
2016年9月3日
原書序言
形形色色的用語表達了我們時代的口頭禪:“充分就業”,“計劃”,“社會安全”,“不虞匱乏”。當代的事實所顯示的,卻是這些事情一旦成為政府政策的有意識的目標,就沒有一件能夠獲得成功。這些漂亮話只有傻瓜才會相信。它們在意大利把一個民族誘入歧途,使他們暴骨在非洲的烈日之下。在俄國,有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有三百萬富農被清洗。在德國,1935–1939年之間曾達到充分就業;但是六十萬猶太人被剝奪了財產,四散在天涯海角,或長眠於波蘭森林中的萬人塚內。而在美國,儘管一次又一次的抽水,可是唧筒也從來沒有灌得很滿;只有戰爭才解救了那些“充分就業”的政治家們。
迄今為止,只有屈指可數的著作家敢於探索上述口頭禪和現代世界中屢次出現的那種恐怖之間的聯繫。現在卜居英國的奧國經濟學家海耶克是這些著作家之一。在目睹了德國、意大利及多瑙河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僵化以後,又眼見英國人所受的統制經濟的思想之毒愈來愈深,不禁憂心忡忡。這種思想直接來自德國的華爾特.臘特瑙(Walter Rathenou)、意大利的工團主義者──而且還來自敢於從前人沒有明說的國家控制論得出結論的希特勒。海耶克此書──《通向奴役之路》──是在這徘徊踟躕的時刻中的一個警告、一聲呼號。他對英國人,不言而喻的也是對美國人說:停住,看看,仔細聽聽。
《通向奴役之路》是審慎的、不苟的、邏輯性很強的。它不是譁眾取寵之作。但是,“充分就業”、“社會安全”、“不虞匱乏”這些目標只有在作為一個解放個人自由活力的制度的副產品時,才有可能達到,這個邏輯是無可爭辯的。當“社會”、“全體的利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成為國家行動的壓倒一切的標準時,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他自己的生計作出計劃。因為,如果“社會”的利益或“普遍的福利”高於一切,國家“計劃者”必然要竊據能夠佔領經濟體系的任何領域的大權。如果個人的權利成為阻礙,個人的權利就必須去掉。
國家“力本論”的威脅,在那些仍然保持着有條件的行動自由的一切產業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常常是不自覺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影響了行動的原動力。正如過去人們致力於跟市場鬥智一樣,他們現在必須致力於跟政府鬥智。不過這裏有一點不同:市場因素至少是相對地服從於客觀的規律,而政府則不免受許多一時的念頭的支配。一個人可以把前途寄託在根據存貨數量、市場飽和點、利率、購買者需要趨勢曲線而作出的判斷上。但是對於一個旨在排除市場客觀規律的作用而且在“計劃”的名義下只要願意就可以隨時隨地這樣做的政府,個人又怎能跟它鬥智呢?彼得.德魯克爾(Peter Drucker)曾經挖苦過“計劃者”,說他們全是沒有樂譜的即興演奏家。他們給個人造成的是不穩定,而不是穩定。正如海耶克明白指出的,這種不穩定的最終結果不是內戰就是防止內戰的獨裁制度。
“計劃”以外的可行之道就是“法治”。海耶克並不是放任政策的崇奉者;他相信一種有利於企業制度的規劃。規劃並不排斥最低工資標準、衛生標準、最底額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它甚至於也不排斥某些類型的政府投資。但重要的是,個人必須事前知道法規章程將如何起作用。如果有一個中央計劃當局的“力本論”罩在頭上,個人是無法計劃他的企業、他自己的前途,甚至他自己的家務的。
在有些方面,海耶克比現代英國人更加是一個“英國人”。他在一定限度內屬於偉大的曼徹斯特傳統,而不是屬於韋伯夫婦學派。可能他也比現代美國人更加是一個“美國人”。如果這樣的話,我期望《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能在美國在可能範圍內有最廣泛的讀者。
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
紐約州,紐約市,1944年7月
前言
當一個社會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寫了一本政治性的書的時候,把這一點說清楚是他的首要責任。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我不想用社會哲學論文之類的更高雅虛矯的名稱來遮掩這一點,雖然我未嘗不可以那樣做。但是不管名稱如何,根本之點還是在於我所要說的一切全都肇源於某些終極的價值。我希望在這本書中還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職責,就是毫不含糊地徹底闡明,整個論證所依據的那些終極的價值究竟是甚麼。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在這裏補充說明。雖然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我可以極其肯定地說,本書中所申述的信念,並非決定於我個人的利害。我想不出有甚麼理由能夠證明,我所認為合意的那種社會,對於我個人會比對我國大多數人民提供更大的利益。其實,我的社會主義的同事們常常告訴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在我所反對的那種社會裏,一定會居於遠為重要的地位──當然,如果我能夠使自己接受他們的觀點的話。我覺得同樣肯定的是,我所以反對那些觀點,並不是由於它們和我在成長時期所持的觀點不同,因為它們正是我年輕時所持的觀點,而且這些觀點使我把研究經濟學作為我的職業。容我對那些依照當前的時尚,要在每一個政治見解的申述中,找尋利害動機的人們附帶說一聲,我本來是大可不必寫作或出版這本書的。這本書必定要得罪許多我盼望與之友好相處的人們;它也使我不得不放下那些我覺得更能勝任,而且從長遠看來我認為是更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它肯定會有害於對那些更嚴格的學術工作的結果的接受,這種學術工作是我全部心願所嚮往的。
如果說我不顧這些而把寫作這本書視為我不可逃避的任務,這主要是因為在當前的關於未來經濟政策問題的討論中,存在着一種不正常的和嚴重的現象,這種現象還沒有充分地被大家覺察到。實際情況是,幾年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被吸收到戰爭機器中去了,他們都因為官職在身而不能開口,結果關於這些問題的輿論,在驚人程度上為一批外行和異想天開的人、一些別有用心或賣狗皮膏藥的傢伙所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尚有著述餘暇的人,很難對這些憂慮保持緘默──當前的種種趨勢必然在許多人心目中引起這種憂慮,只是他們無法公開表達它們──雖然在另一種情境下,我一定是樂於把對國家政策問題的討論,讓給那些對這項任務更有權威、更能勝任的人去做的。
本書的中心論點,曾在1938年4月《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雜誌上〈自由與經濟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一篇論文中初次簡單提出,這篇論文後來增訂重印作為吉迪恩斯(H. D. Gideonse)教授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編輯的《公共政策叢刊》之一(1939年)。上述兩種書刊的編輯和出版人允許我引用原作的若干段落,我在此謹致謝忱。
F. A. 海耶克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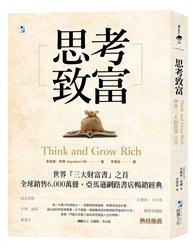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