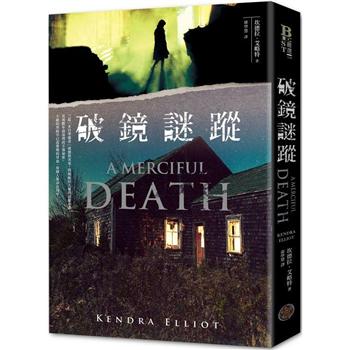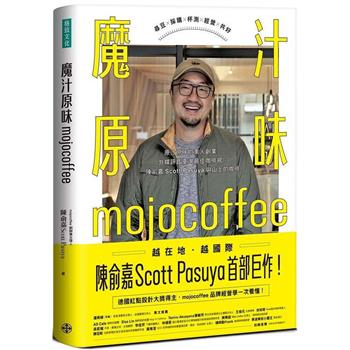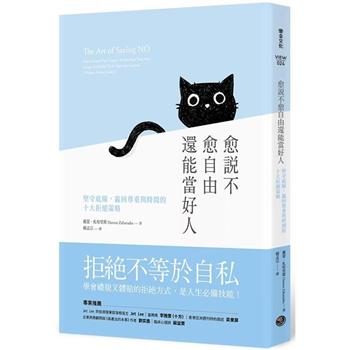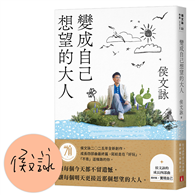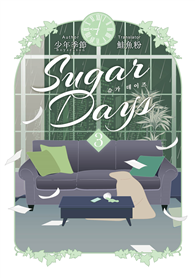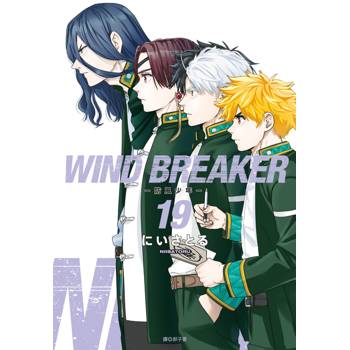從太空塵埃到床底下的灰塵,從輻射落塵到塑膠微粒,
一場看不見的環境危機,正在滲透你我的每一口呼吸。
宛如《星際效應》般令人驚豔的報導文學
一粒沙塵背後,隱含那些地質、生態、歷史、氣候、文化的更替?
一部精采絕倫的人文地理著作,
結合地理學X環境史X旅行田野 X政治批判
帶領我們以塵觀天,洞察這個星球的生機與傷口……
塵埃無處不在。
從書桌牆角堆積的灰塵皮屑、每天出門呼吸的PM2.5懸浮微粒,到生命消逝後化為的塵土——塵埃輕如鴻毛,卻能跨越時間與地理疆界,記錄萬物的生與滅、文明與自然的消長。
塵埃也無比沉重。
隨著現代工業發展,人類燃燒能源與開墾土地,造成環境污染、土地荒漠化與水資源枯竭,塵埃不再只是自然循環一部分,而是化身為飛揚的沙塵暴、有毒的落塵與乾涸的惡土。現今地球每年有超過 200 億噸礦塵飛舞,空氣污染更成為全球第五大死因,每年奪走逾 420 萬條性命。這些文明的殘留物,劇烈改變地球生態景觀,也提醒我們尋找丈量世界的全新尺度。
本書從微物視角,重新探勘人類世的環境歷史。作者歐文斯結合旅行書寫、地理知識與政治批判,穿越內華達沙漠、中亞鹹海、格陵蘭冰原與煙霧中的倫敦,帶我們細察每一粒灰塵中潛藏的地質、氣候、生物與殖民記憶。這些空氣中漂浮的粒子,不只是污染指標,更是環境破壞與歷史不義的殘留,見證了人類如何失去與土地的連結。
本書寫下人類世的億萬塵埃,為這個星球帶來的無數傷口;也透過重構對土地與生命的感知,思索如何受傷地景。塵埃的故事,是文明駕馭自然失敗的故事,也是從廢墟從尋求光亮,從氣候遽變與環境災難中,看到社群、動力、抵抗與變革的故事。
作者簡介:
潔伊.歐文斯(Jay Owens)
作家、數位媒體總監。研究領域包含生態環境系統、科技與媒體文化,關注現代進步與未來願景等宏大敘事,如何與當代複雜混亂的現實產生拉鋸。撰寫有關科技、空間與未來學等文章,散見於《衛報》與《新人文主義者》(New Humanist)等媒體平臺。歐文斯目前居住於倫敦,擔任《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讀者經營主管。
譯者簡介:
方慧詩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策展人員,策有《永續年夜飯──人類世的餐桌》特展;同時為國立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曾任國際博物館協會自然史博物館與典藏委員會(ICOM NATHIST)秘書、去殖民化工作小組成員。與饒益品合譯有《我的野蠻室友》(獲得第十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類金籤獎)、《舌尖上的演化》。
饒益品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畢業,曾於東華大學森林生態學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於法國圖魯茲第三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目前於英國劍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繼續鑽研森林動態。與方慧詩合譯有《我的野蠻室友》(獲得第十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類金籤獎)、《舌尖上的演化》。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過往十幾年來,空污,尤其是pm2.5細懸浮微粒對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一直是臺灣重要政治議題,也因為是政治議題,在政治利益與立場下,迄今很難理性討論與客觀看待空污治理政策。五月十七日最後一部核電機組停役後,爭議更熾。這本書的出現,也許是及時雨,作者「透過讓微觀與巨觀等多種尺度的衝撞」,帶出一個全觀的視野,以塵埃微粒為主題,寫出這本具有全球性格局、知性理性兼具的環境史巨著,閱讀之後,足讓立場退避、政客汗顏。」——詹順貴 環境律師
「近年來,PM2.5、微塑膠的危害漸漸為人們所知。但《人類世的億萬塵埃》讓我們知道塵埃不僅止於此,微小之物既是大自然饋贈,也是人類的自食惡果,承載著人類工業化以來對環境造成的巨大變動,各種有毒微塵、核子試爆的輻射塵,還有人們貪婪的濫用水資源和土地導致的沙塵暴等,已危及人類的生存。
臺灣是人口密度很高的都市化和工業化國家,有著許多類似的情境。如何才能扼止已經失控的人類行為,這是困難的大哉問。謝謝衛城出版的好書,打開了我們對塵埃的全新視野,一起思考如何有智慧的採取行動。」——李根政 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
「歐文斯以抒情筆觸與完整考察,突顯塵埃被忽略的歷史意義……本書為一部扎實且深具說服力的研究,探討微小粒子如何產生巨大影響。」——《出版者週刊》
「一部引人入勝、視野寬廣的著作,探討塵埃的成因與其對人類的影響……歐文斯的書寫感動人心、充滿說服力……讀者將對她如何從塵埃這般微小事物中提煉出龐大洞見感到驚嘆。」——《書單》
「精彩絕倫……歐文斯是一名真正優秀的作家與深思的環境觀察者。她激情澎湃又理性清晰,有力而細膩……本書的獨特性令人感到振奮。」——《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歐文斯以令人敬佩的公正態度,處理《人類世的億萬塵埃》中許多故事,展現深厚的研究功力與對複雜性的敏銳洞察。」——《衛報》
名人推薦:「過往十幾年來,空污,尤其是pm2.5細懸浮微粒對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一直是臺灣重要政治議題,也因為是政治議題,在政治利益與立場下,迄今很難理性討論與客觀看待空污治理政策。五月十七日最後一部核電機組停役後,爭議更熾。這本書的出現,也許是及時雨,作者「透過讓微觀與巨觀等多種尺度的衝撞」,帶出一個全觀的視野,以塵埃微粒為主題,寫出這本具有全球性格局、知性理性兼具的環境史巨著,閱讀之後,足讓立場退避、政客汗顏。」——詹順貴 環境律師
「近年來,PM2.5、微塑膠的危害漸漸為人們所知。但《人類世的億萬塵...
章節試閱
終歸塵土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一場沙塵暴席捲北美大平原,如雪崩般淹沒所經之處。那年三月每天都有沙塵暴,堪薩斯州的道奇城從年初到當時為止,只有十三天倖免於塵埃。然而,在四月第二個星期日的早晨,天氣卻相當晴朗,明媚的陽光和清澈的天空照亮大地。當天的氣溫將近攝氏三十度,是那年目前最好的天氣。人們紛紛換上短袖出門。在奧克拉荷馬狹地,農家無不敞開前門,深呼吸乾淨的空氣。那星期日正巧是復活節前一週的聖枝主日,人們都希望上天能慷慨賞賜個好天氣。
人們開始大掃除,把家裡用來吸附沙塵的濕棉被和毛毯收起來,撕下封住窗戶門縫的膠帶與糨糊條,也打開窗戶。大量灰塵被一桶一桶清出,屋頂被鏟得乾乾淨淨,洗淨後的床單和衣物在太陽下晾乾。那天,奧克拉荷馬州蓋蒙市的循道會舉行了一場「祈雨禮拜」,教友們紛紛前往,向上帝祈求迫切需要的雨水。波夕市的居民則重新舉辦一場兔子圍捕活動,這場活動在一個月前因為沙塵暴而被推遲。在其他地區,許多民眾則出門巡視自家農場狀況,他們發現戶外廁所天花板倒塌、有一半埋在沙土裡;柵欄旁堆積著新形成的沙丘,沙丘個個高達三公尺,被一團團風滾草困住。
同一天早上,在一千兩百八十七公里以外的北達科塔州俾斯麥市,天空開始轉變為紫色,風勢也漸漸增強。氣溫驟降到攝氏十七度左右,強風從北吹向南方與西南方。這場風暴在南達科塔州、內布拉斯加州和堪薩斯州上空肆虐,從地力耗盡的地表捲起乾燥的土壤,形成一團超過六百公尺高的巨大黑暗漩渦。到了下午兩點半,道奇城陷入一片黑暗,空氣中瀰漫的沙塵讓人伸手不見五指。
事件多年後,奧克拉荷馬歷史學會訪問當時三十二歲的艾達.凱恩斯 。艾達回憶自己走進屋內,說道:「我記得下午三四點左右,我開著收音機,聽到廣播中說:『這裡是道奇城,我們要停止播音了。』」主持人沒時間解釋原因就下線了,因為沙塵暴帶來太強大的靜電,讓電器設備和汽車引擎短路,人們甚至能看見帶著電荷的鐵絲網閃爍火花。
羅根.奎格 當時正在朋友家玩撲克牌,那是當時相當流行的娛樂活動。「突然有人起身走出去,跟大家說:『你們快來看。』那東西正越過河流朝我們過來,看起來就像在不停滾動。」奎格兩隻手跟著比劃。「你會想:『好的,這就是世界末日了。』當那個東西靠近時,我甚至懷疑後面是否有神站在白雲、或有魔鬼站在黑雲上。我們真的被嚇死。」
每個人對沙塵暴的描述大都一致。當奈莉.古德納.馬隆 太太被詢問:「沙塵暴接近時是什麼樣子?」她答道:「大概是世界末日的樣子。」
那一天後來被稱為「黑色星期天」。隔天在新聞報導中,該次事件首次被稱為「黑色風暴」 。
❖❖❖
黑色風暴是一九三〇年代,美國中部一場由乾旱、沙塵與經濟大蕭條交織而成的危機。在那十年間,北美大平原從北到南約八百公里、東西約五百公里,總計四千多萬公頃的土地乾涸龜裂,化為塵土。光是在一九三五年間,也就是沙塵暴最嚴重的一年,就有八.五億噸重的表土被風吹起,飄散到遠至華盛頓和紐約等地區。
北美大平原的乾旱是自然現象,平均每四年就會有一年雨水不足。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五年間發生的一次重大旱災,就曾導致野牛與北美原住民相關的生活模式滅絕。當時日益增加的移民聚落讓野牛無法抵達河谷間僅存的綠地。十九世紀中葉,一篇報導曾提及邊疆開拓的商隊,遭遇能見度不超過九十公尺的沙塵暴。而在一八九○年,第一批到內布拉斯加的白人移居者,在嘗試建立農耕生活五年後被迫放棄。因為當年開始發生為期七年的乾旱,讓農民眼睜睜看著種植的小麥田乾枯死去。
然而,一九三〇年代的沙塵暴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災難。翻騰的黑雲、滋滋作響的靜電,以及瀰漫在空氣中的塵土,都顯示這場災害並非單純的自然天災。儘管風勢、乾旱與鬆軟的土壤等自然條件為其提供先備環境,然而從濃厚沙土覆蓋的地景,到遭侵蝕而裸露的農田,這些如地質變遷般巨大的災害規模顯示其根源出於人為,並與最初扛著犁到來、意圖「征服平原」的白人移居者有深遠的關聯。
黑色風暴襲擊北美大陸的心臟,無論在地理位置上或象徵意義上皆是。西馬隆郡、德克薩斯郡和比佛郡位於奧克拉荷馬狹地,是美國本土四十八州中最晚開發的地區,開墾時間約為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七年。當災難發生時,當地居民才經歷一代更替。原先那片土地作為美國開拓邊境的神話象徵,在短短一代內竟然化為烏有,令人不禁懷疑整個開墾計畫的正當性。然而,這種質疑論調無論在當時或現在的文獻紀錄中,都相當少見。黑色風暴只被描述成一場少見天災,而非人禍。人們認為它屬於區域性危機,而非全球土地枯竭最戲劇化的例證。如此一來,無論在過去或現在,有關土地耕作永續性等艱難問題都能被迴避。
黑色風暴是一段關於巨大失落的故事。根據一名堪薩斯州的小麥農夫勞倫斯.斯沃比達 所說,在事件過後,約有三百萬人「流離失所、耗盡體力或飢餓而死」。為了逃離鄉村赤貧的生活,人們不得不搬到城鎮,或推著手推車一路逃往西邊的加州,成為其中一次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內部人口遷徙。 在環境災害與經濟大蕭條加成下,那片短短幾十年間被視為美國心臟地帶的區域就這樣被摧毀,此後也一直沒有恢復到一九一○年的人口數量。但除了統計數據,這場災難還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根據研究,黑色風暴所造成的「沙塵肺炎」 可能奪去七千條人命。但正如斯沃比達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著作中,回顧他離開的土地與生活時表示:「黑色風暴造成的最重大悲劇,多半永遠不會被記錄下來,只留存在逝者摯友與親人哀痛的心中。」
但對一些人來說,這段回憶實在太不堪回首。唐.哈特威爾 作為黑色風暴的見證者,在日記裡記下沙塵暴晚期的生活。這部日記差點被哈特威爾的遺孀維娜燒毀,幸虧一名鄰居路過搶救下來。為什麼維娜想會想摧毀這段如此私密、又同時具有歷史價值的紀錄?我們只能推測,她不希望回憶起那些往事。
◆◆◆
「我第一次遇到沙塵暴是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應該是一九三三年初。」一九八四年,夏克爾福德夫人 在接受奧克拉荷馬州歷史學會訪問時回憶道。
「當時農民已經把土地全部翻耕,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抓住土壤了。」她的丈夫埃爾默.夏克爾福德補充 。
「天氣開始變得很乾,」她繼續說道:「我們這裡本來就經常有風,但那時風開始變得特別猛烈,從北邊的科羅拉多州開始,一直往這裡吹過來。」
「最可怕的是第一場沙塵暴,」同樣是當地人的夏克爾頓先生 說:「那次風大概吹了一整天。當沙塵暴襲來時,我們還以為是地平線突然冒出一大片濃煙,看起來就像眼前的世界著火了。沙塵相當洶湧,不斷有煙霧翻滾,彷彿油井著火般猛烈。」
「如果先不去想沙塵暴造成的破壞,只是單純看雲層,沙塵翻滾的樣子其實很美。」艾斯特.萊斯維格 接受喬.陶德 採訪時生動地描述。 「沙塵暴的顏色很五彩繽紛,有紅色、黃色,還帶有深藍色。」這些顏色取決於沙塵來源。來自堪薩斯州和北部的「黑色風暴」富含有機質的土壤,顏色自然暗沉;來自奧克拉荷馬狹地的土壤含鐵量高,呈現出紅色。更西邊的科羅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吹來的塵土則為灰白色。不同顏色的沙塵有各自獨特又令人不安的氣味,有些辛辣刺鼻,有的油膩令人反胃。
「它們滾動時就像是一堆球疊在一起,每顆球都在滾動,」萊斯維格說道:「但它們不是都朝同一個方向滾動,看起來好像是互相堆疊,這顆往這邊轉,那顆往那邊轉,另一顆又朝遠方滾動。」她用手比出旋轉動作來說明。「然後它們就直直往上飛了!幾乎是垂直而上,可能有三百公尺高。但鳥無法飛越風暴,或說沒有飛過去,而是在沙塵前面飛,好像背後有一張網子不斷逼近,每隻鳥都努力不被追上。」
但沒有人有空觀賞,任何珍惜生命的人如果看到鳥群逃竄,也一定會跟著逃跑。尤其在室外,若找不到任何遮蔽物可能會喪命。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在沙塵暴過後,一名七歲小男孩就被發現被埋在沙塵下,不幸窒息而死。
「沙塵暴發生時,有時會挾帶很強的風,有時卻幾乎沒有聲音,就這樣靜悄悄靠近。」萊斯維格表示:「然後四周會變得跟瀝青一樣黑。」
這就是北美大平原上人們連續幾天、幾週,甚至一整季得面對的感官世界:詭譎的色彩與黑暗、燥熱的天氣跟無盡的塵土。「有些日子裡,一天有好幾個小時都無法看見廚房門外十五公尺處的風車。」卡洛琳.亨德森在一九三五年寫信給農業部長時提及:「有些日子當風暴來襲,外面會變成一片漆黑,人們連窗戶跟牆都分不清楚,只能在像地獄一般的夢中,想像沙塵暴形成的可怕腥紅色光芒籠罩著德州。」
有些日子,暴風肆虐,烏黑一片,甚至連窗戶與實牆都分不清楚,,只能在像地獄般的夢境中想像到那可怕的猩紅光芒,籠罩著天空,那是德州部分地區的『空氣中燃燒著火焰』的景象
常常,這些沙塵暴會伴隨電氣風暴出現,令人更加驚懼。沙塵暴不僅造成打雷與閃電,還會產生大量靜電。當土壤顆粒在空中互相碰撞,小而輕的沙粒會從較大的沙粒上「偷」走電子,形成電場。根據研究,沙漠中的沙塵暴跟塵捲風擁有每公尺超過十萬伏特的電場強度。這種電力能將更多粒子捲起,讓沙塵更加密集,並造成比強風更棘手的災害。
胡安妮塔.威爾斯 在黑色風暴來襲時只有七歲。「我記得爸爸晚上會出門去找牛,」幾年後她回憶道:「他會沿著柵欄走,因為那時柵欄就像通電一樣,他能從空中的靜電看到柵欄上的光。」
其實靜電帶來的電力會將小麥幼苗的頂芽燒掉,即便沒有熱浪、乾旱或蝗災來襲,靜電也會破壞農作。接下來的每年對農夫來說都是場賭注:今年會不會豐收呢? 就這樣十年過去,農民們靠著貸款留在這場賭局中,但每年都註定失敗。
❖❖❖
沙塵暴彷彿永無止境。
才過了一年,北美大平原的籬笆塞滿風滾草,背後堆積的灰塵高到連籬笆上的鐵絲都被掩埋。「在這一大片地區,風與侵蝕的沙子已經抹去所有耕種的痕跡。」一九三五年七月卡洛琳.亨德森在日記中寫道:「牧場成為貧瘠的荒地,小屋門口前只剩下塵土飛揚的淒涼景象。低矮的建築幾乎被埋沒。」這些描述可能會讓你想起一些著名的攝影作品。 昔日的農田開始變成沙丘,不斷飆升的氣溫也創下新高。一九三四年夏天,內布拉斯加州的溫度高達攝氏四十八度;到一九三六年夏天,有超過四千五百人死於酷熱天氣。飢腸轆轆的蝗蟲大軍如今重遊舊地,就像一八七三年和一九一九年在堪薩斯肆虐一樣。蝗蟲不僅吃光原本就發育不良的農作物,連樹葉與晾衣繩上的床單都不放過。
一九三○年代,在奧克拉荷馬州最西邊的西馬隆郡,每平方公里六.○五公噸,這個數量連用來播種隔年農田都不夠。持續侵襲的狂風已成為問題,蟲害更讓狀況雪上加霜。但最嚴峻的挑戰是當地幾乎不下雨,農田裡的作物因此枯萎,甚至沒有發芽。這片原本被視為「五百零八毫米等雨量線」的地區,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的降雨量。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西馬隆郡每年平均降雨量僅有三百毫米,比沙漠的降雨標準只多出一點點。
在黑色風暴發生前三年,一些牛隻靠僅存的飼料還能勉強存活。通常牠們吃的是風滾草,但因為持續咀嚼被沙塵覆蓋的草,牙齒和牙齦幾乎都磨損殆盡。牠們身體也瘦到只剩下皮包骨,皮膚被飛揚的沙塵石礫磨破,眼睛也被塵土弄瞎。有時風暴過後,農民會發現豢養的家畜已窒息死亡,如果解剖牠們,會發現動物體內塞滿沉甸甸的泥土。
人們在沙塵中苟延殘喘。「我們只是努力活下去,直到情況變得太過糟糕。」胡安妮塔.威爾斯回憶道:「我記得我爸爸會出門燻兔子。兔子的問題很嚴重,因為牠們會吃光所有能夠咬下去的東西。我們會出門去找牠們的巢穴,然後挖個洞把牠們燻出來,抓住逃出來的兔子,最後,牠們就變成桌上的食物。這實在是因為當時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但灰塵無所不在,不僅滲入每個角落,也滲入每個人體內。
終歸塵土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一場沙塵暴席捲北美大平原,如雪崩般淹沒所經之處。那年三月每天都有沙塵暴,堪薩斯州的道奇城從年初到當時為止,只有十三天倖免於塵埃。然而,在四月第二個星期日的早晨,天氣卻相當晴朗,明媚的陽光和清澈的天空照亮大地。當天的氣溫將近攝氏三十度,是那年目前最好的天氣。人們紛紛換上短袖出門。在奧克拉荷馬狹地,農家無不敞開前門,深呼吸乾淨的空氣。那星期日正巧是復活節前一週的聖枝主日,人們都希望上天能慷慨賞賜個好天氣。
人們開始大掃除,把家裡用來吸附沙塵的濕棉被和毛毯收起來,撕...
推薦序
每下愈況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每次農曆過年,我媽就會遞給我一塊抹布,叫我去擦紗窗。她說紗窗上黏滿了灰塵,我看起來一副無所事事的模樣,應該擦個紗窗,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媽還會咕噥幾句,說以前她還會把紗窗拆下來洗呢,只是年紀大了,腰不太行,沒辦法這樣打掃云云。
擦紗窗是我對新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有一回,我試著開導我媽,跟她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她就叫我去拆紗窗下來洗。
然後我也覺得我的腰不太行了。
◆◆
《人類世的億萬塵埃》是一本塵埃之書。不論你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神秀派,還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惠能派,都可在當中找到啟發。
為何要為塵埃寫一本書?歐文斯是這樣說的。那是在二○○八年的秋天,她正在倫敦大學攻讀地理學博士學位。她交不出論文計畫書,只好努力找些事做。她發現了桌下有著大量灰塵,且「泛著詭異紫色的絨毛與毛髮卡在椅腳、糾結成一團,長成尺寸十分驚人的塵兔」。她自問,不是才剛打掃過嗎?這些「塵兔」(dust bunny)是從哪跳進來的?她開始思考,這些塵兔豈不是標示了她的「存在未及之處」?也想起了《神隱少女》裡頭的煤炭精靈,想到若塵埃具有意識,她的存在本身會不會有所改變?
歐文斯突發奇想:為何不以塵埃為題,搭配某個地理學理論,寫個酷炫的論文計畫書?然而,她失敗了。原來,當她準備坐下來好好寫個塵埃的計畫書,她總是覺得先打掃房間比較要緊。最後,房間變得格外清潔,反倒是論文計畫書成為某種存在以外之物。她對於「想當個地理學博士」的執念感到好笑,覺得學術界不過是個「老鼠會」,當中的「時代精神」如同塵兔,不久就會被打掃乾淨,然後就被另一批塵兔所取代。她決定,就拿個碩士學位,然後拍拍屁股走人。
對學術界斷念的歐文斯,還是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美其名是以數位之法擴延讀者群,但恐怕就是個「小編」。但無論如何,找到容身之處的歐文斯,覺得可以放鬆一下,跟好友前往加州一遊。出乎意料,當她視學術界為「無物」時,塵埃又開始招惹她。這回的塵埃,不是躲藏在桌底下或牆縫間的塵兔,而是讓天空劇烈改變的沙塵暴。
歐文斯回憶,那是在二○一五年的七月下旬。她與友人準備在猛獁湖(Mammouth Pool)紮營。
一路上,一行人先是經過一片被燒得焦黑的枯木林,接著天空變成黃色,當中掛著一顆血色的太陽。
原來,離猛獁湖不遠的森林正遭祝融肆虐,灰燼懸浮在空氣中,天地為之變色。歐文斯明白,野火再度於加州蔓延了。過去,野火只在入秋幾個月發生,但現在加州的某些地點幾乎全年都在燃燒。追根究柢,這與全球尺度的氣候變遷有關。歐文斯開始體會,不論是躲藏在桌下的塵兔,還是瀰漫在整片天空的灰燼,這些塵埃都宛如「一扇窗」,讓她可以「正視這個時代的災禍」,乃至於「一連串擾亂地球生物地質化學系統的斷層」。不停招惹著人間的塵埃,其實如同一種「管道」,「讓人得以與自身腳下的地質環境,以及人類誕生、定居於這脆弱地表的長遠歷史接軌。」
對於塵埃,神秀與惠能有著南轅北轍的見解。但在《人類世的億萬塵埃》中,你可以得到另一種視野:塵埃不再只是妄念與障蔽的象徵,反倒是我們認識物質世界、乃至於認識自身存在的媒介。
以歐文斯的話來說:「這滿布傷口的世界,乍看之下可能龐大到難以全盤思考。但也許我們能從極微小的事物開始,見微知著、悟出些許智慧。」
◆◆
二○一五年至二○二三年,歐文斯花了八年的時間,解讀塵埃帶來的消息。這時,離她起心動念、想為塵埃寫個研究計畫(二○○八)的時間點已過了十五年。即便歐文斯沒有地理學博士學位,但地理學的視野不停引導她向前。
最讓歐文斯心儀的是「廢棄研究」(Discard Studies)。以歐文斯的話說,此研究取向是「透過研究各式各樣的垃圾,包含廢棄物、汙染物、泥土等,了解社會和經濟系統實際的運作模式」。就歐文斯看來,在追求環境正義時,廢棄研究關注的「被排斥、唾棄的人與事」,而不是言必稱保育、永續、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與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的企業或技術官僚,才是「不可忘卻的要角」。
從加州出發,歐文斯展開一系列田野調查。她做田野的方式不是保持距離觀察,而是讓自己被塵埃環繞,深陷在乾裂的土地,嗅聞甚至品嚐空氣中的懸浮微粒。除了觀照自己的身體經驗,她也透過深度訪談、口述史與日記,試著建構沙塵如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進入人們身體,那些細小無比的顆粒穿過肺泡進入血流,慢慢搞起破壞」。她記錄許多不為人知、有關沙塵的社會運動史,寫下遭遇沙塵攻擊的地方社區如何目睹「居民逐漸病倒,開始追查沙塵最初的起源與始作俑者,並展開反擊」。透過讓微觀與巨觀尺度互相碰撞,她重新調和出一個貼近人類尺度、有血有肉的故事。
歐文斯的田野地包括加州內華達山脈東麓的歐文斯谷、烏茲別克鹹海沿岸的漁村木伊那克(Moynaq)、奧克拉荷馬狹地、地球最北端的格陵蘭冰蓋,還有新墨西哥州的礦場遺址等。籠罩在這些田野地的塵埃,有的來自墾民對土地的超限利用,有的來自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支配,有的來自近代科技的進展,這些塵埃不約而同構成了「現代性的陰暗面」。
不僅如此,歐文斯也花了莫大心力,探索科學家們如何看見以及度量塵埃,現代社會又如何消滅塵埃。她寫道吸塵器等「反塵科技」的發展,成為女性在家庭空間的桎梏。如俗語所說,從外太空到內子宮,歐文斯引領讀者,追溯原本「居家」的反塵科技如何被應用在太空艙、晶片與核武上,以及科學家如何運用塵埃來定年。她感性地說,檢視那些封鎖在冰芯中的塵埃,我們得以「回顧遙遠的地質年代」,同時「也讓我們向前展望,思索地球氣候的歷史資料,對這顆增溫中的星球未來有什麼啟示」。
就如《龍貓》中的煤炭精靈,塵埃讓歐文斯開了眼。深受西方科學薰陶、同時也深陷於白人女性社會規範的她,開始以全新的角度,特別是原住民的世界觀,來理解一粒對人類而言超級巨大的塵埃──Earth,也就是地球。
歐文斯引述奇歐瓦族小說家莫馬代(N. Scott Momaday)的觀察,說道:「人在投身於土地同時,將土地風景融入到自身最基本的生命經驗中。」也體會到:「對原住民族而言,他們生活的大平原並非一種『物品』,不是能被擁有或開發的財產資源,而是一個有生命的存在,並且在物質與精神上,與人建立一種互相依存與照護的關係。」
◆◆
現在是二○二五年六月四日早上九點,天氣雨。空氣品質監測網顯示臺北市的PM2.5、PM10、臭氧、一氧化碳等指標都在標準範圍內,空氣品質相當不錯。
不過,幾十年前的臺北空氣,絕對不是這樣子的。臺灣史學者徐聖凱有篇精彩的文章,叫做〈禁用生煤:日治臺灣的燃煤空汙與煤煙防止運動〉。文章開頭,他引用「歌人醫師」林清月(一八八三年—一九六○年)於一九四一年發表的臺語歌謠:「近來街市直文明,塗炭直燃風袂清。每日烏煙直直請,風來也是飛過間。」指出,讀者切莫以為煙霧瀰漫的都市景觀只存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都市;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由於「北臺大量開採煤炭成為新興廉價能源,應用於全臺工業、交通運輸和北臺家庭之炊爨,亦形成相應之燃煤空汙」,從一九二○年代起,都市仕紳也發起一波「禁用生煤」(多雜質、未經炭化且多雜質的煤炭)的運動。
臺灣當然有自己的塵埃史,也有如歐文斯這樣以身為度的寫作者,以及為生存而奮戰的社會運動者與在地人。徐聖凱的研究進一步提醒我們,反空汙的運動不會只發生在現在,甚至也不能只追溯至解嚴後的一九八○年代末;塵埃很早就成為了某種社會問題,理應為臺灣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日的我們已有了報導者團隊的《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胡慕情的《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這樣優秀的報導作品;希望《人類世的億萬塵埃》能為臺灣讀者帶來啟發,思考臺灣這個島嶼如何透過塵埃,或因為塵埃而與世界各地相連。至少,從歐文斯的觀點來看,以半導體產業名聞全球的臺灣,仰賴的不會只是「地緣政治」這樣超大時空尺度的東西,更涉及一間又一間超高規格的無塵室。
在閱讀《人類世的億萬塵埃》時,我想起腰越來越不好的媽媽,以及小時候學校的衛生糾察隊。當時,擔任糾察隊隊員的同學會以食指與中指抹過窗緣,檢查有無灰塵,決定哪一班可以拿到整潔比賽前三名。我的朋友也跟我說現在塵蟎超麻煩,小孩不時會過敏。關於塵埃的臺灣史,還有很多故事值得寫,也必須寫。看見灰塵,讓我們不再追求明鏡般的潔淨與空無;以歐文斯的話來說:「我們被迫反覆體認到回饋循環和動態非線性系統的存在、橫跨極大範圍的時空尺度、以及極為久遠的地質時間邊際。」
我們也更能看見與同理與水泥廠、核廢料、焚化爐共存的在地人,以及他們的苦難,認知到「從空氣汙染、放射性礦石堆到有毒的湖床。都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外部成本,而是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廢棄物的存在,讓我們認清「人為控制的極限」。
《人類世的億萬塵埃》並不是一本人類或資本主義的罪行紀錄,也不是一篇感慨自然如何消逝的輓歌或悼詞。歐文斯引述人類學者安清(Anna Tsing)《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的話語,表示資本主義是個拼貼、坑坑疤疤、當中存在著許多空間的世界。
如果說《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要把讀者帶到世界盡頭,《人類世的億萬塵埃》則希望讀者「每下愈況」。「每下愈況」語出莊子,意味著在螻蟻、磚瓦與屎溺中見「道」。莊子會有這樣的見解,實際上來自豬市場的「在地知識」。這些鎮日與豬隻打交道的人們,跟莊子表示:豬的小腿越肥,豬就越肥;在越低下與卑微之處,道就存在裡面。
在每況愈下的世界裡,讓我們每下愈況。
每下愈況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每次農曆過年,我媽就會遞給我一塊抹布,叫我去擦紗窗。她說紗窗上黏滿了灰塵,我看起來一副無所事事的模樣,應該擦個紗窗,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媽還會咕噥幾句,說以前她還會把紗窗拆下來洗呢,只是年紀大了,腰不太行,沒辦法這樣打掃云云。
擦紗窗是我對新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有一回,我試著開導我媽,跟她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她就叫我去拆紗窗下來洗。
然後我也覺得我的腰不太行了。
◆◆
《人類世的億萬塵埃》是一本塵埃之書。不論你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目錄
推薦序:每下愈況 洪廣冀
導論
第一章 置身地獄:煙霧、煤灰與現代倫敦的誕生
第二章 讓那片土地乾涸
第三章 終歸塵土
第四章 清潔與控制
第五章 海的遺跡
第六章 落塵
第七章 冰封的歷史
第八章 灰塵是大地代謝之道
第九章 流水之地
尾聲
謝詞
註釋
推薦序:每下愈況 洪廣冀
導論
第一章 置身地獄:煙霧、煤灰與現代倫敦的誕生
第二章 讓那片土地乾涸
第三章 終歸塵土
第四章 清潔與控制
第五章 海的遺跡
第六章 落塵
第七章 冰封的歷史
第八章 灰塵是大地代謝之道
第九章 流水之地
尾聲
謝詞
註釋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