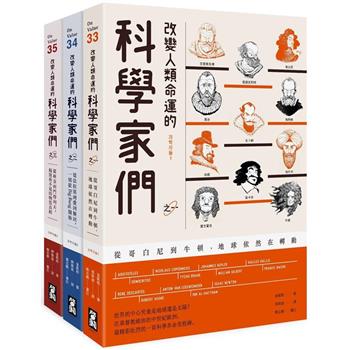序言
中國新文學革命從《新青年》發動以來到現在已二十年,其間起伏變化,不但使今日的人們已有遙遙之感,即當日曾經參加過這運動的人們,偶爾談及,亦不免回首煙塵,若話開元天寶的遺事。這運動到現在自然還要一直推演下去,然而過去的功績既不可湮沒,來日的演進亦要直承着這個基礎,則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我們還記得當日熱狂的情形,假如我們還記得那時一片新鮮的朝氣,與那一瀉千里不可遏制的氣勢,與那腐化的思想退避的情形,我們將如何的會對今日又有復古讀經的聲浪而發呆,而慚愧?而假如我們更記得那時讀者們熱誠的期待,那時新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那時新的作家的與日俱增,我們再看看今日文壇的空虛,再看看那高踞在文壇上的依然還是二十年來的舊人,我們彷彿從一個無限希望的赤心的夢裡,跌到書賈老闆的掌握中,跌到爭奪地盤的污齪中,跌到不為人期待的冷寞中。我們又看見以前望風遠遁的讀經復古的事大膽的搖搖擺擺而來,我們還不感覺得自己力量的退減嗎?讀經復古即使讓它做去也不過是一場無結果的事,我們做一番事業本來也是要能寧奈暫時的寂寞的,然而當我們漸覺得做得有點不太得勁了,回頭看看當年的盛況當可與我們以無限的教訓與自省,至少也將與我們以無限的勇氣的。
文學脫離了幼稚的時期,本來就成為較專門的努力,文學努力在沉默的試驗中,自然也只有待結果成熟後方能為一般所欣賞,這在今日亦並非沒有的,然而彷彿是很少數很少數個人的事業,而文壇上大家通力合作的那片熱誠,坦白純潔的虛心的嘗試已再不留一點痕跡了。建安以來是五七言詩試驗的時期,那發展從魏六朝是直貫到初唐盛唐的,而晚唐五代是詞的試驗時期,那發展亦直達北宋南宋而無懈。雖然文壇上可有暫時的沉默,而一種期待的心情必因沉默而緊張,這是我們所不可不得以自省的。而過去新文學的運動假如能與我們以清楚的借鏡,則過去的運動不但奠定了新文學一切的基礎,且留給後人一個應當如何做去的榜樣,其意義乃更重大了。
前奏曲
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所謂天朝者已失其天朝的威嚴,所謂真龍天子者也漸漸失掉了一般人的信念,而歐風東潮,隨着外侮而來的,同時乃亦有歐洲的科學與文明。一八九四甲午之戰又現於日本,不但遙遠的西洋望塵莫及,即同在東亞的島國也得俯首屈就,朝野人士經過這一次大打擊後,才覺悟於中國的毛病除了沒有堅船利炮之外,全盤的文化亦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於是朝廷亦遷人東渡留學,當時的學者如嚴復則出而譯西洋科學與哲學方面的著述,林琴南遂翻譯西洋司各特
諸人的小說,譚嗣同在《仁學》中更主張廢除漢字,其間關係最重要而與新文學運動影響最大的則為梁啟超。
戊戌政變失敗後,梁氏亡命於日本,於是創《清議報》,又創《新民叢報》,為中國報章雜誌的開端,之後復發現小說有改良政治的功用,於是又創《新小說》,均以感化社會為目的,如《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及科學小說《海底旅行記》,他自己說他為文: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並非自己吹噓的話,當時稍為年青一點的及頭腦稍為維新一點的人,沒有不受他這魔力的吸引的。這新文體的目的,本來在能夠喚醒民眾,因為戊戌政變的失敗,使他覺悟於一般人太沒有知識,太如醉如癡,所以必須筆鋒常帶情感而條理復極明晰的文章,才能喚起全國的同情與贊助,然而在無意間,他帶到文人眼中以「平易的俚語」,以「外國的語法」,使得白話已開始得到它嘗試的機會,啟示了後人以一個偉大的運動的先聲。
與梁啟超同時亦以同樣目的而專致力於文字改革的,則有王照,他在他《合聲字母原序》裡說:
余今奉告當道者:富強治理,在各精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氓,不在少數之英雋也,
朝廷所應注意而急圖者宜在此也。茫茫九洲,芸芸億兆,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襲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焉,苟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術之窮也。
所以他更主張「官話字母」「專拼白語」,其實在他之前譚嗣同已主張應廢漢字,而粵之王炳耀,閩之蔡錫勇,廈之盧戇章,蘇之沈學,亦先後倡改造文字之說,盧戇章有「切音新法」,曾由都察院奏請頒行天下,蔡錫勇先有「傳音快字」,後更與其子蔡璋改良為「蔡氏速記術」,遂開速記之始。
不過這些字母都是方音字母,足以使「同國漸如異域」,所以他主張拼音應以北京話為標準,他說: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係指禮教之實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係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凡也、已、焉、乎等助字為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為務,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欲借文以飾智驚愚,於是以摩古為高。
他以為文、言應當一致,文、言能一致才能「便民」才能教民,他的字母在當日因此很得許多名人的贊助,袁世凱、吳汝綸、周馥、嚴修、勞乃宣,都是他的同志,勞乃宣並採用了「官話字母」作成《簡字全譜》,在光緒戊申(一九○八)年有進呈《簡字譜錄》摺,亦說明:
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其時張百熙、張之洞等的《奏定學堂章程》的「學務綱要」裡亦即規定:「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官話的使用遂暢行全國,當時並有白話報的諸叢書的刊行,至宣統二年(一九一○)中央教育會議乃更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遂成為民國前白話運動的最後的成績。
當時的白話其目的純為可以教民,因為民不懂得文,所以非白話不可,至於懂得文的人自然還是用文言,這彷彿外國教士們因為要傳教,所以把《聖經》翻成中國俗語,至於教士們自己自然還是用原來的文字或拉丁文。白話運動的意義當時僅此而已。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潘酉堂的圖書 |
 |
$ 248 ~ 360 | 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
作者:林庚/潘酉堂/ 整理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8-17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
●文學史遺珠
北大著名學者林庚未刊講稿
●現場實錄
新文學二十年的親歷和反思
●多元視角
文學內部外部因素互動共生
本書原是林庚先生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授課講義,約編寫於1936年至1937年間。時值新文學革命發生後二十年,作為新文學運動的親歷者,林庚對那剛剛逝去的文學階段進行了完整的「現場」總結和反思,堪稱中國新文學二十年的一部反思錄。
全書分為「序言」「前奏曲」「啟蒙運動」「新文學的獨立」「文學與革命」五個部分,既提供了一種原生態的文學圖景,也體現了林庚審視文學史的獨特眼光和闊大的視野。史料的呈現與創見的闡發充溢着一種彌足珍貴的新鮮氣息和元氣淋漓的現場感,「那時一片新鮮的朝氣,與那一瀉千里不可遏制的氣勢」令讀者耳目一新。
推廣重點
1.「清華四劍客」「北大中文四老」之一的林庚先生早年未刊行的授課講義;
2.新文學參與者的「實錄」,洋溢着彌足珍貴的新鮮氣息和元氣淋漓的現場感;
3.摒棄單線條的歷史軌跡,從作家、創作、流派、出版、翻譯、學院、教育、文化、商業、政治的多元角度呈現新文學的豐富面貌;
4.詩性敘述與理性評騭相交融,發前人所未發,無後來之套語,富歷史批評眼光與個人藝術感悟之創見。
作者簡介:
林庚(1910-2006)
字靜希。原籍福建閩侯,生於北京。現代著名學者、詩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後執教於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著有《唐詩綜論》《中國文學簡史》《西遊記漫話》,詩集《北平情歌》《春野與窗》等。
章節試閱
序言
中國新文學革命從《新青年》發動以來到現在已二十年,其間起伏變化,不但使今日的人們已有遙遙之感,即當日曾經參加過這運動的人們,偶爾談及,亦不免回首煙塵,若話開元天寶的遺事。這運動到現在自然還要一直推演下去,然而過去的功績既不可湮沒,來日的演進亦要直承着這個基礎,則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我們還記得當日熱狂的情形,假如我們還記得那時一片新鮮的朝氣,與那一瀉千里不可遏制的氣勢,與那腐化的思想退避的情形,我們將如何的會對今日又有復古讀經的聲浪而發呆,而慚愧?而假如我們更記得那時讀者們熱誠的期待,那時新...
中國新文學革命從《新青年》發動以來到現在已二十年,其間起伏變化,不但使今日的人們已有遙遙之感,即當日曾經參加過這運動的人們,偶爾談及,亦不免回首煙塵,若話開元天寶的遺事。這運動到現在自然還要一直推演下去,然而過去的功績既不可湮沒,來日的演進亦要直承着這個基礎,則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我們還記得當日熱狂的情形,假如我們還記得那時一片新鮮的朝氣,與那一瀉千里不可遏制的氣勢,與那腐化的思想退避的情形,我們將如何的會對今日又有復古讀經的聲浪而發呆,而慚愧?而假如我們更記得那時讀者們熱誠的期待,那時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001 序 言
003 前奏曲
009 啟蒙運動
011 一、《新青年》與文學革命
015 二、文學革命的展開
038 三、《新潮》與「五四運動」
043 新文學的獨立
044 一、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052 二、新文學運動的熱狂
057 三、學衡派的復古
063 四、國故的整理
070 五、翻譯的工作
072 六、《語絲》與《晨報副刊》
075 七、《甲寅週刊》
079 八、五卅慘案與創造社
081 九、《詩刊》
085 十、文學運動的被干涉
089 文學與革命
091 一、太陽社的活躍
097 二、創造社的分散與文藝論戰
108 三、左翼作家聯盟與文學研究會的勝利
1...
001 序 言
003 前奏曲
009 啟蒙運動
011 一、《新青年》與文學革命
015 二、文學革命的展開
038 三、《新潮》與「五四運動」
043 新文學的獨立
044 一、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052 二、新文學運動的熱狂
057 三、學衡派的復古
063 四、國故的整理
070 五、翻譯的工作
072 六、《語絲》與《晨報副刊》
075 七、《甲寅週刊》
079 八、五卅慘案與創造社
081 九、《詩刊》
085 十、文學運動的被干涉
089 文學與革命
091 一、太陽社的活躍
097 二、創造社的分散與文藝論戰
108 三、左翼作家聯盟與文學研究會的勝利
1...
顯示全部內容
|